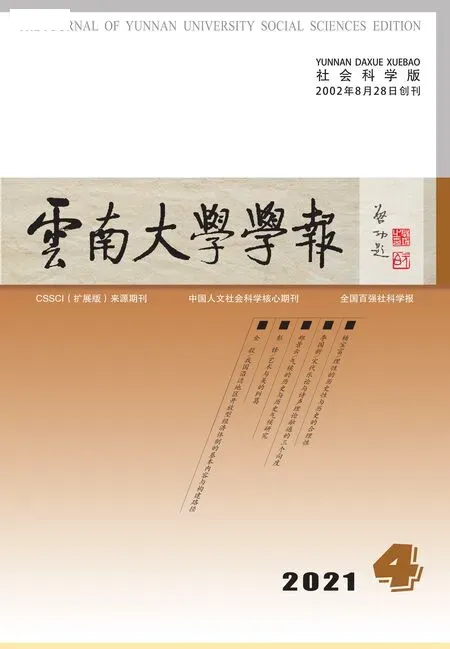宋代乐论与诗声理论融通的三个向度
2021-11-29李国新
李国新
[西南林业大学,昆明 650224]
乐论主要指有关音乐的论述。诗声,简单地说,是诗歌的声音。所有相关诗歌声音的观念、理论、概念等均可视为诗声理论。
承传统诗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诗乐合一观念而来,宋代乐论有独特的诗学背景。从音乐美学、音乐文学等相关论著看,乐学与诗学的融通是文艺之常态。在宋代繁富的音乐理论中,诗学影响着宋代乐学的理论发展与成就。如沈括《梦溪笔谈》中谈音乐之章节不仅在谈乐学的问题,也是在谈诗学背景下的诗乐问题;王灼《碧鸡漫志》中谈的是词的音乐,也大量征引了诗学的观点,或者说是从诗学的角度来解释词学、研究词学。
宋代乐论中的诗声理论杂多,有的理论特色明显、有的理论未成整体关照、有的只言片语,“声词相从”说、“乐为诗作”说、“声转机萌”说等诗声理论最引人注目,且与宋代乐论融通性很明显。
一、“声词相从”说
“声词相从”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乐律·协律》中提出的,其云: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正(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1)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五,胡道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2页。
这段话是谈音乐的,但涉及诗歌、音乐的关系以及其中诸要素间的关系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声词相从”说。
“声词相从”之声、词是两个平行的词。“声”一般指声韵(声律与韵律)和宫商角徵羽(音乐之声,多关乎词调、曲调);“词”一般指文辞、语言。“声词相从”是沈括乐论中在阐释“协律”时提出的。沈括定义“协律”云:“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古代的诗都是可以咏唱的或被咏叹其语言的,再以宫商角徵羽之律法,使其曲折或长言后成音乐。这样看,诗和音乐之协律是建立在“歌永言”与“声依永”基础上的,具体在声音层面的要求是“声词相从”。可见,“声词相从”是诗声理论,也是音乐理论。
一是“声词相从”追求的是诗乐合一的传统诗学观。“声”是诗声、词声、曲声,这些声音有的是纯粹的或散杂声音,有的是音乐性的声音,故“声”可理解为声音,也可理解为音乐。词是文字,也是诗之文字、词之文字、曲之文字,而诗词曲之文字本质上都是有韵律之诗,都有诗性的特点。所以,沈括要求“声词相从”有非常浓郁的诗乐合一的诗学追求。从“声词相从”原文出处可析出几段诗乐合一的表述:“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三句都在言说诗之可歌性,特别强调诗歌的声音属性。沈括云:“古之人欲尽其所言者,必有诗以系之。诗生于言之不足,事有不能以言宣,而见于声辞窈眇曲折之际者,盖有待于诗也。”(2)沈括:《江州揽秀亭记》,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六九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43页。沈括强调,诗存在文字表达不尽的地方,这就需要把诗中的内容通过声辞窈眇曲折地表现出来。这是对《毛诗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句的进一步诠释,将嗟叹、咏歌具体到诗声层面之声辞。只不过沈括将声音的“嗟叹”发展成声音的具体表现方式——“声辞窈眇曲折”,在“嗟叹”的音乐性和诗性表述中,诗之“声辞”得以曲折地呈现出来,实现了诗乐合一的辞(词)性之美、咏叹之美,实际是诗性之美和乐性之美的合一。
二是“声词相从”要求声意(乐声+声情)相谐。沈括认为,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唐人所填之曲等旧俗有声词相从的特点。旧俗即先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提出的时代,歌谣是自然而发、声词相从的。这些歌谣和诗词曲等都是民间老百姓或诗人用来歌唱的,其所歌唱出的声音与歌谣、诗曲等中的文辞是相互联系、吻合的。这种吻合体现为声意、声情(声乐)的吻合。声情(声乐)相随即声音与情感相谐,沈括所言“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即要求曲之哀乐情感(声情)与曲(乐声)之声的一致性。这在《礼记·乐记》乐论中常被论及,其曰:“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这句话在《梦溪笔谈·乐律》中被征引。安且乐、怨且怒是情感、意志,音乐安以乐则诗与声、声与曲安且乐,即音乐、诗辞、声音、曲调都是一致的,表明沈括声情(声乐)相从的观念。孔颖达曾提出“情志合一”说,其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3)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08页。如果从情志意一致的角度看,也有声意相从的可能。沈氏所言“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中的“乐声”即声,“怨词”“人情”即意,这是从乐声、声情相谐的反向来立论的,与声意相从是同义。
三是“声词相从”的最高境界是“声中无字”和“字中有声”。沈括云: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4)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五,胡道静校注,第61页。
沈括的解释纯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只谈了声、字的声音特点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最后“含韫”说明了“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中“字”的本意是内容或意义等。宗白华解释“声中无字”道:“‘字’被否定了,但‘字’的内容在歌唱中反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取消了‘字’,却把它提高和充实了,这就叫‘扬弃’。”(5)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页。宗白华所说的内容即字之意义。这样看,沈括之字是词曲之意义,由此就可理解“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处理的也是声与字词之意的关系,只是沈括将其具化到声与字词之抑扬上了。沈括谈“声中无字,字中有声”的目的就是要将字词的具体意义与文辞消解掉,从而达到声词协调的最高境界——“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
综上,声词相从是沈括在诠释“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时所提出的诗声理论,从这一点看,沈括“声词相从”说是在追求先秦诗学背景下的诗乐合一传统。如“诗志”句中之诗(乐)一样,沈括《乐律》中的诗并不仅指诗,还包括词等文学体裁,但这些体裁的本质特征是诗性文学。诗性文学(诗词曲等)之声应符合字、声整合之要求,故有声意相谐之具体追求。
二、“乐为诗作”说
诗乐关系是中国传统诗学非常重要的话题,一般有诗乐合一、诗乐分离等之说。刘勰《文心雕龙》“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之说是对诗乐合一的深入阐述,同时把声在诗、乐中的地位较好地展现了出来。刘氏强调,乐是以诗为心的。这里的诗包括诗之文字及其背后的情感、意义、思想等,反映了刘勰强调诗的根本性地位和乐的从属性地位的观念。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诗乐合一思想在中国诗学史上开端式的宣言。宋代乐论在讨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过程中,把上述刘勰的讨论内容深化并提出了“乐为诗作”与“以声求诗”两个重要论断。朱熹的有关讨论较引人注目,其云:
来教谓《诗》本为《乐》而作,故今学者必以声求之,则知其不苟作矣。此论善矣,然愚意有不能无疑者。盖以《虞书》考之,则《诗》之作,本为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得其志而不得其声音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钏鼓之铿锵而已,岂圣人乐云乐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时千有余年,古乐散亡,无复可考。而欲以声求诗,则未知古乐之遗声,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协之音律而被之弦歌已乎?诚既得之,则所助于诗多矣,然恐未得为诗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则今之所讲,得无有画饼之讥乎?(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答陈体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13页。
朱熹以古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为依据推论出乐为诗作、乐出于诗,实质在强调诗的言志之根本功能,或者说是为其重理、重意、重志之思想张本。他又批判地提到时人以声求诗的方法,这实际反映出宋人已然存在的以声求诗之观念。声是乐的重要构成,如果这样理解,朱熹“以声求诗”就是后代的倚声填词之类的作法,即先有音乐、后有词曲。所以,朱熹《朱子语类》曰:“或问‘诗言志,声依永,律和声’。曰:‘古人作诗,只是说他心下所存事。说出来,人便将他诗来歌。其声之清浊长短,各依他诗之语言,却将律来调和其声。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调了,然后做语言去合腔子,岂不是倒了!却是永依声也。古人是以乐去就他诗,后世是以诗去就他乐,如何解兴起得诗人。’”(7)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05页。这句话的前半段“古人……和其声”说的是诗言志及古代声依永的传统,是要以乐就诗即乐为诗作;后半段“今人……诗人”批判的是宋代永依声的诗乐现实和以诗就乐的作词之法,即以声求诗。
宋代乐论提出乐为诗作、反对以声求诗,其主要内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乐为诗流。音乐是诗歌的支派,是诗歌的分流,正如诗余为诗之流一样。诗歌是文学的开端,包括诗、乐府、歌等。王灼云:“乐记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8)王灼:《碧鸡漫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3页。志是诗之源头,诗是歌之源头,歌是声律之源头,故有“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之说。所以,诗是包括歌的,不需要在诗外再求其音乐。可见,王灼是反对时人先定音节、制词从之的做法的。和王灼思想表达一致的是王普,其云:“按《书·舜典》,命夔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盖古者既作诗,从而歌之,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乞复用古制。”(9)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30页。这就要我们按照“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要求先作诗然后歌之,而不是先制谱后命词(诗)。宋代学人为何如此关注乐为诗作呢?主要是声乐助于诗。朱熹《答陈体仁》曰:“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达于闾巷,学者讽诵其言以求其志,咏其声,执其器,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则声乐之所助于诗者为多。”(1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答陈体仁》,第413页。朱熹所说的“声乐助于诗者为多”的“多”指的是讽诵之声、咏其声、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等三个方面,这基本概括了声乐的作用。讽诵之声即吟诵诗歌;咏其声即拉长声音来咏叹诗歌;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即诗乐舞合一使诗的作用通过乐、舞来更好地培养读者与创作者的德行。可见,乐为诗流不仅是诗歌的内在需要,也是现实需求,更是传统诗学文学创作的审美需要。
二是强调“声依永”,批判“永依声”。“永依声”是宋代非常独特的诗学、乐学理论,虽被一直诟病,但成为诗学、乐学、词学等客观存在的实践理论。韩伟《宋代乐论研究》提出,宋代乐论已经试图开始进行形式化的转变,在具体实践层面出现了从“声依永”向“永依声”的转变。(11)韩伟:《宋代乐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这一观点是以朱熹、王安石所说为基础来谈的。《朱子语类》曰:“古人作诗,只是说他心下所存事。说出来,人便将他诗来歌。其声之清浊长短,各依他诗之语言,却将律来调和其声。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调了,然后做语言去合腔子,岂不是倒了!却是永依声也。”王安石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12)赵令畤:《侯鲭录》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7册,第407页。朱、王均强调,传统诗学都是按照“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来创作,先有词后有声。由于倚声、以声求诗等原因,宋代客观形成了先有声、后成词的创作方式,这说明宋代非常关注乐与声在诗学、词学、曲学中的作用和取向。吴曾所编《能改斋漫录》中的“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淫乐”之事曰:“明皇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于时才士,始依乐工拍担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13)吴曾:《能改斋漫录》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第537页。看来,“永依声”的创作风尚最早要溯源到唐代李隆基那儿,形成一种文学风气应该是宋代之事。清代沈道宽《论词绝句》曰:“探源乐府溯虞廷,要把诗余比再赓。大晟伶官工制谱,王孙已道永依声。”(14)沈道宽:《论词绝句》,见孙克强、裴喆编:《论词绝句二千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5页。大晟,指大晟府或大晟府整理、制作的乐曲,又指北宋词人周邦彦,因周邦彦曾提举大晟府。“永依声”在词曲发展上指制作词谱的现象,这实际上是要关注词的音乐与声音的审美效果,故王运熙等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说:“‘声依永’还是‘永依声’,是指音乐配合歌词还是歌词配合音乐,这关系到作品是以文学性为主还是以音乐为主的问题。今倚声填词有可能为了适合音乐而对歌词创作有所拘束,影响到其言志抒情的职能,甚至成为乐曲的附庸。”(15)王运熙、顾易生主编,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49页。这一见解有遵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意味。清人何焯的见解比较中和,其云:“然以《虞书》之次序,求之古人,固先有诗而后被之声歌,故曰:声依永。若必待宫商上下相应,发言为诗,则是永依声也。”(16)何焯:《义门先生集》卷六,苏州文奎斋局刻本,第3页。何氏承认“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纲领性地位,但也不废弃永依声在诗学、乐学、词学实践中的作用。“永依声”是宋代乐学、词学中的创作风尚和理念,它应该在“声依永”观念的影响下生存发展并与之共同存在,发挥其理论价值。
三是志本声用。宋代诗声理论的杰出代表郑樵曾云:“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17)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83页。这是志本声用的较好诠释。朱熹云:“然犹曰:‘兴于诗,成于乐’,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圣贤之言诗,主于声者少,而发其义者多。……故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患学者不能平心和气、从容讽咏以求之情性之中耳。”(1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答陈体仁》,第413页。朱熹以为诗为本、乐为末,这一思想无疑有偏激之嫌,是乐为诗作的过度阐释。北宋刘安节云:
学诗之道,有本有用。志之所之谓之诗,此其本也;声成文谓之音,此其用也。……此学诗者所以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有待于太师之所教者也。……六诗之声即此以求之,则声成文而为音矣。……夫惟六诗之章,一出于六律而为之度数,故能播之金石、形之舞蹈、宣之丝竹、达之匏革,而与堂上之歌相和为一。翕如其始作也,纯如其从之也,绎如其乐成也,曾未有毫厘之差者。盖其所歌出于一律,故尔以传。……此六诗之义所以用之天下,而使人闻之者,可以兴,可以群,与乐同其妙用者。太师之教为之开端故也。昔者,舜命夔典乐,教胄子,有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教诗以律,其来尚矣。于舜之世,而夔之乐乃至于百兽率舞、凤凰来仪者,岂特德化之所由致耶?律吕之法抑亦有助焉耳。(19)刘安节:《刘左史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7-9页。
刘氏对声用作了较全面的解释,提出六律、五音是声的重要构成。所以,六诗之声追求的就是使声有规律、有秩序的律,这也是六诗之义所在。所以,最后得出 “律吕之法抑亦有助”诗之结论。此处,刘氏既承认了诗言志的本,又通过以声求诗来强调声之律的重要意义。《宋史·乐志》进一步解释“乐为诗作”道:“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为度,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节其烦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咏;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者,此也。今祭祀乐章并随乐律,声不依咏,以咏依声,律不和声,以声和律,非古制也。”(20)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八,第2981-2982页。这里“乐为诗作”之“诗”进一步具化在“人”——“乐本效人”,这比乐为诗作的观念更理性,也符合诗、乐最终来源于人而服务于人的思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志本声用”是诗之本、乐与声之用,实际说的是人之志与声之审美维度的问题。
可见,“乐为诗作”是从传统诗学的角度立论,其满足的是人之志向、情感的表达和审美需求。宋代乐论虽有以声求诗之主观愿望和实践,但未能突破诗论之局束,总体受志本或声本、乐用诗学思想的左右。
三、“声转机萌”说
“声转机萌”包括两个词:声转、机萌。
“声转”或即“转声”“转喉”“转音”等,这些说法在宋以前就已出现。扬雄《方言》之第十曰:“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乐齐言子矣。”郭璞注:“崽音枲,声之转也。”(21)扬雄:《方言》卷十,郭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页。“声转”常被学界注释为“转注”,明代王应电云:“声出于或有余,或有不足焉。声之有余也,一义而为一声,不能声为之制字也,从一字而转为数声,故曰转注。”(22)王应电:《同文备考》,转引自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第211页。清代王念孙疏《广雅》多用“声转”“声之转”“一声之转”等来说明“音转”,其云:“‘无虑’‘勿虑’‘摹略’‘孟浪’皆一声之转。大抵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字)则惑矣。”(23)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748页。宋代注释“声转”较著名的是张有,其云:“转注者,辗转其声,注释他字之用也。如其、无、少、长之类。”(24)张有:《复古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6页。康保成曾作了大量的考证后解释:(转音)或“转喉的发音技巧是,气发丹田,将四声与切音有机结合起来,唱好一个字的头、腹、尾,同时又在声与声、字与字之间从容过渡,做到‘声中无字’,婉转悠扬,这就是转喉技巧的精粹,也是昆曲有别于其他声腔的重要特征。”(25)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康氏的解释是从戏曲的角度来说。这些解释与宋人乐论中的“声转”之内涵大同小异,主要指声韵的变化过渡、转喉、转变唱诵的方式等三层意思。一句话,“声转”就是要使诗、词、曲的声音过渡不明显、自然和谐。
“机萌”指人的志、情、思维、构思等的萌发。银道源《明道密旨》曰:“因机萌而言,故有意、念、性、神之分。”(26)银道源:《明道密旨》,盛克琦点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23页。银道源把“机萌”理解为意、念、性、神等,这些都是人的志向、情感、意念的东西。《欧阳修集》卷五十八《红鹦鹉赋并序》曰:“又闻古初,人禽杂处。机萌乃心,物则遁去。深兮则网,高兮则弋。为之职谁,而反予是责!”(27)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五十八,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2页。欧阳修直接将“机萌”等同于心。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中的“响在彼统,乃得克谐,声萌我心”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28)刘勰:《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5页。只不过,刘勰把声与机萌结合起来阐述,应该是“声转机萌”之发端。
结合来看,“声转机萌”就是声音的过渡要与创作主体的志向、情感等相符,并呈现自然和谐的风貌。宋人“声转机萌”的提出语境、内涵及意义都有一定特点。
“声转机萌”是在对“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解释中提出的。张载云:“古乐不可见,盖为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只此《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求之,得乐之意,盖尽于是。诗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转其声,令日可听,今人歌者亦以转声而不变字为善歌。长言后却要入于律,律则知音者知之,知此声入得何律。”(29)张载:《张子全书》卷五,朱熹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5页。张载强调,《虞书》所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古乐的经典表述,也可从中领悟古乐内涵及风旨。古乐的获得,除去言志、永言外,还需转声、可听。张载又具体言明转声是以不变字为前提,那就是要转换腔调和声音。从“可听”和不变字来看,张载想说明的是:转声是古乐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但同时要和谐可听、不露蛛丝马迹,达到音不同而字同即不变字的需求。王柏曾云:“夫歌咏者发于天机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饰于仓卒之一语,是皆可以观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祸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时所以赋诗于盟会燕享之际,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为者。盖一吟一咏,声转机萌,事形诗中,意形诗外,真情故态不能矫诬;自非义理素明于胸中,而有能勉强不失于金石笾豆之间哉!”(30)王柏:《诗疑》,顾颉刚校点,上海:朴社,1935年,第45-46页。王柏的解释从赋诗言志、歌永言出发。他强调“转声机萌”才能“事形诗中”“志形诗外”,这把声音的自然之要求表达得较清楚了。
“声转机萌”的内涵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声韵要转换。声韵包括声、韵和调,总结起来就是字之声音。沈括云:“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末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此谓‘声中无字’。”沈括要求清浊、喉唇、齿牙舌都分清,并能在字与字之间自由地转换,即要不同清浊、喉唇、齿牙舌之字都能较容易地转换,不能出现读《尚书》时“诘屈聱牙”的状况。
二是要转喉。李清照《词论》曰:
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3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67页。
“转喉”是“把字音与音乐旋律的结合固定化了,平上去入四声各分清浊,一共八个字调,每个字调与旋律有相应的结合”,(32)叶长海:《曲学与戏剧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3页。这一方法与一般歌唱、朗诵诗词有一些差异,呈现出来的声音非常独特。李清照提到的转喉是词之重要唱法,缺少“转喉发声”可能达不到“众皆泣下”的声音效果。王柏云:“诗何自而始乎?于尧之时,出于老人儿童之口者,四字为句,两句为韵,岂尝学而为哉!冲口而出,转喉而声,皆有自然之音节。虞舜君臣之赓歌,南风五弦之韵语,与夫五子御毋述戒之章,体各不同。历夏商以来,讴吟于下者格调纷纷,杂出而无统。”(33)王柏:《诗疑》,顾颉刚校点,第41页。古代人都是随性冲口而出,再加上转喉之方法,就成了自然之古乐、古诗。
三是要自然。陈栎《定宇集》卷四《论诗歌声音律》曰:“诗出于心声萌动之天,而律根乎阳气萌动之天,皆自然而然,而非人为之使然,故曰天也。”(34)陈栎:《定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第20页。陈栎认为,心声萌动就是要自然、非人为。陈文蔚云:“盖诗者,所以吟咏情性,出于天机之自动,学者于吟哦讽诵之间,可以兴起其善心。故古人于成童之时,已学乐诵诗。教者必以此为先,而学者必自兹始也。”(35)陈文蔚:《陈克斋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8页。“天机”即天性、自然之规律与法则。两位陈氏之论皆强调声与吟哦的自然。张载云:“其人情如此,其声音同之,故闻其乐,使人如此懈慢。……移人者,莫甚于郑卫。……今之琴,亦不远郑卫,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长言,声依于永,于声之转处过得声和婉,决无预前定下腔子。”(36)张载:《张子全书》卷五,朱熹注,第97页。这实际上要求声转自然,不能提前定下腔子。
所以,“声转机萌”是宋人诗论与乐论中非常重要的技巧与方法,其吸收古代诗乐合一的自然观念和后代声音、声律之技巧,糅合成有关诗乐之吟咏的声音属性与情性的意义属性的新观念。
总之,宋代乐论与诗声理论的融通是诗、声、乐发展的必然趋势。另外,“声容”说、“以声为律”说、“超声律”说等也是宋代乐论与诗声理论融通的重要观念。这一融通来自于对先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诗乐合一观念的解释与发扬,对诗与音乐之作用进行了学术定位,并在声律或声音层面上把这一传统观念在宋代诗词曲乐的发展中得以具化,有的在形式层面、有的在内容层面,这是宋代诗乐融通与博弈的结果,也是宋代诗学与诗声理论发展的新变,对推动宋代诗学、乐学有非常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