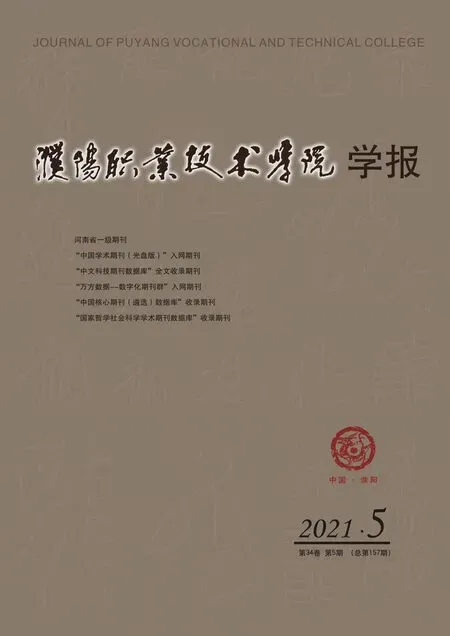荀子的礼法观
2021-11-28徐睿君
徐睿君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先秦哲学的殿君大师”[1](15)荀子一方面批判继承孔孟传统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吸收法家“法”的学说,创新性地提出了他的礼法观,将礼法观作为道德教化的核心,构建了独具特色的“隆礼重法”的礼法架构。荀子礼法观通过符合人情的礼治以达到培养个人道德修养,满足人们合理欲求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根本目的。
一、礼法观理论根基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德治思想,将先秦儒学的理想主义困境拉入现实世界,发展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礼法观,追根溯源,他的礼法观理论渊源在于他“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以及“化性起伪”的人性论。
主张天人合一的孔子强调在顺天命的基础上也要重视人们的道德修养形成人的本性;孟子继孔子天命观赋予天道德人格意义,认为“人性根于心而禀授于天”;荀子发展孔孟思想提出“天人之分”的天命观。
荀子天命观是荀子礼法观的本体依据,在荀子天命观中少了几分神学色彩,认为天是客观自然世界,不受主观意志左右,天依靠自身规律不断变化发展。“人”作为自然独立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天人之分”将“人”从“天”中分离,使“人”具有“制天命而用之”的主观能动性。人既要知其不为地顺应自然,又要知其所不为地利用自然。在荀子天道观中人可以通过一定的目的手段,利用客观世界,达到为人类自身服务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荀子天命观将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人自身价值提到了另一种更高的境界,突出了人的内在价值。
荀子的“眀于天人之分”是“礼法观的逻辑前提”,主要意思是天不受人的制约,国家的治理也是君王的事,与天没有直接关系。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231)客观世界自身没有意识与行为目的性,它的运行是依自然规律来的,不受人事的限制,自然规律与人事直接的相互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人类的灾祸是人自己创造的,与自然规律无关,君王的勤政或者暴政都是人事,与天命无关,这只是一个政治社会的产物。荀子指出:“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知之可以治者矣。”(《荀子·天论》)人类可以通过把握自然规律,安排人事,社会的治乱也在人为而非天。
荀子既将自然和人事加以区分,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自然和人事的关系,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种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也为荀子“化性起伪”的人性论奠定了基础。
自从先秦“性相近,习相远”之后就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性论的争论;孟子从价值应然层面提出人性本善的学说;荀子不同于孟子天赋道德观的性善论,看到了人有堕落的潜质,提出了自己的性恶论。
荀子依据他的自然天道观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人们生下来有趋恶的本性,如果顺应“耳目之欲”将引发“争夺”“残贼”等事情。荀子把人类的本性与人类的自然欲望等同。将人的自然欲望视为人的本性,这些欲望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引起人们趋利避害,发生争夺,“乱理而归于暴”,使得社会进入无秩序的混乱,为了防止混乱必须制定合理的礼义道德引导人们趋善。
荀子认为人性需要经过后天的道德教化,他人性论的突出贡献是他的化性起伪,荀子将孟子人性论的应然问题转为实然,这种实然源于荀子天道观,立足于人的自然生命属性[3](138),在这种人们的天生自然状态下提出了“性伪之分”,其中“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伪”是与礼义密切相关的后天习得之性,这就为性的向善提供了可能。人的本性是天生的,但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去感知生活,久而久之通过实践学习成为“伪”。如果自然本性支配人们的行为活动,那么必将在集体社会中触及他人合理利益,引发争夺。
《荀子·性恶》曰:“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人的天性需要经过后天的学习才能改变,这里礼义法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不难看出,荀子的“化性起伪”为礼义法度的合理性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
从《荀子·礼论》中可以看出,礼能够有效地克制人不合理的欲求,防止恶的扩展,有了礼治才能更好地培养人们自身的道德修养,社会才能避免混乱。在国家治理中强调“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有了礼人们行为不会僭越,能够满足人们的合理欲求;有了法,社会才有公平秩序。
二、“隆礼”与“重法”
“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荀子认为礼与法两者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荀子的礼法观通过设礼义法度对人本性进行改造,培养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规则规范,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尚[4](11)。
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以仁释礼,在孔子看来礼具有教化功能,通过礼来约束自身道德行为,达到自觉修身。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从性善的角度说明谦辞礼让是礼的萌芽,礼是人们日常交往中的美德。荀子在继承孔孟的基础上对礼进行了新的诠释。
对于礼义的解释,荀子认为这是对地位尊贵者要敬重的要求;对年老者要尽孝;对年长者要敬爱;对年幼者要慈爱;对卑贱者要恩惠。“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荀子把礼视为高标准的道德规范,人们不遵循礼就不能很好地在社会上生存,行为规范不合礼的要求事情就不能称心如意,国家不依礼行事整个国家就不得安宁。《荀子·议兵》中对礼解释为“治辨之极”“威行之道”“功名之总”,治国中不遵循礼,将有损江山社稷。在荀子看来,礼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通过后天改造人们的本性,使人们的行为符合规范,而且也是治国理政不可缺少的准则。
礼有满足人们合理欲求的作用。从《荀子·礼论》篇不难看出,礼源于“欲”,他还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荣辱》)。所有人都想拥有荣华富贵,人们的欲望不能实现,便会有争夺各种物质资源的情况,引起社会动乱[5](17)。人们的欲望也各种各样,无穷无尽,但是在现实情况中社会物资有限而人的欲望无穷尽,若没有有效的措施在物资和欲望两者间进行制约,那也必然引发人们之间的冲突矛盾。礼的本质就是“度量分界”,古代圣王制定礼的作用正是为了协调欲望与物资的矛盾,节制无尽欲望。
《荀子》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和孔孟一样都讲究克己复礼,主张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礼的功能就是明分使群,等级结构分明,人人安分守己,这就是礼的别与分。只有制定了礼,君王安心治国,农民精于种田,工匠潜心研究[6](7),有了规范和制度人们才能相互约束,才能保证自己的合理欲求得到满足。
荀子的刑法观一方面打破了先秦孔孟儒家过分重视道德教化,讳言刑法的思维模式,吸收法家将赏罚与人们行为规范挂钩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又重视礼义教化,反对法家过度重视刑法。在荀子看来礼义教化并不是万能的,而法度却能弥补礼义的非强制性。治国理政少不了刑法的作用,对于严重违反社会和谐的暴徒,需要通过刑法加以强制约束。
荀子将法比作标尺,是一种法律准绳,法是衡量功与过的“衡石”,因此荀子的重法不是如同法家那样的严刑峻法,而是慎刑法,他认为,“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要看到商纣王重刑导致被周朝灭亡的历史,不能像法家一样过于重视刑法,对于“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要以礼义教化为主,通过教育培养他们的技能,通过奖赏耐心鼓励他们,通过刑法来惩戒他们,尽可能地使他们有一定的转变,如若不可只能重刑。当然他也反对重罪轻罚,罪至重而刑至轻。
《荀子》曰:“法者,治之端也。”治国理政需要充分协调刑法与罪行的关系。荀子强调合理协调罪与刑之间的关系,反对重刑,反对法家的“象刑”以及“株连”,认为象征性的刑法违背罪行相当原则,“株连”会将品德高尚之人一并处死[7](20)。不讲罪刑关系就会丧失法律的公正性,那么人们便不会遵守法律,法律的威严也就不复存在。
在法律制定方面荀子极其看重法制的适度性,他说:“诛而不赏也,则勤属之民不劝也;诛赏而不类也,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也。”(《荀子·富国》)执法者应该制定统一的法度,对不好的行为进行处罚,对好的行为进行奖赏,这样人民就会有积极主动性,法度的作用也能充分得到发挥。
对于法律的公正性而言,荀子主张“任法去私”“以公义胜私欲”,通过“圣人为王”,保证统治集团能够合理、公正地实施法律,以确保法制不被破坏。为了避免西周时期“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断案形式,“君教出,行有律,吏谨将之无铍滑。下不私请,各以宜,舍巧拙”,这正是荀子对司法公正性的要求,执法者应该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奖赏与处罚,不因底层人民地位低下而忽视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执政者都要始终如一地保证法律的客观公正性。对于犯法的官员也要依法惩戒,才能达到“百吏畏法循绳”的良好治国效果。
三、礼法并施
荀子不仅引法入礼,而且坚持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理念,讲究礼法并施。荀子认为“威有三”,在治理国家中,道德的威力能够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严刑峻法的威力能够消除国家的祸乱;暴虐刑法的威力则会使国家走向灭亡[8](56)。他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巧妙使用礼法的手段,达到“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目标,他将礼法表述为“群居和一之道”。为了人们之间减少欲望的争夺,社会中就产生了礼义法度,两者相互作用,通过“隆礼重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不断调和人们之间的冲突的同时,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井然有序地展开生活活动,人人安居乐业,心满意足。
荀子曰:“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他将礼义教化与刑赏相结合,反对“不教而诛”,认为奖罚都不可能让一个人竭尽全力真心地做某事,起不到教化人民、团结一致的作用,过度的刑法势必导致刑法越来越繁重,人民少了教化就会对繁重的刑法产生困惑,反而会更加容易触犯法律,这对于防范犯罪的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国家也会陷入混乱。
同样,荀子也反对“教而不诛”,反对只进行道德教化而忽略刑法,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难以起到威慑作用。总有一些教而不化的人,对于这类人应该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维护人民的合法利益。总体上来看,荀子主张礼仪教化为主,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民应该多加礼义教化,以确保他们不是为了得到法度的奖赏而做某件事。治理国家时,要充分发挥礼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化民成俗”,在礼义的基础上用刑法加以辅佐,才能保证天下的和平稳定。
一味使用道德教化或一味坚持刑法都不能很好地治理天下,而礼法并施正是治国之策,有利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只靠道德教化就连类似尧舜者也不能“使鬼琐化”;只依靠法律则“不足以尽人之力”。只靠赏罚制度,并不能充分挖掘人们的潜力,不能在危机时刻教会人们舍生取义。要将“先教”视为“政之始”,将刑法视为“政之终”,在道德教化的前提下使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拔不祥”,再加上一定的刑法达到“化恶为善,化私为公”[9](25)。
在治国理政方面,君王要把礼义道德视为最高准则,礼义是不受任何东西所侵害的,更不能为了得到天下而有损礼义,只有执政者都遵循礼义,人们便潜移默化地遵守礼义法度,这样国家也就能安定了。这就是礼法观在“王政”中的具体运用。
礼法观在经济上的体现则主要表现在“富国富民”上。国家要想富强,还要靠人民,要按照礼义制度的要求节俭费用,制定富民政策。君王按照法律制度收取税收,人民按照礼义制度来节约粮食,这样粮食就会越来越多,就能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状态。倘若君主不按法律规定重税收,人民不按礼义要求节制,那会导致国家国库空虚,人民争斗不断。
在治理臣民上君主要公正不偏不倚地按照能力任用贤能,上到“三公”下到士大夫,用礼检验他们的德行和才能并进行任用。对于不同等级地位的人,按照礼义制度来加以区分,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恪守职责,依法办事,以求稳定的社会秩序。
蒋庆曾在《政治儒学》中高度评价荀子的礼法观,认为荀子“既考虑人类行为规范的普遍性,又考虑到人情厚薄亲疏的特殊性;既不排除典章制度对人具有某种外在的强制作用,更强调典章制度的本质在于内在的人性基础”[10](8)。在荀子的礼法观中,始终秉承着礼为体法为用的观念,追求个人道德培养的同时也要求外部制度的制约。他的礼涵盖范围广泛,包括人伦道德和社会等级制度等多个方面,他的法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多个方面。
荀子的礼本质是一种道德存在,天下的人们都应该有礼法一体的道德自觉性,通过修养和改造,从而最终塑造成一个个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总体上来看,荀子的礼法观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在思想上糅合儒法奠定了汉代新儒学的基础,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新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