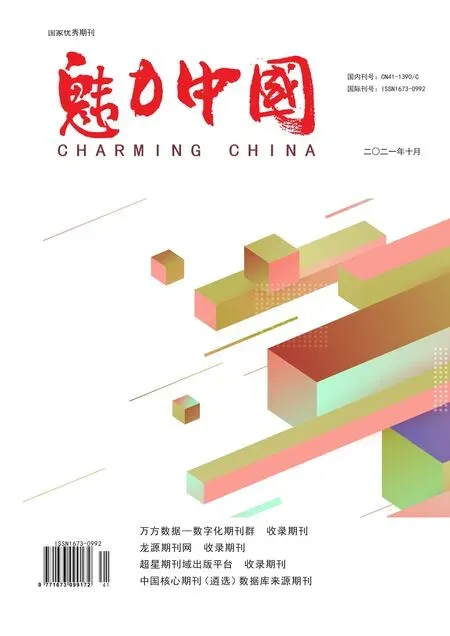表演创作中肢体表达的中国美学特征
2021-11-28胡彧哲
胡彧哲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迈克尔·契诃夫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基于斯式表演体系的精髓——体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训练方法,核心理念是“心理-身体”,他强调应将表演的重心放于角色上。表演创作过程中,演员自身的感情生活和人生经验有限,难以凭自身微薄的经验无法塑造出个性迥异的人物,所以演员只有逐渐走向角色、进入角色,才能使表演为成一项真正的艺术创作活动。“心理-身体”这一核心理念帮助演员在体验的基础上更细致的关注身体,进而创造出更生动形象与人物贴合的角色,帮助演员与角色达到身心合一的效果。演员需通过想象来调整、展现外在动作与内在心理,以保证感受和动作之间相互依存、不分彼此,并通过具有丰富表现力的肢体动作和身体姿势,将人物的内心呈现出来。
一、表演创作中的肢体表达
话剧中,肢体表达的作用同语言表达一样重要,除开能明确有利的引导故事的发展走向、制造矛盾冲突将剧情推向高潮外,更能达到戏剧人物形象饱满立体的舞台塑造目的,同时它还是整体创作与意图的呈现方式。里希特曾说,“剧场演出最关键的是对真实身体和真实空间进行共同体验。”但演员无法确保能与自己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拥有相同或类似的人生经历,因此演员只能“通过下意识、本能的方法,用一种精炼、浓缩的形式来获取角色的心理、欲望和情感,并且运用精确、具有强烈表现力的形体姿势来凸现角色心理、欲望和情感最本质、最具典型性的特征,从而达到从整体上来接近角色,进入角色,乃至准确地表达角色的目的”通过进入角色,成为角色,以此来激发演员的肢体表达欲望。
秦海璐作为拥有深厚戏曲学习经验的演员,在其参演的多部戏剧作品中,可以观察到她扮演的人物角色都具有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鲜明的肢体表达特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原著中的王娇蕊是一个集天真、性感,骄傲、风尘于一体的极具矛盾性的女性形象。由秦海璐饰演的王娇蕊,通过与角色一致的肢体动作将原著笔下的人物呈现得活灵活现。在一幕中,王娇蕊优雅的夹着香烟坐在王士洪的腿上放松自在的抽烟。看似轻浮的举动非但不会使观众产生反感的情绪,反而更好的刻画出王娇蕊的人物形象,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真实。舞台上王娇蕊肢体动作热烈奔放,尽显性感娇态,当故事发展到结尾,其在舞台上的肢体动作和行动也随命运和性格的变化而内敛不少,与前篇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视像画面是单从阅读文学作品或单纯听台词所无法欣赏到的。
原著李碧华版本的《青蛇》,对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有潜在的积极正面的情感倾向,话剧《青蛇》与之贴合,秦海璐饰演的青蛇出场第一幕就以具有美感的肢体动作出现,而非妖魔化处理,以此建立起青蛇正面形象的基础。其次借助肢体语言和身体动作所产生的戏剧张力,从而带来视觉冲击,让观众获得审美体验。作为有着深厚中国戏曲功底的秦海璐,在《青蛇》中,利用自身优势通过肢体行动完美刻画出一条刚化为人形的蛇的形象。在表现蛇的动物习性时,匍匐在地,展现出灵活柔软的身姿;表现人的欲望时,通过肢体间的环抱缠绕进行展现。当青蛇遇到法海试图勾引时,秦海璐饰演的青蛇攀附在辛柏青饰演的法海身上,通过诸多类似戏曲程式动作的造型将蛇的习性生动展现。再如青白两蛇为争夺许仙而打斗及两蛇一同水淹金山寺的那幕,均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程式动作中武戏的打斗场面。以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精准表达人物内心的变化与挣扎,同时两条蛇的蛇性被外化通过肢体完美呈现,表现出人形蛇心的习性和欲望。
可见,好的戏剧需要有张力,除了通过演员的对白体现,肢体表演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二、肢体表达的美学特征
戏曲、舞蹈、哑剧等诸多其他表演艺术都将演员的身体作为重要的创作工具,独特的肢体语言表达方式,又使其展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点。相对于戏曲的“虚拟程式”、舞蹈的“抒情诗意”、哑剧的“夸张放大”,戏剧表演也有着自身的独特的美学特征。
(一)想象与表现一致
当演员接触剧本时,作者的情绪、想象、感觉、创作理念以及他的情感、笑泪,都隐藏在文字背后。因此演员需要基于剧本进行行动和创作,根据角色将自己的意愿、情感与想象实体化,创作不单存于心理或肢体某一层面,仅通过阅读文本来接近、了解的剧本,于演出将是表面的、无效的,无法深入挖掘台词隐藏的含义。演员应基于文学剧本对角色进行“再现”创作,在过程中激发自身情感与心灵对生活的体验。当演员由文本衍生的想象与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相融合后,最终成为对角色创作的情感体验,同时构成演员与角色的关系,肢体表达就是演员情感体现的一种表现方式。如黑格尔所说:“一切情感的激发,心灵对每种生活内容的体验,通过一种只是幻相的外在对象来引起这一切内在的激动,就是艺术所特有的巨大威力。”演员需要利用自己的整个身体,让自己陷入对角色的想象,并投入到剧本对角色要求的各种情绪中去。演员完成“心理”过程后,需将想象出的部分外化为视像,由“身体”进行无声但深刻的表达。
作为青蛇的扮演者,秦海璐曾在访谈节目中表示最初并不认为自己能饰演小青,作为成熟女性的她几乎把白蛇经历过的事都经历过了,不带任何装模作样的在舞台上表演出天真而不做作,是很难的。为了好的舞台呈现,秦海璐在进入剧组后并非只做了研读剧本的准备,而是同导演一起根据人物、剧情修改剧本,设计出体现角色身份、展现曼妙身形的肢体语言。小青这一角色单凭演员对蛇柔软妩媚形象的想象、浮于表面的天真烂漫是无法呈现的,只有调动真实的生活经验去寻找少女时期的纯真状态,在了解自身肢体表达的特点后,通过肢体语言将内心想象化为具体视像,完成符合人物的表情、动作,才能塑造人物形象,传达人物情感。表演创作中肢体语言重在将演员的面部神情及形体动作进行改变,进而展现和描绘出人物的性情特征及心理状态的变化。若演员只有虚浮夸张的行动,无法将想象中体会到的角色情绪用肢体语言表达,便算不上有效表演。
(二)叙事性与抒情性共存
戏剧性是表演艺术最重要也最为明显的美学特征。在戏剧中矛盾和冲突是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以叙事性为第一性。在表演创作中,肢体语言能够通过不同的肢体动作变化,在空间上打破原有的时空进行叙事身份和叙事时空的转变,将人物内心矛盾冲突外化并放大,也能将生活中或思想中无法简单通过语言表达的状态,进行更丰富更具内涵的呈现。演员依靠肢体动作与行动本身将内在感情、节奏进行表现,并根据情绪氛围和角色意识,踊跃调动自身能动性意识与经验,对呈现出的形体特征进行自然、真实、积极的反映。
在叙事的基础上,表演创作中也需要通过肢体语言表达角色的内心,让观众更细腻的感受到语言所无法描绘和表现的人物内心情感。《青蛇》中设计的几场打斗场面,结合中国传统戏曲动作以情带体,以体传情,展现人物当时内心情感的变化,情绪的波动。《红玫瑰与白玫瑰》在体现佟振保与王娇蕊相恋过程的情节中,对现代舞的运用显得流畅而充满活力,演员们通过模拟弹钢琴的动作,配合音乐的旋律与节奏进行步法的快速变化,表现出剧中角色感情的升温。利用适当的肢体表达代替语言,将文字语言转化为可感的艺术符号,同行动意象来实现文字语言的功能,带给观众感官与精神上的双重享受。通过肢体表达的创作将读者从文学作品带上舞台,感受更具生命力的文本价值。
(三)纪实性与诗性相融
中国话剧演员的表演形态区别早期欧洲戏剧中演员夸张的表现形式,更为真实和生活化,一切行动调度都基于真实生活进行,除了对故事情节和对白的要求,更要求演员的表演具有逼真性,要符合生活逻辑。对比西方热情外放的情感表达和表现方式,中国舞台表演方式与中国传统艺术,如绘画、诗歌等相通,追求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意境美。焦菊隐先生曾说“我国传统表演艺术和西洋演剧最大区别之一是,在舞台艺术整体中,我们把表演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同诗歌中的意境与韵律之美,在中国话剧舞台和电影中,叙事性会适当被弱化。话剧中没有技术手段的运用,演员仅以身体为工具进行呈现,而电影则通过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的运用,将焦点聚在演员的细节处理以及周围环境上,对人物的情绪变化进行深入刻画,增强对画面氛围的渲染。
电影镜头中的表演呈现相比话剧略有差异。电影镜头中,演员的肢体细节会根据情节或者情绪的需要,通过特写镜头、长镜头或慢镜头被放大,在这些镜头下,演员表情和形体的表达除了单纯叙事外,还要配合镜头语言进行诗意表达。章子怡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细腻而真实的表情,通过大量的特写展现于荧幕之上,刻意拉长的画面节奏中,肢体的强烈动静对比呈现出带有诗意的效果,并营造出符合角色年龄与心境的纯净美好的氛围。《十面埋伏》中,章子怡的饰演角色假装盲女,削弱了演员的眼神控制,但作为有着中国舞功底的她,通过形体和面部表情,将肢体语言表达发挥得淋漓尽致。影片中水袖击鼓起舞假扮盲女的部分,不仅让剧中人物信服,也让画面前的观众恍惚,忘记她的盲是伪装的。正是演员通过肢体语言代替了诗语言,才让观众从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中,品味到独具中国诗意的韵律节奏。
结语
对演员而言,生活中任何细微的肢体动作出现在视线中都有必要留意和记录,要能根据角色的需求与差异性展现出相异的肢体语言,塑造出众多生动且具差异的人物形象,这要求演员能够将对角色的想象与提炼的生活经验相融合,展现具有个性并贴合真实的人物,使人信服。其中不乏有动作是根据生活动作进行加工、美化的。在帮助演员准确且有效地抓住角色的性格及特点,进入角色的心理和灵魂这一点上,戏曲的程式思维也有相通之处,从外部带动内心,产生心理感受再向外带动肢体动作,进行情感表达使肢体表达具有语言性。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的“双重性”是随着程式性、写意性表演产生的现象而不是去刻意打破生活幻觉。秦海璐及章子怡在其作品中,不仅通过丰富的肢体表达将人物内心细腻情感外化,成功塑造出一众令人印象深刻,极具东方美感的角色,因自身深厚的戏曲功底,在现代戏剧中充分发挥了传统戏剧的表现技巧,将传统戏曲造型艺术与肢体表达成功融合,使戏曲动作变得合理化,增强了表演的节奏感和美感,拓展了现代戏剧及影视表演的潜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