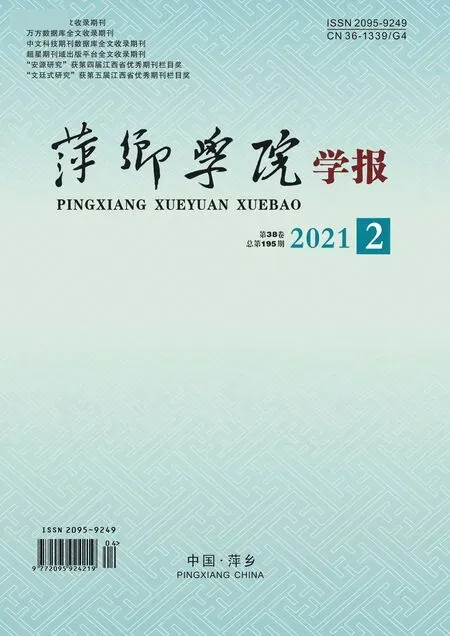儿童视角下的革命成长叙事——评漆宇勤长篇故事散文《安源娃娃安源红》
2021-11-28靳喆安
靳喆安
儿童视角下的革命成长叙事——评漆宇勤长篇故事散文《安源娃娃安源红》
靳喆安
(萍乡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江西 萍乡 337000)
漆宇勤的长篇故事散文《安源娃娃安源红》以安源娃娃玉石为中心,谱写了一代少年革命者成长的故事,再现了1922年前后的安源历史。作品从儿童视角出发来观照这一世界与主题,儿童视角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与游戏精神的彰显;二是采用对比的手法,突出矿工与资本家的二元对立;三是平凡意象与风景的灵动呈现。
《安源娃娃安源红》;儿童视角;成长叙事
漆宇勤的长篇故事散文《安源娃娃安源红》以安源工人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以玉石为代表的一群安源娃娃由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意志坚定的小战士的艰辛过程。这部革命成长题材的作品也是我们透视近代历史的一个小小窗口,作者在调研考察、忠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想象,展示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源这片底蕴厚重的神奇热土所孕育的风云变幻。
一、少年英雄的成长叙事
广义来说,成长叙事包含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中表现人物成长的文学性叙事,其定义可概括为:“叙事者在描绘个体‘主体生成’过程中,以其经历的社会认知能力与实践能力提高、性格心理发展、思维世界观蜕变等相关情节为线索的文学叙事。”[1]《安源娃娃安源红》的叙事围绕安源娃娃们是如何成长起来展开。全书从“扒火车的孩子”开始写起,讲述了安源娃娃们的出身和生长环境。作为煤矿工人子女或农民家庭的孩子,他们丧失了读书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以扒火车当作游戏,从中享受着无尽的趣味;安源的孩子有一个日常重要的任务:捡煤核,穷人维持生活的艰难和辛酸,在这一节里真切地体现了出来。
幸运的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何葆贞等先生的到来,带来了知识与新的思想。他们兴办平民学校,注重实用教育,免费招收工人的孩子去读书,玉石和他的小伙伴们从此开始学习识字、算账。在与老师的交流中,他们认识到“除了原先认命般地等着长大成为矿工和农民,其实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像李先生一样去改变,去争取未来更多的可能性”[2]11。这是安源娃娃们成长转变的第一个关键点:接受新思想的洗礼,重新审视旧的思想惯性。李先生在这里俨然是知识与启蒙的化身,他告诉孩子们:“读了书,可以乘火车到更远的地方去,看比安源山大十倍的山,看比安源街大百倍的街,看比安源村头那个大鱼塘还要大上一万倍的大海。”[2]11安源的孩子们开始对火车连接的远方怀着好奇与憧憬。
然而,远方并非一个美好纷飞的理想国度。当玉石对铁路的另一头怀着美好想象,无比渴望与期待时,李先生借此告诉同学们:铁路的另一头并不仅仅是只有繁华,也有资本家和外国人的压迫欺辱。铁路的另一头也有很多像安源工人一样吃不饱饭的铁厂工人、纱厂工人,也有很多遭遇灾荒和被地主逼迫而无家可归、无饭可吃的农民。这些人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反抗资本家、反抗外国人。这可以说是对安源娃娃们思想启蒙的第二个层面:要懂得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做斗争。此时,中国的大地上普遍存在着饥饿、压迫与屈辱,要坚持自己的利益,就要反对恶霸的欺压和剥削。然而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所以工人要团结起来,改变受压迫的苦难生活。
为了形象地表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对立,在“取暖的日子”一节有意突出了玉石的邻居张二喜、黄工人、欧阳一家的悲惨遭遇。从周围的人事中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不公处境,标志着“玉石们”的进一步成长。作品把工人受压迫的原因明确指向罪恶的资本家,暴露了剥削者的穷凶极恶——“工人们因为没发工资而快要饿死了,矿上的高级职员和老板们却依旧吃得丰盛无比,天天都是大鱼大肉,高级烟酒没断过。”[2]66而劳动大众在李先生的启蒙下深受鼓舞,“工的字形就是顶天立地,做工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工人加在一起就是天!”[2]27人格启蒙和社会启蒙使他们找到了个人和社会的理想。玉石作为安源童子军的骨干,同工人们团结起来,配合斗争形势当小哨兵,张贴标语,参与游行,为斗争发挥自己的力量。在帮助俱乐部完成各项任务的实践过程中,玉石成熟起来,并加入安源青年团组织,在政治上获得认可与命名。
作品以回溯式的叙述完成对“成长”的肯定:“现在,玉石已经老了。曾经的小鬼,曾经的少年,曾经的安源娃娃,也会老去。他想回到1922年,回到那段风云际会的美好记忆,或者,干脆回到1921年李先生到安源来办学校之前,一大群安源的工人孩子在野外不分日夜玩耍嬉戏的时光,然后再缓慢地往后走,路过1922年的1月,4月,7月,10月……对,千万不要漏了9月。那时玉石还年少,那时玉石的伙伴们都还年少,在一面旗帜、一种信念的引导下,由懵懂的孩子慢慢成长为坚定的斗士。”[2]116成长就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不断地跨越和蜕变,进而成为成熟、完整的个人。曾经掏鸟窝、玩弹弓的一群野孩子,在历史的召唤下最后构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组成力量,他们不再是稚嫩、弱小、孤单、无助的儿童,在点点滴滴的积累中,他们如植物一般成长着:“人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黑夜一黑夜地长起来的。正如同庄稼,每天观察,差异也都不太明显,然而它发芽了,出叶了,拔节了,孕穗了,抽穗了,灌浆了,终于成熟了。”[3]在“经受考验——通过考验”的过程中,玉石们也经历疑惑、焦虑、担忧、害怕等心理体验,这些心理体验正是成长行为的基本特征。通过考验的瞬间即“成长”完成的瞬间。
综观以玉石为代表的安源娃娃们的成长轨迹,我们会发现故事的基本叙事范型为:启蒙/反抗/追求/考验/命名。这是一种理想皈依型成长叙事,即以线性时间为维度,将历史的主体在纵向历史进程中考量其精神的成长,在经历考验与磨砺后,使其革命信仰和意志变得坚不可摧,最终体现为对正统观念的认同和对某种信仰的皈依。这一话语方式往往呈现出有惊无险的理想化成长模式,并体现出向集体的成长和阶级意识的生长,合乎社会历史的进程,“成长”的故事因此具有时代共性的特征,成长也具有某种仪式的性质。
二、成长叙事中的儿童视角
一般来说,作家从儿童自身生活层面与儿童经验世界入手,直接描写儿童生活的、关注儿童心灵的作品,大多属于儿童视角。成人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选取“儿童视角”,首先必须使自己来一番角色转换,使自己重新“回到”童年状态,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事策略和语言句式,去重新诠释和表现对象世界。[4]《安源娃娃安源红》立足于玉石这位少年儿童的视角,从以下角度去呈现儿童视野里所观照的世界。
(一)诗性与游戏精神的彰显
成长主题的诗意首先来源于成长自身,本真的存在即是诗。正如儿童文学理论学者吴其南教授所言:“真正的艺术即是‘去蔽’,即是恢复存在自身的澄明。哪里有本真的生存,哪里就有诗。成长即是走向澄明,走向诗。”[5]
作品开篇营造了一种秋日宁静的诗意氛围,展现了一个几乎自足的儿童的精神世界:
“狗尾巴草在风里招摇着自己已经结籽的草穗,高大的樟树依旧浓密翠绿,枯瘦的苦楝树树叶已经泛黄,一颗颗苦楝子成簇成簇地在枝叶间摇摆。秋收已经过去了,收割后的稻草被绑扎起来,堆成一个个圆锥形的稻草垛。
这是宣统年间的普通一天。乡村里的孩子们从下午一直疯玩到傍晚,绕着稻草垛玩抓人游戏,或者躲在高高的田埂下玩捉迷藏。高大的草木、孤独的稻草垛、弯曲的田埂,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游戏场所。
玩到下午太阳渐渐偏西的时候,玉石又一次被伙伴们找到,然后就要轮到他来找别人了。这时,玉石突然提议:‘我们不玩捉迷藏了,我们去萍乡县城玩吧?’”[2]1
儿童对游戏的热衷,使其投入其中进入忘我的状态,他们奔跑、嘶喊、打闹,尽情释放着旺盛的生命力。静默的秋日,喧闹的孩子,一种游戏的自由充盈于天地间。在好奇和快乐的心理驱动下,他们第一次进城看到火车,“一个吐着黑烟的怪物在地上爬着”,并为目睹这个新事物而得意,甚至骄傲地认为“比家乡的小伙伴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的孩子都更厉害几分”,进而产生朴素的联想“如果我也变成一块煤,跟着它们乘坐火车、乘坐轮船,到铁路的另一头,到江水的另一边去看看,那就好了”[2]12。游戏精神是儿童的原始天性,召唤着野性的活力。作者把握住儿童的游戏心理,将游戏精神融注到文本中,比如制作弹弓掏鸟窝、舞狮的风俗、武艺人的昂头碎石等,从而使作品趣味盎然。这也是作者本人的诗性记忆,由于作者对童年生活生动的还原能力,我们从中获得了一种纯然的生活质感。
(二)“矿工/资本家”的二元对立
儿童对世界和人性的认识非黑即白,对是非善恶有直观的认识。作品透过儿童纯真的视角,关注到人的权利的丧失和底层矿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描写苦难的大众的同时也描写对立面资本家,把两个阶级截然不同的生活现状置于强烈的对比之中,来揭示矿工被压迫的黑暗的现实。
玉石目睹了小欧阳因捡炭被当作贼打死,因无处伸冤,结果欧阳夫妇一个上吊、一个投井自尽的悲剧,他也看到无数童工为挣几个铜板在烟熏火燎中生窑火的艰难——“他们每人守着一个火眼,窑子中间竖着一根烟囱,一座窑子有十几根烟囱。一个个被烟熏得面污嘴黑,炉火烤得小脸通红,汗水大滴大滴往下掉,脸上花花遢遢的。旁边放着木柴,火眼里的柴烧着了,还伴着一些干炭饼也烧燃了。他们双手握着扇子使劲往内扇风,柴火顿时熊熊燃烧,柴烧完了再添。一阵风吹来,从土窑里倒灌出来的是辛辣刺鼻的烟尘味,简直令人窒息。”[2]52
这段细致的描写,是当时无数穷苦孩子的缩影,令人动容。他们的辛苦付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深陷被压迫的泥淖。同样具有典型性的是,玉石的同班同学青青,出身于矿工家庭,因贫穷辍学被送往乡下,他的父母为了活下去忍着饥饿下了矿井,“渴了饿了就在矿井下捧口沟里的水喝着,尽管没有发饷,但做工却是不能停的。做着工还有个总有一天会发工钱的念想,不去做的话就真的只能干等着饿死了”。玉石不解地问自己的父母:“青青的爸爸这样饿着肚子去干活,累出问题了怎么办呢?难道矿上就这样不顾人的死活吗?”[2]64此处以儿童纯真的目光烛照出现实社会的残酷与不公,出于内心的公正感对阶级压迫进行了意味深长的追问,有力地否定并批判了资本家的冷酷和贪婪,传达了严肃的贫富对立、阶级对抗的题旨。它也反映出主人公和作者内心深处的悲悯和人道主义关怀,在当下的话语环境中,这种苦难叙述体现的人性关怀与人生态度,依然有着重要的特殊意义。
(三)意象与景色的灵动呈现
用儿童单纯的眼光去观察生活世界,往往能看出成人不易发觉的细节,呈现出原生态般的生命情境,儿童鲜活的感受能建构对世界的崭新体验,所以一些平凡的意象比如“火车”“明灯”“暴雨”“发卡”“俱乐部大楼”等,获得了全新的艺术感觉。火车在孩子眼中是“吐着黑烟的怪物”,一枚小小的发夹,也能折射出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杨秀兰对小发夹的期待,是对美的期待,对一个孩子来说拥有它意味着拥有幸福。俱乐部组织工人联合起来的反抗,才使大家领到加薪和欠饷,一个普通家庭才能为自己的孩子买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物品。玉石们对俱乐部新大楼的建筑格外关注,他们用新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一胜利的象征。
我们还能从外物的体温中感受到某种情绪,这得益于外在景物的拟人化展示:
“傍晚的阳光斜照在安源山上,天空映照出橙红色的光彩,几棵洋槐浓翠的枝叶上沾染着厚厚的煤尘,显得有些有气无力。”[2]82这是工人罢工第一天的傍晚,“厚厚的煤尘”“有气无力”暗示罢工过程的曲折与漫长。
“1925年的春天,安源山上的野花开得格外灿烂。这些扎根在煤渣和黄土中的野草,拼命地张扬着自己小小的花朵,努力装扮着这个特别的季节。”[2]107这是玉石成为一名青年团员的春天。周围的一切充满活力,让人感受到一股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此外,煤炭的形成过程、株萍铁路的建设、盛公祠的建筑风格、“十四夜偷青、十五日听声”的风俗、出狮灯、洗煤等细节描写同样活灵活现,具有丰富的趣味性和知识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儿童感性直观的视角之外,也内隐着作者成人视角对历史记忆的理性审视和深沉感悟。两种视角的相互渗透,使叙事呈现出明朗与纯真、凝重与深沉的融合。
三、结语
巴赫金曾根据《巨人传》《痴儿历险记》《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等经典成长文学作品,总结出成长叙事中个人成长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文关系:“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6]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成长叙事中对于主体生成过程的文学想象,也是民族、社会与个人走向现代化的寓言,成长叙事也具有了揭示中国当代民族秘史的重要地位。《安源娃娃安源红》成功地将一个有关工人阶级的抽象叙事与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连在一起,再现安源历史风云变幻,反映出一个现代的历史主体——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作者怀着朴素的愿望与深情:让更多的中小学生了解安源、记住安源,记住老一辈革命家在安源为人民谋幸福的那段历史。因此,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深刻的教育意义。作者和玉石等安源娃娃、工人们一样,在寻找一种自由、公平、正义、独立的人生存在,对屈辱生活的回望,也是为了提醒当下幸福的来之不易。当玉石回望这段岁月时,我们看到一种人生经验的总结,长大的不只是玉石,还有作家和读者。
[1] 郭彩侠.“主体生成”及其现代性想象[D]. 上海: 上海大学, 2013.
[2] 漆宇勤. 安源娃娃安源红[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7.
[3] 汪曾祺. 羊舍一夕[M]//汪曾祺全集: 小说卷1.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411.
[4] 王泉根. 谈谈儿童文学的叙事视角[J]. 语文建设, 2010(5): 47–50.
[5] 吴其南. 走向澄明——新时期少儿文学中的成长主题[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1): 10–16.
[6] 巴赫金. 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M]//巴赫金全集第三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33.
The Narrative of Revolutionary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Comment on QI Yu-qin’s Novel Prose
JIN Zhe-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China)
The Novel Prosewritten by QI Yu-qin centers on the Anyuan boy Yushi, and tells the growing-up story of a generation of young revolutionaries, reappearing the history of Anyuan around 1922. The works looks at this world and them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The use of children’s perspectiv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manifestation of poetic and playful spirit; second, the use of contrast to highlight the conflicts between miners and capitalists; and third, the dynamic presentation of ordinary imagery and landscape.
; Children’s perspective; narrative of growing-up story
I207.42
A
2095-9249(2021)02-0058-04
2021-02-19
萍乡学院青年科研课题一般项目(2019D0225)
靳喆安(1992—),女,河北保定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校:范延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