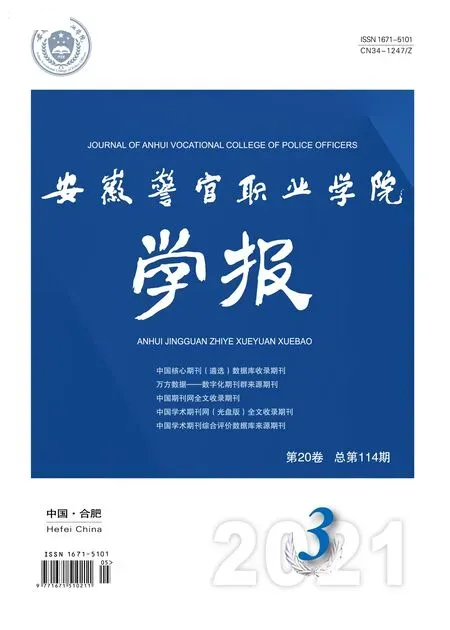真假之外——浅谈文学与虚构
2021-11-28张可鑫
张可鑫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在欧洲语言中,“文学”一词就时下的意义而言,需要追溯至18世纪。“自18世纪以来,文学,等同于法语中的belles lettres(美文),一直常被用来指代虚构的和想象的著作:诗歌,散文体小说和戏剧。”[1]排除其他扩展用法,“文学”一词自成为可能之时,便与所谓“虚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文学”在具有评价与描述功能,而非涵盖一切不限定数量与质量的文字作品时,其被用来指富有想象力的写作,进一步说,在18世纪以后人类所独有的知识型中,“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而成其为“文学”,很大程度上便在于其虚构性,“文学的本质最清楚地显现于文学所涉猎的范畴中。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2]那么何谓“虚构”呢?《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释义是:“凭想象造出来。”[3]而《文学术语词典》与《文学理论》则并未对“虚构”进行明确的定义,只是经常性地将之与“想象”“创造”等词置于相同或相似的位置。文学领域“虚构”定义的模糊性使得对其的探讨需要限定在具体语境之中。
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文学与虚构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现有的“文学”含义之外,向历史回溯文学的本质,而这往往体现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认知结构的人们所秉奉的相互差异的文学观念之中。本文欲列举历史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念——摹仿论、表现说及独立说,探究寓于其中的文学与虚构之关系,亦会涉及一些其他流派的观点与理论,力图找寻藏于“本质”之外的另一种答案。
一、摹仿论
在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为代表的摹仿论传统中,作品被视作是对现实的摹仿与再现。摹仿现实,看似是对虚构的摈弃,一如柏拉图因艺术的拙劣摹仿与象征真理的理式世界隔着三层,而将诗人与悲剧作家驱逐出理想国一般。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并不排斥虚构,“如果有人指责诗人所描写的事物不符实际,也许他可以这样反驳:‘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写的’,正像索福克勒斯所说:他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欧里庇德斯则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4]亚里士多德的摹仿并非机械刻板地复制现实与批判虚构,与之相反,他认为拥有创造成分的文学可以反映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真实。就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而言,相较于记录个别事件、仅仅是反映某种偶然性的历史,文学更能表现一种规律性与必然性。因为这种规律性与必然性在亚里士多德笔下,是与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实——构成对立的,所以其所体现的是一种虚构性。在这个视角下,文学的虚构可以理解为是人类对只能存在一次的人生的不确定性的反叛,对一种与现实的偶然性构成对立的永恒性的期待。文学摹仿说自诞生以降统治西方2000多年,至今仍以发展后的变体拥有一众追随的信徒。托多罗夫在论述文学观念时认为:“普遍上来说,艺术是一种‘摹仿’”[5],且他进一步指出“就其特殊性来说,这并非是任意的摹仿,因为我们不必摹仿真实之物,毋宁说,我们也摹仿未到来的存在和行动。文学是一种虚构:这就是它的第一种结构性定义。”[5]可见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在论述文学与虚构时,在观念上与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有着大面积的重合,并且他直接清晰地指出了文学对现实“不彻底”的摹仿背后的虚构性,及所反映的人类对于规律性的追求。因为是不完全地摹仿真实,所以文学既区别于真实,却又并非虚假,“它既非真也非假,而是,确切地说,虚构的。”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说的“摹仿”,还是在18世纪的某个时刻得到了批判并被赋予了全新含义后的“摹仿”,其都指向真实与创造的统一——虚构。
难以否认的是,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下,摹仿说的虚构之花仍然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无论是忠实地记录还是创造性地预演,自然真实都是刻印在文学虚构身上不曾被摆脱的魔咒。或者可以说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对自然真实的亲睐常常打破虚构介乎真假之间的平衡状态。这恰恰印证着柏拉图洞穴神话的危险隐喻:我们高举19世纪实证主义的火把,行走于幽暗隐秘的文学之洞穴,看文字在火光的映照下翩跹起舞,却不得不在赞赏玩味一番后吐出麦克白式的苦涩叹息:“不过是些在舞台上高谈阔论的可怜演员。”一如巴洛克时期人们对生命存在的质问,遵循摹仿说的文学实践在本质上否定了文学自身——谁又会承认一场缥缈虚幻的梦呢?没有人再关心但丁·阿利吉耶里超凡绝伦的诗才或《神曲》中理性与信仰的辩争,而反映了中古佛罗伦萨的“使我们变得如此凶恶的打谷场”将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流入人们心中的不再是《大卫·科波菲尔》的命运溪流,而是狄更斯本人的生活经历与19世纪中叶英国腐败的司法与唯利是图者的丑恶。对司马迁《史记》的褒扬,将只剩下半句“史家之绝唱”。
即使是位于中间状态的“虚构”所带来的黑格尔式的辩证统一,看似妥帖地解决了真假之间的矛盾,并发掘出了文学的根本,实则却拥有着难以消除的不合理性。例如当提及现代意义上的诗歌——它通常并不唤起任何外部现实而是自足于自身——时,人们无法用虚构来良好地解释它,因为它已几乎不再依赖于摹仿;却又无法立即否认它属于文学,将它从文学的范畴里尽数驱逐。换句话说,诗歌既非虚构,也非非虚构,因为诗人无需通过摹仿去证明某种真实性,也就无需在此基础上进行虚构。诗歌的存在构成了对摹仿说中“虚构”的一种反讽,也让人认识到无法用真实与想象的杂糅来解释虚构或文学。
二、表现说
强调作品与作家之间联系的表现说真正产生于19世纪初兴起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之中,一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两次提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6]所强调的那样,文学作品的本质与主题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主要由所摹仿的人类活动和特性所决定的形式上的原因,而是诗人内心的情感与冲动在寻求倾吐与表现。表现说的主要倾向可以被大致概括为:作品源于具有内在动力的创造性想象的驱使。“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7]“因此诗……从人类心灵中适时而生,将其创造力传给外界的种种形象”[8]。这种创造主要源于个体内部而非客观环境,显然是具有虚构性的,而其背后所隐藏的对人主观能动性的肯定,是浪漫主义思潮中人主体性的凸显与对直觉和想象力的强调,随之浮出水面的是人类对于启蒙时代思想的反思。当演绎推理逐渐否定与蚕食人的形象直觉,文学艺术的审美岌岌可危,而虚构帮助人们在纯粹的理性之外保留些许超验的空间。这并非否定理性与现实,而是在其与人类另外一些拥有悠久历史的,脱胎于近似神秘主义的古老感情间寻求一种平衡。波德莱尔为浪漫主义所下的定义便是“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表现说的“虚构”便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忠实于人的情感,赋予失去了鲜活感的外物以新的生命。
诗歌的意象正是不确定性的载体之一。“它(指诗歌语言)是细致感性的语言,融合了意象。正是意象赋予一首诗冲击力、柔软性以及真实性。诗歌是‘想象的花园,跳跃着真实的蟾蜍’”[9]。此处的“真实”并非自然真实,而是接受者所体验到的真实,是指语言能够让读者迈着想象的步伐进入诗歌的“真实”世界。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集中的玫瑰意象为例,其中有具体可感的、视觉化的玫瑰,“柔和的红,鲜艳的红——玫瑰和石竹竞相怒放。”而更多则是作为隐喻与象征存在的“玫瑰”:或是爱情与希望,“流水没有打扰他的梦,玫瑰也从此不再开放”;或是生命与死亡,“我仰望苍天,低头抚摩泥土培育的玫瑰”;或是宗教与信仰,“我看到玫瑰般俊逸的方济各,在田野经过,比微风还要轻灵”。[10]视觉化的玫瑰将读者导引向体验的真实,即读者透过它于想象中真切地遇见了玫瑰,有特定的颜色,有一定数量的花瓣,有茎,有叶,或是花苞或正在怒放或已然凋零。但毕竟读者与这玫瑰间隔了一层语言的薄纱,因而这种体验的真实实则是虚构的真实。而作为隐喻与象征存在的玫瑰则振翅向抽象的天空,它愈飞愈模糊无法具体可见,逃离了想象的现实领域而追逐感性的以太,换言之,它不再扎虚构之根于现实的土壤,而是作为读者与诗人感情碰撞交互的一种过程和媒介。但其实两种“玫瑰”的界限并非如此分明,而是常在感觉与情感的风中摇曳不定。
另外,在运用19世纪末兴起的精神分析学来探究作家的文学创作动机时,也能发现虚构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将创作家的创作活动与孩童的游戏行为进行关联,因为二者都是在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或者说都在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安排属于自己世界的事物,将假想与现实在有所区别的基础上进行联系:“创作家所做的,就像游戏中的孩子一样。他以非常认真的态度——也就是说,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同时又明显地把它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11]创作家的虚构是对童年时期游戏乐趣的追忆与代替,是对精神压抑的一种反映与升华,从而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平衡,这也深刻影响了作品的形成与呈现效果,“作家那个充满想象的世界的虚构性,对于他的艺术技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效果,因为有许多事物,假如是真实的,就不会产生乐趣,但在虚构的戏剧中却能给人乐趣;而有许多令人激动的事,本身在事实上是苦痛的,但是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上演时,却成为听众和观众乐趣的来源。”[11]弗洛伊德将幻想与真实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比较与区分,然而他的观念中也体现出了单纯的幻想同文学创作的虚构之间的差异:所谓文学虚构,既非通过想象凭空捏造出“真实”的敌人,也非对真实原封不动一尘不变的映照,而是创作者对精神层面自我满足的追求,是一种自发性的完善行为,代表着某种压抑或渴望。
三、独立说
当把文学从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中剥离出出,将艺术品当作一个由各部分按其内在联系而构成的自足体来分析,独立说诞生于“客观化走向”的进程之中。18世纪,一些批评家已然激进地倾向于将超越自然的诗同摹仿原则完全割裂开来,称其为异态世界与第二自然,将诗人创作诗歌与上帝创世相类比,“上帝与诗人,上帝同世界的关系与诗人同其诗作的关系之间的相似性最早导致了下面这条现在广为流行的原则的出现,即诗是伪装了的自我揭示。”[7]322诗如今只需要忠实于自身,诗的真实已经区别于自然的真实,这实际上构成了对文学建立在摹仿基础上的虚构的批判,也是对长期已有的要求虚构须符合通常信念,须首尾相一致等规定的舍弃。在独立说反抗摹仿论的序奏中,虚构既有的存在价值已经有了将被消解或得到重新阐释的预兆。倘若文学形式不再是对“自然”话语的摹仿或虚构性再现,虚构也就不再要求能表现某种实际的意义,或至少不再能以通常的真伪判断标准来衡量。从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诗人王尔德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到20世纪20年代发端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俄国形式主义,虚构开始面临一种窘境:当文学在向世界或作者寻求本质时,虚构尚能够在世界与作品或作家与作品的缝隙间生存;如今只剩下了孤单的文本,虚构需要寻找新的窠臼。如在小说领域,对虚构的表述可以转化为“模拟陈述”,“用‘所指性语言’表达的陈述是‘能被证实的,即与所指事实……相吻合’;而模拟陈述则‘完全依靠其宣泄和组织我们的态度时造成的效果来证实其真实性’”[1]128。独立说对“虚构”的能指性带有接受美学色彩的阐释使文学的所谓“真实”在事实之外找到了新的载体,文学虚构不再是对原有真实的一种超越性表现,而是兀自呈现出另外一种真实。叙述者也不再是摹仿者,而是创造者,“叙述者在一部虚构性作品中作出的这种概括(指主题或论点),无论是明确表述的还是暗示出来的,通常都被认为是对这个世界作出的真实判断”。[1]129
独立说中的虚构还有另外一种重要意义,就是通过一种陌生化将人们从习惯性的,自动化的亦即僵死的感觉体验中解放出来。环境与行为的习惯化让本来鲜活的一切变成了冰冷的符号,人们与语言的距离不断减少而让本应有的审美成为实用又不具有任何美感的信息交互。而文学虚构则创造了一段距离,即使它不再能以创造力所代表的对神的亵渎给予人冲击,其所缔造的陌生化依然可以在人与作品之间构造一段早被遗忘的距离,通过这段距离,人们得以寻回常被掩埋在社会观念与时代思潮下的语言之美。
四、补充
尽管大致分析了几种经典文论中文学同虚构的联系,却还远远未及问题的本质。又或许对文学与虚构关系的认知,同对“文学”自身的认知一样,是一个过程性认识,而非简单地去安排一个定义。笔者欲再另外增补些有关文学与虚构的观点,仅作聊胜于无。文学的存在与人类的独特联系注定它无法摆脱语言文字,因为语言本身具有的建构作用,再如何夸耀自己贴近真实的文体也无法做到脱离虚构。当文字未被书写在纸上还仅仅浮现在脑海之时,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既定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制约了人在超验方式之外对真实的认知,语言是表现“自然”真实的唯一途径,却也是达到“自然”真实的最大障碍。在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即指向虚构。当今诸多创作者希望通过诸如隐喻、破格与谬误等方法来逃离这种桎梏,然而文化的结构在他们学会消解之前就早已经植入了他们的骨髓。
在20世纪文学的所思考步入文论家的视域之后,虚构成为了一种需要被超越的存在。文学作为思想的唯一形式是“思想的思想”。这种思想“首先,是意味着一场与实在的遭遇,超越了虚构的世界。这是以语言为代价的凯旋,即灵肉得到救赎而升入天际的时刻。”[12]思考的文学在对虚构的超越中舍弃了毁灭故事、制造矛盾等兴趣,接受了故事自身。
五、小结
“我不确定文学本身像我们通常声称的那般古老”,然而“某种被我们习惯称为‘文学’的东西已经回溯性地存在了几千年了。”[13]不同时代的“文学”拥有不同的指向,它们不仅仅与虚构之间形成了不同的联系,它们也影响乃至建构了“虚构”本身。在追问本质性的答案时,我们需要深刻,却也需要对所谓“片面的深刻”有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