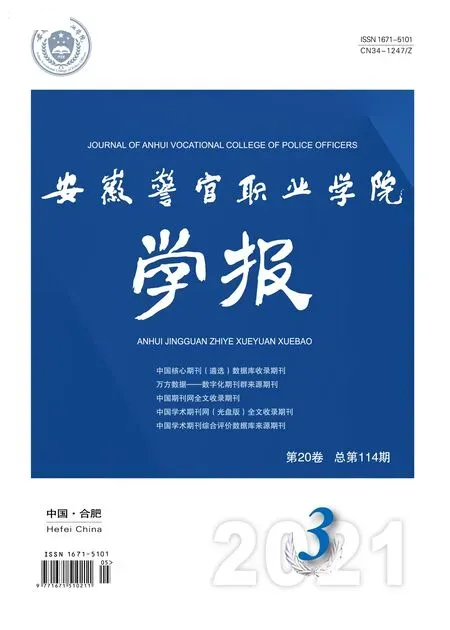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的规则检视与司法支持
2021-11-28程进益
程进益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继2015年国务院批准印发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首次明确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上海自贸区,已有四家仲裁业务与华联系紧密的境外仲裁机构先后在上海设立代表处,①入驻上海并设立代表处的四家境外仲裁机构分别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国际商会仲裁院(IC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和大韩商事仲裁院(KCAB)。根据相关规定开展业务咨询、培训、研讨等与仲裁相关的非营利性活动。2019年8月6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上海方案》),其在“实施公平竞争的投资经营便利”项下明确,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经过登记及备案等行政程序后可在新片区设立“业务机构”。这一规定直截了当地解决了上海临港新片区内境外仲裁机构对境内仲裁市场的准入问题,围绕多年的迷雾在临港新片区率先消散。紧接着,为具体落实中央文件中设定的开放改革任务并提供制度支撑,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司法局分别于2019年8月和10月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办法》和《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业务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上海管理办法》)。②《机构管理办法》对“境外仲裁机构”作出定义:本办法所称的境外仲裁机构,是指在外国和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合法成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仲裁机构,以及我国加入的国际组织设立的开展仲裁业务的机构。本文所提及的“境外仲裁机构”与该文件中定义保持一致。其中,《上海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以穷尽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境外仲裁机构在新片区的业务机构可以开展的具体业务,除原有代表处已在进行的咨询、培训和宣传服务等,案件受理、案件管理和裁决这三项仲裁机构核心功能被明确纳入业务内容,新片区涉外仲裁市场开放局面愈发明朗,境外仲裁机构开设的业务机构形象也逐渐清晰。时隔一年,2020年8月,北京市政府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北京方案》)的请示得到国务院原则同意,该方案将“允许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在北京市特定区域设立业务机构”作为“推进专业服务领域开放改革”的重点措施之一。2020年12月,北京市司法局紧跟政策导向,发布《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业务机构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北京管理办法》)。至此,以上海临港新片区和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试验田,中国内地涉外仲裁市场向境外仲裁机构发出诚挚的邀请。
然而,截止2020年12月,仅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在上海设立“业务机构”(WIPO仲调上海中心)并实质化开展业务,[1]前文所述的四家机构仍以代表处的组织形式在境内开展相关业务。诚然,政策与行政层面的开放准入是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实际开展业务的必然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境外仲裁机构是否真正愿意进入境内受理、管理案件并作出裁决,取决于其对境内市场各要素的综合考量。如果进驻风险显著大于收益,那么即使有足够恳切的政策,其设立业务机构的态度也不会积极。对于现代商事仲裁而言,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影响着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最初意愿能否实现,关系到仲裁程序能否启动、是否合法,[2]这是商事仲裁的起点;而仲裁裁决的成功执行,则意味着胜诉方利益的最终落定和双方争议的彻底解决,这是商事仲裁的终点。然而,由于中国内地仲裁立法理念的落后,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时,相关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最终裁决的执行力都面临着法律规则层面的不确定性,这必然会转化为境外仲裁机构预设的具体风险,阻碍其进入内地市场的步伐。针对上述两则具体问题,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的“大成株式会社一案”一审民事裁定书①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等与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一审民事裁决书,[2020]沪01民特83号。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6日作出的“布兰特伍德一案”一审民事裁定书②布兰特伍德工业有限公司、广东阀安龙机械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案件一审民事裁定书,[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分别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和仲裁裁决执行的适用规则进行了确认和澄清,从司法层面为境外仲裁机构进入境内市场提供了支持。上述裁定在表达仲裁友好态度、消除境外机构疑虑的同时,也为仲裁立法和相关诉讼规则的修订工作明确了症结、提供了思路。因此,本文将分别以仲裁协议有效性与仲裁裁决执行力为视角,检视我国现行仲裁、诉讼相关规则及过往司法判例。在明确问题症结的基础上分析境内法院的两例最新裁定,最终为中国涉外仲裁领域的制度升级进言献策。
二、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分析
(一)现行法律规则下仲裁协议的效力隐患
根据2006年开始实施的《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的法律适用顺序为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的法律,以及在没有约定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的情况下直接适用的法院地法。因此,在当事人没有就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进行特别约定且仲裁地为中国境内的情况下,我国法院通常会适用中国法对仲裁协议效力进行审查。在中国法下,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之仲裁协议的效力障碍起源于《仲裁法》第三章仲裁协议的第十六条,即仲裁协议必须具备的第三个强制要件: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从规则层面而言,该强制要件派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某些仅约定仲裁规则而未指明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将归于无效。例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为意欲将案件提交国际商会仲裁的当事人提供的示范条款仅明确了“……应按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终局解决”,而未提及将案件提交ICC。英国伦敦仲裁院(LCIA)、瑞士商会仲裁院(SCAI)以及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各自提供的示范条款也是如此。在实践操作中,仲裁协议所面临的这一效力障碍需要通过境外仲裁机构的两种安排加以规避:首先,境外仲裁机构在涉境内仲裁业务的示范条款中明确提及“将案件提交至该仲裁机构”这一要素,或是作出相关说明。例如,大韩商事仲裁院(KCAB)中文版本的示范条款明确提及“凡因本合同……均应提交大韩商事仲裁院进行仲裁”,而同示范条款的英文版本仅强调“争议应根据韩国商业仲裁委员会的国际仲裁规则……解决”。可以想见,中英版本的示范条款在是否将案件明确提交仲裁机构这一点上的差别,应是KCAB为中国《仲裁法》有关仲裁协议效力强制要件所做的特殊安排。ICC则是在展示示范条款的同页面以“其他建议”的方式提出:考虑到国家法律的要求,对于意在中国大陆进行ICC仲裁的当事方,在仲裁条款中明确提及ICC国际仲裁法院(ICC International Courtof Arbitration)是一种审慎的做法。其次,境外仲裁机构还可设计特殊的仲裁规则条款,将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规则唯一指引至该仲裁机构,以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四条中“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要求,构成“仲裁协议仅约定纠纷使用的仲裁规则的,视为未约定仲裁机构”之例外。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仲裁协议仅约定纠纷适用的仲裁规则的,视为未约定仲裁机构,但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或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除外。例如,ICC在其2012年版仲裁规则中就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并一直延续至今:“当事人同意按照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即接受由仲裁院对该仲裁实施管理。”
然而,即使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已选定或通过规则推定选定“境外仲裁机构”,该仲裁协议的效力仍面临着第二个考验,即“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属于我国《仲裁法》下“仲裁委员会”的范畴。仅从《仲裁法》文本来看,似乎并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该法所称的“仲裁委员会”,应是指该法施行之初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重新组建的本土仲裁机构,以及施行之后以同标准成立的仲裁机构。②《仲裁法》第十条: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设立仲裁委员会,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第六十六条:涉外仲裁委员会可以由中国国际商会组织设立。第七十六条:收取仲裁费用的方法,应当报物价管理部门核准。第七十九条:本法施行前在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其他设区的市设立的仲裁机构,应当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重新组建;未组建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届满1年起终止。若仅根据文本严格解释,即使并未明文禁止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该法也通过对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范围加以限制,变相地控制了境内仲裁市场的准入门槛。对于还处在观望阶段的境外仲裁机构而言,其不仅在进入境内市场前就对其是否属于《仲裁法》下的“仲裁委员会”充满疑虑,现有的准入政策也未明确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业务机构”是否符合“仲裁委员会”的组建标准。由此而引发的仲裁协议效力隐患,使境外仲裁机构对境内市场望而却步。
(二)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司法态度及其发展
我国法院认定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之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可与上述两层效力障碍相对应而分为两类,即当事人在协议中仅约定仲裁规则而未指明仲裁机构为一类,当事人明确选定境外仲裁机构为另一类。
对于前者,在ICC2012年版仲裁规则正式生效以前,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是一贯的,即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条款因未指定明确的仲裁机构而无效。例如,在著名的2003年旭普林案中,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仲裁条款为“Arbitration:ICC Rules,Shanghai shall apply”,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表示同意江苏省高院的倾向性意见,即仲裁条款从字面上看虽有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仲裁规则及仲裁地点,但并没有明确指出仲裁机构。因此,仲裁条款无效。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3]民四他字第23号。与之观点相同的案件还有1996年诺和诺德案、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诺和诺德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际中医药科技开发公司经销协议纠纷案的报告的复函,法经[1996]449号。2006年法国DMT公司案、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复函,[2006]民四他字第6号。以及2011年江苏对外经贸案。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Salzgitter Mannesmann International GmbH与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仲裁协议效力的复函,[2011]民四他字第32号。在2011年江苏对外经贸案中,江苏省高院曾试图根据当时的ICC仲裁规则(1998年版)第1条(仲裁院的职能是按照本规则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和第4条(当事人如愿按照本规则请求仲裁时,应向秘书处提交仲裁申请书),对当事人仅约定ICC规则而不指明仲裁机构的英文仲裁条款进行解释,从而得出当事人已选定ICC仲裁的表示意思。但最高院在复函中仅以“双方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达成一致”为由认定所涉仲裁条款无效,对江苏省高院所做的规则解释不作回应,刻意忽视了《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设计的第二种例外,即“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情形。这或许是最高院对此问题一贯的司法态度的坚持,也可能是江苏省高院对ICC规则的解释本身略显牵强。之后,ICC发布了2012年版仲裁规则,在第六条第二款明确了当事人约定ICC仲裁规则对ICC管理案件的指向作用。最高院敏锐地察觉了这一变动,并于2013年北仑利成案复函中表达了对此新规则的支持。在该案复函中,最高院认为根据2012年版ICC仲裁规则,ICC对仅约定适用其规则但未同时约定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合同争议具有管辖权,应当认定当事人的约定属于“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情形。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宁波市北仑利成润滑油有限公司与法莫万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请示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74号。虽然北仑利成案中最高院体现出对仲裁的友好态度,但上述司法态度的发展与变动也恰恰证明了此类仲裁协议所面临的效力风险,因此,除ICC以外,对于意欲在境内仲裁的境外仲裁机构而言,通过上文所述的两种特殊安排以明确仲裁协议选定的仲裁机构,对于保证仲裁协议的合法有效是确有必要的。
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的仲裁协议多因仅约定仲裁规则、未选定仲裁机构而直接被法院认定无效,真正需要法院对“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属于中国仲裁法下“仲裁委员会”这一问题进行解释和判断的案例鲜少出现,但正如上文所述,这一问题恰恰是这类仲裁协议在中国法下确认有效的一道关键门槛。2013年以前,立法与司法的讳莫如深,以及最高院在前文所列案例中对此类仲裁协议所持的消极态度,都使得这一问题的答案一直被笼罩在迷雾之中,令境外仲裁机构及当事人踟蹰不前。2013年2月,最高院针对神华公司案作出的复函更是加深了这一疑虑。在复函中,最高院虽未就《仲裁法》第十六条中所指“仲裁委员会”是否包括“境外仲裁机构”作出回应,但却认为《仲裁法》第二十条所指的“仲裁委员会”应是依据《仲裁法》第十条和第六十六条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并不包括“外国仲裁机构”。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与马瑞尼克船务公司确认之诉仲裁条款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4号。通常认为,在立法者未做特殊声明的情况下,一部法律中的同一概念之内涵与外延应当是保持一致的,更况且《仲裁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条同是第三章仲裁协议下的具体条文。因此,最高院似是通过神华公司案的复函隐晦地排除了境外仲裁机构作为我国《仲裁法》下“仲裁委员会”的适格性,进而否认了相关仲裁协议效力。然而,2013年3月最高院在龙利得案的复函中却发表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在该案中,合同当事人约定因合同而发生的纠纷由“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同时还约定“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Place of Jurisdiction Shall Be Shanghai, China)。最高院首先确认了合同当事人对于“管辖地”的约定应理解为“仲裁地”,应以中国法为判断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其次,最高院罗列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三个强制要件,并认为:既然涉案协议已“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那么“涉案仲裁协议应认定有效”。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BPAgnati S.R.L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的请示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13号。这是最高院首次明确,若当事人明确约定将纠纷提交一境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即其协议已满足《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一强制要件。
(三)大成株式会社案:对关键问题的适时澄清
虽然最高院在2013年的龙利得案中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之仲裁协议效力这一问题表现出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但由于复函的内容并未体现充分的解释和说理,故其结论仍然略显单薄,给该领域的学者和从业者留下了讨论的空间。结合当下政策形势,龙利得案复函虽得出结论、却未能彻底澄清的问题仍集中在对《仲裁法》第十六条“仲裁委员会”的理解和解释上。2020年6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大成株式会社一案的判决书,在案涉仲裁协议效力认定这一争议焦点中,法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三点说明,有张有弛地论述了现行《仲裁法》下“仲裁委员会”这一概念实然的局限性及其对“境外仲裁机构”应然的包容度,最终确认了案涉仲裁协议的有效性。
该案案涉合同中仲裁条款约定,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对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当事人应首先尝试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将该等争议最终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纠纷产生后,合同一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面对与龙利得案类似的法律事实构成,本案法院在确认其具备管辖权且准据法为中国法的前提下,首先表明了观点: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案涉仲裁协议具备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仲裁机构SIAC,应认定有效;而后对上述观点展开了说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六条: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法院首先确定了龙利得案中最高院复函所应具备的批复类“司法解释”效力,那么龙利得案复函本身的结论即可作为本院判决的依据。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四条: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其次,该法院认为,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我国《仲裁法》在立法之初的确缺乏国际化视野,仅对由本土仲裁机构受理的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进行一般和特别的规定,与国际商事仲裁存在脱节。因此,如果从《仲裁法》本身出发,结合各章法条中出现的若干处“仲裁委员会”及上下文,确实很难将ICC、SIAC等境外仲裁机构解释进《仲裁法》第十六条“仲裁委员会”的范畴。但是,在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境外仲裁机构不得管理仲裁地点在国内的仲裁时,“司法不能以立法不明为由拒绝裁判”。上述问题固然需要立法层面解决和完善,但上述龙利得案法院复函正是我国司法“在顺应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弥补仲裁立法不足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其法律效力与现实意义均不可忽视。基于上述论证思路,法院确认了涉案仲裁协议的效力。
大成株式会社案的法院判决虽是以龙利得案最高院复函为判案依据,但其文书中对于原本立法不足以及现有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的提及,实是在为两案相同判决结果背后的司法裁量理由作出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仲裁条款“争议提交至SIAC在上海仲裁”本被新加坡高等法院解释为仲裁地在新加坡,法官在判决中认为,如果以中国为仲裁地而以中国法为仲裁协议效力准据法,那么中国法律对于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可以在中国管理仲裁的法律是不确定且变化迅速的。③See BNA v BNB and another[2019]SGHC 142,para.116.该判决最终被新加坡最高院上诉庭推翻,上海作为仲裁条款中唯一确定的地理位置,最终被确定为当事人在条款中约定的仲裁地。④See BNA v BNB and another[2019]SGCA 84,para.103.由此,若将新加坡最高院上诉庭的最终判决视为其向中国大陆伸出的橄榄枝,那上海一中院大成株式会社判决无疑是对其最友好且积极的回应。但与此同时,新加坡高等法院的判决也向立法者发出警示:仲裁领域年久失修的落后立法已经危及中国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信誉与影响力,境外法院确会基于中国相关法律的不确定性而避免将仲裁地解释在境内。⑤还可参考香港最高法院审结的Z v A一案([2015]HKEC 289),该案中,法院考虑到在中国内地作出的国际商会裁决存在在中国内地无法执行的风险,从而将仲裁地解释为香港而非中国内地。因此,后续立法的修订与完善已然刻不容缓。
三、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之裁决执行力分析
(一)现行法下裁决执行适用规则的僵局
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我国实行国内仲裁裁决和国外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双轨制,对于两类裁决分别适用不同的执行规则。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规则为《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纯国内仲裁裁决执行)和第二百七十三条(涉外仲裁裁决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规则则为《民诉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上述三条文得以区别适用的标准在于所做出裁决的仲裁机构分别是“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与“国外仲裁机构”,即根据我国《民诉法》,仲裁机构的国籍决定仲裁裁决的国籍,并指向不同的执行规则。因此,从法律规则层面而言,对于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所做裁决,我国法院将根据仲裁机构的外国国籍确定适用《民诉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对其予以承认和执行。此时,缔约国高达166个、覆盖世界主要国家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通常会成为法院办理此类案件首先考虑的国际条约。然而,根据《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得以适用该公约承认与执行的裁决共包含两类,一类为在申请承认与执行地所在国以外国家领土内作成的裁决,另一类为虽在申请承认与执行所在国领土内作成,但被该申请国认为 “非内国”的裁决(not considered as domestic awards)。两类裁决以仲裁地在申请国领土外与内作界分,前者为原则,后者为例外,即《纽约公约》是根据“仲裁地”决定仲裁裁决的国籍,并以此决定公约的适用问题。因此,若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所做的裁决向境内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此时仲裁裁决地与申请地发生重合,《纽约公约》只有在该裁决被中国境内视为“非内国裁决”时才得以补充性适用。
根据商事仲裁国籍理事会(ICCA)发布的《1958年纽约公约释义指南:法官手册》,缔约国通常认为的“非内国裁决”包含三种类型:按照另一国的仲裁法作出的裁决、含外国因素的裁决和无国籍的裁决。[3]无独有偶,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指南》也将上述三类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的主要形式。[4]其中,“按照另一国仲裁法作出的裁决”只可能产生于一种情形,即当仲裁地为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法院地但该仲裁的适用法却为外国仲裁法时。此类裁决是《纽约公约》缔约当时工作组对“非内国裁决”的最初构想,其目的是为了在公约适用范围上同时包容“仲裁地标准”与“仲裁程序法标准”,以消解大陆法系国家对公约单独适用“仲裁地标准”的不满。①See Bergesen v.Joseph Muller Corp.,710 F.2d 930-932.但在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当事人特别约定适用仲裁地国法以外的外国仲裁程序法的情形已鲜少发生,因为这极易导致裁决国籍的消极冲突而架空仲裁地法对该裁决的司法审查。[5]其次,由于公约并未明确定义“非内国裁决”,且条文中“认为”(considered)的表述似是赋予了缔约国自我决定何为“非内国裁决”的权利,有关缔约国便通过国内立法和司法审查实践将“非内国裁决”的含义从上述原始构想扩张至了“含有外国因素的裁决”,并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界的认可。这一扩张肇始于1983年美国第二上诉巡回法院审理的Bergesen v.Joseph Muller Corp一案,在判决中,上诉法院认为“非内国裁决”并非指在外国作出的裁决,而是在另一国法律体系内作出的裁决,例如根据外国法宣布的裁决,以及仲裁当事人的住所地或主要营业地位于被申请国外等情况。②Id,932.同时,法院还认为,美国议会在《美国联邦仲裁法》第202条即已明确了“非内国裁决”概念的定义:③Id,933.完全产生于美国公民之间的上述法律关系应当视作不属于公约的范围,除非该法律关系涉及位于外国的财产,或面临国外履行或执行,或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国家有合理关系。④9 U.S.C§202(2010)最后,由于无国籍裁决与本文所讨论的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之裁决关联不大,且其本身尚存在较大争议,故本文不做深入分析。
基于以上对“非内国裁决”概念的释明,将本文所指的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所做裁决解释为《纽约公约》下的“非内国裁决”将有牵强附会之嫌。首先,虽然作出该类裁决所依据的程序是境外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规则,但该“仲裁规则”仍须遵守“仲裁地国法”,即中国仲裁法的强制性规定,否则将影响所做裁决的效力。[6]同时,实践中仲裁当事人通常也不会就仲裁程序法做特别约定。因此,该类裁决并非“按照另一国的仲裁法作出的裁决”。其次,美国作为普通法系判例法国家,其对于“非内国裁决”概念的自我认定(consider)不仅有联邦上诉法院司法判例予以解释和说明,还有《纽约公约》执行立法(Implementing Legislation)《美国联邦仲裁法》第202条的成文法支持。相较而言,我国作为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不仅现行法律体系中未对“非内国裁决”的定义及适用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非内国裁决”这一概念也仅寥寥出现过两次,⑤一例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外仲裁裁决案,[2004]锡民三仲字第1号;另一例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DUFERCOS.A(德高钢铁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ICC第14006/MS/JB/JEM号仲裁裁决案,[2008]角仲监字第4号。两例判决中地方中院所表达的意见远不及缔约国自我认定(consider)的标准,参考价值堪忧。因此,虽然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所做裁决具备“含有外国因素”的表面特点,但借此概念对该类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实际缺乏国内法律依据,[7]也不满足《纽约公约》对成员国自我认定的要求。因此,即使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和指引,我国法院会依照《纽约公约》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所做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但实际上该类裁决并不属于《纽约公约》本身的适用范围。此时,该类裁决在境内的承认与执行陷入了规则层面无以适用的僵局。
(二)最新司法实践对规则僵局的突破
现行法下产生上述规则僵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民诉法》认定裁决国籍以“仲裁机构国籍”为标准,而《纽约公约》则采“仲裁地标准”,二者标准不一。如果我国也以“仲裁地标准”确定裁决国籍,那么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所做裁决将因“仲裁地”在我国境内而被认定为国内仲裁裁决,《民诉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关于涉外仲裁裁决的执行规则得以直接适用,从而与《纽约公约》无涉,规则僵局自然打破。实际上,不仅仅是《纽约公约》,“仲裁地标准”已然成为国际商事仲裁认定裁决国籍最重要和最通常的做法,得到各国立法实践的支持。[8]在我国理论学界,以“仲裁地标准”认定仲裁裁决国籍也早已呼声已久。[9][10][11]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明确了以仲裁地来确认仲裁裁决的国籍,①该通知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做出的临时仲裁裁决、ICC等国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进行审查。虽然此规定仅关涉境外仲裁机构在香港仲裁的情形,但也反映出规则制定层面对“仲裁地标准”的考量与接纳。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DMT案中也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新加坡做出的裁决认定为新加坡裁决而非法国裁决,从而以中国和新加坡均为缔约国而适用《纽约公约》对该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DMT有限公司(法国)与被申请人潮州市华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潮安县华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2010年10月12日。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以“仲裁机构国籍”认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正在向“仲裁地标准”转变。
2020年8月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布兰特伍德一案民事裁决书首次在境外仲裁机构境内仲裁的情形下体现上述对于国籍认定标准的理念更新,明确了该种裁决的性质及执行规则。涉案仲裁协议约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提交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根据国际惯例在项目所在地进行仲裁。”经法院审理查明,仲裁条款中所载“项目所在地”为中国广州市。广州市中院在判决中明确,案涉仲裁裁决属于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视为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布兰特伍德公司可参照《民诉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申请法院执行,而非其坚持主张的《纽约公约》或《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由此,该案判决以裁决国籍“仲裁地标准”为基础,在确认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之裁决为“中国涉外仲裁裁决”的同时,打破了因裁决国籍认定标准不一而造成的执行规则僵局。申言之,“涉外仲裁裁决”性质的认定也解决了我国法院撤销该类裁决的权利来源问题,使我国法院对该类裁决进行全面司法审查有法可依。
四、结论:我国《仲裁法》与《民诉法》相关规则亟待修订
鉴于《纽约公约》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统领地位及其对仲裁地的强调,各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往往聚焦于一流仲裁地的打造,其中,加快仲裁规则修缮、接轨国际通行做法是形成竞争力的应有之义。我国近年来主动向境外仲裁机构传递开放境内市场的信号,法院也以司法判例的形式对沉疴痼疾予以澄清——实践先行的局面业已展开,立法层面的行动应迎头赶上。通过检视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之仲裁协议效力与裁决执行力的相关规则,梳理过往与最新司法实践案例,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仲裁的风险症结已浮出水面,我国《仲裁法》及《民诉法》相关规则的修订与完善方向愈见明朗。
为邀请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开展业务,首先要吸引其将内地作为仲裁地进行仲裁,从而在充分感受境内仲裁环境的基础上自发地萌生出进驻境内仲裁市场的想法。而对于尚未在境内设立业务机构的境外仲裁机构而言,其所面临的风险是共通的,即前文所述的仲裁协议效力的不确定与裁决执行适用规则的僵局。我国《仲裁法》与《民诉法》在这两方面存在的规则漏洞时刻阻碍着境外仲裁机构对境内市场的探索,因此相关修订和完善必须切中肯綮、刻不容缓。具体而言,首先,未来《仲裁法》应对接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上的国际通行做法,弱化“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性影响,降低仲裁协议有效性门槛。[12]即使保留选定仲裁机构作为仲裁协议效力的强制性要件,也建议摆脱现行法下“仲裁委员会”所特有的地方行政色彩,在设立主体、组建条件等组织规范上为“境外仲裁机构”保留空间。其次,未来《民诉法》应以“仲裁地标准”替代现有的“仲裁机构国籍标准”以认定仲裁裁决国籍,从而与《纽约公约》适用范围接轨并逐步适应国际商事仲裁通行做法。由此,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所做裁决因“仲裁地”在境内而应被视为我国国内裁决,进而根据国内裁决的司法审查规则进行执行或撤销,以此突破前文所提及的因认定标准不一而产生的规则适用僵局。在此,现行《民诉法》第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四条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认定“涉外仲裁裁决”的提法早已过时,也难与同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认同涉外纠纷可提交“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规定适配。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未来《民诉法》应重新对“涉外仲裁裁决”进行定义,以解决法律本身的内部矛盾,也保证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所做裁决之涉外仲裁裁决的性质认定有法可依;也有学者提出,或可考虑取消涉外裁决的提法,而将仲裁裁决分类简化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国内裁决与国际裁决两分法,[13]进而对现行《民诉法》中国纯国内裁决与涉外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归入《仲裁法》调整。
最后,若上述修改均能实现,不论境外仲裁机构是否进驻境内市场设立业务机构,其本会面临的仲裁协议效力与裁决执行风险都将迎刃而解。但在此之前,即上述规则尚未修改但特定区域市场已经开放准入的当下,规则制定者仍应以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设立的业务机构性质予以明确,以化解境外仲裁机构对上述风险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