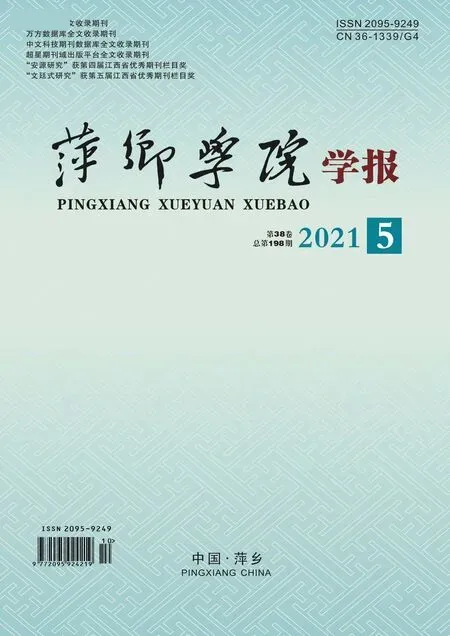从单系抚育到双系抚育:家庭生育假的检视与形塑
2021-11-28刘浩锴
刘浩锴
从单系抚育到双系抚育:家庭生育假的检视与形塑
刘浩锴
(东南大学 法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部分学者提出延长女性产假以保障其权益。然而,延长产假的本质是将女性囿于家庭中,反而会造成女性在职场中的隐形歧视。强调女性职责的单系抚养理念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完善家庭生育假制度必须秉持双系抚养的理念,男性与女性都需要承担家庭职责。双系抚养有利于发挥父亲角色的作用,促进家庭和睦,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女性在职场中受歧视的状况。家庭生育假的构建应当以产假与育儿假为核心内容、以建立法律规范体系为主线、以完善配套措施为抓手。
三孩政策;单系抚育;双系抚养;父职理论;育儿假; 就业歧视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提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我国六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变化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此次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其实距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足六年,可见,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造成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严峻问题。社会普遍认为母亲是养育后代的中心,较父亲更具有体贴、细腻等优点,应当承当更多的照顾子女的家庭职责。因此,社会中不乏延长女性产假制度的呼声[1]。然而,一味延长产假制度并不利于保障女性的权益,反而使女性困在“家庭”中,在个人职业领域遭受更多的隐形歧视[2]。简言之,一些看似有利于女性权益保障的措施在实践中反而成为其障碍。
“产假是指女性在产前、分娩和产后的一段时间内依法享有的有工作保障的休假,其目的在于保护母亲和新生儿的健康,以及为新生儿母亲提供工作保障”[3]。与产假相配套的还有陪产假、育儿假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称谓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如瑞典已形成父母双方共同承担抚育职责的家庭生育假制度①,我国部分地区虽然规定有陪产假,但时间一般较短,实践效果亦较为有限②。我国的家庭生育假制度目前是以母亲的产假为核心,其实质是强调女性的家庭育儿职责,所体现的是单系抚育理念。然而,这样的制度不利于女性权益的保障与新生儿的健康成长,更不符合我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应当秉持双系抚育理念,凸显父亲在家庭育儿中应当承担的职责,从而构建完善的家庭生育假制度,实现女性权益保障、新生儿健康成长的效果。
一、问题检视:单系抚育的运行困境
(一)对女性的“生育惩罚”
“生育惩罚,又称生育代价,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由于生育而对自身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4]。生育包括受孕、分娩、产后哺乳等过程,十月怀胎与分娩自然是由女性所直接承担,而产后新生儿的哺乳养育等事项也往往会加之于女性身上。与之对应,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代价也体现在生育的每一个过程中。
在就业过程中,用人单位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男性,即便女性与男性同样可以满足岗位的需要,女性也依旧会受到一定的不公正对待[5]。女性在被面试时也往往会被问询“是否结婚”“是否已有小孩”“未来什么时候要孩子”,甚至还必须向公司保证一定时间内不生育等[6]。换言之,在就业之前,女性就已经被隐形地剥夺了部分就业机会。在实际工作中,女性一旦受孕,其职业前景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例如:2017年央视2套《遇见大咖》节目中,女副总裁意外怀孕告知其老板,其老板直言“你多休息一会儿,也给其他兄弟一些机会。”[7]这个女副总裁所担心的并不是能不能休产假的问题,而是产假结束之后她的原有职务是否能够继续担任的问题。对老板而言,员工休产假后其工作熟悉程度、身体承受力等均有所下降,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亦会调整该员工的岗位。可见,女性确实因生育而承担了过多的代价。
这种生育代价正是由单系抚育理念所造成的。单系抚育理念下,女性承担了过多的养育新生儿的职责,而男性在哺育新生儿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在实践中,男性几乎不会因为伴侣怀孕、分娩等而在职业发展上遇到阻碍。片面强调女性责任的单系抚育理念有违宪法所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更不符合实践的需要。
(二)立法供给不足,配套措施缺位
产假是生育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关于生育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首先见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生育法》),但是其规范是原则性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③。其次则是国务院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以下简称《劳动规定》),该规定虽然明确了女职工的产假期限与生育津贴,但其适用主体仅仅是“职工”④。《社会保险法》中享受生育津贴的亦是“职工”⑤。《生育法》中生育假的主体是符合生育政策的夫妻,也就是说只要符合生育政策,那么无论其是否就业,都应当享有生育津贴等福利。然而,《劳动规定》等法律规范一方面排除了失业人员、无业人员等的适用,另一方面也将男性排除在生育保障制度之外。在德国,登记为失业人员的女性依旧有权享有产假津贴,而男性同样享有育儿津贴[8]。简言之,我国生育保障适用主体较为狭窄,缺乏统一的、可操作的上位规范。
配套措施缺位,生育保障制度的落实情况不容乐观。首先是缺乏对用人单位落实生育保障制度情况的主动监督机制。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的数据,有48.5%的已生育女性未曾休过产假[9]。相对于用人单位,职工居于劣势地位,难以与之对抗,即便通过投诉、诉讼等路径可以捍卫自身权益,亦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10]。其次,用人单位在具体实践中的执行标准不一。《社会保险法》规定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我国许多用人单位都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的方式,基本工资往往比较低[11]。在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混淆视听,故意采取较低的标准发放津贴。再次,职工享受生育保障待遇之后,往往并不能回到原岗位,其工资待遇等较之前也会有所下降。用人单位在与职工的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往往可以凭借各种手段找补自身在职工生育保障上的损失。
(三)抚育成本过高,父亲角色缺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生儿的抚育成本迅速上升,其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前者包括医疗费、抚养费、教育费等直接性支出,后者则是指为抚育孩子而损失的受教育或增加收入的机会成本[12]。女性进入产假后,其收入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在产假结束之后如果继续工作往往面临着调整岗位、降低工资的局面[13],而且此时还需在新生儿的照顾上支出更多的照料费用。如果不返回工作而选择照顾新生儿,那么家庭的负担便全系于男性身上。在通常的情况下,男性一方的工资往往无法负担家庭的整体开支。
其次,父亲角色的缺位不利于新生儿成长。斯宾塞认为:“父亲是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引路人。”[14]父亲在幼儿智力发展、情绪意志发展、性别角色发展、性格发展、社会性发展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在单系抚养理念下,母亲承担了更多的家庭抚养义务,而父亲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供物质保障的工具人,缺乏时间和精力去参与新生儿的成长过程,进而导致父亲角色的缺位。
二、逻辑转换:双系抚育的理论证成
(一)父职理论对父亲育儿职责的要求
父职理论包含父职角色与父职实践两方面,前者指男性源于本能的亲职行为等,后者指父职角色的扮演与实践的过程[15]。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抚养分工中,父亲扮演的是经济扶养人的工具性角色,强调其经济功能,而甚少关注其家庭抚养功能,因此在孩子的哺育成长中是缺席的。如今这一状况已发生巨大改变,育儿已成为父职的重要内容。参与到育儿实践中的父亲会被称之为“奶爸”,自2013年热播的《爸爸去哪儿了》也正是人们对父亲角色参与育儿活动的关注与呼吁。当下我国父职理论的内涵较以往更加强调父亲在育儿中的参与度,其直观表现是父亲花费更多的时间陪伴、照顾孩子[16]。
在生育保障制度中,父职理论的应用便是增加父亲的陪产假、育儿假。在瑞典,在每个孩子满8岁之前(不管孩子是由父母亲生还是收养、父母结婚与否),父母共有480天的育儿假。其中各有60 天分别指定给母亲和父亲,剩余的60天父母各一半,但相互之间可以转让[17]。在挪威,父母共有29到39周育儿假,其中父亲承担10周不可转移的育儿假。当今世界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规定了较为规范的父亲育儿假制度,其理念是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父或母任一方至少要承担一定期限的育儿责任。我国部分地区虽然规定了父亲的陪产假、护理假等,但缺乏统一的上位法规范,而且父亲的育儿假一般只有7∽20天,较国外有很大差距。如何合理延长父亲育儿假,使其与母亲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是践行父职理论新内涵的需要,是构建我国生育保障制度的关键。
(二)家庭分工转变要求双系抚育
以前我国的家庭结构是以男性工作赚钱、女性相夫教子为主轴的“男外女内”格局。因此,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男女的不同分工为基础构建的。但这种分工逐渐发生了变化,女性具有了更强的经济功能。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三产业逐渐超过第二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高度繁荣,使女性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再次,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女性具有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更长的受教育时间,具有更强的就业能力和权利意识[18]。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地位的提升带来的是女性权利意识进一步的觉醒和女性话语权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希望自己被约束在家庭之中,更希望能够首先取得个人的成功[19]。而且,随着生活成本及育儿成本的不断攀升,传统的依靠男性赚钱养家的方式几乎无法维持家庭开支,女性也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实现家庭的有序运转。家庭分工已由男主外女主内变为男女共同承担经济与家庭责任,家庭分工的转变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应当随之变更。因此,生育保障制度的完善不应当将女性限制在育儿上,而应当使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庭职责。
(三)双系抚育的多重益处
女性在漫长的怀胎期间要承受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压力,生理上包括恶心、厌食、产后漫长的恢复期等[20],心理方面许多产妇曾患过不同程度的产前或产后抑郁[21]。男性参与到生育过程中,有利于其了解整个生育过程的艰辛,理解女性的不容易,方便其照顾女性,缓解女性的心理压力。其次,父亲角色的彰显有利于新生儿的健康成长,包括对新生儿衣食等生活方面的照顾,也包括对新生儿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良性塑造。同时,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培养男性的家庭责任感,加深对伴侣的理解,促进家庭和睦。
增加男性的家庭职责有利于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出于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考量,用人单位往往对女性存在隐形歧视。即便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歧视等,但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女性的隐形歧视很难发生大的改变。现行生育保障制度其实质是将生育成本加之于女性身上,但是生育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更是国家延续的关键,生育成本应当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22]。资本追逐利润,用人单位天然具有排斥承担成本的倾向性。在国家、用人单位、男性、女性之间必然需要将成本均摊,其中最具可行性的便是增加男性的生育成本。女性的劣势地位是与男性相比较而言的,如果男性同样需要承担同等的生育成本,那么女性的劣势地位自然会有根本性的扭转。
三、实践展开:家庭生育假的制度形塑
(一)构建以父母育儿假为核心的家庭生育制度
家庭生育假包含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多种制度,其核心功能在于为家庭提供“生”“育”的时间和相应的经济帮助。笔者认为家庭生育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产假与育儿假。产假应当包括产妇的受孕、分娩等过程,以及其丈夫一定期限的陪产假,这是针对“生”。其次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育”的问题。新生儿的哺育是夫妻共同的义务,不应当因为女性的生理特点而将该责任一味强加给女性。因此,育儿假制度应该是赋予夫妻共同的、总和的时间,其中夫、妻每方都必须承担一定期限的、不可拒绝的哺育义务,而剩余期限则由夫妻共同商议决定。另外,还需明确生育假的适用主体应当是所有符合生育政策的夫妻。
与之相关的是享有假期时生育津贴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在挪威,生育津贴数额的确定与育儿假的长短有关。生育津贴的基准数额是父母前三年的收入平均值。如果父母享受49周假期,则获得100%津贴;如果享受59周假期,则获得80%津贴。育儿假越长,获得的津贴越少[23]。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在保障新生儿利益的同时调动夫妻劳动的积极性。我国可以参考这一政策。我国一贯的做法是以职工所在单位的平均工资来确定,笔者认为我国收入差距较大,且部分人未就业,应当以地区月平均收入为标准来确定津贴数额。参考国际惯例与我国实际,生育津贴的地区标准应根据育儿假长短等因素来灵活确定。生育津贴的另一问题则是由谁支付。我国现行制度下生育津贴是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单位未缴纳生育保险的由单位支付。笔者认为应当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使未就业的人也能享有生育保险。
(二)制定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规范体系
我国现行规范中只有女性的产假与男性的陪产假,并无育儿假制度。2019年国务院以指导意见的形式鼓励试行育儿假⑥。“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将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辽宁省、广东省等地同样在探索育儿假制度⑦。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逐步、多层次、全方位推进。首先应当在《生育法》《社会保险法》等基础性法律中对家庭生育假制度进行原则性确认,而后在具体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中具体试行这一制度。
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要坚持渐进性的原则,在基础性法律中不能直接作太过具体的规定,而应当凸显其原则性、底线性,具体的执行措施应当由下位法完成;其次,要结合地区特征,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理念不尽相同,应当赋予地方,主要是省级行政区一定的裁量权,使其结合地区特点制定更有效用的法律规范;再次,要合理调整产假与育儿假的关系,目前我国的产假包含了部分育儿假的内容,应当合理界定产假与育儿假的边界,制定更加合理、规范的生育假制度。
(三)完善家庭生育假的相关配套措施
首先要建立家庭生育假落实的主动监管机制。目前并没有承担监管生育假落实情况的机构,而当事人权益保障则只能依托于事后的救济。事后救济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不利于及时保障。卫生健康委员会专门负责人口问题[24],与此息息相关,因此,笔者建议赋予卫健委以主动监管的权力,以保障该制度的落实。
其次要大力发展公共托幼服务及相关产业,发挥社会化抚养的作用。其好处有三:一是节省父母的时间、精力,将其从烦琐的新生儿照顾中解放出来,使之可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以取得报酬等[25];二是有利于新生儿健康成长,公共托幼服务具有更强的专业性,提升对新生儿的照顾水平[26];三是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父母的劳动能力被解放出来可以从事其本职工作,同时托幼服务的繁荣可以带动新生儿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效果。
最后,要完善生育保险基金的建设。在三胎政策的大背景下,实行家庭生育假制度后,生育保险基金必然要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因此,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完善生育保险基金的建设[27]。比如加大财政投入扩大生育保险基金池,合理优化税收政策助力基金池建设等[28]。
四、结语
从单系抚育到双系抚育的演进是家庭生育假制度的大势所趋,是由当下经济发展水平所导致的家庭分工转变所决定的。而构建这一制度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合理分配生育成本,不能将生育成本过多放置于其父母身上,同样不能一味强加于用人单位。在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如何合理调配社会资源,恰当安排该制度便是问题所在。另外,我国人口众多,国外的经验虽然值得参考,但必须结合我国实际,不能一味效仿、照搬照抄。制度的发展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①在瑞典,父母共有480天育儿假,父亲母亲各必须承担60天,余下360天父母各一半,但可以相互转让。参见胡玉坤:《瑞典育儿福利改革的借鉴与启示》,《中国人口报》2019年5月20日,第3版。
②我国许多省份规定的有父亲的陪产假,但一般都在7∽20天,比如:2014年《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3条规定“男方所在单位给予七日护理假”,此处的护理假即陪产假。再如《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规定“男方享受十五日的陪产假”。
③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5条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与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保持一致。该条文规定了夫妻享有生育假的奖励,但是却并未明确该奖励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实现该奖励。
④参见2012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7条、第8条。
⑤参见2018年《社会保险法》第56条。
⑥参见2019年5月国务院《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⑦2020年8月《辽宁省女职工权益保护办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第18条第3款规定“鼓励用人单位对依法生育的夫妻,在子女3周岁以下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日育儿假”;2020年3月广东省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积极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休假”。
[1] 刘明辉. 产假延长及待遇提升的双重影响及完善建议[N].中国妇女报, 2017-08-22(B01).
[2] 林燕玲. 女职工假期设置对女性权益维护的影响及国际经验比较[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8, 32(3): 15-34.
[3] 李西霞. 生育产假制度发展的国外经验及其启示意义[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14(1): 100-106.
[4] 廖敬仪, 周涛. 女性职业发展中的生育惩罚[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20, 49(1): 139-154.
[5] 余秀兰. 女性就业:政策保护与现实歧视的困境及出路[J].山东社会科学, 2014(3): 48-53+128.
[6] 傅静. 从性别歧视的角度简析女大学生就业问题[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1(1): 86-89+93.
[7] 遇见大咖: 刘强东[EB/OL].(2017-02-03)[2021-07-15]. http://tv.cctv.com/2017/02/03/VIDESFTd3MKGsaUu2LCdyMCb170203.shtml.
[8] 冉昊. 德国生育津贴制度变迁的社会功用分析——从“养育津贴”到“父母津贴”[J]. 贵州省党校学报, 2019(1): 69-78.
[9]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EB/OL].(2018-12-02)[2021-07-15]. https://chfs.swufe.edu.cn/datacenter/apply.html.
[10] 王友青. 企业带薪休假制度落实的现状及对策分析——以西安为例[J]. 消费经济, 2010, 26(2): 60-62+66.
[1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郑东亮,张丽宾. 2012年中国劳务用工行业就业指数报告[J]. 经济研究参考, 2013(33): 3-27+57.
[12] 吕春娟. 全面二孩视域下国家分担未成年子女养育成本制度建构[J].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5(4): 75-83.
[13] 刘娜, 卢玲花. 生育对城镇体制内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8(5): 10-19.
[14] 赫伯特•斯宾塞. 斯宾塞的快乐教育全书[M]. 周舒予, 译.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2-5.
[15] 刘中一. 角色虚化与实践固化:儿童照顾上的父职——一个基于个体生命经验的考察[J]. 人文杂志, 2019(2): 106-112.
[16] 王雨磊. 父职的脱嵌与再嵌:现代社会中的抚育关系与家庭伦理[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3): 63-70.
[17] 王向贤. 社会政策如何构建父职?——对瑞典、美国和中国的比较[J]. 妇女研究论丛, 2014(2): 49-54.
[18] 房莉杰, 陈慧玲. 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J]. 人口学刊, 2021, 43(2): 86-97.
[19] 陈文联. 从依附走向自主: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轨迹[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1(2): 237-242.
[20] 范玲, 吴连方. 产妇分娩期的生理及心理特点[J].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05(5): 276-278.
[21] 刘兰芬, 赵贵芳, 张志华, 等. 产妇产前的心理状态及相关因素分析[J]. 中华妇产科杂志, 1998(7): 24-26.
[22] 邝利芬, 程同顺.“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下女性基本权利的保障——基于性别公正的视角[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6, 18(4): 63-68.
[23] 童文胜, 汪文靓. 挪威育儿家庭政策的经验[J]. 当代青年研究, 2015(6): 115-121.
[24] 何亚福. 卫健委“三定”方案折射人口政策转向[N]. 中华工商时报, 2018-09-13(003).
[25] 周佳民. 托幼公共服务对农村女性劳动参与时间的影响[J]. 兰州工业学院学报, 2020, 27(5): 112-116.
[26] 和建花. 生育新政呼唤托幼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N]. 中国妇女报, 2015-11-03(B01).
[27] 范维强, 刘俊霞, 杨华磊. 生育、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与养老金待遇机制调整[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0, 35(9): 17-25.
[28] 林海鑫.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21(11): 76-78.
From Single Parenting to Dual Parenting: The Inspection and Shaping of Family Maternity Leave
LIU Hao-kai
(Law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o extend maternity leave for women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However, the nature of extending maternity leave is to confine women to the family, but it will cause invisibl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the workplace. The single parenting concept that emphasizes women’s responsibilities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To perfect the family maternity leave system, the dual parenting concept must be adopted. Men and women both need to assum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Dual parenting is conducive to playing the role of father, promoting family harmony,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reducing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maternity leave should take maternity leave and parental leave as the core content to establish a legal system and improve supporting measures.
three-child policy; dual parenting; paternity theory; parental leav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2021-09-08
刘浩锴(1998—),男,河南禹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司法制度与人权保障。
D922.1
A
2095-9249(2021)05-0048-05
〔责任编校:王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