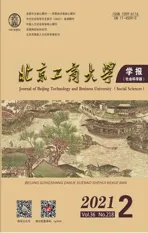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时间银行”演变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2021-11-28吴振东
陈 功, 吴振东
(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 北京 海淀 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和出生率不断下降,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以60岁以上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占总人口10%和7%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指标,当上述指标分别超过20%或14%时,标志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1]。202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数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数的12.6%,宣告我国已从老龄化社会向深度老龄化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源闲置。相对来看,人类预期寿命增加导致离退休老年人非工作时间增加,在我国弹性退休政策尚未出台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大量闲暇时间及其人力资本未被充分利用,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源闲置。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负担加大。首先,我国已从政策性低生育阶段进入文化性低生育阶段。预计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在2037年前后进入超少子化——超高龄化并存的人口年龄结构状态[2]。少子化将直接导致老年人抚养比上升,其中失独和贫困老年人群体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其次,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带来巨大养老财政负担。2018年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 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负6 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①。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财政养老或政府养老供给仍面临着持续压力,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动能。
三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要求。由于我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当下我国既要及时解决好老龄化治理问题,也要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等问题,推动老龄化治理的同时,促进老龄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但是目前,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社会资源难以跨区域流通,数字化技术应用不足,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尚未完成,急需发挥科技在老龄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2019年1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②。而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和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发展要求。因此,我国不仅需要从国家层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更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充分利用新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积极发挥老年人人力资本在社会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实现人口老龄化事业与老龄化社会的协同发展,变人口老龄化之“危”为经济社会发展之“机”。
人口老龄化也是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人口问题。国外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创新发展同时,创造了诸多理论与发展机制,其中“时间银行”机制被广泛应用与养老、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近年来也不断引起各国政府与学者的关注。该概念由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Edgar S. Cahn)于20世纪70—80年代探索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径时提出,“时间银行”概念即倡导人们通过“时间银行”提供社会服务并记录服务时长,以服务时间换取时间货币,用时间货币把闲散的时间利用和储蓄起来,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从中“支取”时间货币并予以兑换他人的服务[3],从而实现社会时间与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构建新的社会互助网络,促进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时间银行”在国外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已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然而当下,“时间银行”在我国还处于发展阶段,实践和理论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本文旨在从理论层面分析“时间银行”在演变过程中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作用,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
二、“时间银行”的演变及评价
(一)演变历程
1.“时间银行”实践的萌芽期(19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劳动货币和劳动银行的产生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从物质运动层面探究时间的价值,马克思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从人类实践劳动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时间,认为物质运动不过是时间的空洞的延续,而实践劳动才是充实的劳动时间[4],突出了时间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时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时间刻度、物质运动的标尺,而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和发展的过程[5]。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人的积极存在不仅是物理时间的延续,更重要的是通过相对有限的生命时间实现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因此,人的劳动时间也是其社会时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社会时间也可转换成“充实的劳动时间”,而不仅仅是“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6]。
于是,如何充分利用社会时间,特别是利用独立于工作时间以外的社会时间,并以非工作以外的社会时间产生新的价值,如交换价值、购买价值,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部分国家与地区曾就此进行了大胆尝试。19世纪初,在美国、英国的部分地区,劳动货币(labour money)开始萌芽,社会劳动时间成为新的货币并用于交换,其中代表性的是美国人约书亚·沃伦(Josiah Warren)于1827—1830年成立的以社会劳动时间为交换媒介的辛辛那提时间零售商店(cincinmati time store);1832年,英国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英国成立了国家公平劳动交换机构(National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以社会劳动时间为单位发行面额不等的劳动纸币(labour notes);英国约翰·格雷(John Gray)等人探索成立了全国商会,并以此作为中央银行发布社会劳动货币(labour currency),便于人们以劳动纸币为媒介交换产品。但由于对产品价值和产品象征的时间具有争议,制度与价值标准体系尚未成熟,该机构于1834年倒闭。到了1848年,又有人在劳动货币的基础上探索了时间欠条(time chits)制度③。总之,这一时期,社会劳动时间已出现货币价值化和可交易化的特点。
随着人们对社会劳动时间货币的探索,劳动货币银行开始出现。日本人水岛辉子(Teruko Mizushima)于1973年在日本创立了“志愿者劳动银行”(Volunteer Labour Bank)。1998年日本《非营利组织法》规定其不能轻易使用银行一词,后改名为志愿者劳动网(Volunteer Labour Network)和志愿者人力资源网(Volunteer Human Resource Network)。虽然名称中去掉了银行一词,但水岛辉子创立的“志愿者劳动银行”却是第一个以银行命名的劳动货币存储机构[7]。
上述组织与机构的产生,表明人们开始重视社会时间的价值与作用。不过,仍有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如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认为这种背景下的劳动虽然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但却是一种与商品生产完全不一致的生产形式,劳动货币实际上不是商品经济中的货币。恩格斯认为没有把劳动货币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而是直接假定了社会劳动,这是一种与商品生产完全不一致的生产形式,这种“劳务费”是不可能成为货币的[7]。这一阶段,把社会劳动时间作为新的交换媒介在实践层面并没有产生更大范围的社会补偿和社会货币代替作用,即劳动货币和劳动银行的实践没有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没有形成支持其长期发展的理论基础。所以,劳动货币不会产生替代市场经济中货币的作用,其更多只能是部分地区、部分人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胆尝试和实践创新。然而,社会劳动时间货币化的理念和实践却促进了人们对社区货币的认识与探索。
2.“时间银行”实践的探索期(20世纪80—90年代):社区货币的发展及合作共产理论的提出
先前劳动货币和劳动银行的萌芽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除了市场交换,人们还可以利用社会劳动时间等媒介建立非市场交换机制。这些概念的萌芽,为人们认识社区货币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三个相互影响的问题:一是底层人民在获取生活必需品和基本服务上的不平衡,二是家庭、邻里和社区重建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三是人们对于上述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而产生的不满[8]。传统的市场供给无法保障所有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受到影响,人们开始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有学者指出,如果常规经济没有为人们获得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足够的机会,人们就会寻找替代方法[9]。为解决上述问题,人们开始探索通过非市场经济路径创造一种新的交换机制和系统,从而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推动社会互助、社会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新的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社区货币(community currency)成为人们寻找在主流市场经济之外运作的替代货币和替代机制[10],它的出现也是对市场经济交换系统的重要补充。社区货币通过连接一个人际社区网络来扩大交易,参与者利用目录、通信、公告栏或网站公布其希望提供或获得的商品及服务,人们在这个系统中联系、协商合作,用赚取的信用积分进行交易[11]。这期间,社区货币主要有三种形式,地方交换贸易系统(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简称LET)、时间美元(time dollar)和时间系统(hours system)[9,12]。
地方交换贸易系统和时间系统是20世纪80年代同时产生的两种社区货币。相比时间系统,地方交换贸易系统产生更早。1983年,第一个地方交换贸易系统产生,人们基于该系统,通过电话、互联网或支票向中央协调人报告并开展交易[10],已有39个国家设立过1 500个地方交换贸易系统[13],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和非洲等不同地区多达2 000个社区建立过该系统[14-16]。但其低交易量和高管理成本严重阻碍了这一社区货币系统的发展[17]。为降低管理成本,1991年美国伊萨卡市纸质地方货币系统产生,比较有代表的是美国伊萨卡时间系统(ithaca hours),该系统将纸质货币价值直接与市场货币美元挂钩[18]。这一优势使该系统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快速发展并获得公众认可,仅1991年就有82个伊萨卡时间系统在美国运行,但该系统无法追踪时间交换频率和人员退出情况,也无法收集相关数据[10],因此并未得到广泛运用。
相比上述两种社区货币,1983年在美国迈阿密、佛罗里达等地出现的“时间美元”[10]更加灵活有效。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Edgar S.Cahn)提出,为回应社会互助网络和非正式邻里支持的需求[19]。“时间美元”系统可将社区中失业者从社会负担转化为社会资产,实现人的价值,并通过建设新的社会支持网络,为解决20世纪末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路径。在“时间美元”这一系统中,人们通过帮助他人赚取“时间美元”,再通过使用“时间美元”购买他人的基础服务或商品[8],交易的基础货币为社会劳动时间[20],1小时服务获得1“时间美元”。可见“时间美元”更加注重人的社会时间价值对等,而非社会时间所代表的市场经济价格,不属于市场货币体系[21]。人们可以通过“时间美元”支付贷款手续费、换取物品修理,利用“时间美元”为他人提供子女照顾和教育、开展志愿服务和赈灾等[11]。相比其他社区货币,“时间美元”更重要的价值是具有合作共产的价值导向。
Cahn[22]在“时间美元”基础上提出了合作共产理论,认为“时间美元”是实现合作共产目标的一种机制和工具。合作共产理论主要包含四种核心价值[23]:一是资产。即社会的真正财富与资产是人,每个人都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二是重新定义的工作。即有一些工作无法用钱支付,培育健康的孩子、维护家庭、激发社区安全使其充满活力、照顾体弱多病的人、纠正不公正、让民主可以正常运行等都应该属于工作的内容。三是互惠。即社会需要人们的互惠与互动,互惠可以让所有参与的人,包括服务的接收者和给予者都能发挥社会作用。四是社会网络。即社区是通过建立支持、信任构建网络,信任、互惠和公民参与能够激发新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通过互助又能形成新的社会网络。
在社区货币发展阶段,合作共产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中每个人的重要性,认为每个人都能成为生产者和贡献者,都能通过社会时间的合理利用实现人力资本增值[24]。该理论要求人们改变对社会服务“产生”的理解,包括如何理解专业人员、用户和社区的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转变[25],认为每个被服务过的人也能成为社会服务的生产者,老年人和残疾人也具有社会服务价值与作用。合作共产理论也是一种对资源、伙伴关系的新思考[26]。通过互惠与社会网络的建立,能够促进个人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实现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价值。
从劳动货币到社区货币,社会时间与个人价值得到充分肯定,社会交换机制也逐步成为独立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和政府交换机制以外的新机制,成为人们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而社区货币,如“时间美元”的大规模推广及合作共产理论的提出又为“时间银行”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3.“时间银行”实践的成熟期(20世纪末至今):制度化和全球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计算机和数字化信息技术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和联系提供了助力,社区货币也开始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与应用。从“时间美元”到“时间银行”(timebanking)的术语转变出现于1999年的英国。这是由于“时间银行”这一相对无国界的中性术语更具有可接受性。不过当时这一术语的表达更多为“时间银行”社会交换机制、系统或某一项目。1995年,埃德加·卡恩为了促进“时间银行”机制的可持续发展,着手建立了美国“时间银行”机构,直接促进了“时间银行”机制的全球化发展。据统计,2015年美国已有500家注册时间银行机构,欧洲、亚洲、非洲、北美和南美等地区超过30多个国家出现“时间银行”机构的运营[27]。自此,“时间银行”成为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社区货币之一,也成为不同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
这个阶段的“时间银行”具有以下特点④:
一是统一社区货币的交换原则和价值标准。“时间银行”机制中赚取和消费的均为“时间美元”或“时间积分”,每个“时间银行”机制都遵循一个基本的规则,即所有的社会劳动时间都具有等同的交换价值,“时间美元”这种社区货币不可出售,也不能兑换成市场经济下的货币,只能应用在社区资源建立、慈善事业推进、个人支持提供或社会问题解决等方面。
二是实现了社区货币机制的制度化和组织化,成立了“时间银行”机构与组织以及发展联盟,推动了制度标准的发展。
三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社区货币线上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从社会资本粗放式发展向科技化发展迈进。“时间银行”组织开发了基于互联网的Community Weaver线上软件APP,用于服务和管理“时间银行”相关活动。这一线上平台的开发,为跨地区间的“时间银行”通兑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实现了“时间银行”之间资源的整合和系统化发展。
四是完善了“时间银行”的核心理论。在合作共产理论四个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即资产、重新定义的工作、互惠、社会网络,又增加了尊重价值,尊重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人们所珍视的一切自由的基础,也是民主的核心和灵魂,因此人们应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对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尊重。
(二)对“时间银行”实践的评价
1.“时间银行”实践中的经验
“时间银行”的演变穿插于不同历史背景中,服务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体现了从劳动货币概念到社区货币机制再到“时间银行”组织化的发展脉络。通过梳理“时间银行”发展脉络,可以总结出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经验。
一是通过利用个人的社会时间产生新的社会价值。“时间银行”发展萌芽期的标志是将社会劳动时间看成一些新的交换货币,从而产生劳动货币和劳动银行。劳动货币和劳动银行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在这一逻辑和机制下,将自己工作生活以外的自由与闲暇时间通过这两大机制,帮助他人并获得他人服务及商品,特别是能让人们充分开发其自由与闲暇时间,实现其非工作与生活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价值增值。劳动货币的萌芽激发了人们对时间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强调每个人的经济社会时间都可以通过社会服务与社会交换产生新的社会价值,从而满足非市场经济机制下个人社会发展需求。因此,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注重生产力的提高,也要重视社会时间的价值开发与利用,强调时间的社会化管理与分配。
二是通过建立市场与政府分配机制之外的社会交换与分配新机制集聚社会资本。在探索期阶段,“时间美元”等社区货币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社会交换与分配方式[28],源自人们对市场的谨慎和政府的不信任[29],是对经济和政府失灵而做出的反应。社区货币并不是用来替代货币经济,它提供了一种额外的交换与分配机制。“时间美元”根据人们所提供的服务产生新的劳动价值,这一劳动价值的衡量不再是单一的货币价值,而是人与人平等的社会时间价值的衡量。通过“时间美元”这一新的社会交换与分配机制,个人尤其是低收入者能获得某些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是无法获得和购买到服务[30],为人们寻求社会服务提供了新路径,赋予了社会交换更多的维度[31],通过“时间美元”社会货币系统实现了人力资本、知识技能资本、信息资本、物质财富资本在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社会间的集聚、流通与分配,这种再分配不是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而是根据人们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的自由与平等的再分配。
三是通过运用数字化手段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从“时间银行”探索期到成熟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的现代化发展,而在线软件的开发和推广是重要保障,其将不同地区的“时间银行”机构点连在新的社会交换与分配网络中,也为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流通构建了现代化的社会交换与分配网络。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手段的帮助下,“时间银行”能够将不同社区的“时间银行”系统中的社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信息资本、技术资本及时更新储存在“时间银行”系统上,再利用数字化和数据化的匹配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社会资本供给的即时对接。通过数字化技术扩大了社会交换与分配机制的作用,实现地区间社会资本的跨区域流通,推动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2.“时间银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一是社会化运动难以保障“时间银行”可持续化发展。“时间银行”在演变过程中,主要是由不同地区、机构或不同社会爱心人士发起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不论是水岛辉子建立的“志愿者劳动银行”,还是埃德加·卡恩建立的美国“时间银行”联盟都是非政府组织,这些机构在发展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财物的可持续化供给。如,瓦莱克(Valek)发现捷克两所“时间银行”的建立都是以个人为主导,认为捷克“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为较低的资金资助和人力资本匮乏[32];瓦莱克(Valek)还发现俄罗斯最大的“时间银行”由当地商人安德烈·伊万什金(Andrey Ivanushkin)个人发起成立,而成立的“时间银行”过于依赖该创办人的个人热情、领导能力及筹资能力,个人的过度依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时间银行”难以持续发展[33]。有学者对美国的“时间银行”进行过全国调查,发现受到资金、会员、软件、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仍然有很多“时间银行”难以可持续发展,甚至出现了破产[9]。
二是文化与语言差异难以实现“时间银行”标准化发展。虽然美国“时间银行”组织提供了“时间银行”机构成立方面的培训和线上软件,但不同地区、国家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不同,必然导致同一套发展理论和模式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在文化层面,有学者指出经济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缺少导致更难认同“时间银行”交换文化;而在语言层面,跨地区与跨社区的语言差异也对“时间银行”软件的通用性提出挑战[34-35]。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时间银行”受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例如,在新西兰利特尔顿(Lyttelton),人们参与“时间银行”动力更多的是利他的因素,并不是为了实现服务的交换[36]。希腊一家“时间银行”设计了独特的计算与交换原则,该“时间银行”并不按照埃德加·卡恩设计的1小时兑换1小时原则,而是采取了服务换服务,即不管服务花了多少时间,只注重服务的对等交换,该国另一家“时间银行”不按平等原则计算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市场价格原则,以与商业市场类似的价值标准对服务进行估价,如15个时间积分换取一次理发,20个时间积分换取一节数学课等[36]。因此,在肯定合作共产理论和“时间银行”机制作用的同时,还需要从不同国家本土化的角度,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因素。
三、我国“时间银行”发展的现状及困境
(一)我国“时间银行”发展的现状
20世纪末,我国老龄科研中心将“时间银行”理念和机制带入国内,1998年上海市虹口区的提蓝桥街道最早将“时间银行”应用于我国互助养老事业的发展[37]。此后,广州、南京、武汉、深圳等地也不断出现了“时间储蓄”项目和“时间银行”机构。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时间银行”的发展,先后出台多个政策文件鼓励开展“时间银行”养老与志愿服务。例如2012年出台了《志愿服务记录办法》、2016年制定了《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等[38],2019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则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积极探索“时间银行”等做法。上述国家宏观层面政策的出台为“时间银行”在我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不论是国家宏观政策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都将“时间银行”看作创新我国互助养老、志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办法。
由于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近年来我国“时间银行”发展开始加速,“时间银行”在我国已至少达到128家规模。从分布上看,我国“时间银行”呈分散状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时间银行”呈现集中分布状态(主要在省会城市);从组织属性看,“时间银行”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主导型、企业主导型三种类型,且当前以政府主导型为主,即“时间银行”的创办、运行、监管主要由政府(街道居委会)负责;从参与对象上看,以组织动员辖区内低龄老人为主,但也覆盖部分大学生、白领、社区热心人士等,而服务对象以空巢、独居高龄老年人为主,兼顾辖区内所有有服务需求的群体[39]。总之,“时间银行”在我国主要以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开展,重点应用于养老,兼顾志愿服务、社会治理等功能。
(二)我国“时间银行”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是社会对“时间银行”概念认识不清导致的参与问题。“时间银行”并未在我国得到大规模的开展,宣传路径和宣传力度相对不足,加之我国社会文化环境中长期弘扬学雷锋、办好事等乐于助人与奉献精神,人们难以完全认同“时间银行”概念中的互惠价值,其有偿性也容易引发人们对志愿服务“做好事不求回报性”的质疑[40]。同时,受认识水平的影响,人们也容易根据市场经济中劳动强度和劳动价值的关系对“时间银行”通兑原则中单位社会劳动时间相等提出否定看法,从而影响参与意愿与服务通兑。
二是“时间银行”发展规模导致支持不足的问题。由于我国“时间银行”仍处于地方探索阶段,各地发展规模相差较大,多数仅覆盖单个地区和社区,因而受众面较小,不利于时间银行的推广与社区货币的流通,既不能充分调动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也不能提供更多的社会人财物支持,难以促进跨地区的社会资源对接,实现整合化发展[41]。此外,由于国内尚在探索阶段,“时间银行”制度建设滞后,并未形成健全的安全保障政策、保险政策、风险评估政策等政策支持体系。
三是数字化发展水平落后影响资源整合与流通。各地“时间银行”发展水平不同,部分“时间银行”停留在纸质化,尚未实现数字化发展和在线APP开发,导致服务需求与匹配难以实现精准对接,无法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跨区域、跨机构的“时间银行”线上互联,促进服务通兑和资源共享,难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
四、“时间银行”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与启示
(一)发展思路
随着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的逐步重视和各地“时间银行”的不断探索,以及国内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加之我国5G、大数据等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时间银行”将在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方面发挥着更大作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时间银行”还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对“时间银行”的正确认识。“时间银行”在我国发展,应尊重本土社会文化价值,强调老有所为、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传统文化,并从生命周期的角度促进人们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科学认识,提升其对互助养老以及养老储蓄的重视,在突出“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的同时,应积极维护其时间储蓄的功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现公益和互助双重属性[42]。同时,要进一步提升公民对时间的珍惜和时间社会属性的重视,促进公民充分开发个人闲暇时间价值,发挥个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力资本作用,强化对“时间银行”机制作用与价值的科学认识。
二是推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我国“时间银行”相比国外最大的优势在于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推动了“时间银行”的快速发展,政府主导应从法律政策等制度层面不断加强顶层设计,为“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人财物政策引导,解决好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安全风险问题,做好制度兜底。同时,需要发挥自下而上的作用,调动社会不同人士的广泛参与,促进社会资本和政府资本在“时间银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聚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
三是发挥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整合与创新作用。 应由政府主导,推动我国“时间银行”线上平台建设,开发国家“时间银行”APP平台,免费为尚未实现数字化建设的“时间银行”提供信息化服务,同时尽可能实现对个人已有“时间银行”在线平台的兼容,将不同地区“时间银行”纳入国家“时间银行”线上统一平台,实现数据的统一管理,以数据化、平台化形式搭建全国“时间银行”网络,实现不同地区“时间银行”的整合发展,以规模化发展促进“时间银行”更大层面社会资本的线上与线下流通,借助“时间银行”大数据的应用与分析,以数据科学助力“时间银行”事业的创新与发展。
(二)发展启示
纵观“时间银行”的演变历程,其强调了时间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交换价值,指出了“时间银行”社会交换与分配机制可以作为市场和政府分配机制以外的新分配路径,肯定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在推动社会资本跨区域流通与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助力作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结合“时间银行”演变历程中的实践经验,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创新与发展提出了以下政策启示。
1.以“时间银行”开发我国社会人力资本
时间是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客体。德国学者萨弗兰斯基(Rudiger Safranski)认为人们生活在严格的时间政体下,时间交织的网络变得紧密,个人被捆绑在自己或他人制订的时间计划中,如何最理想地利用时间、节省时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内容,而时间也转变成某种类型的客体,人们可以通过分配、利用和管理来处理时间这一客体[43]。“时间银行”的核心逻辑是重视不同人群的时间管理与利用,通过对时间社会属性与价值的开发,赋予“时间”客体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多动力。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闲暇时间多,科学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引导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社区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要求,更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开发国家人力资本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国家需要从宏观层面探索时间客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时间银行”社会时间管理与开发机制作用,加强公民的时间价值教育,营造时间管理的社会氛围,形成全民时间管理意识,积极引导老年人、在校学生、党员干部、社区群众、爱心人士等不同人群通过“时间银行”机制充分利用个人闲暇时间、自由时间,广泛参与社会养老、社会治理、社会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
2.以“时间银行”集聚和发展我国社会资本
社会交换与分配机制是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路径。当前,在完善市场和政府分配机制的同时,要积极探索社会再分配机制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激发社会活力。“时间银行”机制不仅能应用于互助养老、社区发展,还作用于商业项目、救灾、司法服务、人才培训等诸多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是当下我国建设社会交换与分配机制的新工具。因此,应推动我国“时间银行”机制应用从单一的养老互助功能向社会整合、社会服务、社会分配、社会网络功能演变,突出“时间银行”的社会资本集聚与分配作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中每一个人的价值与作用,通过“时间银行”机制把社区、高校、企业和社会不同组织连成一个社会支持网络,实现线下社会资本、闲散社会资本在“时间银行”这一社会交换机制中的整合与集聚,构建跨行业、跨城市、跨地区的“时间银行”社会资本支持体系,推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公益资本、信息资本、知识资本等社会资本在“时间银行”机制中的交换与流通,发挥“时间银行”这一社会交换与分配机制对市场、政府机制的补充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在养老、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力量。特别是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等背景下,市场与政府分配机制难以及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通过“时间银行”发布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快速连接当地社会资本,鼓励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财物支持,实现市场、政府、社会三种分配机制和资源的辩证统一。
3.以“时间银行”的数字化建设来完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化建设和大数据应用是实现老龄化背景下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通过“时间银行”数字化建设,促进线下“时间银行”机构数据和线上平台数据的对接,实现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机构在“时间银行”平台的数据对接,促进“时间银行”实现服务时间的全国通兑。整合不同地区的社会资本,推动社会治理主体从部分志愿者到全体公民、从单一社区向全国扩展,实现治理单元的网络化和整合化,从而构建政府—社会—个人多元协同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实现“时间银行”从原先的老龄化治理工具向老龄化社会治理工具的迈进。此外,依托“时间银行”数字化平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跨区域快速流通,及时引导不同社会组织、个人利用互联网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时间银行”打造成为对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需求、社会资本供给可实时监控的数字化大数据管理平台,构建国家“时间银行”社会资本库与数据库,根据国家“时间银行”数据库中大数据的动态变动情况,实时掌握不同人群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区域社会资本的供给情况,为完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新决策参考,以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调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时间资本、数字资本,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手段的精准化,使“时间银行”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新工具。
注 释:
①资料来源于任泽平、罗志恒、孙婉莹的《中国财政报告2019》一书。
②2019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资料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9-11/23/content_5454778.htm。
③维基百科网站,www.wikipedia.org。
④Timabanks USA官方网站,TimeBank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