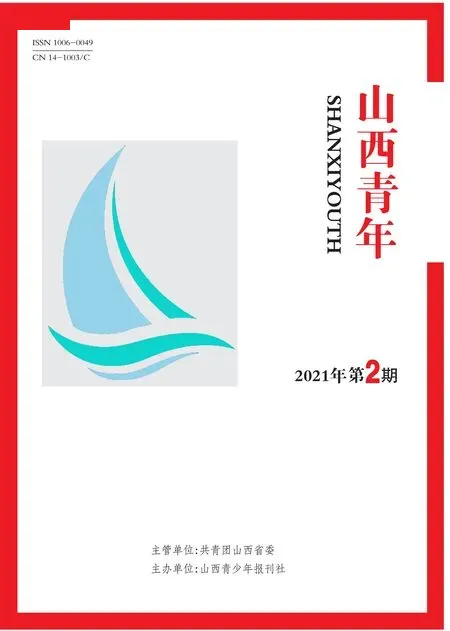《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的两面性特征研究
2021-11-28张小敏
邰 航 张小敏
(山西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0)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路;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1]蒲松龄创造式的建造出一个几近梦幻的世界。在那里,他用饱含深情的笔调勾勒出清代书生的轮廓,借以传递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亲身感悟与凝重思考。分析这一有所寄托的“书生”群像,会发现他们带有无法摆脱的两面性特征。本文从三个角度来探析书生形象的两面性。
一、价值观:自我实现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性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这是先贤圣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学而优则仕的最终理念,是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书生所应坚持之理。《聊斋志异》中,书生为了考取功名,寒窗苦读十年已是司空见惯:《大男》中的奚大男,四五岁时,见塾中学生吟诵,自己也跟着读,便“送诣读”;《姊妹易嫁》中,张公喜爱毛公,“即留其家,教之读”,在毛公尚为孩童之时,便教其读书识字;《陆判》中,朱尔旦之子年至七八岁,其父“灯下教读”;《书痴》中的郎玉柱,即使家贫无以食,仍时常“昼夜连读,无间寒暑”;《凤仙》中的刘赤水,在心上人的督促激励之下,“闭门研读,昼夜不辍”;《褚生》中的褚生,面对这来之不易的读书生活,“攻苦讲求,略不暇息”,甚至寄宿于书斋之中,“未尝一见其归”。他们为了早日夺取桂冠,不惧环境之清寒,不畏生活之贫苦,或居于书斋之中,或选一偏僻居所潜心研读。
所读圣贤之书,教导书生出仕本应是为了顺应儒家理想,致力于识得民间苦,解得百姓忧,得天之道。然而,《聊斋志异》中,书生对于金榜题名如此热切,如此渴望的原因却并非如此。例如《罗刹海市》中的马骥,在父亲的劝说之下,“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便放弃学业继承父之商业。由此可见,读书虽是书生的第一选择,但是当更有利的第二选择出现之时,他们还是会做“择木而栖”的“良禽”,因此这类书生读书明德之心不真;再有《王子安》,与鲁迅的《孔乙己》有异曲同工之妙,科举之后喝得酩酊大醉,梦见考中进士,“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呼唤长班,长班来晚,王子安欲起身泄愤扑打,却最终摔倒在地。毫无疑问,这是对科举制度的讽刺批判,然而,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王子安这类书生对于读书,对于科举理解的偏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书中已将书生应当肩负的使命讲得明明白白,读书不为名利,在于功德,在于百姓,在于大道,然而“王子安”却与之背道相驰,将中举作为自己的终极人生目标,这样一想,他如此这般的结局便是情理之中了。而倘若“王子安”遵循书理,将中举只是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一步台阶,那还会出现如此啼笑皆非的故事吗?因此,书生将科举当作自己跨越阶级的跳板,为了一举成名荣冠乡里的目的而读圣贤之书,这一动机与动作行为本身就是存在矛盾性的。
究其矛盾因缘,一方面是经济因素,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聊斋志异》中书生自身家庭条件大部分为穷苦之家,例如《狐嫁女》中,以“历城殷天官,少贫,有胆略”为开头介绍殷尚书少时家困;《娇娜》中,孔雪笠“落拓不得归,寓菩陀寺,佣为寺僧抄录”;《成仙》中,成生“贫,故终岁常依周”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生生存的艰辛。而科举本身就是耗费钱财与精力之事,书生能满足日常所需已是实属不宜,更多的还挣扎在饥饿与寒瑟的边缘,因此他们对于科举不免抱着鱼跃龙门,不愁吃穿,春风得意的幻想;另一方面便是环境因素。由于认知的狭隘,社会、乡亲以及家人对于科举的理解便是锦衣玉食,家财万贯,当人云亦云,使得高高在上、朱轮华毂成为科举的代名词时,这样的概念不免会潜移默化至书生的潜意识中。
二、道德观:君子人格与道德沦丧的矛盾性
“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4]标榜了德行对于君子的重要性。书生自幼读书,所读正是君子之道,并以其道行其事。《聊斋志异》虽是记奇叙怪之作,其中也不乏人世间的情,正如老舍所言“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书中对人情伦理也进行了一定的描写。而书生作为《聊斋志异》中较为特殊的群体,可以说是鬼狐与世间联系的枢纽。在人世与异域中的交错挣扎中,或是坚守儒家“五常”的伦理道德阵地,或是没落士节,人格精神逐渐消退,使得书生这一整体自身的道德理念更显矛盾。
从孔子创立的“仁、义、礼”,到孟子发展的“仁、义、礼、智”,再至董仲舒完善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道德标准的核心,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在倡导。同样,在《聊斋志异》所处的时代,儒家信仰浓厚,书生幼习儒学,使得他们在现实压迫之下,仍然坚守着五常伦理,散发着人性启蒙之初那抹明亮的光辉。“仁”有《水莽草》中祝生的善良仁慈,他被水莽草所毒害,“不得轮回”,欲转世则要自己毒死另一个人,循环往复。然而,祝生并没有找替死鬼,甚至帮助别人不被水莽草所害,“为之驱其鬼而去之”;“义”有《狐联》焦生的正直,“读书园中,宵分有二美人来,颜色双绝”,但焦生正色严拒,“仆生平不敢二色”;“礼”有《青梅》张生的克制理性,对前来示好的青梅正色拒绝,言“昏夜之行,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智”有《于去恶》中于去恶的豁达大智,在知道考官目盲不识真才之后,欲罢考,在朋友劝说下勉强参加考试,但还是坚持自己特色,最后“兄教弟读,引为乐事”;“信”有《成仙》中成生与周生互相帮助的默契,成生贫困,周生接济,周生有难,成生鼎力相助不违誓言,成生顿悟仙道,也拉着周生一起成仙。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书生在生活的重压下都能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其中一些人也会不堪其重,堕落道德泯灭的深渊。譬如《霍生》中,霍生与严生嬉笑相谑,霍生偶然间得知严生妻子私处秘事后,造谣生事,大肆宣扬,致使严生妻子清白被毁,被迫自杀,导致严家夫妇二人相继离世的悲剧发生;《丑狐》中的慕生,因厌狐女黑丑,不肯与其同好,但当狐女拿出钱财元宝之后,慕生态度大变,马上“悦而从之”;《九山王》的李生,在狐叟一家以礼相待,重金租借之后,“阴怀杀心”,便使用火药残忍地杀害宽厚待人的狐叟一家。由此可得知,《聊斋志异》中书生的道德层面并存着坚守与没落的两条支路,呈现出复杂矛盾的状态。
三、婚姻观:两情相悦与男性本位的矛盾性
爱情,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从《诗经》时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已开始描写爱情,而《聊斋志异》作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其中的爱情故事自是不乏少数,且都脍炙人口。自问世以来,大量的读者都为其中的男女相恋故事如痴如醉,沉迷其中。然而,不仅故事动人,故事背后的矛盾性更能引起我们的思考。
《阿宝》中,孙子楚与阿宝的爱情故事跨越了世间的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他们的爱恋,从一开始被当作看客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到皇帝感动进行赏赐,从刚开始对二人之间爱情无果猜想的理所当然,到后来二人情比金坚、生死契阔的顺理成章,这样大的转换,在与人物一起经历波折之后,却觉得合情合理。由此,我们不免得猜测作者蒲松龄心中的婚姻爱情理想,他也是崇尚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至情至性之人。
然而,在以写情为重的《娇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关于爱情的矛盾理想状态。《娇娜》中,孔雪笠,因缘与皇甫一家相识相认,在交往逐渐深厚之时,突发疾病。在娇娜为其治疗之时,孔生对其一见钟情,“一道强烈的电弧”使孔生忘记了剜骨去皮之痛,这样一来,一次本该血淋淋的手术场景却成了男女之间缠绵的情感传递。随后,孔生因娇娜年纪太小无法娶亲作罢,而娶了同样貌美的松娘,之后娇娜也另作他妇。事情进行到这里,我们不免为孔娇二人的感情扼腕叹息,也衷心希望孔雪笠与娇娜能够在各自的家庭中收获幸福。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生死相救之后,二人“矢共生死”,而娇娜也成为寡妇,最终变成了孔雪笠身旁永远的“腻友”。何为腻友?作者在文中结尾已给出答案“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而“腻友”的出现,是建立在男性家庭幸福已然存在的基础上的,即书生家庭美满幸福,但仍会有枯燥乏味之时,此时的“腻友”便是婚姻之外的情感刺激,其价值就在于给予书生最愉悦的情感体验。“腻友”这一概念的提出,便是对《阿宝》中“一双人”这一概念提出异议。
而在《连城》中,作者关于一双人的婚姻理想的否认表现得更为露骨。乔生、连城二人以诗相识,暗生情愫,在经历了乔生为连城割肉治病,双双殉情,还阳以及转世等等一系列的波折之后,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照常理来说,经历了这么多生生死死,乔生、连城之间应是容不下第三个人的。然而,作者却给乔生强加一妾,即长沙史太守女,以实现作者一男双美的婚姻爱情理想。类似的还有《青梅》中的阿喜与青梅,《嫦娥》中的嫦娥与颠当,在这里,作者努力表达在男方看来娥皇、女英式的完美爱情,努力塑造消除妒忌、和睦相处、情同姐妹的妻妾之情,甚至在《小谢秋容》中直言明示:“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惧得俩哉!”从最初作者赞扬的《阿宝》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再至《连城》中作者称颂的二女共侍一夫的和睦,使得我们关于蒲松龄的婚姻爱情理想的思考更加具有矛盾性,使其更具神秘感。
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艰难谋生,所谋之科举也寂寥渺渺。愤懑无奈之际,一笔一人一生,便创作了如此鸿篇巨制,且蒲松龄自身就是书生,对于书生群体,有着独特敏锐的嗅觉。文中通过对这一形象两面性的探寻,使我们感受到作品中书生群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也能了解到那个时代书生的整体面貌,从更深层次理解《聊斋志异》的背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