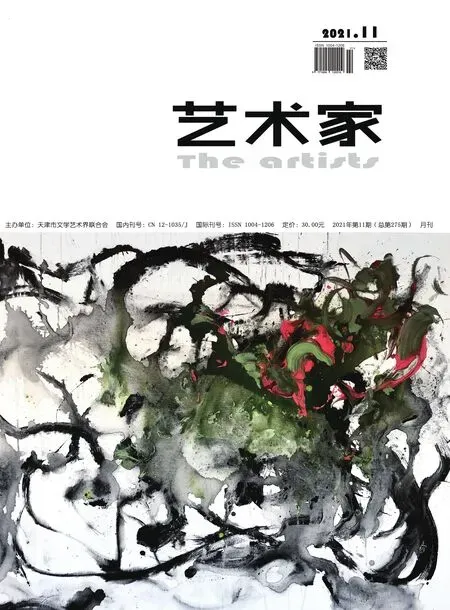论西方生态美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发展
2021-11-27郭硕博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郭硕博 四川美术学院 艺术人文学院
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人类的审美也随之变化。这不仅导致公众对生态系统的理解发生改变,还使人类开始认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生态美学应运而生,它是对人与自然作为一种生态整体从而产生美学欣赏的研究。随着这种美学思想不断拓展,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自然生态,还包括人类心理学领域,以及受人类影响而改变的社会生态。
一、对自然的观念转变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在文本中使用physis一词指称自然,并且这种“自然”已涉及一种内在的生成法则,因而是有生命的、有机的,意味着自然而然地生长、衰老、死亡。到古罗马时期,人们开始用natura 表征自然。基督教创立后,自然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从“神—人—自然”一体化转向“神→人→自然”的等级秩序。依照《圣经》所述,上帝处于一切创造物之上,而人则从上帝处获得支配和使用自然的权力,因此人高于自然。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甚至开始强调把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神的信仰分离,而且这种“自然”是可被观察、研究和测量的对象。文艺复兴时期则出现了多元化的自然观,其中包括将自然视为充满生机的有机体的“有机论自然观”、认为人类是上帝委派的自然管理者的“基督教田园主义”,以及后期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将自然视作可以拆卸装配的机器的“机械论自然观”等。
自18 世纪开始,有关自然生态的思想开始分化出两条脉络。其一是由卡尔·冯·林奈等人提出的对待自然的“帝国式态度”,认为大自然是如同一台具有内在联系的机器,经由上帝的“第一推动”而不停运转的自然经济体系,因此人类应当通过自身的理性实践,推进对自然的统治。另一种则是由吉尔伯特·怀特提出的“阿卡狄亚式态度”,这种田园主义观点主张要尊重自然本身,提倡简朴和谐的生活。这种观念其后由梭罗等人继承,并发展成一种浪漫主义生态学,通过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朴素的、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到19 世纪,达尔文在提出自然进化论的同时,亦强调自然是一个活的生物共同体,并且自然永远都是人类最终的家和亲族。不论从何种角度看,自然界并不是一个与人类隔绝的、可以时时去观光的邻国一样的独立王国,而是一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统一体,是一个人类必须毫无保留地予以依靠的、相互联系的、极易受到干扰的系统[1]。因此,一种新伦理观逐渐出现,人类开始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复杂联系的世界,其中的万物相互依存,受制于自然规则。人类不过是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并不优于其他物种。
作为达尔文的追随者,怀特海认识到“将世界视为一个具有相互关联历程的网络,而我们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我们所有的选择和行动都影响着我们周围的世界。”[2]因此,从历程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过往仅关注自身喜好与经济利益的利己主义是“狭隘肤浅的”,而科学对自然界展开的分析既是简单化的,也是不顾及全局的,导致的是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
由于此前对自然资源的恣意掠夺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大自然在进入20 世纪后开始显现出其祛魅的一面,尘暴、洪水以及人工合成药剂导致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在经历了各种生态灾难后,为了使物质和能量的富有生机的循环尽可能迅速、有效和永无止境,人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并研究以生态健康为中心的生存之道,尝试唤醒大众的生态意识[3]。由此,集体性的生态运动逐渐出现在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一书中提出,思想是文化传统的产物。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只会诞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克莱门茨的顶级群落理论也只会出现于美国中部平原地区。1976 年,曾任环境保护组织高山协会主席的麦克洛斯基指出:“在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经济组织方面,真正需要一场革命。因为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追求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知识。”[4]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万物都是生物共同体的成员,而所有的生命都有生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二、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到生命共同体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自然生态体系中的所有存在者都可被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发生关联并相互依存。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就意味着生存在其中的每个个体彼此都需要共享能量收入。即便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明显。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消费在工业文明的刺激下不断攀升,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这也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但在生态美学的视角下,人与自然之间本应是一种相互依赖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消费者与商品库存的二元对立。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自然资源是可耗尽的。因此,为了保护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人们必须抵抗大众认知中根深蒂固的经济增长优先论。面对当下的生态困境,人类必须用一种新的思考与行动方式,重塑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模式。约瑟夫·克鲁奇指出:“我们不仅一定要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而且也一定要作为整个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仅与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国人和我们的文明社会具有某种形式的同一性,而且我们也应对自然的和人为的共同体一道给予某种尊敬。一个虽非感伤的,但却无情的事实是:除非我们与除我们之外的其他生物共享这个地球,否则我们将不能长期生存下去。”[5]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认知转型,在威廉·莫顿·惠勒等诸多学者身上有所体现。从20 世纪初始,他们在作品中不仅对人类赖以生存却又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表示担忧,还对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傲慢狂妄态度与行为模式提出警告。从1948 年起,小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接连出版《我们被劫夺的星球》《地球极限》,并制作保护濒危物以及水资源的相关影片。1962年,雷切尔·卡森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书中通过大量的理性科学分析,批判了人类为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控制和管理自然的自我毁灭式生产模式,促使公众重新审视环境污染问题。1979 年,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一书中,对彼时资本主义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模式和人们滥用土地的文化传统对大平原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查尔斯·埃尔顿在70 年代出版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人类自身生存境遇的担忧:“在优先经济生产,特别是在田地上大量生产商品作物的情况下,人类环境本身可能会逐步变得暗淡而单调,并且还被当作是一座工厂而不是生活的地方。”[6]
生态美学之父利奥波德从他的大地伦理出发,设想出一种“生态共同体”,尝试重构一种更贴近人类情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存状态。正如利奥波德所述,“聪明工匠的首要预防措施,就是保存每一只齿轮和轮子。”[7]为了使这种共同体理论获得必要的合理性,必须在生态学外找到其理论支撑的来源。而生态美学可以让人类转变对自然的审美态度,正视生态系统,从而让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从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中摆脱出来,寻找一条智慧的共生道路——即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有机物之间的关系,从只有一方获得生存利益的偏利共生,到走向协同合作的互利共生。
结语
在人类步入21 世纪的最近二十年中,自然的境况与怀特海以及唐纳德·沃斯特的时代相比早已呈现出新的面貌。人类不仅在社会、经济、科学等层面发生诸多改变,对自然界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与之前相比,如今的世界处在更加动荡的变化氛围中。在这种时代境遇下,生态系统的发展状况更加频繁地受到人与自然相处模式的影响,为了实现二者和谐共生的目标,人们必须从审美认知的转型开始,改变曾以技术与经济为中心的自我毁灭式发展的思想,重新审视人类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与自然世界中发生的各种变化相匹配的程度。鉴于这种对立场认知的转变,为了实现从二元对立的经济发展模式到多元共生的动态平衡,人类必须从对待自然的狭隘经济学立场中跳出来,以一种生态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自然,尊重生态自身的存在法则与完整性。当代生态美学的目标之一,就在于建立一种新的观念模式,即应从价值体系的高度保持各种变化的多样性,从而形成符合当下时代的行为模式。唯有从保存生态多元性的审美角度出发,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们才能与周边环境共同形成能够抵抗不利生存变化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从自然中与其他有机体共同获取各自所需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