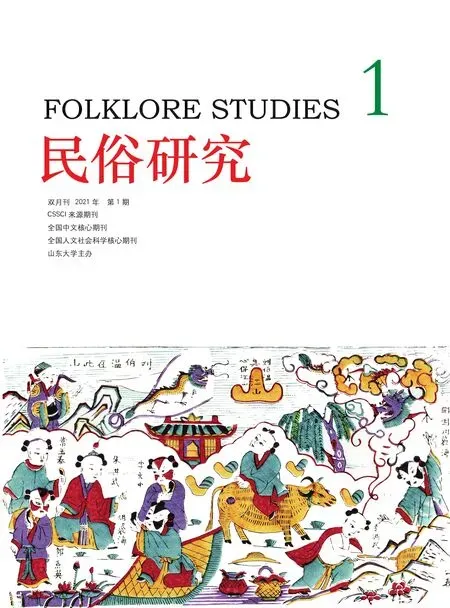美国民俗学的实践理论
——兼论西蒙·布朗纳的有关阐释
2021-11-27鞠熙许茜
鞠 熙 许 茜
2020年暑假,因COVID-19肆虐全球,原定于2020年春季来访中国的西蒙·布朗纳(Simon J. Bronner)、安东尼·布切泰利(Anthony B. Buccitelli)和张举文三位教授,只得线上授课,于7月至8月间为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带来十余场精彩的演讲。此外,又于9月分别举办了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公开讲座,吸引了数千名受众。其中,布朗纳教授的课程包括五个主题:世界民俗学史,美国民俗与民俗学史,实践理论及其方法,传统的概念,物质文化与遗产。在每期讲授中,布朗纳教授始终强调中美民俗实践的对比,他在YouTube、Bilibili等各大视频网站中寻找并观察中国民俗的影像,不断对照自己的美国民俗研究经验,试图了解当下的中国民俗实践,也反思同类主题的美国民俗背后有怎样不同的心理与认知逻辑。本文侧重论述其讲座的主要思想内容,并对讲座简要评述,特别介绍了他对中国民俗实践的理解与研究设想,希望有助于国内学者对实践概念的探讨。
一、北美的民俗与民间生活研究:历史、问题及其国际联系
作为对权力等级与社会、技术变迁的回应乃至挑战,关于民俗与民俗生活的学问很早就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发展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回顾学术史,不仅是对民俗学学术史本身展开分析,更是将其视为分析当下民俗的工具。布朗纳曾对美国民俗学史做过细致研究(1)Simon J. Bronner, American Folklore Studie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6.,在本次讲座中,他更强调从世界联系的角度去回顾美国民俗学的历程。世界民俗学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古俗与古物研究时期,诗论、自然主义与民族主义时期,以及工业化、殖民主义与现代化时期。三个阶段基本上对应于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中世纪、1520-1820年左右的中世纪后期至现代早期,以及1820-1960年代的维多利亚到现代晚期这三个历史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非截然分开、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之间交叉重叠的。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人们已经产生了对古代、古人和古物的兴趣。公元之初的古罗马人常常讨论过去的风俗(custom)与民情(mores),他们经常思考诸如“为什么古希腊的英雄们生平如此类似”一类的问题,并由此出发做了很多神话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中世纪的盎格鲁-萨克逊语中,已经有了folctar(大部分人的知识)与boclar(书本知识)的区别,这表明作为“民众知识”的Folk-lore这一概念已现雏形。公元9世纪左右,随着全球旅行时代的来临,诸如《一千零一夜》《马可波罗游记》等作品让欧洲人的目光狂热地聚焦于他者的风俗习惯上,而正是对他者的认识启发了欧洲人重新理解自己的传统。随后兴盛一时的《圣经》起源研究、《吉尔伽美什》等史诗的研究、中世纪民间歌谣研究,乃至包括马克思·缪勒(Max Muller)对吠陀文献的研究等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现代民俗学一般将自己的创始人追溯至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作为一位自然主义哲学家,赫尔德强调自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他的民族诗学(volkspoesie)理论指出,只有贴近土地的农民,才能体现自然的精神,才是民族精神的底层。(2)参见[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格林兄弟的故事搜集与比较语言学研究,也应该放在这一思潮背景下去考虑。格林兄弟所搜集整理的童话有七个不同版本,他们直到1819年之后才开始重视故事异文,这段民俗学的早期历史深刻地反映出了民俗学者之于民俗的反作用。(3)参见张举文:《一位改变英语世界对格林兄弟童话认识的学者:杰克·齐普斯》,《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随着工业化与殖民主义的推进,民俗学研究进入了文化进化论与传播论的时代。这一时代中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民俗学者约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Jacobs,1854-1916),他提出了“我们就是民众”(We are the folk)的想法,并引入了民之能动性的概念,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阿兰·邓迪斯对民俗的概念界定。
总之,在古典时代,民俗被视为历史文本,主要用于文化哲学的发现。随着科学的发展,启蒙时代对宗教信仰与地方性差异问题的追问,为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然而随后而来的殖民时代使民俗成为“原始”的同义词,民俗学在这一时期与民族主义和自然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二战结束后,文化被媒介化,新的语境生成了新的意义,在当下时代中,民俗学也在日常生活研究与遗产保护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
早期美国民俗学沿用了欧洲民俗传统研究模式,但正如前文所说,欧洲民俗学诞生于自然哲学,以农民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当时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不存在像欧洲那样历史悠久的“过去的民俗”,也没有一定规模的均质化的族群,甚至因为没有许多的接壤国家而几乎没有“边疆”。这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它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边界不断扩张,居民的族群、人种、宗教和语言有可观的多样性,东部地区自耕农放弃土地后迅速城镇化。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尚在,与此同时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又在新大陆上形成飞地。布朗纳注意到,美国民俗学以“乡土”(vernacular)为关键词,正是因为乡土性是美国的基本气质。当时的美国也是未来导向的国家,相信自己就是“天选之地”,承担着人类未来的使命。最初的美国民俗学从搜集牛仔歌曲开始,因为他们相信牛仔是美国精神的代表。
与西部牛仔相比,美国东部显然更具欧洲特点。但这里的欧洲移民并不满足于怀念遥远的故土,而是创造出了大量新的美国符号,以构建新的美国认同。例如当时出现的菜品“中国杂烩”(Chinese chop suey),这是一种中国食材的大杂烩,但却是美国特有的食物,随后成为美国独特的民间饮食象征。类似的例子还有“山姆大叔”的形象。在大航海时代,美洲新大陆被想象成印第安公主的样子,然而随着美国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完成,代表美国革命的“山姆大叔”成为了新生的美国民族符号。美国民俗学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第一代美国民俗学家例如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用folk来定义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对他来说,folk指的是另一个族群,而不是普通人。(4)参见Roger Williams, A Key into the Language of America.London: Printed by Gregory Dexter, 1643.亨利·罗威·斯古尔克拉夫特(Henry Rowe Schoolcraft)致力于搜集印第安人神话,认为这就是民俗。(5)参见Henry Rowe Schoolcraft, The Literary Voyager, Sault Ste. Marie,1827. Henry Rowe Schoolcraft, Algic Researches, Comprising Inquiries Respecting the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First Series: Indian Tales and Legend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839.类似的还有约翰·范尼·瓦斯顿(John Fanning Watson),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搜集土著人的传奇与神奇故事,并把这些知识称为“传统知识”(traditionary lore)。(6)Simon J. Bronner,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Folklore to the Humanities”, Humanities,2018 7(1), pp.10.1879年,美国民族学办公室(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成立,这是一个政府机构,旨在组织搜集民俗。1888年,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简称AFS)成立,其目标是研究正在迅速消失的遗留物,如英国古俗、黑奴民俗、印第安人部落、墨西哥人习俗,等等。1891年,芝加哥国际民俗学会(Chicago Folklore Society)成立,这是一个旨在用国际比较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组织。与AFS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强调要研究现代的、工业时代的民俗知识。
在布朗纳的著作《美国民俗研究:学术的历史》(7)Simon J. Bronner, American Folklore Studie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6.中,他将美国民俗学史分为三个阶段。不过,他在本次系列讲座中指出还应再加上第四个阶段——超级时代(Hyper Era)。
第一个阶段是寻根时代,早期的民俗学家们走到山林与大地的深处,搜索被隐藏的过去,发现美国的先辈及其特征。来到美国的英国学者们钟爱阿帕拉契亚山的歌谣与工艺,认为这些歌谣与故事更能代表英国文化,是在当时的英国已经听不到的古老回响。黑人蓝调音乐也兴起于这一时期,一种属于非裔美国人的传统被建构起来。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民俗学特点的作品是查尔斯·斯金纳(Charles M. Skinner)的作品《我们自己土地的神话与传说》。(8)Charles M. Skinner, Myths and Legends of Our Own Land.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J.P. Lippincott Company, 1896.在这部作品中,土地被理解为联系起所有美国人的纽带,来自大地上的民俗与故事就是美国得以成立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民俗研究的专业化时代。一百多年来美国努力构建新国家新民俗,到了1930年代大萧条来临,美国进入了普通人与草根文化的时代。联邦政府大量参与和组织民俗的记录与研究,这促进了专业民俗研究的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各种民俗学理论争相发展起来,例如与地区主义有关的文化传播与融合论,使用民族志方法对身体性与微观功能主义的描写,对跨国文化与流行文化的研究等。布朗纳在讲座中总结到,当时在美国民俗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有三个问题。一是美国是否有一个共同文化。作为移民国家的民俗,究竟是民族国家的,还是移植而来的;是分隔的欧洲文化的一部分,还是以个人主义为起点的新文化。二是美国民俗的多样性。由于美国的流动性、宗教性与个人主义,美国民俗的差异性巨大,多样的大众历史与大众文化更加剧了这一图景的复杂程度。三是美国与世界的联系。美国是例外吗?还是说,美国正是在跨国联系中才形成的?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末的技术时代,此时交流、移动、技术与个人艺术成为了关键词。结构主义、记忆理论与口头程式理论渐次兴起,它们关注秩序、象征性、结构与模式,并主要形成两种研究路径。一是认知与语境的研究路径,例如象征主义、符号互动论等,它们强调符号、投射与框架(frame)等概念。二是后结构主义、表演理论与主位研究的路径,这一类方法更强调关注个体经验与交流过程。也正是在此时,邓迪斯从更小、更灵活的角度重新定义了民俗群体,他认为两个或以上利用民俗获得认同的人就构成了“民”,这一方面将例如握手等身体语言、物质文化纳入了“俗”的范畴,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语境的重要性。这一定义对布朗纳的实践民俗学有直接启发。例如,邓迪斯研究现代办公室语境中出现的漫画,这类在大众媒体上流传的作品本来不属于民俗研究的范畴,但它其实来源于一个更久远的传统,被广泛复制且有各类变体。透过这些“异文”间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办公室漫画背后的象征含义。邓迪斯发现,现代复制技术如传真机并没有取代民俗,反而促进了民俗的传播。(9)Alan Dundes, Interpreting Folklo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布朗纳本人对吓唬美国儿童的睡前故事Boogieman的研究,就很明显沿用并发展了邓迪斯的思路。(10)Simon J. Bronner, “Rethinking the Boogieman: A Praxe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on, Form, and Cognition of a Troubling Folk Character”, In Simon J. Bronner, The Practice of Folklore: Eassays Toward a Theory of Traditi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9, pp.120-158.
第四个阶段,当然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超级时代,数字文化与实践理论的兴起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越来越多的民俗以媒体和移动网络为载体,其传播非常迅速,以至于形成某种“超级社会”(Hyper Society)。原来界定民俗的“小群体”“面对面”等特征不再适用,大量传统以被发明的、被管理和被组织的面貌出现,例如青少年群体中层出不穷的新民俗现象和现代民间艺术运动的兴起。新的、个性化的,同时又充满民俗风格的艺术作品为我们提出了关于手工、能动性、行动与物质性等多方面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日常生活与遗产研究的转向,使得旅游、可持续性、乡土性(vernacular)、家庭与个人的民俗等问题日益成为焦点。民俗学不仅探讨“旧”,也更强调去探讨“新”。传统不仅是“旧”的、需要保护的,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同时也是“新”的,即不断面对新的问题、处理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接受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改造。
总之,由于缺少世代连续的祖先谱系,美国民俗学基于其新大陆的特征而发展出不同于欧洲式民族国家的国家民俗学(National Folklore)传统。对于美国而言,民俗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争的关键,美国的社会与历史也将民俗学引向了强调主位与个体的发展道路。然而数字化与全球化的推进为这一学术传统带来巨大挑战,这迫使美国民俗学反思自己的历史,并促进了实践民俗学理论的兴起。
二、布朗纳与民俗学实践理论的提出
西蒙·布朗纳的实践民俗学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史脉络中产生出来的。
布朗纳于1981年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哈里斯堡分校美国研究与民俗研究杰出教授,该校美国研究博士生专业创始人;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教授,曾长期在莱顿大学、大阪大学和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指导过几代有影响力的民俗学生,2013至2014年期间任美国民俗学会(AFS)会长。他广博的知识和大量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研究涉及有关犹太人和儿童的民俗,物质文化和男性气概,校园传统和互联网民俗等话题。著有《民俗学基础》《美国民俗研究:学术的历史》《阐释传统:现代文化中的民俗行为》《遵从传统:美国文化话语中的民俗》《民俗实践》等几十部专著和大量民俗学研究论文。(11)Simon J.Bronner, Folklore: The Bas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American Folklore Studie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6;Explaining Traditions: Folk Behavior in Modern Culture.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1;Following Tradition: Folklore in the Discourse of American Culture.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The Practice of Folklore.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9.编著包括《美国民俗生活百科全书》四卷本、《美国青年文化百科全书》两卷本,以及《宾州德裔历史和文化百科全书》《阿兰·邓迪斯论文集》《拉夫加多·赫恩文集》等多部。
在美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理论流派曾给民俗下过不同的定义。早期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与进化论的民俗学认为,民俗是过去的知识;传播论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学者将民俗视为文本,只是在传播与迁移过程中附加了地域和时间信息;文学与语言路径的研究者关注文类(genre),将民俗视为一种不用书写的独特文学;而功能主义和民族志的学者则将民俗视为社会的产物,认为民俗源自集体且从根本上是为了回应集体的需要;以阿兰·邓迪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学派民俗学家,认为民俗是思想的投射,有一定的模式性,可以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并进行比较;后结构主义与表演学派的学者则相信民俗仅仅是独特情境下的个人体验,不具有可比性,并有意将“传统”概念从民俗研究中排斥出去,认为民俗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艺术性交际如何在特定时空内以特定方式发生。布朗纳早年受欧洲民族志和民俗生活研究范式影响,关注物质文化和社区生活。(12)参见“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imon J. Bronner”, Journal of Ethnology and Folkloristics,11 (2), 2017, pp.137-143.他认为表演的研究路径仅仅能说明单一性或突现性,而实践研究路径意味着民俗行为的总体性与优先性,在民俗与民间生活的研究中有着更广泛的解释力。(13)[美]西蒙·布朗纳(Simon J. Bronner):《民俗和民间生活研究中的实践理论》,龙晓添译,《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4期。他提出,民俗活动中最重要的是重复性的、身体化的、可变的以及可传承的行动、姿势与做法,即实践。基于此,他提出了新的以实践为中心的民俗定义。
以实践为中心重新定义民俗,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阐释“传统”。布朗纳强调,民俗不等于传统,但它的确是传统的重复与变异。因此,故事不再是文本,而是“故事化”(storying),物不再是器物,而是“物质化”(materializing)。传统进入了过程与行为,就形成了民俗。以实践为中心的民俗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将文类的表达视为行为。故事、物品、仪式、姿态都不是静态事象,而是过程。第二,民俗与习惯、惯例和表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习惯与惯例少有象征性价值的参与,而表演具有高度风格化的特征,这与以传统为核心的民俗并不完全相同。第三,民俗是知行合一的产物,也是象征化、仪式化的实践。第四,民俗是群体、个人、情景与日常生活得以被解释的框架。行为研究显示,我们每天约有40%的日常行为是重复性的动作,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传统化与象征性的,民俗学的任务就是弄清楚这些重复性行为在怎样的框架下得以执行,以及它们对于行动主体在特殊情境下的意义。第五,作为行动基础的缄默的(tacit)传统知识与人的能动性。人们的民俗行为必须基于某种知识,但这些知识常常是缄默的,因此民俗学的另一个任务是要追问我们行为的知识源头,并辨认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模式。与此同时,人们也不是在单纯地服从传统,而总能通过调用能动性来选择何时何地以及如何选择性地利用传统。民俗学要理解生活的神秘之处,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我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如何做出的选择,以及我们在怎样的情境下出于何种目的做出了选择。
根据布朗纳阐释的实践理论,民俗就是从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知识又被应用到实践中去,这意味着它始终与传承有关,通过模仿、吸收、潜移默化而起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实践民俗,但通常只有当一些行为看上去与流行文化相悖时,其中的传统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因为民俗是文化的传承过程,是长时间的、一贯的,它是我们今天行动的依据,构成对某些外来强制力量的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学的实践理论恰恰对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现代性理论提出了质疑——传统不是能动性的反面,而是能动性的来源。民俗学的实践理论也与布尔迪厄(P. Bourdieu)和奥特纳(Sherry Ortner)等人类学家的实践理论不同,后者关注特定社会中的规则如何出现,而民俗学者更偏向于从精神与思想层面追问传统何以成为传统。在讲座中,有听众提到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问题,布朗纳强调,马克思注意到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控制自然和生产工具来控制工人,葛兰西(Gramsci Antonio)进一步指出,国家控制的关键一步就是控制文化、斩断传统、操控民俗。这一想法在福柯的思想中也有体现。民俗学的实践研究,必须关注知识的规训与制度的秩序如何与人的民俗实践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实践论正是实践民俗学的重要知识来源。
我们相信,布朗纳所提出的民俗学实践理论可以用于很多方面的研究,既可以用于理解日常生活中重复的仪式性行为,也可以从文化发展性技能的角度理解叙述与玩耍。小到人们如何打招呼与道别,如何哄孩子睡觉,如何许愿与祝福,大到“Black Lives Matter”这类社会运动、地区经济的规划与发展、博物馆与遗产管理、学校教育等等各种现象,民俗学者都可以从实践的角度去思考民俗如何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框架,如何唤起并调用那些最基本的形式与行动。
三、传统与传统知识:朝向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心意(Mind)理论
对布朗纳而言,实践理论的核心关键词是传统。民俗学的目标之一是要总结出一套理论,以解释究竟是什么激发、活化与生产了传统。研究现代性社会的心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者们常常预测传统会随着现代化而消失,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所以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要保持传统?在什么情境下人们会需要传统?这一部分也是布朗纳此次讲座的重点内容,以下,本文将从“我们为什么需要传统”“传统的特性”“传统的类型”“传统与遗产”“传统的心意理论”五个方面来总结和介绍他的观点。
我们为什么需要传统?布朗纳认为这可能有四方面的原因。首先,传统是语素,所有的创新、发明、现代性与权力都与传统的具体表达有关。这正像如果没有语素,就没有言辞一样。其次,在社交过程中,人们需要利用传统来相互聚集并建立认同,这也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如果没有群体,是否还存在传统?再次,传统是民俗生活得以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不仅与记忆有关,还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最后,心理学与认知理论认为,传统帮助人们建立起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机制,例如避讳、算命、禁忌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传统的特性是“便利”(handiness,也可理解为“顺手”)。传统(tradition)一词来源于罗马传统中的“贸易”(tradere)。交易与交换诞生于人与人的直接接触之中,由此才产生了传统。几乎所有的传统都伴随着有形的、可触摸的文化经验,而“手”正是这种文化经验的象征。在民俗观念、实践及其传承中,“手”的象征意味总是与“脑”相对而言,如果我们说某些事情是脑力活动的,隐含意思就是它不需要动手做,没有交易,也不是技艺。手,就是做的象征。而“顺手”意味着利用现有的资源与框架,这是一个传承与创造相互交织的过程,是在因循守旧的基础上极为灵活且便利地进行改造,以适应当下的具体情境。即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总是包含着身体行动与物质感知的部分,这就进入到感知民俗学与身体知识的研究领域。在社会交往中,人们的“接触”动作可以建立社会,也可以表达思想,甚至可以建构宗教——想想教皇为何用手触摸信众,再想想中国酒宴中人们划拳行酒令的举动。
传统可以分为八个类型。第一,最基本的是指传递有价值之物的时间性过程,这与它的罗马语源“交易”有关。第二,物之传递的空间性或表演性过程,例如笑话的传播,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类型。第三,统称非制度性的知识,尤其是大量的、智慧的公共知识。第四,与某一文化群体相关的指导性原则。例如表示自己的时候用手指自己的鼻子还是指胸口,等待的时候是“亚洲蹲”还是坐在地上,在不同文化人群中有不同的原则。第五,倾向于重复某些行为的个体。当我们说某些人很传统,往往是因为他们重复某些东西,例如古老的歌曲或谚语。第六,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中规定的标准、形象、规范或理想。第七,某种思维模式或思想体系。第八,有时也被视为对抗进步与现代性的消极范畴。
第四个方面是传统知识与遗产概念。传统知识是学习的结果,传承、模仿、演示、习俗与参与,都是传递知识的手段。例如参加某一个节日,就是在学习某一类传统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传统一定是地方性的或者原始的,这绝对是个误解。我们从身体活动与生命历程的发展中,习得各种行为方式与观念,这些行为与观念反映同时也塑造了我们的宇宙观与世界观。要注意的是,传统与遗产有关系,但并不是同一回事。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我们事实上是在谈论我们自己的集体记忆和对过去的想象。它不一定符合事实,不一定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所调用的传统,而更多的是我们对过去的言说。
从心理与认知的角度看传统,布朗纳再次强调,传统是创造、创新与改变的基础和原点,因为“过去”是权威的来源,传统就意味着选择的可能性。传统能给面临选择的人们提供舒适与稳定的感觉,在讲座中,布朗纳举了一个中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一位女性讲述着几千年前埋在这里的皇帝神话,但在村庄辽阔的大地上看不出任何远古村庄的线索,一切景物与人的生活都处于急剧变化之中。然而当地女性还坚持讲述传统的故事,这使得这片土地在她们眼中与过去建立起联系,仿佛在动荡不安中找到了连续性的支点。当然,除了口头讲述或仪式表演,传统也可以是社会性的一般知识与主动的身体参与。在紧急事态下,传统还是某种象征意义的投射以及表现许可的框架,例如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大家举着的“武汉加油”的牌子常常使用红色,这种颜色的象征含义在此处就意味着唤起某种记忆、情绪,并表达对某种行为框架的许可。
四、物质文化与文化景观:将物质研究融入非物质遗产与传统知识
前文提到,即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总是包含着身体行动与物质感知的部分。那么,对景观和物质的理解如何能帮助我们了解传统知识与民俗生活呢?
物质文化由那些被跨越时空地制造、塑造、更改与使用的事物组成,这也是民俗学实践研究的重点。布朗纳强调,物质文化是物品被织入个人与群体日常生活的方式。“织入”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文本(text)这个词本身就与纺织(textile)有关,人们在纺织过程中将不同的部分联接在一起,才能最终完成一件作品。(14)关于物质文化与民俗生活的详细讨论,参见Simon J. Bronner, Grasping Things: Folk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Society in Americ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5.它强调其过程性,而不仅仅是结果,这是这一概念优于“文化遗产”概念的地方。布朗纳曾在《抓紧事物》一书中详细讨论了物质文化与民俗生活的问题(15)Simon J. Bronner, Grasping Things: Folk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Society in Americ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5.,在本次讲座中,他高度凝练并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将民俗物质文化的概念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在表述层面上,民俗物质文化代表了那些通过非正规方式——如模仿、演示、习俗、口耳相传等——习得的传统技能,即“民俗性的”(folkloric)。在社会层面上,正是那些民俗物质文化使得某个传统社区的生活方式被具象化,例如我们认为美国的亚米什(Amish)人是传统社区,正是因为他们的民俗物质文化呈现出过去的特征。在言辞与象征的层面上,民俗物质文化指那些凸显或者被感知为传统性的形式、形象与设计,即传统的表象。传统和这些表象的关系,正如同语言学中语素与言辞的关系,语素本来就带有一定意义,当它们在特定语境下以特定方式被使用时,就成了言辞。民俗物质文化就是传统(语素)的言辞,举个例子,中国传统如果是语素的话,开封的犹太人教堂中所呈现的中国传统,就是民俗物质文化。民俗物质文化可以有建筑、工艺品、服饰、饮食、医药等不同文类,与民间故事不同的是,这些文类通常都包括形式、建造与使用的习俗(实践)等几个方面。物品的实用功能当然是首要的,这包括生计、社会、心理、情感等各种用途,但装饰部分也很重要,因为它们往往具有象征含义。我们可以用比较的、历史地理的、感觉的以及生态的等各种方法去研究它们。
民俗景观指的是经由人们的活动与居住所形塑的景观,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是复数的,但始终都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复杂系统中的一部分。民俗景观与民族志景观不完全相同,后者是被某一人群所定义的遗产资源,例如那些带有宗教神圣意味、纪念性或家园感的场所,这些场所往往与特定的行为相联系。要注意的是,景观也是行动者,它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形塑人们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被保存和保护的“古迹”或“遗产地”。
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都曾聚焦于物质文化和景观,然而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和他们不尽相同。民俗学者关心的是文化之间的关联,关心传统如何被用于交流与实践,尤其是器物和空间发挥能动作用的实践。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就是分析房屋与景观中如何体现出民俗观念,布朗纳指出,这正是他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开端。
从物质的视角看一栋房屋,我们会注意到它的结构、对称及实用性等特征,而从秩序的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房屋轴对称的形态正是人身体的表达,它是由家庭单元所定义的另一种人类身体形式。以四合院为例,这种严密地将人的身体包围起来的样式,是一种经典的建筑形态。人们在四合院里控制花草树木,也就是控制自然,而与此同时房子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容易面临危险,因此针对房屋建造的仪式多样且常见。对美国人来说,院子是更令人着迷的建筑部件,它代表着农场、财富,也意味着对英式贵族庄园和草坪的模仿,是对房屋主人阶级地位的公开展示。观察房屋的细节及其演变历史,我们就能分析出人们隐藏于物质背后的认知语法。类似的研究可以推广到各个方面,从园林、博物馆,到药房、餐厅、烹饪,到风靡全球的李子柒的视频。
总之,布朗纳总结道,要理解实践中的传统,绝不能割裂物质与非物质。当民俗学者谈论“物质文化”时,我们事实上强调的是那些被物质化和象征化了的观念、信仰与世界观。物品如此,景观也是如此,它们都同时是文化与自然的造物。
五、中美民俗实践的比较与讨论
从布朗纳的讲座中我们可以看出,实践的解析往往意味着行为模式的比较性理解,因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识别实践的关键特征及其模式,进而理解行为模式背后的认知特征。正如他在文章中强调的,从实践的角度去看民俗,欧洲和亚洲可能比过去学者们原以为的更接近美国。(16)参见Simon J. Bronner, The Practice of Folklore.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9, pp.64.和他的写作比起来,布朗纳在北师大的系列演讲强调中美民俗实践的比较,大量使用了中国案例,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不断讨论、互动与相互启发也催生了新的想法,推进了他对美国民俗的思考。对中美案例比较与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的实践研究方法,也可以为中国民俗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美国民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移民的创造,事实上,美国第一部城市民俗学的研究就是以费城华裔为对象。(17)参见Stewart Culin,“China in America: a Study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the Eastern C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ad befor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ection of Anthropology), at the thirty-sixth meeting, New York, 1887., Philadelphia,1887.作者斯图尔德·库林(Stewart Culin)记录了费城华裔的烹饪、药物,特别是他们的游戏与独特的社会结构,这些民俗中的很多今天依然存在。这项研究对AFS费城分支影响巨大,此后城市民俗的研究就成为AFS的重要取向。但中国民俗在美国的流变(或者反过来)并不是中美比较的关键,布朗纳更强调的是在当下的时空格局下,处于大洋彼岸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他所举的例子可以大概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中美都有但实践逻辑却大相径庭的民俗。布朗纳多次举到的木雕就是一个典型。木雕是布朗纳博士论文的主题,当时他关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木雕者,这些人致力于用一整根木条雕刻出整条木质锁链,并且不会重复制作同一种式样。布朗纳的研究表明,这一地区的木质锁链雕刻民俗有六大模式。第一,制作者都为男性,尚未发现女性制作者。男人们用简单的刀具制作这些手工艺品,不需要复杂的技术与工具。第二,这些制作者们来自德国移民社区,通常成长于乡村,从小就学会了制作木锁链,但成年后在工厂工作,很长时间远离了这门手艺。直到上了年纪之后,他们才重新开始雕刻。第三,制作者们都是老年男性,绝大多数是从乡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工业地区居住。第四,木锁链不是为了销售,而主要是为了赠送给朋友或年轻人。第五,木雕几乎不上色,制作者希望能保持木头天然的颜色。第六,制作与赠送的过程中常常伴随一些固定的语言表达程式,例如,“我猜你肯定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出这个的”。以此为开头,话语交流得以开启,而在此种框架之下进行的交流,总是与力量和能动性有关,即:即便是一位老人也是有力量、值得关注的。(18)Simon J. Bronner, The Carver’s Art: Crafting Meaning from Wood.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6.在中国,类似这种木雕的工艺品也非常常见,例如福建软木画与同心套球“鬼工球”。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中餐馆都用软木画来创造一种“中国氛围”,这似乎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东西。但软木画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矛盾性,即制作者所追求的东西和实际成品之间有矛盾。制作者追求雕刻的逼真,然而成品却刻意保留原木的颜色,表明它与“逼真”之间的距离;木料本来是3D形态,制作者却偏偏先将其处理为2D后再雕刻,然后再以层叠的方式造成3D的视觉效果。既然如此,为何不一开始就保留木料的3D性呢?布朗纳认为,这也许是因为中国木雕刻意追求向内看(look inward)的视角所致,这一点在鬼工球的雕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锁链雕刻的技术诀窍,在于从木料的外部入手,切去不需要的多余部分,它呈现出一种向外看(look outward)的外向型特征。而鬼工球却需要不同的视角,这让布朗纳觉得它们虽然都是雕刻,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俗实践。鬼工球的技法要求制作者在雕刻之处,首先设计好最内层的图案与技法,虽然雕刻的实际过程从外向内,但思考方式却是由内至外的。这似乎正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与道德化特征,即行为实践以内省式精神为导向。例如《老子》所说的,“当其无,有室之用”“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空”与修身的思想一脉相承,表现在雕刻鬼工球和软木画上,就体现为雕刻的过程本身是自我反省与自我对话的过程,这与印第安纳州男性雕刻锁链主要为了社会交流和展示力量的心理相当不同。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跳皮筋游戏,在美国最多只有一两个人参加,然而中国的跳皮筋却通常是多人游戏,有时甚至能达到8人乃至10人以上。如果说美国的跳皮筋本质上是与音乐歌谣配合的个人舞蹈的话,中国儿童的跳皮筋玩法更多,规则可简单可复杂,更像是一种社交与集体活动的实践。中国和西方都有墓园,但西方墓碑上没有逝者的照片,按照《圣经》的观念,逝者的灵魂看到自己的形象还在人间就无法上天堂。但照片在中国墓碑上却很常见,这反映出与灵魂(soul)不同的精神观念。
第二种,中国有而美国没有的民俗。典型例如孝道的观念与实践,这一观念在西方很少见。虽然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孝道观念不如以前强,但在遍布城乡的民俗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观念的表现。例如中国人喜欢吃“团圆饭”、客厅里挂着“全家福”,这些民俗所传达出来的世系观念,与美国的家庭观是根本不同的。最令布朗纳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祖孙文化。美国民俗学研究通常将老幼之间的跨文化差异视为理所当然,然而中国的“隔代亲”现象却可能提供反例。在统计上,中国有大量孙辈与祖辈共同居住,祖辈在孙辈的成长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哺育与陪伴角色,至少比西方(包括日本)的数量大得多。那么,在美国研究中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流动”概念,即思想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过程,是否在中国出现了“跳跃”的现象?例如练习毛笔字的行为。习得书法作为缄默(tacit)的传统知识,伴随着身体的运动而传承某种基础性的文化气质,通常是由比父母更老的长辈传授给孙辈的。幼年时期日复一日练习书写汉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祖孙之间的相处与知识流动,会给中国民俗带来怎样的深刻影响?
另外一种美国没有的中国民俗,是儿童游戏“老鹰捉小鸡”。儿童游戏本身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但即使是同一个游戏,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会呈现不同的样貌。例如布朗纳关注的“捉迷藏”游戏全世界都有,但美国孩子们玩捉迷藏时,“鬼”(美国孩子称之为it)是弱势的,是被戏弄的对象,孩子们笑着分散远离它,没有人愿意当那个“鬼”。而在德国的捉迷藏游戏中,“鬼”是强势的,孩子们更倾向于服从它的权力而不是反抗它。布朗纳认为,对几乎全世界的儿童而言,捉迷藏也许是他们最早接触到的同辈间组织性的游戏,儿童从这一游戏中学到了关于社会组织的最初经验,正是经由这类民俗游戏,人被社会化了。如果说美国的捉迷藏游戏更有个人主义倾向,孩子们在游戏中被鼓励成为独立的个体,并且去挑战带有危险性和控制欲的“鬼”(父母的隐喻),那么德国的游戏则是教会了孩子们权威的概念与服从的必要。(19)Simon J. Bronner, American Children’s Folklore. Little Rock: August House Publishers, 1988, pp.175-198.同学们在讨论中补充到,与之相比,中国的捉迷藏游戏更为复杂、多样化,更具有仪式性,甚至“鬼”的这个名称本身根据地域的不同也有不同说法。并且中国孩子最初体验的社会化游戏可能并不是捉迷藏,而是“老鹰捉小鸡”。这种在中国极为普遍的儿童游戏,能够让更小的孩子参与进来,通常由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玩儿,但却基本不见于欧洲与美国。与“捉迷藏”比起来,“老鹰捉小鸡”更强调集体精神,一群小鸡在母鸡的带领和保护之下共同对抗老鹰,这种集体性的思考方式在孩子们年幼时就被灌输给个人,而通过这些跑动、尖叫、欢笑的身体性行动,群体与集体的重要性被深深烙印在儿童的“身体知识”(bodylore)或“身体民俗”之中。
张举文教授在总结布朗纳的系列讲座时曾强调,讲座的基调是如何理解传统、实践与物质。国内民俗学界对这些问题已有很好的讨论,但在具体方法论上却尚感欠缺。本文认为,中国作为拥有几千年传统的民俗实践之国,也同时正在经历高速社会化与超社会化的过程,布朗纳所提供的系列工具概念与关系性的视角,或许会对我们的研究构成很好的补充。他所强调的以实践与传统为核心的民俗学研究,与当下中国关于实践民俗学的讨论可以在多个方面交流讨论。他虽然从未来过中国,但对中国民俗强烈的好奇心与“局外人”的视角,也为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并找到新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启发。从这两方面意义上说,实践民俗学在中美之间的合作与比较研究,或许正是起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