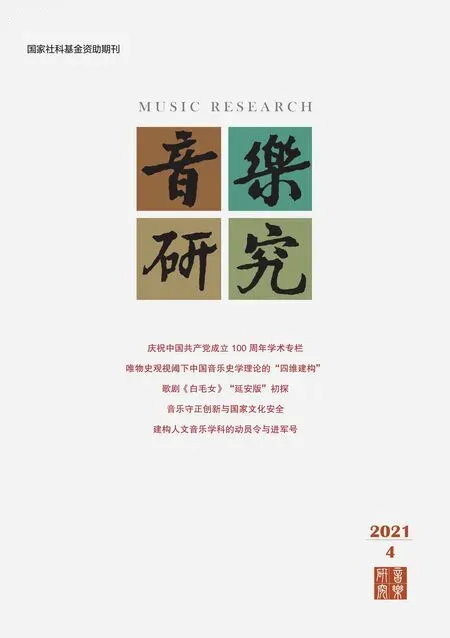早期红色歌谣在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
2021-11-27于晓晶
文◎于晓晶
早期红色歌谣,特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苏区)歌曲(以下简称“红军及其根据地歌曲”)。这些红色歌谣基本上是填词歌曲,其曲调主要来自各革命根据地(苏区)的民间音乐(主要是民歌)、中国近代军歌、学堂乐歌、苏俄革命歌曲,以及当时中国的城市歌舞音乐。正因为红色歌谣为填词歌曲而非原创歌曲,并具有集体创作的特点,所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口头传播中,其词曲逐渐出现了差异和讹误。当这种词曲上的差异和讹误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曲意义就发生了变化,进而带来了革命叙事重构,即口头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这种“重构”是用音乐谱写的土地革命战争史,是“互文性”前提下的土地革命叙事,它使红色歌谣成为土地革命战争的文化记忆。
一、口头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
口头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缘于红色歌谣在口头传播中的词曲变化。在通常情况下,词曲变化是渐变、细微的。然而,如果在口头传播中发生了较大的词曲变化,甚至有的词曲变得面目全非,以致演变成为另一首歌曲,展露出新的内涵和意义,那么,这就发生了革命叙事重构。口头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由红色歌谣在口头传播中逐渐产生的差异和讹误①关于早期红色歌谣传播中曲调的差异和讹误及其原因,参见李诗原《苏区歌谣民歌式传播中的差异及其解读——音乐学术研究的反思和探讨(五)》,《音乐艺术》2020 年第1 期。所致,是红色歌谣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及其根据地歌咏活动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现象;它既是红色音乐在口头传播时代的必然结果,又体现出红军及其根据地革命斗争对红色音乐发展与传播的影响。
(一)从《红军歌》到《我们的旗帜插遍天下》《瞄准放》
在中央红军及其中央革命根据地广泛传播的《红军歌》,是一首填词歌曲,其音调来自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红军歌曲《红军最强大》。②石磊《中国军歌初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 页。它最先在中央根据地和湘赣根据地传播。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歌》,最早见刊于《青年实话》第6 期(1931 年12月22 日)。湘赣根据地的《红军歌》,可见“永新石印本”中的版本,该石印本的具体出版时间不详,笔者推测应不会早于1931年8 月。③出版时间大致在1931 年8 月后,因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石印局成立于1931 年8 月。参见注①。这首《红军歌》究竟由何人,在何时、何地根据苏联红军歌曲《红军最强大》填词并带入红军及其根据地,尚待考证。从现有史料可知,《红军歌》在红军其他战斗序列及其根据地都有传播。由于《红军歌》的音调来自苏联,是一首和声小调的歌曲,其中还有弱拍起唱的切分节奏,所以比较难唱。也因为如此,《红军歌》在红军及其根据地都被“唱走了样”:从曲调上看,不仅与《红军最强大》有出入,还与中央根据地和湘赣根据地的《红军歌》有所不同;从歌词上看,各个根据地的版本都不一样。这一现象即是“口头传播中的差异与讹误”。尽管上述《青年实话》和“永新石印本”中的《红军歌》在刊登和印刻前经过了整理,但其中的差异与讹误也难以掩盖。口头传播的《红军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演化出不同的版本,有中央根据地的《我们的旗帜插遍天下》、川陕根据地的《红军歌(一)》、川滇黔根据地的《瞄准放》。这三首歌曲都来自《红军歌》,但其曲调与原曲出入过大,歌词也有所不同,而演化成了新的文本。这些新文本与《红军歌》原歌词的内容和思想主题已有很大不同,产生了革命叙事重构。
以湘赣根据地的《红军歌》为比较原本。其歌词是:
同志们快快拿起枪,我们是工农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要创造人民的新世界。敌人发抖了,奋勇地向前冲!我们是无敌的红军,拼热血头颅,把革命完成,这是我们神圣的战争。
与之相比,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歌》没有大的变化,仅是“要创造人民的新世界”变为“我们是苏维埃新世界”,“这是我们神圣的战争”变为“这是世界最后的战争”。由此可见,湘赣根据地的《红军歌》与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歌》在词曲上虽稍有出入,但属同一个版本,未造成革命叙事重构。
比较起来,《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则是由《红军歌》衍生出来的另一个文本。④《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载《中央苏区歌曲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90 页。该歌集中同时载有中央根据地传唱的《红军歌》(第286 页),说明《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与《红军歌》已成为两首歌曲。其歌词为:
同志们快快起来拿着枪,要创造苏维埃共和邦,敌人发作了,奋勇向前冲!(杀)杀向旧世界,建立苏维埃!(杀)霹雳啪,霹雳啪。勇敢冲,勇敢杀,杀向旧世界,建立苏维埃,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
显然,这首歌的意义已与《红军歌》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红军歌》是一首宣示中国工农红军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则是歌唱苏维埃政权的歌曲,对于《红军歌》而言就是革命叙事重构。《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的曲调虽不乏《红军歌》或《红军最强大》的影子,但其中赣南民歌的旋法也十分明显,这无疑是原曲调在口头传播中不断被“异文化”所“改造”的结果,可以被认定为“另一首歌曲”。这种曲调上的变化也使新文本的叙事得到进一步强化。
《红军歌(一)》的曲调,与两地《红军歌》乃至《红军最强大》都有很大的出入,歌词更是有所不同:
同志们快快起来拿起枪,与压迫者做一殊战,我们是被压迫的人类解放者,无产阶级革命军将人类一切寄生虫消灭,到那时新社会实现。我们是工农阶级的武装,要打倒那黑暗的权威,我们是被压迫的人类解放者,无产阶级革命军将人类一切寄生虫消灭,到那时新社会实现。⑤《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7 年版,第597 页。
虽然《红军歌(一)》的歌名没有变,但歌词的思想内容却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我们是被压迫的人类解放者,无产阶级革命军将人类一切寄生虫消灭,到那时新社会实现”,已明显变成一首旨在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歌曲。与《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一样,其歌词并非重新填词而成,而是在口头传播中不知不觉逐渐演变的结果,其中也不乏其他革命歌曲(如《国际歌》)歌词的“掺入”。
《瞄准放》⑥董有刚主编《川滇黔边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07——208 页。是中央红军长征所留在该地区的《红军歌》的衍生品,是口头传播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新文本。《瞄准放》与中央根据地《红军歌》的曲调已判若两曲,⑦参见注①,第178——179 页。歌词前半部分基本相同,后半部分则有明显差异。尤其是原曲“拼热血头颅”变为“冰雪的道路”,显然是口头传播中因发音相似而产生的讹传。这反映出口头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并不一定是有人刻意为之,而是自然产生的差异和讹误所致。
(二)从《土地革命歌》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型于1935 年秋冬的陕北,其前身是红四方面军及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歌》(或《土地革命快要成功了》)。《土地革命歌》则来自冯玉祥部军歌《民族立宪歌》⑧谭恒功、黄彦如《冯玉祥军歌选》,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22——23 页。,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的编歌者利用《民族立宪歌》的曲调重新填词而成;⑨这首歌曲即川陕根据地的《红军十大纪律歌》,参见《中央苏区歌曲集》,第605——606 页。它大致产生于1932 年12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根据地之前。编歌者不仅保留了《民族立宪歌》的歌词结构(“九字句”),还保留了原歌词中的一些词句或表述,采取一种置换的填词方式。由于《民族立宪歌》是一首立军规的歌曲,《土地革命歌》承袭了它的性质,一开始便是一首纪律歌曲。
在1934 年9 月程子华从中央根据地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前,在中央根据地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没有完整传达到红四方面军及其鄂豫皖根据地。因此,《土地革命歌》作为一首纪律歌曲,并没有完全反映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红军通用纪律的内容,而是在传播中歌词内容不断演变,发生了革命叙事重构。早期(1932 年12 月前)的《土地革命歌》,首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传唱到川陕根据地,并在口头传播中产生了《红军战士歌》。《红军战士歌》歌词与《土地革命歌》《民族立宪歌》相近,填词方式均是一种保持歌词结构的置换。⑩参见《中央苏区歌曲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15——616 页。
如果说《土地革命歌》还在极大程度上依托于《民族立宪歌》,那么,《红军战士歌》的思想内容与《民族立宪歌》已有一些差异。《红军战士歌》较之于《土地革命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重构。1932 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后,红25 军留守鄂豫皖,于是《土地革命歌》继续在鄂豫皖根据地传唱。1934 年9 月,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并向红25 军传达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红25 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于1934 年9——10 月,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套用《土地革命歌》的音调和歌词结构,编写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程坦一边编写,一边让部队战士试唱。1934 年11 月,红25 军撤出鄂豫皖开始长征。当红25 军1935 年12 月到达鄂豫陕边,一首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老红军吴高升唱,李民仆、张发机、喻文贤、景春芳、陈淑琴记录)就产生了。⑪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歌谣三百首》(1985 年内部印刷),第406——407 页。
显然,这首鄂豫陕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相对于《土地革命歌》而言,体现了叙事重构。1935 年9 月,红25 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完整内容传到了红十五军团。程坦根据完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修订了鄂豫陕根据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于是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⑫参见《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年版,第25 页。。
二、现代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
现代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色歌谣出版和革命历史题材歌舞创演中的革命叙事重构。如果说口头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那么,现代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则是刻意为之的。
出版中的革命叙事重构,源自编辑都对红色歌谣在出版前的整理和修订。一般说来,这种整理和修订的前提是保证红色歌谣的完整性及其艺术性,同时也保证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歌谣中革命叙事的完整性、真实性和逻辑性,最终旨在确保红色歌谣作为革命叙事表现和讴歌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土地革命旗帜、掀起土地革命风暴这一不朽功绩的有效性。
革命历史题材歌舞创演中的革命叙事重构,主要是创作者在利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歌谣进行创演时,忽视这些歌谣原有的生成语境和历史背景,将其移花接木式地用于歌舞剧中的其他历史场景,并赋予这些歌谣以新的历史内涵。在创演过程中,这些曲目的词曲得到了修改,甚至是重新修正、编创曲调,重新编订、填写歌词。不难发现,这种革命历史题材歌舞创演中的革命叙事重构,无疑也是为了使这种革命历史题材歌舞能表现和讴歌土地革命战争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歌谣,作为一种具有一定真实性的历史文本,就成为歌舞中用来表现革命历史的原始文本。
(一)红色歌谣编辑出版中的革命叙事重构
在20 世纪50 年代的红色歌谣整理出版中,这种革命叙事重构就已体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成立《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这是第一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及其根据地歌曲集,1954 年由该编辑部内部印刷,195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歌曲集共收录了208 首歌曲,成为早期红色歌谣在新中国传播的重要媒体。208 首歌曲是从全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区搜集到的,主要来自革命根据地(苏区)当年印刷的油印本、石印本及各种报刊资料,也有一些来自老红军和根据地民众的珍藏和口述资料。这本歌曲集在出版前得到了修订、整理和编辑,使一些曲目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内容有了较大的提升,由此发生了“革命叙事重构”。
例如,在《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中,《国际歌》署名“鲍狄尔词,狄盖特曲,萧三译”。但实际上,这首《国际歌》唱词既不是1923 年6 月15 日瞿秋白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版本,⑬《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共产国际号”),1923 年6 月15 日出版(广州),第155——156 页。也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及其根据地传唱的《国际歌》歌词。因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及其根据地广泛传播的《国际歌》,是萧三和陈乔年1923年夏根据瞿秋白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版本重新编订的。⑭关于萧三、陈乔年1923 年在苏联修订瞿秋白译配的《国际歌》的情况,参见萧三《〈国际歌〉歌词的修改说明》,载《萧三诗文集》(译文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 年版,第16 页。将湘鄂赣根据地传唱的《国际歌》⑮《湘鄂赣苏区革命歌曲戏剧选编》,武汉出版社2013 年版,第1——2 页。与《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中的《国际歌》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变化。湘鄂赣版《国际歌》第一段歌词中的“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在《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中变成了“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与“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是有区别的,不仅在于“新社会”与“天下”的不同,更在于“是”与“要做”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一般现在时,表明“已经是”,后者则是一般将来时,表明尚不是“天下的主人”。还有,湘鄂赣版《国际歌》第二段歌词中的“要杀尽那些强盗狗命,就要有牺牲精神”,在《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中变成了“要争取平等自由幸福,要消灭剥削压迫”。二者意义完全不同,而且“平等自由幸福”“消灭剥削压迫”也是新中国的提法。总之,《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中的《国际歌》,是在新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修订出来的,时代的烙印较为明显。从思想内容和表述的政治性而言,1962 年版《国际歌》的歌词改动,就明显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口吻和要求,故其中的革命叙事重构毋庸置疑。⑯关于《国际歌》在汉译中的革命叙事重构,参见邓科《冲突中的革命歌曲翻译——以〈国际歌〉汉译为个案》(The Translation of Revolutionary Song into Conflicts:A Case Study of Translating “The Internationale”into Chinese),西南大学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英文版)。
(二)革命历史题材歌舞创演中的革命叙事重构
革命历史题材歌舞剧创演中的革命叙事重构,以1961 年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 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所用的两首歌曲为例展开分析。
1.《八月桂花遍地开》
原名《庆祝工农政府歌》,产生于1929年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29 年12 月25 日,鄂豫皖红军第11 军第32 师攻占河南省商城县,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为庆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地“双河班”班主王霁初与陈世鸿(苏维埃政府下设的文化机构“红日社”总编辑)编创了《庆祝工农政府歌》。歌词由陈世鸿编写,曲调由王霁初根据当地流传的民间曲调《八段锦》改编。歌曲完成后,吴靖宇(时任商城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县文化委员会主任、“红日社”社长)对歌词进行了修改,使《庆祝工农政府歌》⑰同注⑪,第110 页。最终定型。在《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中,《庆祝工农政府歌》置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部分。
在1961 年创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庆祝工农政府歌》被作为中央根据地革命歌曲来运用。在该剧表现土地革命战争一节中,《庆祝工农政府歌》被改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并用一种载歌载舞的形式,表现1931 年11 月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的成立,歌词还有“活捉张辉瓒、打垮罗卓英,消灭白匪百万兵”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等内容。⑱参见舞台艺术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八一电影制片厂1963 年。
在1964 年创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这首用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再一次用来表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的成立。很显然,这里用“八月桂花”象征全国各地建立的根据地,“遍地开”则是形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普遍建立。
从表现一个县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庆祝工农政府歌》,到表现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体现出革命叙事的重构。也正因为如此,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成为一首江西革命民歌。在197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中,《八月桂花遍地开》注明“革命民歌,江西省文化组整理、改编”⑲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编《战地新歌》第三集,第19 页。,在197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建军五十周年歌曲集》中,《八月桂花遍地开》则注明“江西民歌,焕之编曲”。
2.《十送红军》
1961 年,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在创演《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时,为了表现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与人民群众的依依惜别之情,选用了一首江西革命民歌《十送红军》。这首歌曲由“朱正本、张士燮收集整理”,来源于多首江西革命民歌(也包括传统民歌),甚至还有说是来自赣南采茶戏中的《长歌》。孙伟认为,这首歌曲是描写井冈山根据地民众1929 年1 月送别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开赴赣南闽西的情景,而不是描写中央根据地民众1934 年10 月送别中央红军长征的情景。⑳孙伟《〈十送红军〉的历史真相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2 期,第35——37 页。笔者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各战斗序列及其根据地都有送别红军的歌曲,这首《十送红军》的曲调来自江西是无疑的,但其歌词内容也吸取了各根据地送别红军的革命歌谣内容,甚至还有民间音乐表现送别的歌曲内容。这首《十送红军》如今已承载了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前根据地民众送别红军的革命叙事,因此,其创编就建构了中央根据地民众送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的革命叙事。
三、革命叙事重构的意义
早期红色歌谣在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是红色音乐传播中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但又是长期以来一个未能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及其根据地的红色音乐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几乎都是填词歌曲,传播方式均为口头传播,传播途径限于根据地(苏区)的群众性歌咏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红色歌谣的编创和传播都具有类似民歌的性质。口头传播中的差异和缺陷,和类似民歌的无明确作者的特征,都为红色歌谣在后来传播中的词曲改写提供了空间。于是,革命叙事重构就成为传播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在现今的红色歌谣传播中,革命叙事重构也较为普遍。任何一种历史叙事在传播中都会出现“重构”现象。
本文所谓的早期红色歌谣“革命叙事重构”,实质就在于早期红色歌谣歌词题材内容和思想主题的重构,即红色歌谣在歌词内容上的变化。换言之,歌词改写带来了歌曲题材内容和思想主题的变化,最终使歌曲所承载的革命叙事不同于原曲所承载的革命叙事。
革命叙事重构是一种在总体上尊重革命历史的改写,并未发生思想主题上的颠覆;它是一种基于革命历史的叙事重构,而不是脱离革命历史的叙事重构。这是早期红色歌谣在传播中革命叙事重构的基本性质定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口头传播中,这些改写和重构是自然而然的,是无意识的。在后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现代传播中的改写,则出于一种旨在满足政治宣传需要和艺术表现需要的理性思考,其目的是保持革命叙事的完整性,并使红色歌谣具有一种思想高度,进而保持其在政治宣传中的有效性,增强和提升革命历史题材歌舞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这种革命叙事重构具有基于政治宣传和艺术创作的合理性。
红色歌谣在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口头传播中,革命叙事重构从客观上使红色歌谣在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宣传和军事斗争中的作用发挥得更为充分,或者说使其宣传作用最大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的现代传播中,革命叙事重构也旨在使早期红色歌谣更能满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因此,如果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口头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提升了音乐在政治宣传的地位和意义,并显示出音乐的不可替代性;那么现代传播中的革命叙事重构,则使土地革命战争史呈现为一部为红色歌谣谱写的革命历史,使红色歌谣作为土地革命战争的文化记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