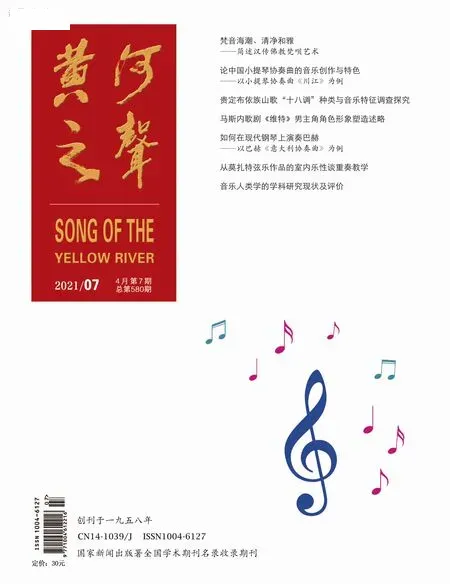非遗视野下临县伞头秧歌的文化生态学研究
2021-11-26索美超
索美超
伞头秧歌是广泛流传在山西西北临县、离石、柳林、方山等吕梁地区的民间歌舞艺术,因起源和盛行于临县,故称临县伞头秧歌。其发端可追溯至古代的祭歌和民间的迎神赛会活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演化形成今天临县伞头秧歌的歌舞样态。2008年临县伞头秧歌被列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成为关注的热点,为其保护、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国务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明确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可见,临县伞头秧歌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在临县传衍已久,并且它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伞头秧歌在临县源起并可以长足发展,是与临县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因此,本文从非遗的视角出发,对作为非遗的临县伞头秧歌进行文化生态学研究,揭示文化生态对其源起和发展的影响,为当下临县伞头秧歌的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可行的策略和路径。“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2]临县伞头秧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源起、发展和演变受到该地域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的共同影响。
一、作为非遗临县伞头秧歌依存的自然环境
某种文化现象的形成与其依存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存在着极其多种多样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又都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产生着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3]临县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是临县伞头秧歌源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临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黄河中游,东依吕梁山,北靠兴县,南接离石、柳林,地形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地表梁峁相连、沟壑纵横。因地处高山沟壑,土地凹凸不平,群众日常耕作、行走时上下颠颤的定性动作对临县伞头秧歌“走”“扭”“摆”的动作语言特征有着重要影响。其脚下动作以秧歌典型的十字步、扭走步、进三撤一步、进二扭两步等走为特点的步伐为主,上身动作则以腰部的扭和手臂的摆动为基本动态,如伞头的夹臂扭走步,楞女子的秧歌步等。因此,在伞头秧歌主要表演形式“过街”“大场子”“小场子”中都以走贯穿始终,身体以扭、摆为典型动态。临县地理坐标处于中纬度,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受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影响,降水少、蒸发量大,河流受季风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水量随降水变化不稳定。因此,受气候和水文影响,临县干旱缺水的气候条件使得临县伞头秧歌行使着祭神求雨的重要功能,这是其源起和盛行的尤为重要因素。
临县伞头秧歌依存的地理环境从古至今变化较小。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们作用于自然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出行劳作从原来的人力、畜力转化为机械化,科学地作用于土地。即使面对干旱少雨的年份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得以缓解。因此,临县伞头秧歌的源起受到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无论其功能还是动作语言的定型都打着自然地理的烙印。由于社会变革,人作用于自然的能力增强,依懒性减弱,自然环境对伞头秧歌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小,其祭神祈雨的功能逐渐褪去,但历经人民的代代传承,尤其是2008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的国家干预政策,其舞蹈语言更为丰富,功能亦更为多元。
二、作为非遗临县伞头秧歌社会文化的变迁
临县伞头秧歌,除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外,社会文化对其源起和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更为明显和直接。自古至今,社会更替,文化演进,是普遍的规律,而这些意识形态无不作用于当时的艺术形式。农耕文化、晋商文化、宗教文化,抗战时期的政治环境,当代社会的科技发展等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都体现在临县伞头秧歌的发展演变中。
(一)古代临县社会文化对伞头秧歌的影响
1、农耕文化作用下的神灵崇拜
临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地表被厚厚的黄土覆盖,土质疏松,易于耕种,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区。因此,“面朝黄土背靠天”的农民靠天时地利的农业生产维持生计。而在古代蒙昧时期,由于人对自然缺乏科学的认识,认为风、雨、土地、河流、山川等自然现象都由神灵主宰,从而产生了神灵崇拜意识。每当遇到干旱年份,或者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人民都要通过表演伞头秧歌载歌载舞以酬神娱神,与神灵对话,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如伞头秧歌唱词所言:“风神爷爷显一显灵,行雨离不开你铺云,你老家倚住半扇扇门,千万不要叫起黄尘。”临县伞头秧歌这种祭神的仪式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仍非常流行,“每年秧歌队出场的第一天,均需由伞头率领装扮好身子的秧歌队首先到村外祭祀‘田神’、‘风神’‘雨神’、‘河神’以及大大小小的庙宇,意即祈求神灵保佑人畜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4]从临县伞头秧歌表演的场图“闷葫芦”“蒜辫子”“三盏灯”“蜘蛛结网”“南瓜蔓”“十朵莲花”等图案中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农民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中抽象总结而来,是农耕文化的显著体现。
2、道教文化的渗透
临县毗邻北方道教圣地北武当山,全县还有宝珠山道观、九凤庵道观、真武庙等道教场所,民间道徒众多,道教信仰普遍。临县伞头秧歌受道教影响,在表演场图和道具中融合了许多道教文化元素。临县伞头秧歌中“大场子”和“小场子”的许多场图是从道教仪式中演化而来。如“八卦阵”“四门斗底”“八仙过海”“天地牌”“蛇盘九颗蛋”等图案是从道家“转道场”祭祀活动中的借鉴而来,而“转道场”是由寺庙中道士做道场时的“转九曲”演化而来。另外,临县伞头秧歌中的道具虎衬,直径约14厘米,是由金属制成的中空圆环,里面装有铁珠,摇动时发出哗啦的响声。作为指挥队伍的号令,虎衬是由道士所用的法器响铃变化而来。两者的声音极为形似,并且都是为了模仿风雨之声,具有通神祈雨的功能。
3、晋商文化的推动
明清至民国时期,临县晋商贸易繁荣,推动了伞头秧歌的发展。临县碛口镇是商贸重镇,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位于黄河中游拐角处,是河运连接陆路的枢纽。据《临县志》记载:“在京包铁路未建之前的170多年间,每日有五十余只木船往来于碛口码头,大批粮、油、皮毛、盐碱、药材等杂货,自陕甘绥蒙等地源源运载而来,棉布、绸缎、茶叶、陶瓷、烟酒、火柴、粉条等物品,自太原、汾州等地由陆路驮运至碛口,转销于大西北。”[5]正是因为碛口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文化在临县交流碰撞,丰富了伞头秧歌的形式和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晋商贸易的繁荣为伞头秧歌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据临县伞头秧歌老艺人口述,碛口镇作为晋商的聚集地商贾众多,每当遇到喜事或庆典活动他们就会重金邀请伞头秧歌队表演,甚至还会打赏,秧歌队就会用积累的资金扩大队伍、置办行头,从而推动了临县伞头秧歌的发展。
(二)抗战语境下临县伞头秧歌的畸变
吕梁作为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中心区域和首府所在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号召,文艺成为当时宣传抗战、团结群众的重要手段。在这一历史时期,延安派出了许多文艺骨干力量来到抗战根据地吕梁山一带,对影响较大的民间舞蹈进行改造和加工以更好的服务战争的政治需要,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这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易于传播的伞头秧歌成为了改造的对象,其表演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容上,取消了宣扬封建迷信和丑化人民的部分,改为批判懒汉、歌颂领袖、党和人民,以及宣传抗日、民主等;形式上,取消祭神拜庙,改为拜国旗、领袖和英烈,秧歌队中增加了工农兵形象等。[6]由此可见,临县伞头秧歌在抗战语境之下,受政治力量的干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畸变。
(三)当代临县伞头秧歌社会文化的变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进入了工业化信息化文明,人民的科学意识增强,封建迷信思想破除。农民作用于土地的方式由原来的人力、畜力转向机械化、科学化,人与土地的关系渐渐疏离。在此语境之下,临县伞头秧歌褪去了古代神灵崇拜的色彩,褪去了最初酬神娱神、通神祈雨的功能,而转向节日欢庆的娱乐狂欢和文化交流传播的艺术载体。
1、民俗景观的节日欢庆
一年一度的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仪式性节日,也是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民俗节日,而临县伞头秧歌作为一种普遍的民俗景观,在元宵节前后竞相上演,成为人们春节节日仪式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春节是农民在一年劳动过后,身心放松,表达愉悦之情的重要节日,而载歌载舞的临县伞头秧歌成为了民众节日欢庆的表达方式。伞头秧歌在街头和广场表演,分为过街、大场子和小场子三种形式,一支秧歌队人数不等,多则二三百人甚至几百人起舞,少则七八十人。秧歌队由乐队、彩旗、门旗开路,中间穿插有小会子表演,龙舞、狮舞、腰鼓等收尾,锣鼓喧天、气氛热烈。伞头负责指挥队伍、调动演员情绪,带领队伍走出各种队形,并即兴编词演唱来歌颂美好生活等内容,赢得阵阵喝彩。在场的民众紧随秧歌队浩浩荡荡,甚至一起舞动,构成了节日欢庆的壮丽景观。作为非遗的临县伞头秧歌不但承载着历史的文化记忆,亦随着时代变化而推陈出新,并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展现着现代人的精神风貌以及国家和人民日新月异的新变化,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互动下的一种文化景观显现,而这种文化景观深入人心,便强化了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成为了地域文化的象征符号和集体意识。
2、民俗文化的交流传播
当代临县伞头秧歌起到了交流传播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作为吕梁临县民俗文化、山西文化的代表参加各种文化交流传播活动,不仅弘扬了山西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体现着山西民众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上世纪九十年代,临县伞头秧歌参加了沈阳国际民间舞蹈邀请赛、北京第九届龙潭杯全国优秀民间花会大赛、郑州国际公园文艺等。2008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临县伞头秧歌成为山西民俗文化的象征和标志。2011年临县建起了“秧歌文化广场”,这为临县伞头秧歌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场所,进一步推动了伞头秧歌的发展和普及。2020年11月7日至8日,临县伞头秧歌《喜庆丰收年》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精彩亮相。作为山西参与进博会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其不但用特色浓郁的山西民间舞蹈形式歌颂党和国家,展现了农民生活的新变化,而且把优秀的山西文化、黄河文化呈现世界各国观众,起到了重要的交流传播的功能。
三、非遗视野下临县伞头秧歌的文化生态保护
临县伞头秧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中,不断吸收其它艺术养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成为山西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优秀代表。当下,随着其文化生态的变化,作为非遗的临县伞头秧歌角色减少,内容和形式异化,演出匮乏,正面临着生存危机,亟需抢救和保护。针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尤其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7]对于临县伞头秧歌的传承和保护,既需要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手段进行学习使其后继有人,也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等具体措施进行干预,保存其成果和形式,但从根本上来看,传承和保护临县伞头秧歌最为有效的途径是保护它赖以生存不断发展的文化生态,使其与民众的生活真正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葆有其持续的生命力。
为此,应该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对临县伞头秧歌的文化生态保护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积极努力。第一,临县伞头秧歌承载着当地民众对平安、健康、长寿、丰收等美好愿景的信仰,尊重民众追求美好事物的信仰,并使其葆有这种信仰,是其存续的文化思想基础。第二,作为非遗临县伞头秧歌是山西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扶持临县伞头秧歌非遗工程建设,让传承临县伞头秧歌的老艺人及村民以此为谋生手段。第三,临县伞头秧歌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承载着临县的文化特色,与临县旅游文化相结合,建设“临县伞头秧歌活态历史博物馆”,形成旅游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使游客在游览观光之余欣赏纯正的伞头秧歌表演,同时也可以作为村民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第四,积极推进临县伞头秧歌的产业化发展。一是地方艺术院团对临县伞头秧歌的发展和创新,使其进入市场之中;二是打造临县伞头秧歌舞台精品和演出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临县伞头秧歌真正与人民的生活联结在一起,在人们的生计中发挥重要作用,才能在当代焕发出新的价值。
结 语
临县伞头秧歌是在临县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下,农耕文化作用下的产物,并受到宗教文化、晋商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临县伞头秧歌不仅体现着临县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文化生态,并随着文化生态的改变而变化,而且反映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临县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面貌,体现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目前,临县伞头秧歌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文化信仰、主体身份、活动空间等文化生态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民众从古代的神灵崇拜、宗教信仰进入科学时代,农业生产从精耕细作的手工转向产业化、机械化操作。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土地不再是农民唯一的生计方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渐渐疏离。在这种变革之下,临县伞头秧歌不像古代一样,作为人们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民众娱乐的一种手段,节日欢庆的民俗文化,或者地域文化交流传播的载体。加之当下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便捷化、网络化,作为娱乐手段,临县伞头秧歌受到了巨大冲击。因此,面临原初文化生态土壤的脱离和当下娱乐文化的挑战,临县伞头秧歌正在走向衰落甚至面临危机。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临县伞头秧歌如何传承和保护是面临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顺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历史规律,让临县伞头秧歌积极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才能持续发展,永葆活力。一方面作为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活态保护,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元素,积极创新适应新时代人的审美需求,发挥其重要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