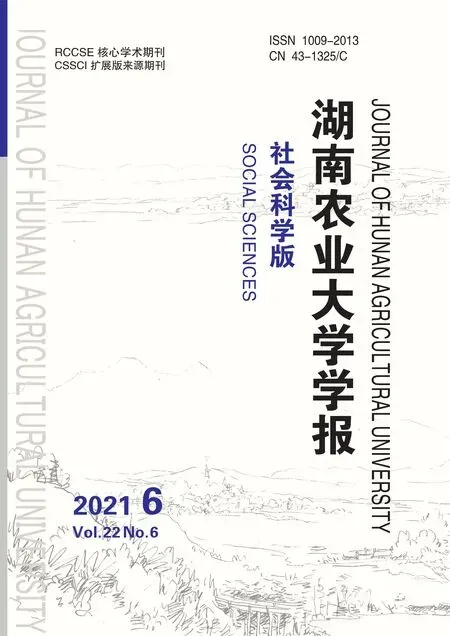我国农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制度问题及其完善
2021-11-26王彬辉叶萍
王彬辉,叶萍
我国农用地污染风险管控制度问题及其完善
王彬辉,叶萍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但这些制度在法律概念、风险管控标准、风险决策、管控沟通以及法律责任竞合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建议进一步明确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法律概念,设定土壤生态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两类风险管制标准,并实现参数本地化,完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决策和沟通交流制度,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农用地土壤质量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农用地土壤污染往往具有隐蔽性、稳定性、被动承受性、不可逆转性等特点,容易引发一系列风险[1]。农用地土壤污染一方面会造成土壤肥力降低、土壤退化,甚至导致地下水污染,威胁生态环境安全,另一方面土壤中的污染物质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构成极大危害。近年来,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农用地土壤污染致害事件频发,造成的损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建立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规范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行为,降低或消除因土壤被污染而产生的人体健康、农产品质量、生态环境安全等潜在危害,已是迫在眉睫。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明确了“风险管控”的土壤污染防治理念,要求“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出发点,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体现了分类管控要求,强调“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实施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治理”。之后,针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是,从具体制度设计来看,已有制度大多是关注工矿污染源监管和治理、重金属污染防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控制等方面。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工矿区污染源风险管控不同,强调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要求加大保护力度,推进安全利用,全面落实严格管控,加强林地草地园地土壤环境管理等,以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
农用地土壤污染对农业生产与发展形成了严重阻碍,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非常迫切,学界对此开展了广泛研究。蔡美芳等[2]指出应将污染农用地的修复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结合起来,以食品安全效益作为综合治理的首要目标。王伟等[3]认为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严重,专门立法应坚持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遵循污染防治规律,设计具体法律制度以实现农用地可持续利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双重目标。胡静[4]分析了农用地的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提出责任主体种类及对个人责任方面修改完善的建议。上述研究主要围绕农用地土壤污染来源调查与累积、土壤重金属污染与风险评价、农用地土壤污染修复与安全利用,对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性研究较少。农用地土壤污染的严重性以及土壤修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导致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十分紧迫,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概念界定、风险管控标准、风险管控决策沟通机制及相关法律责任追究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鉴此,本文拟在对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建设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一、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现状及其特点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2020年编制的生态环保“十四五”规划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防风险”。对农用地土壤污染进行风险管控,将其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事前严防、事中严管、事后处置的全过程、多层级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范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打好“净土保卫战”的必然要求。经过几年的发展,以风险管控为核心的理念已逐渐显现于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制度构建过程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已初具规模。
1.国家层面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
“土十条”明确了“风险管控”的土壤污染防治理念,其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规,逐步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2017年11月的《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将管控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根据分类管理原则规定了农用地分类管控要求;2018年8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污染防治法》),首次在法律上明确“公众健康风险”“生态风险”的概念,第四章专章还规定了“风险管控和修复”,对农用地分类管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安全利用方案、风险管控措施等进行了具体规定,填补了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法律空白。《土壤污染防治法》将风险管控作为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从“质量管理”进入“风险管控”阶段,表明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已成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核心制度[5]。
《土壤污染防治法》明确授权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并将其定性为强制性标准。2018年8月生态环境部颁布实施的《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以下简称《农用地标准》)属于技术性法律规范,规定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具体内容,为开展农用地分类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6]。该标准针对土壤污染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的关系,划定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创造性地提出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并根据这两个标准值,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进行分类管理。
除上述法律法规外,国家层面还颁布了基于风险的污染场地管理规范体系,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等政策性文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
2.地方层面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
我国环境风险管控工作启动较早的省、市,根据国家层面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及管控制度规范和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政策和技术规范。上海市2016年制定的《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强调源头管控,防止对土壤环境的污染和危害,要求对农用地土壤污染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并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北京市2018年推出的《北京市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规划》分析了北京市土壤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土壤详查结果,按用地类型、污染程度等提出了分类分级管控措施,对重点的污染物超标地区开展控制与防范,探索建立污染地块土壤治理修复全过程风险管控机制,为确保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需的土壤环境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导。江西省2021年颁布的《江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重点关注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两个领域,明确提出加强污染源头控制,防止新增土壤污染;对于已受污染土壤,突出加强土壤的风险管控和修复。迄今为止,除上述省(市)外,浙江、重庆、广东、福建等省(市)均对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做了制度安排。但是,这些地方性政策偏宏观层面管理,没有专门针对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特点进行具体、详细规定,操作性不强,管控效果不佳。
3.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的特点
一是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导向。相较于建设用地等其他地块,农用地与农产品生产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一体的,农用地土壤中的污染物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直接构成危害。因此,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指导思想和目标是“双目标”导向,即保障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以《农用地标准》为例,它是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评价标准的基础与核心,其制定是以保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主要目标,兼顾保护农作物生长和土壤生态的需要[7]。从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角度看,《农用地标准》制定了镉、汞、砷、铅、铬等五种重金属的风险管制值;从保护农作物生长和土壤生态的角度看,除了制定上述五种重金属的风险管制值和风险筛选值外,还规定了铜、锌和镍等三种重金属的风险筛选值。
二是以风险源、暴露途径、风险受体为制度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由风险源、暴露途径和风险受体三要素构成,缺一不可。风险源是威胁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引发危害发生的致险因子,包括污染物排放、固体废弃物尤其是有毒有害物质随意丢弃等。暴露途径是污染物通过水、空气等介质迁移到达人体的方式,一般包括饮食、呼吸吸入等。风险受体是指被污染土壤及其周边环境中可能受到污染物影响的人群或其他生物、地表水、地下水等。我国一般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制度设计。
三是实行全过程风险管控。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包括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风险评价、风险等级确定、分类管控措施、成效评估等环节。全过程风险管控的特点贯穿于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中。以《土壤污染防治法》为例,第二章第12条明确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以强制性标准防止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行为的任意性,第四章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土壤污染责任人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农用地风险管控措施进行了规定,第六章对未履行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相关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体现了“事前严防—事中严管—事后处置”的全过程管控特点。
二、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的问题
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已初步建成,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农用地标准》中。在这两部法律法规中,仍存在着法律概念界定不明确、风险管控标准不完善、风险决策与管控沟通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责任竞合等诸多不足。
1.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法律概念不明确
《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土壤污染定义为“因人为因素导致某种物质进入陆地表层土壤,引起土壤化学、物理、生物等方面特性的改变,影响土壤功能和有效利用,危害公众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基于该定义去延伸理解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存在一定局限,因为,这部法律仅仅强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的人为因素,相对忽视了土壤污染中的自然因素。环境风险作为由“环境”与“风险”组成的复合概念,强调在一定区域或环境单元内,由人为或自然等原因引起的具有潜在损害可能性的情形[8]。引起这种风险产生的原因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特别是我国部分土壤中重金属的天然本底值高的省份,如湖南、江西、云南等,即使没有人为活动,土壤中的重金属超标也会对生态环境或者人体健康带来危害。但从《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土壤污染的界定看,显然是将这类土壤的环境风险、农产品安全风险、公众健康风险防控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这将会直接影响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实施的社会效果。《农用地标准》中虽然明确提出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概念,认为土壤污染风险是指因土壤污染导致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作物生长或土壤生态环境受到不利影响,但概念中的“不利影响”是一个模糊概念,且并没有体现出“风险”应有之义。
2.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不完善
环境标准“是指为了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体健康,对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统一的各种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各种标准的总称”[9]。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控系列标准,包括对污染物以各种形态进入或有可能进入土壤的行为和方式进行管理、控制和预防的标准及其他相关配套标准,如,农用地土壤环境背景值、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农用地土壤生产力和土壤修复值标准、土壤基础环境标准系列等[10]。《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废止后,新颁布的《农用地标准》成为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评价标准的基础与核心。根据《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农用地标准》为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但是,结合理论与实际来看,《农用地标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基本项目风险管制值不全[7]。该标准中的风险筛选值共涉及11个污染物项目,却只制定了镉、汞、砷、铅、铬等5种重金属的风险管制值。实践中进行农用地土壤风险评价及土壤环境质量分类时,如果有铜、镍和六六六、滴滴涕以及苯并【a】芘等含量特别高的特殊情况,则无标可依。二是风险管控标准种类单一。《土壤污染防治法》将环境风险分为生态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两大类,两类风险无论是污染物种类、项目还是敏感受体、毒性参数来源等均具有明显区别。有国家针对两类风险分别设定了两套标准,如,美国环保署发布了旨在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环境风险筛选值》和旨在保护生态安全的《土壤生态筛选导则》[11]。我国《农用地标准》主要从人体健康角度考虑,规定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并没有区分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三是风险管控标准中列出的有机污染物种类少。随着农药、化肥的大量施用,有机物污染已成为目前农用土壤中的重要污染源,但《农用地标准》中仅将六六六和DDT、苯并【a】芘3项的指标列入污染筛选值,这显然是不够的。四是一些重要参数未能实现本土化。因缺乏污染物理化性质参数、不同途径的污染物毒性参数、农用地土壤参数、地下水参数等基本参数,制定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时参考国外权威数据库的参数。在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时不能参考域外参数,需国内的人体暴露参数数据,但我国目前仅体重、皮肤表面积、呼吸速率等参数有全国或典型区的调查数据[12]。
3.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决策与管控沟通机制不健全
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中风险决策与管控沟通机制存在明显缺陷:
首先,决策参与、沟通主体单一。对于技术性强的规范,制定者更倾向于倚重“技术理性”,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形成了“专家理性模式”。而“专家理性模式”却存在着诸如信息不足、独立性不强、规制俘获等问题[13],如,根据《农用地标准》来判断某块农用地是优先保护、安全利用还是严格管控,将直接约束该农用地使用人(不管是土地直接承包人还是土地流转使用人)的使用权限,也会因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影响到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经营者、消费者等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其次,风险决策、管控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参与沟通、监督的权利缺失。《土壤污染防治法》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的义务分配给了行政机关和土壤污染责任人,在风险评估、管控过程中,并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和土壤污染责任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交流义务,也没有赋予利益相关者全过程参与和监督的权利。如,该法第54条规定了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对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地块采取风险管控措施的责任;第55条规定了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地块的土壤污染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安全的,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农村、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制定污染防控方案,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第56条规定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地块的土壤污染责任人有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的义务。上述规定均未明确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正当的利益诉求机会,不利于风险管控措施的具体实施。
4.农用地土壤污染管控存在法律责任竞合
“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与环境风险的特殊属性决定了现代环境法的主要基调:不是要根除产生环境风险的行为或被动防止环境风险,而是要调适可能引起不合理、不可欲危险的风险行为,并尽量公正地分配环境风险。”[14]法律责任的明确是分配环境风险,实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的重要保障,《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六章列举了行为人违反本法所应承担的各种责任情形。但是,相关条文对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界定依然不够清晰具体,且没有与其他环境单行法律法规充分衔接,从而导致了以下两种法律责任竞合问题:
一种情形是因同一行为产生多重危害结果而导致的法律责任竞合。如,土壤污染责任人在土壤风险管控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行为的法律责任竞合。《土壤污染防治法》第40条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进行土壤风险管控与修复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进行处置。也就是说,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应分别适用《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土壤污染防治法》第91条规定了造成二次污染的法律责任。实践中,如果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造成了周边环境的二次污染,应依据何规定进行处罚?于是就产生了法律责任竞合问题。
另一种情形是同一行为触犯多个法律造成的法律责任竞合。如,向农用地排放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清淤底泥、尾矿、矿渣行为的法律责任竞合问题。《土壤污染防治法》第87条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泥,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违法排放上述物质,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需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之前,针对向农用地排放上述三类物质的违法行为,《水污染防治法》第83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68条、《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53条均有明确规定,应该依据哪种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同样出现了法律责任竞合问题。
三、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完善
针对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明确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也是进行法律思维和推理的根本环节[15]。明确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法律概念,是完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法律制度的前提,界定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需先对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进行界定。“风险”是“某种危害发生的可能性或概率以及发生这种风险所造成后果的影响程度”[16],这种风险将有可能导致损害发生,可视为存在“潜在的损害威胁”。鉴此,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可以界定为因土壤污染导致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作物生长或土壤生态环境受到潜在的损害威胁,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所致损害可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法律概念应该明确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目的是降低或消除因农用地土壤污染而产生的人体健康、农产品质量、生态环境安全等潜在风险,有效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其次,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责任主体是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当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存在争议时,由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在两种法定例外情形下,政府是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责任人。第三,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纳入常态化、全过程管理,系统构建事前严防、事中严管、事后处置的全过程、多层级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体系,包括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信息公开和沟通交流、风险管控具体措施的实施等。
2.健全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属于技术性法律规范,是科学技术知识和价值判断的交织[17]。与传统的限值型环境标准直接设定最高允许浓度指标值比较,风险管控型标准能够针对具体地块的背景值、周围环境参数、暴露途径等因素计算土壤污染的风险概率,规定筛选值与管控值,在其与具体的环境危害之间设置“安全距离”。针对现有标准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是应分别从农用地生态安全和农产品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角度考虑,设定两类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标准,即农用地土壤生态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农用地土壤人体健康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
二是增加风险管制项目种类。建议在《农用地标准》中增加基本项目铜、锌或镍的风险管制值;化学农药中有机磷、有机氯对人体和动植物影响较大,风险管控标准中可加入此类有机污染源的风险管控值。同时,兼顾污水灌溉等的影响,增加土壤中硫化物、石油类等指标的风险管控值。
三是尽快实现参数本地化。加强本土化的剂量效应研究与暴露研究,制订我国人体暴露参数手册及环境背景暴露的参考值。地方政府也应加强对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未做规定的项目的探讨研究,制定地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18]。
3.完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决策、管控沟通制度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涉及多个部门的权力、责任,同时也关系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因此,建立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风险沟通制度,可以保障风险决策管控过程的公正性、程序的合法性以及结果的科学性。
首先,建立公平公正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决策框架。当前,基于合作国家的行政法治理念,在国家任务变迁的背景下,公私协力的环境风险治理模式与决策框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9]。构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决策框架,一方面,要建立透明公开、来源广泛、具有较强独立性的风险决策机构,保证利益相关者均等的表达诉求的机会;另一方面,必须规范风险决策程序,以程序的法定、公开增强公信力,以此确保规制活动开放有序,能充分接纳各类信息,又审慎小心地对已有信息仔细权衡、慎重作出政策选择[20]。
其次,要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信息公开。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理的前提是解决利益主体掌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风险的本质在于发生损失与危害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信息的缺乏造成的。当不同主体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高度不对称时,极易导致风险的社会放大,如厦门PX事件出现的“涟漪效应”[21]。所以,加强信息公开是有效治理环境风险的基本要求。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信息应该由地方政府农业、林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依标准联合发布。除了传统的听证会、新闻发布会、信访等发布渠道外,政府还应该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博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媒介,减少与非政府组织、普通大众的信息隔阂。
第三,要确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风险管控协商对话制度,调和“技术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关系。农用地所有权人、农用地承包经营权人、土地流转使用权人以及土地污染风险管控第三方治理方等各方主体通过协商,将各自的利益、立场表达出来,使风险管控决策中设定的风险水平在各自的可接受范围。
4.进一步明确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法律责任
为保障农用地土壤污染管控制度的顺利实施,有必要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包括在责任原则上,针对“严格、连带、溯及既往”的严格规定设置合理的缓冲机制,责任时间界限、责任比例界限[22]等应是风险社会下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法律责任设置的特殊要求。
具体而言,针对同一违法行为多重危害结果导致的责任竞合,建议根据《立法法》“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行政处罚法》中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以及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同一环境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不同环保法规实施行政处罚的复函》中规定的“择一重处罚”原则进行处罚。如土壤污染责任人在土壤风险管控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行为,造成周边除土壤污染外的其他环境要素污染时,依据处罚较重的规定进行处罚。
针对同一违法行为触犯多个法律造成的责任竞合,建议优先适用《土壤污染防治法》。如,向农用地排放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清淤底泥、尾矿、矿渣行为的法律责任竞合问题,建议优先适用《土壤污染防治法》。相对于《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而言,《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新法,相对于《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而言,《土壤污染防治法》法律效力的层级更高。因此,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的行为,应优先适用《土壤污染防治法》第87条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周留鑫.农业土壤污染防治法律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3):17-18.
[2] 蔡美芳,李开明,谢丹平,等.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与防治对策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4(12):223-230.
[3] 王伟,包景岭.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思考[J].环境保护,2017(13):55-58.
[4] 胡静.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谁的责任?[J].中国生态文明,2019(1):48-52.
[5] 张真源.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8.
[6]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解读问答[EB/OL].http://www. nies.org/news/detail.asp? ID=1488.
[7] 袁国军,卢绍辉,梅象信,等.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延伸理解及其评价标准现状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20(2):84-89.
[8] 吴贤静.土壤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J].法商研究,2019(3):140-149.
[9] 韩德培.环境保护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15.
[10] 李敏,李琴,赵丽娜,等.我国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优化研究与建议[J].环境科学研究,2016(12):1799-1810.
[11] DEFRA and The Environment Agency 2002.The contaminated land exposure assecement(CLEA) moded technical basis and algorithms (CLR10)[C].Bristol,UK:R&D Publication CLR r&d Publication Clr 10,2002.
[12] 宋静,陈梦舫,骆永明,等.制订我国污染场地土壤风险筛选值的几点建议[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11(3):26-33.
[13] 李奇伟,秦鹏.城市污染场地风险的公共治理与制度因应[J].中国软科学,2017(3):56-65.
[14] 杜辉,陈德敏.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的进步——以共识性环境伦理的法律化为主线[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32-40,139.
[15] 雷磊.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J].法学研究,2017(4):74-96.
[16] PIDGEON N.Risk analysis,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Report of a royal society study group[J].The Royal Society,1992(6):89-101.
[17] 吴贤静.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的法理重述与制度改良[J].法学评论,2017(4):165-174.
[18] 罗丽.依法治土,还需哪些配套?[J].中国生态文明,2018(6):71-73.
[19] 杜健勋.环境风险治理:国家任务与决策框架[J].时代法学,2019(5):9-14.
[20] 季卫东.依法风险管理论[J].山东社会科学,2011(1):5-11.
[21] 郑石明,吴桃龙.中国环境风险治理转型:动力机制与推进策略[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1-21.
[22] CHURCH T W,NAKAMURA R T.Beyond superfund:Hazardous waste cleanup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J].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1994(7):15-58.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of soil pollu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China
WANG Binhui, YE Ping
(Law School,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oil Pollution have initially established soil pollu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s for agricultural land, but these systems have many deficiencies in legal concepts,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tandards, risk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legal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improvement, it is suggeste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legal concept of soil pollution risk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land, set two risk control standards of soil ecological risk and human health risk, realize parameter localization, improve the decision-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soil pollution risk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further clarify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gricultural land; soil pollu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s
10.13331/j.cnki.jhau(ss).2021.06.011
D922.68;X321
A
1009–2013(2021)06–0090–07
2021-07-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FX145)
王彬辉(1974—),女,湖南双峰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黄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