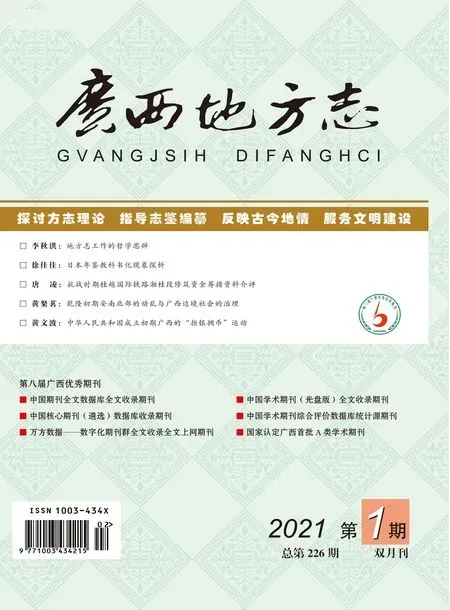乾隆初期安南北部的动乱与广西边境社会的治理
2021-11-26黄粲茗
黄粲茗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乾隆以降中越边境的一系列变化受到安南的影响非常显著,历来被作为透视清代中越关系进程的重要切入视角。①相关研究参见郑永常:《论清乾隆安南之役:道义与现实之间》,《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96年第22期;孙宏年:《清代中越陆路边界桂粤段交涉述论(1644—188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02期;柳岳武:《乾隆时期的安南政策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5期;段红云:《乾隆时期凭祥州、思陵州与安南界务纠纷的处置智慧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4期。在涉及乾嘉时期中越边境相关问题中,大多数学者乐于从国家层面的各种要素进行探究,而有关这些边境纠纷、安南政局形势对广西边境地区产生了何种影响,仍然存在讨论的余地②陈文对1644—1840年中越两国在边境的跨境管理问题的探讨对本文的写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选择的时间跨度较大,讨论的对象又偏重于安南方面,在涉及对广西边境社会影响这一方面的内容还比较缺乏个案的剖析,因此还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参见陈文《清代中越陆地边境跨境问题管理(1644-1840)》,《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01期。。因此,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试图以乾隆初年的安南北部动乱为切入视角,对此问题做出一些探讨。
一、安南土酋韦福琯与高平莫氏后裔的叛乱
明朝嘉靖时期,安南后黎朝的政局陷入动荡,权臣莫登庸篡国,建立莫朝,得到明廷的承认,其被封为安南都统使。但是后黎朝仍有一批流亡在外的君臣,并在安南中部重新建立政权以对抗莫朝,万历时期,后黎朝逐渐强大,而莫氏陷入衰微。“时莫氏渐衰,黎氏复兴,互相构兵,其国益多故。”[1]万历十九年,黎氏击败莫氏,后者退缩至高平一带,黎氏向明廷请求入贡,祈求获得明廷的承认。然而明廷此时奉行“不拒黎,不弃莫”的双重承认政策,即认可莫氏在高平地区的统治秩序,同样也认可黎氏的复兴以及对安南全境统治的诉求(除了高平地区之外)。庙谟既定,中外从同,黎、莫双方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从此越南北部同时存在两个政权的状况得以确立,虽然双方依旧存在冲突,但是这个情况至明朝灭亡依旧没有改变。“自是,安南复为黎氏有,而莫氏但保高平一郡……然迄明之世,二姓分据,终不能归一云。”[1]
清朝定鼎,盘踞在高平的莫氏政权与安南王室黎氏开始接连请求入贡,清廷依旧延续这个双重承认政策,前者被封为安南都统使,后者为安南国王。但是双方依旧不断相互攻击,虽然黎氏曾在康熙六年(1667)攻下高平地区,但是依旧被清廷勒令归还莫氏,双方的割据状态仍然受到清廷承认并保护,并且清廷也倾向于维持这个现状。这样的政治局面在康熙年间被打破,由于莫氏在三藩之乱中与吴三桂暗中勾结,其在高平的统治地位不再受到清廷承认,而黎氏的实力较莫氏更为强大,在莫氏失去清廷的保护后,黎氏又收复了高平地区,安南北部重新统一。[2]
但是后黎朝在安南北部的统治并不稳固。在乾隆五年(1740),两广总督马尔泰奏称从上年开始,安南北部已经发生动乱,而这些地区与广西、云南接壤,此次动乱恐怕会波及边疆,虽然有情报称叛军已经同安南朝廷媾和,但是清高宗仍命令马尔泰亲自前往边境巡阅,进一步确认事实。[3]乾隆六年,安南的形势被进一步侦知,右江镇总兵张朝宣奏称以安南禄平州土酋韦氏为主的叛军仍在肆虐安南北部,他已下令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戒备。[4]针对这个特殊情况,广西巡抚杨锡绂奏称由于安南朝贡道路正好经过战区,安南恐怕不能如期入贡。同年,安南土酋韦福琯的叛军被安南官军击溃,贡道开始恢复正常。[5]虽然清廷认为韦福琯的就擒会使边境重新恢复宁谧,但韦氏造成的动荡让一些潜在的王位觊觎者窥视到了安南朝廷的虚弱,这对安南名义上的执政家族黎氏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一个与其纠缠了两个世纪的仇人又再次出现。在进入安南为叛军服役的内地民人中,有两位名为莫保、莫康武,其真实身份为安南高平莫氏政权的后裔及拥趸。“粤西镇安府、归顺州等处,与交趾保乐地方接壤。现匪徒莫保与黎氏有仇,集党报复。”[6]在韦氏叛军覆灭后,安南北部又陷入莫、黎纷争的兵燹。清廷虽然无意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但是为了避免广西边境地区受到这些动乱的影响,清廷在此阶段也作出了一系列的措置去进行应对这个情况。
二、限制内地民人的出境滋事行为
乾隆七年(1742),清廷收到情报称有本国民人出境卷入安南内战之中,并直接为叛军头目服役:“查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兵部火票递到大学士等抄寄广西提督谭行义奏称:‘内地民人叶蓁为韦福琯谋主,周老六为枪棒教师,较寻常汉奸更为重大。’”[7]14所谓“汉奸”初指边疆地区从事不法行为的汉人,后指所有在边疆滋事之徒。[8]由于边疆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官府往往疏于管控,以至于一些不法之人得以藏匿于此。如同清高宗在乾隆七年的上谕中所称:“粤西地处遥远,汉土交错,村寨最易于藏奸,而文武官弁稽察废弛,相沿成习。”[9]有清一代,“汉奸”问题一直是比较突出的矛盾,从未得到彻底解决。随着安南局势的变化,一些“汉奸”越过边境并卷入安南内战之中,这无疑在政治上会给清廷抹黑,对此清廷已经意识到防止“汉奸”出境与阻隔夷人入境同等重要。清廷除了将各隘口封锁,还饬令各沿边土官及汛塘兵丁纠察“汉奸”:“左江镇属二十余州,土司间有不法生事者,一由该官弁纵役骚扰,一由怠驰长奸,养痈贻患,更有内地汉奸勾通衅事。现饬界连土司之各汛营弁,毋致仍前滋扰讳饰,并禁汉奸潜入。”[10]为此,清廷加强对这些叛军的组成结构进行调查,侦知许多内地民人特别是沿边府州的民人已经充当叛军的中层头目。实际上,这些人原本在安南寻求谋生的机会,在韦福琯叛乱后又被安南朝廷召募,被许以重赏而协助平叛。韦福琯就擒后,安南当局在善后措施中处置不当,导致一部分人脱离军队并四处劫掠,虽然清廷已经尽力召回这些内地民人,但是效果并不太令人满意。原因在于安南官军亦在招募内地民人,如果清廷尽数召回,那么安南官军将会损失一部分兵力,所以安南方面的官员多有推脱。为此,杨锡绂建议清高宗对安南国王宣谕,不许招募内地民人充当士兵,此外,如安南方面抓获为叛军服役的内地民人,除了被清廷点名要遣返之人,其余可直接按照安南律法进行判决,不必再遣送回境。在此条协议生效之前,因藩属国无权处理宗主国的犯罪之人,安南方面俘获为叛军服役的内地民人时,大多会遣送至清廷境内,而清廷再负责进行安插、惩治事项,以至于为叛军服役之人往往有恃无恐,这意味着即使被安南官军抓获亦无生命之虞。[11]257通过这些手段,使一些内地民人企图为叛军服役时会有所畏惧:
自韦福琯造逆谅山,该国王调高平、牧马两府夷官合兵剿捕,探闻领兵官员因招致内地久在安南无赖民人及厂上矿徒,许以重赏,令其帮同攻打韦逆。及韦逆攻破,不足以厌此等无赖之欲,于是遂散而肆行劫掠,其中亦有为夷官收用者……虽安南恪守藩封,素称恭顺,此等匪徒彼亦知系无赖之辈,然以内地之人在外滋扰,终属未便,以臣愚见,仰恳皇上圣裁,或宣谕该国王,凡滋事匪徒擒获之日,即系内地民人,亦尽法处置,并令严饬夷官嗣后不得收用内地民人为先锋等官,其指名饬拿者俱解回内地,以凭惩治约束,则内地民人在夷地者将所有畏惧,而不敢肆行。[7]146-147
除了双方高层的紧密合作,沿边地方官员也互相配合,如安南高平督镇官陈名冧请求接壤的归顺、镇安等地官府协同缉捕。“先是,贼围高平阅二月余,城内资粮匮竭,(陈名)冧抚循土兵战士,悉力拒守,以便宜发官囷给赐。潜遣人致书归顺、镇安、隆平州官①查云南、广西并无隆平州这一地名,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40《黎显宗景兴六年》则记为龙州、凭祥,当取此说。,尽拘贼孥小。”[12]1114从乾隆八年开始,莫氏的复国武装集团一直横扫安南北部,至乾隆十年达到高潮,并攻占安南诸多府州。“安南夷匪莫康武等,初犹止窃踞夷境之文兰、驱驴等处。兹据沿边禀报,夷境之处东、处南、宣光、清化、安广、太原等郡,俱为莫康武所有。”[13]直至乾隆十六年(1751),这场叛乱才被彻底镇压。而在此期间清廷所做出的一系列措置,确实对结束安南内战起到了影响。除了严格限制内地民人出境,还对内地民人擅自潜入安南的惩罚措施做出修改。以至于杨锡绂曾误解清高宗之意,越过司法程序直接杖毙非法前往安南的内地民人,而引发了清高宗的不满。[14]清高宗虽然鼓励使用重典,同时也认为惩戒应当在法律框架之下执行,从此案侧面也可看出广西确实在逐渐加重对擅自出境民人的惩罚。此案虽系由误解上意所起,但是清高宗亦承认该犯可置重辟,只是责备杨锡绂的手段过于激进。
在清廷与安南政权共同宣布将对为叛军服役的内地民人进行严处之后,使企图越境的内地民人陷入纠结之中,在选择阵营时多少有所顾虑,导致叛军的兵源得不到有效补充,最终力有不逮。正如牛军凯所言:“莫保、莫康武复国活动的最终失败,除了越南黎朝尽力攻剿外,应该还有以下原因。由于清朝方面了解到其兵力大多是内地民人,广西和云南地方官在边境阻止民人出交和派人召回参与莫保、莫康武叛乱的民人……因此莫保、莫康武的军力得不到继续补充,战斗力逐渐下降。”[15]153
三、边防体系与边贸体制的调整
(一)沿边防御体系的完善
1.增派驻军以资弹压。当安南发生内乱之时,广西巡抚杨锡绂认为边境关隘数量众多,仅靠边境的常规驻军恐怕无法有效防御,因此请求从左江镇再调拨一百名士兵前往毗邻边境的下石西土州驻扎弹压。[16]最为紧要的是,此时清廷已经平定广西北部苗瑶人民的起事,亟待采取善后措施,而此时安南局势变化使边防一时吃紧,导致新设立的龙胜协无法抽拨地方士兵布防②乾隆六年,囿于财政上的困难,清廷对地方行政、军事设置作出修正。在此条例生效之后,各省在原则上不能再增添士兵,止可在本省抽拨分配。《清高宗实录》卷143载:“雍正元年以前,共额设马步兵五十八万二百余名。后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处,增设十一万六千余名。嗣经军务告竣,议裁二万余名,尚多浮冗,请将各省标镇协营详查续添兵丁,或可全行裁汰、或可量加裁减。倘有不便裁减者,将马兵改为步战、步战改为守兵。或有地要营单,必须添设,止准于通省酌量抽拨,毋轻议增。”,不得不向朝廷申请重新募兵,这直接给地方财政增添了负担。[7]95因此,在听闻安南已经派出军队前往镇压叛军后,杨锡绂迫切希望安南官军迅速平息叛乱,使朝贡、边境局势能够恢复至动乱前的状态,使广西边境地方能够摆脱外部动乱的威胁,使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7]95
2.修葺关卡,完善边境官员的巡查制度。除了增派驻军,清高宗下令对广西全部关隘进行检查,以便应对安南形势恶化后造成的其他后果,杨锡绂对此回复称:
……镇南关,则雍正二年经原任太平知府甘汝来复设重关,建立城墙,今加查勘,完固无损。其余各关则地非紧要,关房亦随时修葺,现在俱无损坏。至于隘口,粤西所属颇多,其与湖南、贵州、云南、广东各省连界者均系内地,各地方官俱随修葺,然非关要害。惟与安南接连,如……(注:由于此段皆为沿边关隘名字,涉及关隘过多,引文过长,已省略)俱与安南接壤,实属粤西沿边一带藩篱,二年以来因安南内讧,分拨汉、土兵役驻扎守御,其隘房等项已饬汉土地方官添造修葺,现在亦俱完固,均可毋庸议修。嗣后如镇南一关损坏,应请动公修葺,其余仍令各该地方官照旧修葺防守。所有粤西境内旧设边、腹关隘情形,并现在完固防守得宜。[7]111-112
同时两广总督策楞督促地方高级官员亲临边境巡查:“西省贴近安南,值该国盗匪窃发之时,边防尤关紧要。饬令文武大员督率汉土官兵,在于各关隘口防范稽查,以杜汉奸夷匪潜出窜入。”[17]乾隆九年(1744),新上任的两广总督马尔泰再次督促边境地区的官员要加强对边境关隘的周期性巡查:
至南、太、镇三府沿边关隘,自建卡拨守以来,奉行尚未周密,应令各该地方官相其险易,及时增培,每年冬月沿边查勘一次,垒石坍塌者修之,建栅朽坏者补之,濠沟淤积者浚之。[18]
乾隆年间的镇安府知府傅埾在回忆当初纂修《镇安府志》时常常陷于政务倥偬之中,除了每年一度前往省城桂林述职之外,巡查关隘是其职责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下车数载,频岁一赴省,又巡行属邑,勘查边隘,几于席不暇暖,故屡搦管而屡辍笔,迁延两载后告成。”[19]而龙州厅通判张大海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在其赴任之初即有修志之意,但囿于政务纷繁,尤其是巡查边境消耗了极大时间、精力,最终没有能够修成地方志:“余己未冬来守兹土,急欲修志为己任。无奈边关要地,首重查巡。”[20]
3.强化沿边兵弁的巡查。乾隆十五年(1750),云南土富州土目李世昌等五人从镇安府荣劳隘出境,前往交趾缉拿罪犯,在原路返回的途中却受到镇安协兵弁的阻止,以至于其在两次请示皆无法入境后,不得不从偏僻的坡利后山偷渡,在此过程中不幸遭到匪徒的攻击,五人皆牺牲,犯人亦被劫走。该案使清高宗大为震怒,对此评价称:“该土目等既持有关文,再经往返,该州协等何以不行禀明该抚,妥协办理?惟事始终坚阻,所奏殊未明晰。至称坡利山非设卡隘之处,兼系土山,可以私越一节,尤非慎重边防之道。”[21]于是下令广西官员对边境管理体系重新制定章程。针对这个指示,广西巡抚舒辂提出除了在坡利重新设置卡防,还对沿边各隘兵弁巡防的方式、纪律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并于沿边各隘,各制巡旗一面、号簿一本,令各隘兵勇,每日持旗执械,自本隘巡至邻隘,即将该隘兵勇姓名,查到缘由,登记号簿,逐日互巡。如巡查不到,许邻隘首禀,不首并罪,夜则击梆谨守。防汛各弁,逢五逢十,彼此会哨外,不时于所管卡隘往来查察。该管都、守每月亲查一二次,如兵勇偷安,汛弁懈弛,究革详参。[22]
(二)边贸体制的调整:边防、边贸、边民的平衡
即使安南的动乱给边境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但是边境贸易没有因此而中止,而是通过调整制度来适应新的形势。为了防止一些企图从这场安南内乱中获利的“汉奸”假冒商人出境的情况,杨锡绂建议在专门提供商贩出入境的平而、水口两关①沿边三关是指镇南关、水口关、平而关。其中镇南关只有安南入贡时才开放,其余二关为专门提供内地商贩出入贸易的渠道。实行腰牌制度:“惟平而、水口两关,乃向来客商往交贸易必由之路,会经前抚臣金鉷奏明留此二关,听内地客民出入,以通货贿,但未立稽查之法,未免奸良莫辨。令酌定请领腰牌之法,以为查验之准,并令太平府通判就近专管稽查,以专责成,目下照此办理。”[7]144
虽然平而、水口关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给边贸提供了渠道,但是却对宁明州的商贩造成了困扰。出于边防的需要,靠近宁明州的由村隘遭到封禁,只能通过两关出境。但是如从两关出境,则需要增加十日的旅途才能抵达交易货物的地点,无疑增加了许多贸易成本,因此这些商贩不惜铤而走险,直接偷渡出境,虽然遭到阻拦,但收效甚微。同时官府的缉捕也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影响,由于商贩的货物多需本地人充当担夫,随着商贩出境贸易受阻,势必造成那些依附于边贸的民人失业为盗:“缘由村隘距宁明州一百一十里,宁明商贩愿从出入。盖因由村隘系通交趾禄平、文渊、驱驴等处,为货物聚集之所,若从平而、水口两关出入,必须绕道数百里,计程十余日,不如径从由隘出口之便,虽经封禁,踰越终不能免。且明江五十三寨土民,原系思明土府管辖,因恃顽藐法,土府黄观珠不能管束,分土归流,于雍正十年归并宁明州管辖,此等土民全赖挑贩营生,若将由村隘封禁,恐失业者聚而为匪,必百计包货偷越,转于边防无益。”[23]
为此,两广总督马尔泰针对这个情况提出了新的建议,大致包括三点:一是将靠近宁明州的由村隘开放,既便利了商贩的贸易往来,又使当地民人得以继续通过担运货物谋生;二是促使当地的商会会馆与官府、乡村头人互相配合,加强出入隘口的管理;三是对从平而、水口两关和由隘出境的商贩交易地点做出不同的限制,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进行贸易,安南方面则有权利进行惩罚:
再由村一隘,当年题定封禁,原以平而、水口两关既开,商民得出入贸易,殊不知交阯驱驴地方为货物聚集之所,距由隘不远,径捷利倍。……即明江五十三寨无业贫民,挑担营生,亦藉就近为商雇觅,由隘一开,诚属便商利民。惟是边民非比齐民,若不立法防范,使出入有数可稽,恐奸匪隐混窜逸。查宁明州向置会馆,设立客长,以为由隘出入之公所,应令该州慎选老成殷实数人充当,凡客货出隘,许客长将客人姓名籍贯货物,及发往何处,一一注册,报该州查实,给与印票,并刊立木榜,不许客长藉端需索。其五十三寨挑夫,亦令该州将姓名住址造册取结,给与印票,令理土同知于该隘查明印票,给腰牌放行,有印票、腰牌者,方许放入,其入关客人姓名,从何处卖货入内,令该同知注册,报宁明州查对。倘有滥给印票者,责在宁明州,滥给腰牌,私放出入者,责在理土同知。凡客人在外贸易者,彼处若有回头客货,自应略为等待,应酌给半月限期,过期即饬头人、保人严询究处。……至商贩由平而、水口出关贸易者,止许在太原、牧马附近之处交易;从由隘出口贸易者,止许在谅山、驱驴附近处交易,不得逗遛交境,倘冒险远出,许夷官拦回责处。[24]
由此可见,清廷在面临边防压力的情况下,也尽力保护边贸的发展与边民的利益。这些措置有效地减少了外部环境动荡对边境地方社会的冲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边境在乾隆四十年(1775)曾遭到关闭,但是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乾隆五十四年(1789),安南的西山朝廷在获得清廷承认其合法统治地位后,立马请求重新开放边境:“复请于高平之平(而)、水(口)关、谅山之由村隘开市通商,抽免商税,南宁府设立牙行,清帝皆许之。”[25]76从此以后,中越陆地边境的贸易形式得以长期巩固下来。
四、行政建置的调整
(一)基层政区隶属关系的调整
该时期清廷对沿边行政建置做出的调整也是值得注意的。乾隆八年(1743),因沿边各土州仅上下冻土州、思陵土州从无流官驻扎之例,缉查边境一事皆委之于土官,为了应对安南内讧所造成的边防压力,此二地又亟需流官常驻。同时,又受制于乾隆六年(1741)所通过的一款条例,地方政府已没有权力增添佐贰官。[26]杨锡绂只能在边防形势与行政资源之中寻找平衡,为此他提议将宁明州吏目兼管下石西土州,原下石西土州的吏目移驻思陵土州;永康州吏目兼管罗阳土县,原罗阳土县的典史移驻上下冻土州。通过这一转换,使流官的势力进一步抵达边境的基层政区:
窃查太平府属之上下冻土州、思陵土州俱地处极边,与安南犬牙相错,一切隘口巡缉稽查颇为紧要。乃向来各土司地方俱设有流官,如州同、州判、吏目、巡检等员协同稽查弹压,惟上下冻、思陵二土州未经设立,一切巡查等事,仅责之土官。迩年以来,因安南地方滋事,虽时亦委员巡查,并拨兵前往驻宿隘口,然官非长驻,究不足以专责成。查乾隆六年八月准部咨,嗣后各省倘有地方应须人员管理,止准于通省随时改调,既不得具奏增添等因。臣就二土州地方四面形势,再思筹酌,查土司中有下石西土州者,地小而切近宁明;有罗阳土县者,地小而切近永康。宁明州之吏目可以兼管下石西土州,永康州之吏目可以兼管罗阳土县,应请将下石西土州原设之吏目改为思陵土州吏目,罗阳土县之典史改成上下冻土州吏目,如此一转移间,官俸役食既不加增,而要地均得人弹压,于边防甚为有益。[7]156
乾隆十二年(1747),因湖润寨土官病故,无人承袭,又值安南多事之秋,为加强对边境的管理,两广总督策楞提议将归顺州州同从旧州地方移驻湖润寨:“湖润寨土巡检岑作柱病故,无人承袭。该处毗连夷境,必得专员弹压。因思归顺州与该寨接界,现设州同一员,请即移驻等语。查各省土司地方,需员管理者,例准于通省内随时改调,应如所请。归顺州州同准移驻湖润寨地方,改为归顺州管辖,其一切户婚田土细事,该州同就近判断,如遇命盗重案,仍令该知州承审。”[27]
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小镇安地理位置重要,而土官的继任者却尚处幼冲,无法控御下属的土目,清廷以此为由将其革职。两广总督杨廷璋提议将归顺州州同改为镇安府通判,从湖润寨移驻小镇安,此后小镇安也被称作“小镇安厅”。而湖润寨则由南宁府宣化县那南寨土巡检移驻,作为交换,那南寨巡检司的事务由金城寨巡检司管辖:“镇安府属小镇安土司,地处极边,壤接交趾,与滇省毗连,实为西粤要地。原设土司巡检,职分卑微,难以控制。现在应袭土巡检岑绳武,幼稚无知,失察土目舞弊,应请将岑绳武革去世职,家属徙居桂林。其小镇安土司改为流官,将归顺州州同一缺改设镇安府通判,驻扎小镇安,令其整饬化导。其湖润寨地方,将南宁府宣化县那南寨巡检移驻,那南地方事务,归并金城巡检管理,并改铸关防印记。”[28]
归顺州州同自设立以来,其驻地、职能不断变动。如果说雍正时期归顺州州同只是作为改土归流后入驻旧州地方绥辑土民的一个善后措施,那么乾隆时期归顺州州同驻地的两次变动,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日益靠近边境,而且最终转变为镇安府通判,使其在职权上更进一步。这一过程也体现了清廷对安南局势变化所做出的应对,亦是该时期安南局势对边境地区造成影响的一个缩影。
(二)“道”的隶属关系及职能的调整
乾隆九年(1744),清廷调整广西左、右江道的管辖区域。原因在于潜入安南境内从事非法活动的民人中,有不少来自于滇桂交界的泗城府。通常认知中右江道为苗疆重地,左江道为边防要区。此时将泗城府从右江道划归左江道,不仅是对政区的调整,亦是清人对广西地理认知、边防观念发生变化的反应,因为泗城府并不接壤安南。浔州府在过去被认为是安南通往内地的水路枢纽,作为边疆重地,而划归左江道管辖。随着乾隆初期广西边境形势的变化,浔州府被划归右江道管辖:
窃照广西向设左江、右江二道,左江一道统辖浔、南、太、镇四府,驻扎南宁;右江一道统辖柳、庆、思、泗四府,驻扎柳州。一则苗疆要地,一则边防重区,当日分隶原属匀整。惟就目前情形而论,则泗城一府宜隶左江道辖,而以左江所辖之浔州改隶右江,庶巡查便,而弹压更为得宜。盖泗城一府虽不与交趾连界,而紧连云南之广南及本省之镇安,实与交趾相隔不远。近年匪徒滋扰,交趾令其党类入内,哄诱愚民出交,而泗城之西隆、西林等处土民遂多由广南及镇安偷越外出者,虽经盘获匪棍严加惩治,其被诱之民亦陆续唤回,但交夷一日未靖,即一日须加防范,而稽查督率,必该管道员时加巡历,方不致有名无实。查泗城一切事件达左江易而达右江难,左江道巡查太平、镇安,顺道而至泗城易,若右江道巡查泗城,旱路则须经由思恩及九土司地方,山路崎岖,非十余日不能到,水路则由浔州经过左江道驻扎之南宁,而后可到泗城,其劳逸难易,判然可观。从前之因仍其旧者,以地方无事,即道员亦罕至其地,今边境既时须经历,则泗城断宜改隶左江道管辖,俾得一体巡查整饬,而以腹地之浔州一府就近改隶右江,如此一转移间,于政体既非纷更,而于边防诸事甚为有益。[7]171
乾隆二十一年(1756),两广总督杨应琚提议将左江道道台兼兵备道之衔,可直接指挥沿边四镇的都司以下武职,使左江道道台的权力获得强化:“广西左江道有控压边关,抚辑土瑶之责,应加兵备道衔,节制南、太、泗、镇四府都司以下武职。”[29]毋容置疑,这些调整的背后明显是针对安南的局势变化。乾隆年间摄理左江道台的查礼对自身的职权有着深刻见解:“粤西三道,独左江(道)带兵备衔,以地控交趾也。辛巳十月(乾隆二十六年,1761),余奉檄摄行道事,因诗以自嘲兼自勉云。”[30]73此次关于左江道辖区、职能的调整因此得以长期固定下来。直至中法战争后,边防危机的出现,这个局面才被打破。[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