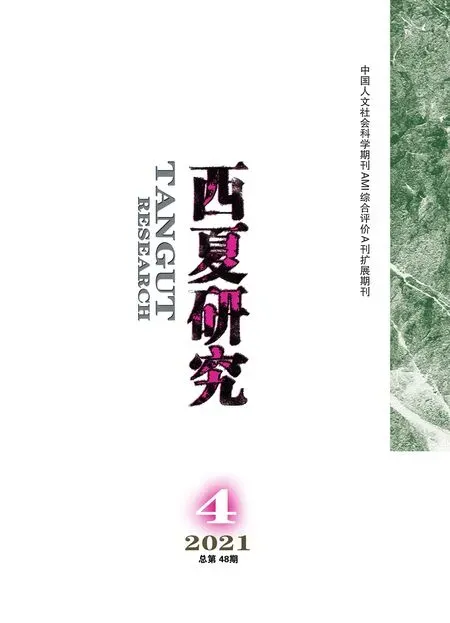黑水城汉文版刻避讳字补考
2021-11-25佟建荣郑佳茜
□佟建荣 郑佳茜
黑水城汉文文献涵盖宋、辽、夏、金、元等朝代,是与敦煌文献、殷墟甲骨、居延简牍(包括其他地区出土)齐名的20世纪我国四大地下出土文献之一。近年来随着文献研究的展开,一些文献中的避讳字先后被择取出来,应用到了断代、版本等研究当中。已择取全面且含义较明朗的文献有TK6《吕观文进庄子义》、TK7《广韵》、TK290《新唐书》、TK315《汉书》、TK316《资治通鉴纲目》、TK322.5《初学记》、Or.8212-1243《春秋正义》等。涉及的避讳字有“玄”、“弦”、“朗”、“珽”、“敬”、“胤”、“匡”、“筐”、“殷”、“恒”、“炅”、“侦”、“遉”、“贞”、“煦”、“竟”、“桓”等①。笔者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所有黑水城汉文版刻文献进行再次爬梳,按笔画顺序(同一组者按第一个字的笔画)对未曾摘录或者判断不准的避讳字作逐一考证。
共、供、洪
缺末笔的“共”、“洪”,黑水城文献中仅见于《刘知远诸宫调》。
最早注意到该文献中“共”、“洪”缺笔的是王昊《黑水城出土〈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和著作权综考》一文。文章指出文献中的缺笔“共”、“洪”,皆为避辽道宗(1055—1100)“耶律洪基”之名讳,并据此提出,该文献为“辽金配刻本”。[1]
笔者以为此处的“共”及“洪”非避辽道宗耶律洪基之讳,而是避金显宗完颜允恭之讳。查《史讳举例》,辽避“洪基”之“基”而非“洪”,“洪基”下有讳例“贺国主生辰,客省副使王克基,辽史作克纂,盖辽道宗名洪基也”[2]117。
《金史·地理志》河北西路卫州苏门县下注有“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河平,避显宗讳也。明昌三年改为今名”[3]608。《史讳举例》依据该条记录,于显宗讳例下列“改共城县为河平”[2]118。金显宗“体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讳允恭”[3]410。《史讳举例》虽没有“洪”的讳例,但“洪”含有需避讳的“共”,必也在金讳当中。
学界对《刘知远诸宫调》为金刻本的讨论已很充分。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在初次著录时,就将其判断为金刻本。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即认为《刘知远诸宫调》是流入西夏的金版[4]。近些年来,讨论越来越多,争议主要在成书年代,至于刻印年代基本上都认同金本之说。龙建国在《〈刘知远诸宫调〉应是北宋后期的作品》一文中认为该作品形成于北宋,“金代改编”,用“金代改编”表达了对金刻本之说的认同[5]。武润婷《也谈〈刘知远诸宫调〉的作期》一文提出该文献不仅是金刻本,而且是金代作品,并找到了确凿证据。文章指出龙建国发现的反映北宋历史背景的名词术语如“二税”、“青粮伞”、“急脚”、“十将”、“团练”、“节级”、“经略安抚使”等在金朝也存在,而“本破”、“射粮”、“九州”等术语及依官印重量表官阶的制度为金朝独有,不见于北宋。金可以继承宋,宋不可能预知金,所以该文献为金作品。[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刘知远诸宫调》中的“共”、“洪”缺笔是避金显宗允恭之讳。
缺末笔的“供”,仅见于TK177《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中,该文献两处“供”皆缺末笔。《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在黑水城文献中有22个编号,TK177是唯一一个版面分为上下两部分的本子,上方为佛画、下方为经文。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判断为12世纪末刻本,《俄藏黑水城文献》判断为宋刻本。
《金史》卷五十三《选举三·右职吏员杂选》:“笔砚承奉,旧名笔砚令史,大定三年,更为笔砚供奉,后以避显宗讳,复更今名。”[3]1185《辽史·百官志三·校勘记》中有:“承奉,石刻中并作供奉。金避章宗父允恭嫌名,改为承奉。”[7]798
除《金史》外,“供”字避讳不见于其他朝代,TK177中的缺笔“供”当为金讳,TK177也应该是金刻本,而非宋刻本。
明
“明”,缺最末两笔,是黑水城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缺笔字。TK1《妙法莲华经》中有12处缺笔,TK3《妙法莲华经》中有10处缺笔,TK4《妙法莲华经》中有21处缺笔,TK11《妙法莲华经》中有2处缺笔,TK15《妙法莲华经》中有1处缺笔,TK98《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中有1处缺笔,TK100《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中有1处缺笔,TK141《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中有4处缺笔,TK148《观无量寿佛经甘露疏科文》中“明”字皆缺笔,TK107《佛说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全文5处缺笔,TK184《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全文2处缺笔,TK164《〈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刊本》全文2处缺笔,TK165《〈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刊本》全文2处缺笔,TK254《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有1处缺笔。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记:“宋改元明道,元昊避父讳,称显道于国中。”[8]13993此条记载一般被学界看作是西夏有避讳的证据。如韩小忙《西夏避讳制度初探》一文即据此条史料认为西夏在建立初“已开始为本国避讳”[9]。王曾瑜先生用此条史料来证明西夏有为“其最高统治者汉名避讳”[10]的习惯。在黑水城文献研究中,学者一般也将文献中“明”缺笔视作避夏太宗“德明”讳的结果,并进而将其作为判断某一文献是否为西夏本的依据。如史金波就利用“明”字缺笔,将TK297等一系列文书判断为西夏历书[11]。
在以上15个编号的文献中,TK1、3、4、11、15为七卷本《妙法莲华经》,其前有西夏仁宗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其后有年款“时大夏国人庆三年(1146)岁次丙寅五月”。TK98、TK00皆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是同一文献的不同部分,其中TK98发愿文中有“今皇太后罗氏恸先帝之遐升,祈觉皇而冥荐。谨于大祥之辰,所作福善,暨三年之中,通兴种种利益,俱列于后”[12]372等内容。其中的罗太后即为仁宗仁孝皇后。TK164、TK165《〈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刊本》发愿文中亦有西夏仁宗仁孝尊号。所以,以上文献皆为西夏刻本,其中的“明”为西夏讳。
TK148《观无量寿佛经甘露疏科文》,全文无年款信息,不过文中除“明”缺笔外,“常”、“顺”两字也缺笔(详见下文)。同时避讳“明”、“常”、“顺”,且在时间上同黑水城文献有关系的只有西夏,所以,此处“明”也应当是西夏讳。
TK184《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全文无年款,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判断为元刊本,《俄藏黑水城文献》承孟列夫之说。孟列夫之所以有元刊本之说,主要是在21世纪之前,学界一直认为《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汉译本最早出现在元代。比如《大正藏》第20册所收《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即被定位为元刻本,经题下的译者“释智”及经文后的缀文者“道圆”也随之被定为元代人[13]。2004年,卓鸿泽在其论文Tibetan Buddhism in Ming China中首次指出《大正藏》中的释智为西夏人[14]23。2006年,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在对俄藏西夏文译本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残本进行研究时,也意识到释智可能是西夏人[15]。2015年,崔红芬在《俄藏黑水城文献〈密咒圆因往生集〉相关问题考论》一文中利用“文殊菩萨五字心咒”、“十二因缘咒”两咒语的在《大正藏》本《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与西夏天庆七年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的译法,以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西夏剃度党项族和藏族行童时必诵读的经文,指出《大正藏》本《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出现在西夏,且早于西夏天庆七年[16]。2015年,惠宏、段玉泉在其论著《西夏文献解题目录》中指出《大正藏》本《圣妙吉祥真实名经》题款中的“出家功德司”,仅见于西夏,“道圆”也是西夏人,而非元代[17]346。至此,西夏翻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已经证据确凿,《大正藏》所收录的本子当为西夏译本。比较《大正藏》本与TK184,我们也会发现TK184中的偈语与《大正藏》本没有差别,尤其是陀罗尼反映的读音也相同,具有明显的河西方音特点。所以,TK184应该是西夏译本,其中的“明”为西夏讳。
TK141《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全文无年款信息。巧的是前文提到的西夏本TK98中明确记载,仁宗仁孝皇后罗氏施印“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又黑水城文献TK120《佛说父母恩重经》的发愿文中也记载“呱呱等”为其亡父“中书相公”开阐“法华、仁王、孔雀、观音、金刚、行愿经、乾陀、般若等会各一遍”。“中书相公”,据聂鸿音先生考证是替西夏天庆七年本《密咒圆因往生集》作序的“贺宗寿”[18]。从以上资料看,西夏境内曾大量印刻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TK114为西夏刻本,其中的缺笔“明”是西夏讳。
TK254《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全文无年款信息,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判断为宋刻本。《俄藏黑水城文献》认为有可能是宋本也有可能是西夏本。文献中除了“明”缺笔外,“真”也缺末笔。日本学者竺沙雅章据《辽史》中“女真”记作“女直”的内容考订此处的“真”缺笔,是避辽兴宗耶律宗真名讳,进而指出“明”也为辽讳,TK254为辽刻本[19]。
传世文献中有辽避“明”讳的记载。《辽史·兴宗纪》“己巳,宋以辽师伐夏,遣钱逸致赆礼”[7]240。“钱逸”,《宋史》[8]226、《续资治通鉴长编》[20]3843均记作“钱明逸”。夏太宗德明,在《辽史》中全部记作“德昭”,韩小忙《西夏避讳制度初探》中指出,“昭”改“明”,为避耶律明之讳[9]。
综合文献中的缺笔“真”、TK254中的缺笔“明”,诚如竺沙雅章所论,为避辽穆宗耶律明之讳,而非夏太宗德明之讳。
据以上所考可知,黑水城文献中可以确定的“明”讳有两种,一为西夏讳,一为辽讳。
至于西夏避“明”源出元昊避父讳的说法,笔者以为值得商榷。西夏建立初期,除改掉宋朝的年号外,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见到西夏执行“避讳”,相反,倒是有不避讳的例子。如康定元年(1040),也就是“元昊避父讳,称显道于国中”的八年后,元昊派遣入宋约和使臣即名“李金明”[20]2989。所以,所谓因避父讳而改年号,更可能是元昊的政治手腕,找了个借口堂而皇之地有了自己的年号,为另起炉灶做准备工作。
黑水城文献中出现缺笔“明”且有年款的文献皆同仁宗仁孝有关,要么如TK1是仁孝所施刻,要么如TK98为祭仁孝而施。据此,笔者推断,让西夏明确避“明”的应该是仁孝而非元昊。与元昊强调番性、排斥汉地礼仪不同,仁孝时期大力推行儒学,尊孔为帝,儒学在西夏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此背景下,作为汉地礼仪之一的避讳,在西夏受到重视并被执行也是自然的。
顺
黑水城文献中缺末笔“顺”出现于5个文献中,分别为TK1《妙法莲华经》、TK4《妙法莲华经》、TK9《妙法莲华经》、TK148《观无量寿佛经甘露疏科文》、TK139《佛说父母恩重经》等。
黑水城文献中的TK1、4、9为七卷本《妙法莲华经》的不同部分。上文已述,黑水城出土的包括TK1、4、9等几个编号在内的七卷本《妙法莲华经》为西夏仁宗仁孝时刻印。仁宗父崇宗名乾顺,此文献中缺笔“顺”当为乾顺之讳。
TK139《佛说父母恩重经》、TK148《观无量寿佛经甘露疏科文》两文献无年款信息。
TK148中,与“顺”同时缺笔的还有“明”。上文已述,可以确定避“明”讳者有辽、西夏两朝,辽朝没有避“顺”的历史背景,而西夏有崇宗乾顺,所以,此处的缺笔“顺”也应当是崇宗乾顺之讳。《佛说父母恩重经》,黑水城文献中除TK139外,还有TK120及Инв.No.759、5048、6570、6670、6876等几个西夏文译本。有关几个西夏文译本,聂鸿音考其内容没有丝毫差异,为西夏仁宗时鲜卑宝源所译,底本即是以TK139为代表的一部佛经[21]。而TK139在内容上又与TK120完全一致。《佛说父母恩重经》是中国佛教史上一部重要的伪经,伪经在内容上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其具体的内容、文字表述略有不同,如黑水城出土的多部《高王观世音经》。考虑到TK139与TK120在内容上的一致,以及其与西夏译本的关系,TK39应当也是西夏本,其中缺笔“顺”为西夏讳。
擁
黑水城文献中发现4处缺末笔的“擁”,分别在TK14、TK16、TK17、TK18四个编号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其中TK14、TK18有“大夏乾祐二十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的题款。TK14、17行款版式一致,出自同一套雕版。TK16与TK14行款略有差别,字体风格非常相近,也应该是同一时期的文献。四编号皆为西夏刻本。
《史讳举例》中没有避“擁”讳例,但有“雍”。“雍”讳见于后晋及金,与黑水城有关者当是金。《金史·地理志》有“宋雍丘县,札巳国也,正隆后更今名”[3]589。据陈垣先生研究,金将“雍丘县”改名“札巳国”当为避金世宗讳,世宗名完颜雍[2]117。
除《金史·地理志》中的史料外,《辽史》中也有金避“雍”讳记载。道宗女撒葛只初封郑国公主“咸雍中徙封魏国”,其后校勘记第六条下记“雍原作‘和’,陈大任避金世宗雍名改,元人回改遗漏,今回改”[7]1012。
文献中的大夏乾祐二十年即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适逢金世宗完颜雍去世之年,作为西夏政权的最高代表,罗太后在她施刻的经文中避宗主国讳,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故此处的“擁”当是西夏避金讳之例。
常
“常”,缺末笔,出现在TK141《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TK148《观无量寿佛经甘露疏科文》中。
TK141、TK148中皆无年款信息。TK148中与缺笔“常”同时出现的还有缺笔“明”与“顺”。考察中国历史,同时避“明”、“顺”、“常”的,最有可能的就是西夏了。西夏有太祖德明、惠宗秉常、崇宗乾顺。“常”缺笔当是避惠宗“秉常”之讳。TK141,上文已考证其为西夏刻本,同时又有缺笔“明”,所以,缺笔“常”亦当为惠宗秉常之讳。
尧、烧、晓
缺末笔的“尧”,缺所含“尧”之末笔的“烧”、“晓”皆见于《刘知远诸宫调》。
传统典籍中“尧”讳见于金。《史讳举例》中指出“天德二年三月,宋参知政余唐弼,宋史、系年录俱作余尧弼,盖《金史》臣避世宗父讳宗尧追改”[2]44。结合上文论及的学界对黑水城《刘知远诸宫调》版本的讨论,此处的“尧”当为金讳。
传统典籍中未见“烧”、“晓”讳,此两字显然是因含“尧”部而缺笔,以避金睿宗宗尧讳。
除以上诸例外,还有TK166的“眩”、“敬”,TK228《新雕文酒清话》中的“眩”、“敬”、“筐”等也未见于之前的研究当中,介于其含义已为学界熟知,此处不再赘述。这里要补充的是见于TK159《夹颂心经》中的“敬”。《俄藏黑水城文献》在公布文献时已指出其中的“敬”字缺笔。与黑水城文献时代相当的“敬”讳,只有宋。但奇怪的是TK159为西夏文献而非宋文献②,这是西夏文献与宋代文献联系的表现?还是与如“任得敬”类曾在西夏历史上权倾朝野的人物有关?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以上有关黑水城出土版刻文献避讳字的考证,虽然零乱分散,数量有限,但涉及到宋、辽、夏、金等朝代,在避讳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仍有一定的价值。
首先,补充了一些新的避讳字。“常”、“顺”、“洪”、“烧”、“晓”、“擁”等皆为首次出现。其中的“常”、“顺”为夏讳,“洪”、“烧”、“晓”、“擁”为金讳。
其次,由于文献形成的历史时期的特殊性,黑水城文献有如“明”这样辽、夏两个朝代都避讳的字,也有如“擁”这样出现在西夏文本中的金讳,还有如“敬”这样出现在西夏本中但指向不明,这类字我们显然不能依据经验来判断。
另外,西夏避讳集中出现在仁宗及涉仁宗时期文献的现象也值得注意,尤其是其中的“明”到底是不是源起于元昊避父讳,也要重新思考。
注释:
①有关TK6《吕观文进庄子义》,傅增湘在《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该文献中“‘玄’、‘匡’字缺末笔”;汤君《黑水城文献〈庄子义〉考》(《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一文在“玄”、“匡”之外,又发现“‘敬’‘殷’‘恒’‘贞’等字皆缺末笔,‘煦’字亦一律作‘呴’”;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又补充了缺笔的“筐”。有关TK7《广韵》,聂鸿音《俄藏宋刻〈广韵〉残本述略》(《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一文指出其中的缺笔字有“玄”、“朗”、“珽”、“敬”、“弦”、“胤”、“炅”、“侦”、“遉”及及含“玄”诸字;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聂文基础上又补充了“匡”、“殷”、“竟”等。有关TK290《新唐书》,《俄藏黑水城文献》指出其中的“贞”、“匡”、“玄”、“伏”、“吴”等字缺笔。有关TK316,段玉泉《黑水城文献〈资治通鉴纲目〉残页考辨》(《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一文指出其中的“桓”字缺末笔。有关TK322.5,段玉泉《俄藏黑水城文献〈初学记〉残片补考》(《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其中的“玄”字缺末笔。有关Or.8212-1243《春秋正义》,段玉泉在《英藏黑水城文献Or.8212-1243号残页补考》(《文献》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其中“玄”字缺笔。
②佟建荣在《黑水城所出的一组原刻与翻刻实物资料——〈夹颂心经〉考察记》(《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中指出:黑水城出土的TK158、159为一组原刻与翻刻资料,其中的TK158有年款“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八月壬申朔陆文政施”,为西夏刻本。再从内容结构看本身看,此佛经在经文正文前加有“金刚经启请”内容,分题下皆有“颂曰”二字,此类型经文现目前只见于西夏作品,是西夏编撰的佛经文集。所以,TK159为西夏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