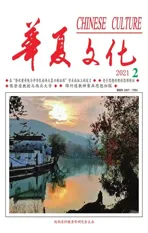“宠”的多重面相——侯旭东《宠》读后
2021-11-25王成伟
□王成伟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原是侯旭东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长文,后经删补,于2018年1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围绕贯穿于西汉时期的信—任型君臣关系展开讨论,考察这一关系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循环过程,解释了这一关系长存的背景、动因与基础,以及在这一视角下所构建的西汉历史。作者以古今相通的人性为行文纽带,重视湮没于历史深处的非理性因素,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史,为摆脱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
作者重新解读史料,重返历史现场,梳理出时人围绕“宠”形成的言行逻辑。本书主要分析了信—任型君臣关系的表现、展开、原因以及拓展。书中前三章首先审视西汉的君臣关系,将君臣关系分为礼仪型君臣关系和信—任型君臣关系,并通过穷举式的个案“深描”(thick description),呈现出以个人情感为基础的君臣亲近关系,“宠”便是对这一关系的高度凝练和特征概括。不同于信—任型君臣关系的是,礼仪型君臣关系是国家构造中的普遍性君臣关系,是经过正式册命确立的关系,通过这种渠道所形成的君与臣,大多是在例行公事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接触与互动。尽管礼仪型君臣关系下的臣子不能直接而频繁地进入皇帝的私人生活圈,但例行公事上的接触,也会使臣子逐渐受到皇帝的宠幸。在此基础上,礼仪型的君臣关系转换为信—任型君臣关系成为可能。事实上,作者在案例分析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同样的,以宠信为基础、以任命为结果的信—任型君臣关系亦可以转换为礼仪型君臣关系,臣子被皇帝委以官职后,臣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就一番事业。
因此,礼仪型君臣关系和信任型君臣关系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明确的界限,模糊的关系边界增加了臣子命运的偶然性。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往往在君与臣的人际关系中扮演主角,站在人性的角度上看,皇帝对那些既精明能干又能够处处替皇帝着想的臣子自然抱有好感。例如文景时期的晁错,入朝以来,因削藩和改革法令而“书数十上”,尽管文帝没有听从,“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景帝即位前,晁错“以其辩得幸太子”,被称为“智囊”。景帝即位后,凭借多年的君臣交情,晁错一跃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所以,晁错受两代帝王之宠并非偶然,依靠的正是超群的文化素养,在此背后也暗含着晁错职位的迁转。换言之,起初为礼仪型君臣关系框架下的晁错,凭借一流的政治才能获得皇帝的关注和重视,转而进入信—任型君臣关系的框架,而这一关系框架又给晁错带来了职位的升迁,强化了文帝、景帝与晁错的礼仪型君臣关系。
起源于礼仪型君臣关系框架下的晁错,以文化素养为后盾,很容易成为皇帝的宠臣。然而,在受到君宠后,将潜藏的才能爆发出来的臣子则相对较少,但亦有名垂青史的人物,例如武帝时期的卫青。骑奴出身的卫青身无尺寸之功,亦无多少文采,他依靠其姐卫子夫的受宠,意外地获得了武帝的宠幸。不过凭借君宠而进入礼仪型君臣关系框架下的卫青,并未停止进取的脚步,也没有因倚仗君宠而目无百官。从元朔五年(前124)春征讨匈奴班师后的情形便可见一斑。卫青凭军功受封大将军,在感慨皇恩的同时,亦流露出一丝不安,似乎是信—任型君臣关系给卫青带来了不稳定的感觉,使卫青迫切希望以军功来巩固君臣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卫青与武帝共同构建的信—任型君臣关系框架则逐渐出现了礼仪型君臣关系的特点。
从卫青的成长史来看,源于信—任型君臣关系框架下的臣子,随着潜在才干被激发,逐渐受到皇帝的重用。宠臣身居要职,使信—任型君臣关系变得不再单纯。故而以晁错和卫青二人的案例来看,信—任型君臣关系和礼仪型君臣关系不能完全割裂,这两种关系不仅界限模糊,而且可以相互转化;一旦臣子同时走进这两种关系的框架之下,必然形成权倾朝野的政治局面,因为他既有接近皇帝的机会,又有掌控朝政的能力。但这样的臣子并不一定会威胁皇帝的统治,一方面与臣子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素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建设、皇帝对君臣关系的定位以及皇帝个人的权力控制力有密切的联系。
在本书中,作者将“宠”和“信—任”视作“王朝中‘结构性的存在’,皇帝与诸多臣民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这种信—任型君臣关系贯穿于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古今相通的人性,成为今人与古人对话的重要基础,以熟人社会为特色的古代中国,皇帝也在建立属于自己的关系网,没有任何一代皇帝是孤立于宫廷之上的。作者以西汉为切入口,只是对这种信—任型君臣关系的一种进行尝试性研究。对于其他朝代而言,以往亦有学者研究这种情感化、非理性的君臣关系,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解释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便是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和张彦晓的《信任与荣宠:宋代留身制度述论》。仇书选取了魏晋易代的历史瞬间,分析了作为曹魏政治权势网络成员的司马氏家族的关系网,继承了曹魏政治网络的西晋政权,为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将魏臣转化为晋臣的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的。司马氏家族由“宠”的被动地位转换为主导地位,从“争宠”的角色走向君臣关系的中心,极大地影响了两晋的政治文化。若将信—任型君臣关系的框架放置到魏晋易代的时期,可以发现,晋朝的建立孕育着士族的兴起和“世官”现象的普遍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宠”不再只是由皇帝的个人喜好所决定的了,皇帝的近臣以血缘为基础,以承袭的权力为后盾,成为信—任型君臣关系的主导力量,使信—任型君臣关系畸形化,破坏了信—任的链条。这样的君臣关系,表现出西晋时期君权膨胀受限的政治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晋之后中国南方近300年的政治走向。
而宋代的留身制度,则不同于魏晋时期“宠”的面相,宋代的信—任型君臣关系由皇帝主导。留身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是君宠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皇帝对臣子控制的强化。而从留身制度的执行效果来看,“亲贤臣”的皇帝,留身则为正义之臣所发扬,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便资于治道;反之,留身则为小人所利用,祸乱朝政。因此,宋代的“宠”,相较于魏晋而言更具有两面性,“宠”的主导权受到皇帝的绝对支配,皇帝的意志直接影响到留身制度的执行效果。事实上,宋代中央政治生态呈现出的集权特征,很好地表现在留身制度上。皇帝对臣子的宠幸,使皇帝冲击了宋代的政治生态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排挤,助长了官场中的争宠之风,造成政治生态的局部恶化。故而结合西汉、魏晋和宋代三个历史片段,可以勾勒出“宠”和“信—任型君臣关系”的政治文化意义:皇帝通过“信—任”,不仅体现了选择宠臣时的态度与偏好,而且彰显了权力的至高无上,一旦这种“信—任”链条断裂,则意味着皇权的衰落,而“信—任”关系的确立,也使得国家的命运充满了随机性,贤臣辅政,则国泰民安;奸佞当道,则民不聊生。
纵观全书,《宠》可以说是作者在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新突破,也是近年来将社会学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成功案例之一,复杂社会关系网络被应用于西汉历史的研究体系中,展现出西汉历史人物的血肉形象。“宠”的研究模式,为学界探索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提供了新的角度,作者以西汉时期的“信—任型君臣关系”为坐标系,从人的关系网络出发考察西汉王朝的历史脉络,而魏晋之际和宋代的“宠”,则呈现出另一种人际网络的历史面相,这种面相体现着时代的历史底色,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宠”的历史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