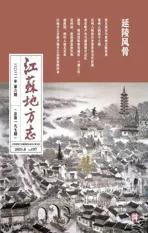行脚南京
2021-11-25◎吕峰
◎吕 峰
(江苏徐州 221006)
六朝古都的南京,金陵霸气已消,剩下的只是平和厚实的一种庄重,被历史擦亮的一抹斜阳给人一种静谧的安详,如清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说的那般:菜佣酒保皆有六朝烟水气。去南京,哪怕只是走马观花,哪怕只是浮光掠影,都会让人感到温暖无比的烟火气息,像宿醉之后的一碗温热的稀粥,熨帖,滋润,舒泰身心。
昆曲·良辰美景奈何天
昆曲,一种精致典雅的艺术,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六百年前,昆曲来到南京后,在历史的嬗变中,逐渐成为南京的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在南京,你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昆曲特有的魅力。
明清以来,昆曲与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出现了兴化部、华林部、李渔家班、曹寅家班等名扬全国的专业昆班,且清音小部和文人唱曲之风亦绵延不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每天都要欣赏《琵琶记》。明人汤显祖在南京生活了七年,写出了《紫钗记》传奇;清人孔尚任以秦淮名伶李香君为摹本写了《桃花扇》;闲情大家李渔在南京生活了二十年,营建了芥子园,在园子里自编自导自演,刊行了《笠翁十种曲》,蜚声清初剧坛,所谓“十曲初出,纸贵一时”。
昆曲一度因过于风雅繁难的表演风格而走向没落,如今它又重新散发出迷人的魅力。白先勇先生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气概,重新演绎《牡丹亭》。此后,《牡丹亭》 《西厢记》 《长生殿》等剧目纷纷在世界各地排演,一时间昆曲成为热门的词汇,从网站到手机彩铃,都能听到昆曲的吟唱之声。在南京,几乎处处可闻悠扬的昆曲声。听着昆曲,可体会到南京的性格,也可了解南京的历史与未来。
一次,行脚南京,朋友带着去朝天宫江宁府学欣赏了一出精妙绝伦的《牡丹亭》。在一片现代的高楼大厦之中,一处古色古香的清静院落,不朽的爱情传奇,在宁静的水面中的古戏台上娓娓道来,没有麦克风,没有扬声器,演员全靠嗓子和身段,裙裾暗香迫近眼眉,曼拂轻纱构成了恍惚如生的意境。表演者的动作语言细腻丰富,俯仰之间,绰有态度,一颦一嗔,皆有神韵。现场也没有伴奏带,唯有乐师的现场演奏,贯耳即闻曲笛幽咽,丝弦婉转如琢如磨,无法挥去的古意交缠着无限的幻想扑面而来,那种惊艳之美似乎瞬间即飞至眼前身边,带来妙不可言的观剧感受。
夜晚,漫步在南京城,古老的昆曲灵活地以一种韧性的状态存在着,实在难得。歌榭,茶楼,剧场,均可听曲,虽然这些表演不能算是炉火纯青,可是给外行听听,也是足够的。听着听着,一颗浮躁的心忽地就静了下来,稳了下来,城市的喧嚣与嘈杂,人生的不快与烦闷,全都消失殆尽,一种老南京特有的静谧闲情,便从心底深处徜徉开来。
有一家茶馆竟以牡丹亭命名,走进去,素素的窗帘茶几,沙发的抱枕上绣着牡丹,一朵、半朵娇艳地开着,粉白的,鹅黄的,黛紫的,甚为雅致。墙壁上悬着诸多与昆曲有关的图片,最喜欢那些演出的海报,每一个角都光彩照人,都光芒四射。走进去,我立刻喜欢上了这种淡淡如水的清素之气、清雅之气。坐下来,泡了一壶南京的雨花茶,清正素淡。音箱里的曲子如浊世里的清音,唱词或清妍,或艳丽,字字珠玑。茶香袅袅间,低吟浅唱里,六根清净,恍若误入桃花源中。
昆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观赏,看不懂不要紧,看得不大懂也不要紧,只要身心愉悦,即达到了目的。一次,我在一位朋友的驾驶室里发现了几张昆曲的碟片,以为遇到了知音,谁知朋友却说他不懂昆曲。他告诉我,之所以存有昆曲的碟片,是因其好听且耐听,“它们的节奏很慢,甚至可以跟着哼唱,开车时,可放慢速度,避免事故”。刹那间,我明白了,昆曲表达的是一种闲情逸致,檀板笛声,阵阵悠扬,带出了中国文化中最婉约最柔软的部分。
很难有一种艺术像昆曲这样,曲高和寡却绵延不衰,也很难有一种艺术像昆曲这样,荣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无狂喜过望,照旧以原有简单的形式被吟唱着,颇有些“青山元不动,白云自去来”的意境。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也有人说,这才是所谓的道行。其实,我们所爱恋的昆曲,就是活生生的娇美容颜,就是清亮亮的婉转歌喉,就是万方的仪态和毫不屈就的矜持,它能带来衣香鬓影、曲笛幽咽的非凡感受,去领略跨越时空的动人力量。
南京已经洗脱浮丽,不需要张扬,自有大家气派,正如省昆的风格,不标新立异,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功底深厚。“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到了南京,如果不到朝天宫江宁府学听一出昆曲,那无论如何都是一件遗憾的事。
秦淮河·六朝烟水溢金陵
秦淮河,一条闻名遐迩的河,也是一条弥漫着浓郁的历史气息和人文气息的河。它环绕着金陵古城,不知疲倦地流淌了两千余年,也滋润了两千余年。两千余年的时光太漫长,它也因此经历了无数的历史变迁和人世沉浮,既有无尽灿若星辰的繁华,也有繁华逝尽的苍凉。如今,这条依然汩汩流淌的河,成了南京这座古都的文化标签,它留下了太多的故事,让人去寻觅,去缅怀,去回味。
相传,秦淮河为秦始皇南巡时所开凿,引淮水入城,故得此名。从此,秦淮河即与秣陵、建康、金陵、南京联系在了一起,且一直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如文人雅士所称颂的那样,“锦绣十里春风来,千门万户临河开”。在人们的想象中,秦淮河当是一条波宽浪高的大河,去了之后,才发现它竟是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河沟。河面相当于一条道路的宽度,两岸是吸引人目光的秦淮人家。那些房屋是清一色的粉墙黑瓦、飞檐翘角,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层次分明,水墨画般的典雅。
对秦淮河,我是充满向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那些脍炙人口、余音在耳的锦绣文章,或诗,或文,或曲,都已熟记在心,如杜牧的《泊秦淮》,如刘禹锡的《乌衣巷》,如王安石的《金陵怀古》等,最让我难忘的是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皎月方来,桨声汩汩,这是何等的风神别具,令人无限神往之。
第一次去秦淮河,是在白天。因时间的原因,只匆匆地走访了江南贡院、夫子庙、媚香楼、乌衣巷、朱雀桥等。虽是匆匆的一瞥,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南贡院从建立开始,即担当着为国选才的神圣使命,也曾是无数寒门学子们驻足仰望的殿堂。在贡院里,我听到了唐伯虎、郑板桥、吴敬梓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像流星一样划过江南贡院的夜空,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闪耀着启迪后人的光芒。
从贡院出来后,我喜欢站在朱雀桥上看乌衣巷,看那些高墙黛瓦的深宅大院。“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刘禹锡对王谢家族由显赫一时到最终没落的由衷感叹,更是秦淮河两岸历史变迁的真实写照。如今,昔日的豪门大宅变成了寻常的百姓人家,巷子两侧的铺面成了民间工艺品店,也让我真正明白了“繁华亦有落尽时”。此外,在李香君的媚香楼,我感受到了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秦淮河畔那些青楼女子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她们像一株株喋血的桃花,芳华绝代。
因为朱自清和俞平伯的文章,我更喜欢夜色下的秦淮河。后来,终于得偿所愿。夜幕落下后,河两岸的灯渐次亮了起来,印在河里,水面出现了无数交相辉映的灯盏。泛舟其上,夜色迷离,远处传来丝竹管弦声,极有昔日秦淮河的味道。泛舟秦淮河,沿途的古迹颇多,印象最深的是名为桃叶渡的古渡口。遥想当年,大书法家王献之伫立秦淮河岸边,将他对爱妾的相思全部融进了那首“桃叶复桃叶,渡江无舟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的诗里,不禁为之神往。
秦淮河自古即是文人骚客的聚居地,河两岸酒家林立、商船昼夜往来,勾栏瓦舍夹杂其中,那些寄身其中的乐伎歌女,轻歌曼舞、丝竹缥缈、灯红酒绿,文人才子流连其间,从此拉开了风月金粉的序幕。李白、王昌龄、岑参、杜牧、王安石、苏轼、孔尚任、曹雪芹、吴敬梓等都曾先后来过此地。在无穷的波光灯影中,我来到了根据史料记载复建的王昌龄夜宴处,一座宽阔的厅堂面河而开,门前有王昌龄拟写的对联“门映淮水绿,月照金陵洲”。厅堂里有王昌龄、李白、岑参的塑像,身临其境,像置身于大唐的盛世之中。
在秦淮河玩累了,可弃船登岸,夫子庙周边茶楼饭店云集,小吃满目皆是。秦淮八绝、小笼包、煮干丝、如意回卤干、什锦豆腐脑、状元豆、南农烧鸡、糖芋苗等,都让人垂涎。黄裳在《金陵五记》中形容道,“那拥挤的人群,繁盛的市场,那种特有的气氛,是只有夫子庙才有的”。一碟桂花鸭,一碗鸭血粉丝汤,一笼小笼包,对着秦淮河的夜色,真的是快意至极的人生体验。
余秋雨在《五城记》里这样写南京:“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确实如此,一条千年流淌的秦淮河,浓缩、沉淀了南京所有的历史,既有朝代的更替,也有人事的兴衰;既有繁华落尽的王谢楼阁,也有荡漾碧波的金粉画舫;既有数不尽的刀光剑影,也有无数的风花雪月;既有商女的歌舞升平,也有“秦淮八艳”的亡国之恨,蔚为大观。
历史一页一页翻过,时光一年一年走过,秦淮河那一汪水兀自地流淌着,秦淮河畔的故事亦将被一代代人演绎着、传诵着。
栖霞寺·禅宫遥对石城开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这句诗既是南京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也是人们对当年佛教兴盛的追忆。时光已逝,在南京繁华印记的背后一直氤氲着挥之不去的禅韵,每一座山几乎都屹立着一座寺庙,如鸡笼山有鸡鸣寺,钟山有灵谷寺,雨花台有高座寺,清凉山有清凉寺,栖霞山有栖霞寺,牛首山有宏觉寺,山是名山,寺是名寺,山与寺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引人去探寻。
栖霞寺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集山、林、寺于一体,山上山下、寺内寺外,草木葳蕤林立,环境清雅,为寻幽探胜的绝佳去处。早春,栖霞寺迎来了山寺桃花盛开的绝妙时光。山上山下散布着一株株灼灼其华的桃花,它们将山峦、将古寺、将幽潭装点成了粉色的梦境,亭台楼阁、飞檐黑瓦,掩映其中,美不胜收。满树的繁花堆云叠雪,映衬着黄色的庙墙、斗翘的飞檐,给人一种极度震撼的美。风中裹挟着挥之不去的花香,若有若无,却始终萦绕在鼻翼。只需自然地呼吸,即能将那份香吸入腹腔。
“茶煎谷雨春”,春日亦可来栖霞寺喝茶。茶是新茶,那些新叶上下翻滚、浮沉,汤色清脆,茶味清幽。等水定了,茶叶都站了起来,齐刷刷地,像养了一杯子的小树苗。面对绿莹莹的满杯碧色,像是在饮春水,悠悠然不可名说。栖霞山的茶极具名声,为南茶文化的发祥地,茶圣陆羽曾居于栖霞寺,上山采茶,并在寺里写成了《茶经》初稿。试想一下,松下拾枝,泉边汲水,烧柴煮茗,何等之惬意。此时,我的神经舒缓了,我的目光迷离了,像魂游天外,迷醉在青山绿水间。
在栖霞寺喝茶,满眼即是山景,茶香与梵音相得益彰,光阴仿佛在一把小小的茶壶里展开、铺陈。与禅师对坐,茶香袅袅间,听禅师讲茶。“茶遇水舍己,而成茶饮,是为布施;叶蕴茶香,犹如戒香,是为持戒;忍蒸炒酵,受挤压揉,是为忍辱;除懒去惰,醒神益思,是为精进;和敬清寂,茶味一如,是为禅定;行方便法,济人无数,是为智慧。”一时间,似乎走进了茶的纵深处。
“名山与高士,人地两相倚。”栖霞寺发端于南齐隐士明僧绍的“舍宅为寺”,初名栖霞精舍,后扩建成寺。因他的无私,才有了一座记录了半部金陵史的寺庙,堪称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行走在栖霞寺,历史遗存随处可见,散发出绵延不绝、薪火相传的古韵气息。舍利塔为南唐遗物,亦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石塔,塔身上的佛经故事虽经风雨的剥蚀,依然鲜活灵动,成为金陵佛气长存的千年佐证。
千佛岩是南朝石窟,佛像依山崖而凿,有佛、有菩萨、有天王、有力士、有飞天、有供养人等,气势壮观,线条流畅,人物丰满,极具魅力。一尊尊佛像仿佛都有生命,都有着自己的呼吸和脉搏。可惜的是,有的浮屠石刻已破损斑驳。即便如此,仅仅那些残存的现状,足以让人感慨先民的智慧。摩挲着残存的石像佛身,精美的线条、飘逸的衣褶,让人产生鬼斧神工般的惊奇,并在心中生出一份敬仰。
去栖霞寺,最好是在深秋,层林尽染的枫叶将古寺装点得如霞似火,美轮美奂。徜徉寺内外,一边看着色彩斑斓的枫叶,一边听着古寺的梵音,心中不免多了一份悠远古朴的宁静,妙不可言。一次,与朋友在寺里走着,天上落起了雨,遂寻一处回廊听雨。雨是细雨,落在屋顶,声音时有时无,那微响、那低语,从屋顶上荡漾开来,回声从空寂的四周围拢来。我和朋友坐于回廊里,仿佛浮于烟云之上,四下无人,凄迷的雨丝,飘荡着禅意,让我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处何地。
往事越千年,栖霞寺历经沧桑,迭有兴废。如今,寺庙又焕发了勃勃的生机,拥有了俯视一切的姿态和随时萌生的美感。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栖霞寺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都有禅韵。踯躅在栖霞寺,好像沉浸于无边的静谧里,内心的喧嚣如潮水般退去,整个人都清爽了起来、轻盈了起来,有置身禅宫净土的世外之感。那种际遇、那种感受无法用语言描述,让我不禁轻声念起唐人皮日休的诗:“泉冷无三伏,松枯有六朝。何时石上月,相对论逍遥。”
禅宗四祖道信曾说:“快乐无忧,是名为佛。”行脚栖霞寺,那是一个久远的梦,无论是稽考摭拾或稗乘野史,无论是亭台楼阁或繁华浅草,无论是佛像雕塑或摩崖石刻,都可以演化出许多美丽的故事,让人萌生许多的感动。栖霞寺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禅香在鼻,禅声在耳,禅韵于心,一日沉迷,足抵十年的尘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