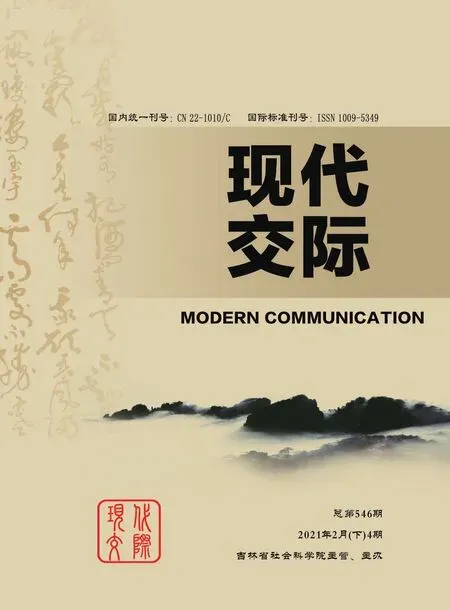浅析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的演进逻辑
2021-11-25管予祯
管予祯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贯穿主流哲学研究,而且总是成对出现。在哲学中,这样的“对子”并不少见: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社会与个人、无限与有限、“一”与“多”……这些“对子”的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研究的问题也是同一个。透过这漫长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较其他哲学更为纵深的思想与实践格局。
一、古希腊哲学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的解读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上泾渭分明地将两者对立起来,只选择其中一个进行讨论。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是一”的命题,在他看来,以往的“存在”是特殊性的存在,是短暂的、有限的“多”,而他追求的“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一”。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用“阿基里斯追龟”和“飞矢不动”进一步对巴门尼德的存在哲学进行辩护:如果“存在”不是“一”而是“多”,就会形成悖论。智者学派则大多在谈论“多”,关注不断变化的特殊性存在,并将它们用抽象的方法描述出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正是他们的重要论断。
柏拉图在批判智者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了“理念论”。他将具有普遍性的“理念”预设为真理,现实的、特殊性的东西都是“理念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讲,柏拉图并不是一个二元论者。他虽然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严格区分,但是“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产物和附属。他将“理念”作为方法论来研究现实,用“理念”所代表的“一”批判现实的杂多,并引导现实不断向“理念”靠近。因此,柏拉图同巴门尼德一样,全面肯定普遍性的真理,不断贬低特殊性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思想,提出了“四因说”,并最终将其浓缩为“形式质料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规定了事物的本质,包含着事物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因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决定性的因素;质料则是消极的、被动的、被决定的因素。形式把质料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个有定型的个别实体。形式合成质料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因此形式是真正的实体,最高的形式是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质料虽然是最低等的“多”的存在,却也没有像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一样完全被灭失。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相较前人而言有一定的进步性。
二、中世纪宗教哲学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的解读
早期的中世纪宗教哲学是柏拉图主义的产物。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这一“彼岸”固化为天国,现实世界作为“虚假的存在”完全被消解。中世纪宗教哲学发展到经院哲学时期,逐渐划分出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别:唯实论者主张普遍的是真正的实在,个别的东西不过是现象;唯名论者则认为个别的才是真实的,所谓的普遍不过是概念、语词而已,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唯实论和唯名论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完全对立,只关注二者的区别,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显然是极为狭隘的。虽然在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上唯实论与唯名论都没有取得创新性的成果,但它们的对立为近代哲学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三、近代西欧哲学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的解读
哲学发展到近代,脱胎于唯名论的经验论与脱胎于唯实论的唯理论在认识的来源这一问题上的争论是时代的主旋律。经验论者主张个别且杂多的感觉经验为知识提供了来源,认识的过程开端于对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感觉经验,通过经验归纳的加工,进而获得普遍必然的真理。唯理论者则否认经验的作用,认为知识必须建立在普遍的理性基础之上。唯理论者将不言自明的天赋观念作为认识的来源,在经过一系列的理性演绎后形成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显然,在认识论领域里经验论和唯理论各执一端,都是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缺乏辩证的综合眼光。但是相互对立的两派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在反对宗教神学方面却是一致的,这也正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历史先进性所在。
四、德国古典哲学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的解读
康德毕生致力于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矛盾,也是哲学史上第一位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平等对待的哲学家。康德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拿到认识论领域来解决。他认为知识的来源有两个——先验与经验,先验是理性的,经验是感性的,所有知识都以先天综合判断的形式存在。“先天”是普遍的理性,范畴是它的工具,“综合”依靠个别的、特殊性的现象获得感性经验。对认识活动的主体来说,先验的范畴存在于主体的头脑之中,用来保证获得的知识具有先天性和普遍必然性,个别且杂多的感性经验提供认识的材料,经过范畴的加工整理从而使主体获得知识。因此,知识的形式是先天的,内容则是经验的。在康德那里,知识不是简单的对外在事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由主观建构起来的。康德以独特的方式突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动性,让对象去“符合”知识,具有“哥白尼革命”式的意义。康德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调和对立的两种认识论,首次尝试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
遗憾的是,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和谢林都不具有这种调和、统一的意识。费希特继承了康德的建构主义,将主观建构发挥到了极致。康德预设了“物自体”作为感性经验的起点,费希特则用“自我设定非我”的命题取消了具有特殊性的“物自体”。他认为包括“物自体”在内的一切特殊的、经验性的“非我”都是由“自我”通过先天范畴设定、整理而来的。如果说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只是否定特殊性的作用,谢林的“绝对同一”则是要将特殊性从哲学中彻底驱逐出去。谢林认为哲学必须发端于一个主体与客体不曾分离的、绝对同一的本原,代表普遍必然的理性是派生一切的唯一本原。谢林认为,“在黑夜里,所有的奶牛是黑色的”,可见他所追求的是无差别的、最高的“一”。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多”作为“不合法”的存在,应当被完全消灭。费希特和谢林都是只关注普遍性并将它发挥到极致,不关注特殊性甚至试图消灭它,这种片面的做法显然不是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的最佳方案。
康德用先天综合判断来调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种做法在黑格尔看来,只是像“用抽屉装杂物”一般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在这里“抽屉”代表先验范畴,“杂物”则是感性杂多,康德将感性杂多简单而机械地用先验范畴进行包装,但二者的本质都没有实质的改变,特殊性还是个别的存在,普遍性还是一般的存在,并没有实现有机的、完全的结合。针对康德的不足,黑格尔在辩证法的逻辑体系下,采用“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推演方法,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黑格尔将谢林所定义的、不包含任何差别的、绝对的“同一”设置为“正题”,“正题”中的普遍性是最初的、抽象的、无物存在的“一”。这样的“一”逐渐发展变化,差别开始显现,特殊的、个别的、杂多的、感性的存在是黑格尔的“反题”。作为“正题”的普遍与作为“反题”的特殊共同发展,最终的结果是两者有机结合,得到包含着特殊的、更高级的普遍,得到以“多样性的统一”为内容的“合题”。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普遍性与特殊性都具有合法地位,并且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普遍性具有了区别于以往的、更为丰富的内涵,普遍性与特殊性实现了实质上的结合。在认识论的问题上,黑格尔同样是这种历史的、变化的辩证思维。对于真理问题,以往哲学的“真理符合论”被黑格尔的“真理过程论”所取代,实体与主体相统一,实体获得了主体的能动性与发展潜能,为其发展为更高的实体提供了无限可能。在黑格尔那里,普遍性较特殊性而言更为重要,个人是差别性的、特殊性的存在,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于普遍性之中,普遍性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绝对精神。可见,黑格尔的解决方案是宗教式的,他将包含着特殊性的普遍性设定在虚无缥缈的彼岸,只是在思维逻辑上实现了二者的统一。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的解读
黑格尔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虽然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但却局限在思辨领域。马克思将这一问题置于现实中,将原本处在彼岸的真理放在此岸来获得,在有差别的现实世界中实现普遍。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理论是一元论,而经常出现的是二元论思想。二元论思想出现的原因是哲学家们将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观念论,独立了出来,并将其作为前提来讨论,用固定的、现成的、死板的常识性思维去认识世界,专注于认识论,不断追问世界究竟“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预设论。马克思认为预设论犯了顺序性的错误,前提与结果在预设论那里本末倒置,预设的、固定性的东西应当是结果而不是前提,它是由某种原因造成的,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所坚持的是生成论,用活的哲学性思维去实践一切美好,并在实践中改造世界。
在马克思一元论的思想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是绝对对立的,哲学的工作就是在现实中通过实践将二者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以“人”为例,传统哲学通过抽象的思维方式,将“人”定义为特殊的、个别的存在,社会被认为是普遍性的代表,他们对人的本质有着各种直观、机械的猜测,并试图在个别的、特殊的人的身上寻求答案。如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良心、理智和爱,鲍威尔认为是自由,施蒂纳认为是“唯一者”……这些都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预设论。在他们看来,人如果要成为人,需要做的只是去“符合”预设,不符合预设的人是“例外”,这显然荒唐至极的。良心、理智、自由等一切美好的事物不是像预设的那样生来就有,而是在现实中不断实践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马克思否定了以往哲学家们从有差别的个人身上寻求人的本质的方式方法,二是他给出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内涵——“个人是社会存在物。”[2]马克思不把人的本质当作预设好的东西,认为人的本质在社会关系中得到体现。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的本质是不相同的,这是因为个人在进入社会之前必须具有社会性,不具备社会性的人不可能融入社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是社会的、动态的、历史的、实践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等同于社会,有差别的、特殊性的个人与普遍性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普遍性与特殊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马克思与黑格尔最大的不同在于,黑格尔局限在思想理念领域,而马克思则转换视野,在现实中寻求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真正的统一——共产主义的方法。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没有问题,理想与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一场运动而不是一个目标。虽然彼岸的理想难以实现,但是此岸的实践不能因此停滞不前。因此,理念只有批判的意义,却没有建设的意义,只是一种样本和标尺,马克思要做的是在有差别的现实世界中去实践、去实现,去把理念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