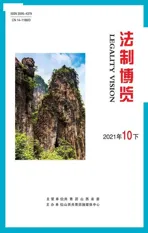实务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界定
2021-11-25齐立霞
齐立霞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一、问题由来
2019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发布,专门就行政协议案件的起诉、受理、审判等诉讼活动进行了规定,但该文件的发布并没有平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界定的争议,反而在实务届激起了更为广泛地讨论。有人认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协议,因为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实施之前,一旦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出让合同,行政机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利于国家土地利益的保护,因此当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只能按照民事合同对待。而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实施后,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协议享有优益权,如果相对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处理决定,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原来的问题就解决了。目前来看,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笔者认为,这种倒推认定法可以作为支持行政协议的理由之一,但决不能因这种倒推而认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因为此时合同性质的认定,已经不仅限于能解决法律困境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审判路径的选择,何种性质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是如何在多种可保护的法益之间寻求平衡。
二、不同审判路径的差异
(一)民事合同
如果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界定为民事合同,那么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基于平等的法律地位签订的合同,在诉讼中双方是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的。双方均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诉请范围也比较广,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继续履行合同、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等。在处理方式上,与民事争议区别不大。对于判决结果,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但是否适用调解的问题,值得讨论,根据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依法进行调解。那么在民事案件中审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当然可以调解。与行政协议一样,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时,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1]
(二)行政协议
如果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界定为行政协议,那么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双方是基于行政管理关系签订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在诉讼中双方地位是不对等的。诉讼中,只能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诉讼,行政机关没有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但是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处理决定,并在符合条件下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两者对比,我们发现,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的界定,关系到行政机关是否享有行政优益权,关系到行政机关能否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三、法律规定与审判实践中的处理
(一)认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系行政协议的主要理由:《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土地管理法》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方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土地使用者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十五批指导性案例》中第76号案例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行政协议案(前文提到的研读案例),该案涉及合同的解释问题,承办法院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作为行政协议进行了审查。但其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为行政协议,并非该案审查的焦点,能否以该案认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行政协议有待商榷。
(二)认为国有建设用地属于民事合同的主要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年11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334次会议通过,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修正)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纳入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2020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1次会议通过),仍然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合同纠纷作为民事合同案由中的子案由进行规定。2017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和2020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均采用列举法列举了行政协议的范围,也是仅将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特许经营协议等进行了列举,均没有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协议。而在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制定和发布过程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的性质问题已经争议比较大,司法解释在列举时仍然回避了这一合同,其用意耐人寻味。[2]
笔者认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案件按民事纠纷处理较为适宜。一是从权利保障角度,作为民事合同处理,由双方以平等主体身份经过民事质证、辩论,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非诉审查案件多数是书面审查,即使召开听证会也只是针对部分案件事实,与开庭双方公开质证相比,调查的全面性、深入性必然受影响。尤其是目前房地产解疑项目较多的背景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签订的背景较为复杂,行政非诉审查难以较为全面调查案件情况。二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与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合同有一定区别,后者在合同履行中的行政色彩较浓。《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仅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即出让前供地需审批环节,一旦出让合同相对方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其按照合同约定缴纳土地使用金并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土地,即可完成合同履行。合同履行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矿产权等国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合同签订后,取得矿产使用权的一方需依照规定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等审批手续,方能取得采矿权,进行开采。采矿许可证的审批和使用期限决定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合同履行过程中受到的行政监管较多,政策性强,合同具有短期性、不稳定性等特点。三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履行过程中无明显的行政管理内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前,行政审批、核准环节较多,一旦土地规划经过审批,符合出让条件后,受让方只需要依照合同约定缴纳出让金,依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受让方的义务较为明确、单一,中间不涉及行政机关具体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内容,双方违约行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四是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作为行政协议,据此作出履行行政协议的《决定书》,进入非诉执行程序,缺少法律依据。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兜底条款,难以包含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且根据最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等文件,并未对之前(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发布以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照民事合同纠纷的性质对待的问题作出改变。五是考虑到各法院的实际情况,由民事法官审理较为妥当。[3]
综上,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界定并未明晰,合同性质界定,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主张方式和法院审判路径选择,目前法律规定比较健全的情况下,个人认为两种模式审理均能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同路径选择,只是侧重不同。期待实务界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尽快有最终确定,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案件审理更加规范、合理、合法,裁判尺度更加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