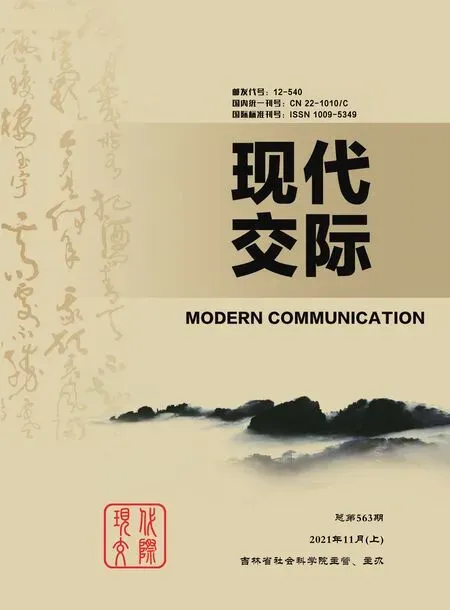网络语“××脑”限制因素的多维度探讨
2021-11-24罗顺
罗 顺
(喀什大学 新疆 喀什 844099)
从汉字字形产生、演变的过程及造词法的发生、发展角度来看,人的身体部件一直是汉语文化中汉字字形和词语单双音节变化中的源部首和源语素。古代汉语常用身体部件词有“面、口、齿、耳、目、指”六个。“脑”作为身体机能的重要器官,发挥着调控并支配整体生命活动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现代汉语中,随着认识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脑”作为身体部件的造词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增长,而是固定在一定的意义之中,反而是一些隐喻意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由于过去对“脑”的认知停留在《说文解字》的概念阐释中,而不是有科学依据的命名;二是由于隐喻作为我们生活的重要认知方式,其多角度的发展丰富、主导了我们的语言生活。因此,本文从隐喻的认知方式着手,探究以人们的认知方式、语言单位生成基础的“××脑”的限制因素为主要内容,辅以语言的语用因素进行探讨,深入地了解以身体部件为基础的网络语的发展限制。
一、认知隐喻的因素
认知隐喻作为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在汉语中也很常见,汉语常常将“脑”隐喻为一个容器,即三维空间,可以容纳东西,如“脑袋”[1]:
(1)例1:每次都不知道他脑袋里装了些啥。
(2)例2:到了考试,就会发现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少了。
莱考夫(1987)发现,在人类认知的意象图式中,“一个容器图式,即一个具有界限的图式,是有‘内’和‘外’之分的”。正因为汉语将“脑”概念化为一个容器,所以有“脑中”“脑子里”的表达,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脑的发展更多地向容器内的偏向,也因此“脑”的内外差别在容器的空间隐喻中偏向于向容器内的表达。
(3)例3:我们要把知识牢记在脑中。
(4)例4:有些东西是一直存在在我的脑子里的。
也正因为“脑”被隐喻为一个容器,所以有“脑海”“脑容量”等表达,仿佛“脑”内的空间可宽可窄、可虚可实,还可以量化。
(5)例5:脑海里的那些记忆被一次次唤起。
(6)例6:海量的知识需要更多的脑容量。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汉语常常以三维空间为原始域,构建有关“脑”的非空间目标域,将三维空间映射到“脑”上,使“脑”成为某种可以量化、可摸、可视的三维实体。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于“脑”的隐喻认知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体现在人们利用“脑”的表达大多存在于三维空间的表达中,且在三维空间中偏向于内向性的表达,缺少二维性空间及一维性空间的表达。这种封闭性使“脑”在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的结构变为一个较为简单的整体,构建的心理空间也较为简单。
以莱考夫对“理想化认知模型”为视角,探讨“脑”的空间隐喻结构化,和“脑袋”“脑子里”的表达类似,从隐喻的三维特征出发,“恋爱脑”“事业脑”这种“××脑”的使用,在空间隐喻中可以解释为:将“脑”视为容纳某一事物的容器,这里所容纳的就是“恋爱”及“事业”这两种抽象的事物。也就是说“××脑”的结构整体表达的是一个容器图式的概念,所构建的心理空间也是容器的心理空间。
这种三维的空间隐喻也可以从方位上来理解,解释为“脑子里面的东西全是恋爱/事业”,这种方位其实着重突出了其“脑”中心的位置上全是“恋爱/事业”。
二、生成词库的因素
隐喻的认知机制造成了不同的语言表达,但语言发展除了使用主体的认知影响之外,还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语义的生成衔接着结构主义到认知学派的过渡,语义的生成离不开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词语。
在生成词库理论中,词在动态组合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动态性和弹性,会通过生成机制生成多个具体的意义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在限制词库义项的数目时,学会捕捉词在上下文中潜在的无限意义,在词汇的表征和语义生成机制中对语义进行选择。生成词库理论的词汇表征最为复杂的是物性结构,物性结构包括构成角色、形式角色、功用角色及施成角色四个层面。在限制词库义项数目的时候,生成词库理论提出了语义生成机制,并基于论元的选择分为类型选择、类型调节及类型强迫三个组成部分。
物性结构与百科知识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Pustejovsky(2001)将名词分为三类:自然类、人造类及合成类。自然类通常是与物性结构中的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有关的概念,比如石头、猴子;人造类通常结合了物性结构中的功用角色或施成角色,如桌子、椅子;合成类名词或称“点对象”,由自然类和人造类组成,是一个复合概念。
根据以上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恋爱脑”“事业脑”在生成词库理论中属于合成类名词,与物性结构的各个角色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生成词库理论中,我们借用宋作艳(2010)[2]物性结构在认知语言学范畴化中的三种途径来解释新造流行词语的“生成”基础:
首先,从“恋爱脑”“事业脑”中“脑”这一源语素的单独成词的角度来看,在《现代汉语词典》[3]中主要有以下几个义项:
1)名词,动物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位于头部。人脑管全身知觉、运动和思维、记忆等活动,由大脑、小脑和脑干等部分构成。
2)头。
3)名词,脑筋。
4)指从物体中提炼出的精华部分。
5)事物剩下的零碎部分。
从“脑”的义项解释来看,基本义项“1)”中“动物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位于头部。人脑管全身知觉、运动和思维、记忆等活动”说明“脑”在身体中的位置及作用,属于物性结构的功用角色;“大脑、小脑和脑干”说明其组成部分,属于物性结构中的施成角色、构成角色。粗略地来看,义项“2)”和义项“5)”都是人们在认识上对“脑”的形式体现,属于物性结构中的形式角色。基本义项“4)”中“从物体中提炼出”的属于施成角色,而“精华部分”则属于形式角色。
其次,从其定中复合名词或短语中的修饰关系来看,新造流行词语“恋爱脑”“事业脑”及原有词语“刽子手”“段子手”,修饰成分描述了事物的功用、产生方式、典型特征等,和物性结构的四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最后,从对名词和名词性成分进行分类的手段角度,即分类词角度,不难看出“恋爱脑”“事业脑”是指以一类思维方式在个人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特质总结,“刽子手”“段子手”是指以一类生存方式为谋生手段的人的特质的总结。
根据以上解释,如果将“恋爱脑”“事业脑”这类新兴流行名词称为复合类合成词,“脑”在构词上发挥着类后缀的功能。这种类后缀功能的发挥关联着语义基础与物性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即功用角色。因为人“脑”是“管全身知觉、运动和思维、记忆等活动”的重要调节系统,具有统领的功用,所以“恋爱至上的思维”和“事业至上的思维”才能以此为基础进行。这里便体现了“××脑”的造词理据及生成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假设以下构词:
(1)前+职业名词:学生脑、教师脑、医生脑、会计脑……
(2)前+动作动词:学习脑、演奏脑、销售脑、创作脑、表演脑……
基于前面我们将“××脑”的语义理解为“××思维模式”的情况,就整体性质而言,是名词性的偏正复合词。名词性的偏正复合词修饰成分有形容词、动词、数词、方位词等,这里由于数词方位词在性质和语义上无法和“脑”产生联系;因此,我们将社会特征明显的名词和主观意识强的动词作为思维模式的修饰成分放入“××脑”结构中。可以形成:(1)类社会特征明显的职业名词+“脑”的情况,(2)类主观意识强的动作动词+“脑”的情况。单纯就语言的形式和语义的组合来说,这两个方面的假设是符合构词的形式规律和人们的语义认知的。
三、其他语言因素的影响
1.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影响
汉语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有着较为完备的造字和用字系统,即便是顺应世界发展的词式书写或使用,汉语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基于人的身体构造及对身体构造的最原始的认识,在古代汉语中,最基本的身体部件在《说文解字》中是“总十二属”,显然是对于“脑”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理性认识的深入,脑的思维功能作为词汇意义的重要部分开始进入复合造词的行列。如果将在“恋爱脑”和“事业脑”之外的“××脑”构词作为潜词,其显性的因素在现代汉语发展中可能受到社会文化语用和语言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的制约。
对于现阶段的现代汉语基本的发展来讲,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下来的词语已然发展得较为完备,过去由于缺乏理性认识,对于“脑”的认识不够充分,“脑”作为人体思维功能区的重要身体部件没被发现,其思维功能大多被“心”代替,并以“心”作为基本词汇沉淀下来。因此,现阶段的“脑”只能用基本功能引申出来的“思维模式”意义进行复合构词,而不是像基本词汇那样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2.语言使用的现实制约
语言中最不稳固的使用就是词汇的使用。通常情况下,汉语是在常用词基础上对新词进行再造、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言的使用者,除开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是人们求新求异心理的需要了。在“脑”本身的使用过程中,“思维模式”的意义并不少见,最基本的就是“头脑”一词的使用,这样的词语稳定性强,没有过多附加色彩,最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
而“恋爱脑”“事业脑”在语言使用中通常具有贬义色彩,且两个词语一直活跃于各种偶像剧影评或者宣传推广中,其造词意义的极端化倾向加重了使用过程中贬义色彩的程度。具体的“××脑”使用通常出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话语中,具有不稳定性,这便使它们的使用频率受到了限制。同时,“恋爱”和“事业”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话题,其涵盖面比其下位概念中会用到的词汇要广,也因此在需要“思维模式”的言语交际和语言使用中,具有一定的难以替代性和概括性。
另外就是语言使用中可接受度的问题。新词的产生和使用通常要经过社会交际的接受,可接受程度越高,使用越频繁,反过来也会促进新词的发展和使用上的成熟。将“××脑”代入职业名词和动作动词后作为类后缀进行类推具有潜词发展的雏形,但是,如果要进入现实社会的言语交际,在现实发展中没有出现思维的极端化现象明显的情况下,前面按照语义生成可以构造出来的词属于一种潜词,潜词本身不具备较高的可接受度,也因此生成“××脑”的造词会受到可接受度的现实制约。
还有较为实际的一点就是,从修辞角度来看,这里应该还有转喻的现象,将这种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语以部分代整体,以人的性质特征代替一整类人。比如,形容一个人“他就是个恋爱脑”,我们可以进行反向思考,这句话中对于“他”的界定,实际上是将“他”归为“恋爱脑”这一类人中,而“恋爱脑”就自然成为一类人的代名词了。
总的来说,“恋爱脑”“事业脑”除具有不稳定性,贬义色彩明显的特点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难以替代性和概括性。同时,同类其他造词的可接受度低也成为语用的现实制约,修辞手法作为语言艺术化的手段并不是所有交际活动必须使用的,这进一步加深了“××脑”在语用上的限制。
四、结语
根据分析我们发现,从认知的角度看,“××脑”是隐喻思维方式在思维中形成的容器图式,解释为“满脑子都(装的)是××”“××在脑子里(的中心位置)”;而从生成词库的角度看,“××脑”又可以根据功能的不同,析出“××至上的思维”的语义基础。这就从人们的认知基础和语言基础两个不同方面对“××脑”进行了解释,但语言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规律,也因此有了语用方面的制约。
即使分析了“××脑”的多种限制因素,还是存在可以进一步考察的地方。比如于芳探索了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脑”的词群,可以用其理论中的创新隐喻对“××脑”进行不同角度的考察,可以将“恋爱脑”“事业脑”理解为“沉迷于恋爱的思维模式”及“沉迷于事业的思维模式”,这虽然和生成词库理论中的语义生成机制所产生的表达较为相似;但这种创新隐喻的表达是在社会经验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或者社会行为的解释,是一种“××脑”构词前部特征的侧重,和生成词库中对于“脑”意义的侧重有所不同。而汉语对意合的重视,隐喻的认知方式,将社会现象和身体部件类名词在概念上进行整合,会形成更多类似的表达,这种类似表达在复杂语言现象中该怎么进行解释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