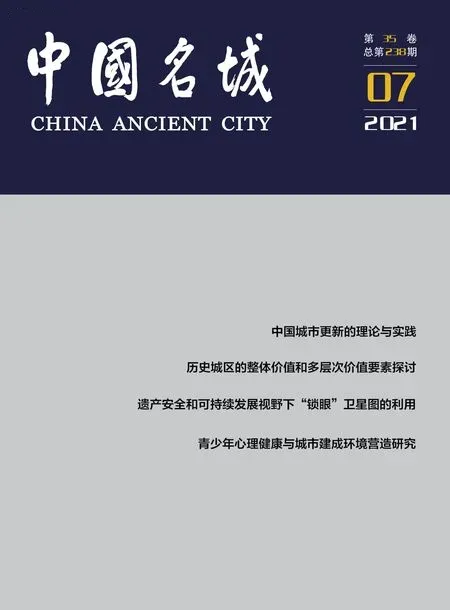国外逆城市化的研究
2021-11-24霍露萍
霍露萍
(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西安 710128)
引言
城市发展阶段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不同的变化过程[1],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城市中心区出现了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房价上涨、城市管理混乱等“城市病”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企业为降低成本,追求利益,开始向中心区外围迁移,形成一种工业郊区化现象;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中心区人口逐渐向外迁移,形成人口郊区化现象;人口在外围居住的需求增加,外围住宅区建设加快,形成住宅郊区化现象。这些现象被学界称为相对于城市集聚的离心分散化现象,实质上也代表了大城市地区已经开始了疏散化(逆城市化)进程或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发达的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在城市集聚发展的同时逐渐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发展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逆城市化发展对城市发展的有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逆城市化降低了中心区的人口密度,提高了大城市地区外围的人口密度,使人口密度分布趋于更加均匀的状态;其次,疏散了劳动密集型和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降低了环境污染;最后,金融、贸易等效益更高的服务业取代了原有的工业,从而提高了中心区土地利用率,并促进了中心城区商业金融、贸易、房地产业的发展。反之,逆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首先,逆城市化增加了通勤距离,增大城市通勤流量,进而增加了交通压力;其次,逆城市化导致城市向外不断蔓延,侵占了城市边缘区的优质土地,破坏绿地、林地等资源,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再次,人口外迁和郊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不匹配,导致人户分离现象大量存在,增加了人口管理难度;最后,乡村规划滞后于人口外迁,导致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与布局在疏散化出现后相对混乱。国外学者对于逆城市化的内涵界定具有很大的争议,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Berr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人口的分散过程。第二阶段在21世纪初,以Mitchell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城市等级的转变,人口由城市向农村流动[2]。第三阶段以Feinerman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3]。中国大城市地区已经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大城市地区逆城市化的研究较少,甚至有的学者不认同中国已出现逆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具体而言,中国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不同进展阶段呈现不一样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至20世纪末,大多学者对国外逆城市化问题的转述,未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为避免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中国应控制大城市发展,合理发展中小城镇的观点。第二种解释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郊区化或“非转农”现象。第三解释认为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4]。所以,对于逆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至今也有40多年的历史,而其作为城市发展阶段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具有显著影响。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亦提出,将城镇化和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以此表明逆城镇化对于中国现阶段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关系。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关于逆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进展,对于中国正确认识逆城市化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文章从逆城市化的内涵界定、形成的动力机制、研究的内容等方面进行论述。
1 逆城市化的内涵界定
1.1 逆城市化的概念
Berry在1976年提出美国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已经来临。逆城市化已经取代城市化而成为塑造这个国家居住模式的主导力量。Berry根据Tisdale在1942年提出的城市化概念,推理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指出逆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分散的过程,它暗示着一种从较集聚的状态到低集聚状态的过程。逆城市化的特点是小规模、低密度、异质性的下降,在国家相互依存的半径范围内迅速扩大。1978年,Daniel Vining、Thomas Kontuly在《大都市地区人口分布的国际比较》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工业化国家中心城人口的数量随着这些国家的边远地区和外围地区人口的流动逐渐下降,且这种下降趋势一直在持续……在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人口的边缘化和农村地区的净流动。”[5]A. J.Fielding在1982年分析了1950—1980年西欧人口再分配情况,并以法国为例,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得出,逆城市化并不是城市人口减少的结果,也不是郊区化的更大范围,更不是经济衰退的暂时影响[6]。随着逆城市化现象逐渐显现,其他学者也对逆城市化进行了相关界定。大多数学者认为逆城市化的概念并不等同于城市化,而是指郊区地带以外大都市区域的低密度扩张。Moreno在1987年通过研究西班牙的人口分布得出初期的逆城市化以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为特征[7]。Champion将逆城市化定义为城市人口和经济向偏远高质量环境的扩散[8]。Domingo等通过研究1975年至1986年西班牙瓦伦西亚省的人口分布情况,发现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及退休人员大多居住大城市的郊区[9]。Arroyo认为大都市地区人口的重新分布是城市层次和等级的转变,并且是向更少的等级和多级关系转变。Panebianco、Kiehl研究发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居民人口向乡村流动已经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这种在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出现的人口统计上的变化被人们称为“逆城市化”现象[10]。Mitchell认为逆城市化是指在城市等级制度下的移民运动,即大量人口从城市迁移到农村[2]。Kahsai、Schaeffer通过实证分析得出20世纪50年代之后瑞士核心城市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并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期之间达到了逆城市化的高峰[11]。Feinerman等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流动,即逆城市化现象已经十分显著[3]。可见,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逆城市化就是人口从城市流入农村的一种运动,而且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
1.2 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及疏散化的比较研究
1.2.1 城市化、郊区化与逆城市化的异同
Hope Tisdale在1942年提出城市化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并且以两种方式进行:集聚点的增加和个体集聚规模的增加,它暗示着一种从低浓度状态到更集中状态的过程,并指出城市化是空间人口集中的过程,通常被测量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的相对变化[12]。Fielding认为都市地区不论是城市化还是郊区化,都是以人口分布情况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来判断[13]。“落户城市化”是净迁入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大城市(包括大都市区)总人口份额的增加而增加。而“落户逆城市化”是净迁入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它是随着包括大都市区在内的最大城市人口迁移率高于其他规模的人口的迁移率[8]。“大都市区城市化”是以郊区为代价,大都市区人口逐渐聚集在中心城的过程。而“大都市区的郊区化”是中心城市的居民人口逐渐向郊区流动的过程[14]。
1.2.2 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之间的异同
从净迁入人口和总人口之间关系看,城市化表现为净迁入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随着大城市地区总人口份额的增加而增加[8]。城市化是以郊区为代价,大都市区人口逐渐集聚在中心城的过程[12,14]。然而,由于郊区化的发展,都市地区人口再分配研究逐渐成为分析的重点内容[13]。逆城市化表现为净迁入人口与总人口规模的负相关关系,它是包括大都市区在内的最大城市人口迁移率高于其他规模的人口迁移率[13,15]。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过程通过城市生命周期和极差城市化模型联系在一起[16-18]。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均属于城市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二者的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郊区化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先有郊区化,后有逆城市化;二是二者产生的原因不同,郊区化是城市化自然形成的结果,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的必然产物。二者对于郊区的发展均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1.2.3 郊区化、逆城市化及疏散化之间的关系
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均被包含在疏散化之中。离心疏散表现为由人口从乡到城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城乡双向流动的过程,即大城市地区出现了中心区人口增速低于外围地区人口增速,而外围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国外相关研究者将其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郊区化和逆城市化。郊区化是指城市化地区内部从中心市区向外围郊区的分散过程;逆城市化属于城市化地区向非城市化地区的分散过程[19]。
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农村人口迁移,从而导致城市化的发展,大城市地区的发展通常是以郊区和非都市地区人口的迁移为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离开城市,这首先导致了郊区化,接着是逆城市化。人口迁移的初衷是为了获得工作或教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开始追求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这种迁移是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居民生活周期的变化共同导致的。
2 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造成逆城市化现象的驱动因素有很多方面,通过梳理文献可分为以下4种。
一是交通、通讯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人口迁移。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有人口向市中心集聚转向外围地区的集聚。如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人口由中心向外围迁移,改变了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Nathaniel Baum-Snow通过研究1950年至1990年间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和中心城市人口的变化,评估了新的有限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中心城市人口下降的贡献度,估计得出通过中央城市的一条新公路将其人口减少了大约18%。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州际公路系统,中心城市总人口将增长约8%。而随着网络的全面覆盖,人们可以实现在家办公的便利条件,不用再选择在较为昂贵的市中心居住,转而选择在郊区居住。企业在考虑成本的基础上,会选择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区进行生产,吸引部分劳动力转向外围地区,进一步促进人口的外迁。城市经济增长区域逐渐分散在郊区,非大都市地区和中心城市周边地区。而原有的中心城出现重工业增长缓慢,甚至不增长的局面。
二是经济因素和人口的发展促进逆城市化发展。Champion认为,逆城市化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某些特殊事件的影响,且受经济和人口的因素最大。以美国20世纪70年代“逆城市化”现象形成来看,其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人口因素主要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大多数人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大学,而大学大多位于美国的非都市区,这些大学生大多涌入非都市区,从而导致非都市区人口的增加。他认为,这一时期的“逆城市化”现象属于一种反常现象,当这一时期的经济和人口因素过去之后,城市发展自然进入正轨[8]。Gkartzios观察到希腊城市和其他各省在经济危机方面的差异[20],而该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也提出希腊农村可作为一种避难场所[21]。Kyriaki Remoundou等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选择靠近大城市的农村地区,这样可以融入国际流动人口,并且认为经济危机造成了城乡人口流动,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和失业者而言[22]。
三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导致人口回流。Ladanyi、Szelenyi指出逆城市化的动因包括农村地区在时间、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政策方案方面导致的人口外流减少[23]。Geyer提出,最初人口流动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得工作和教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流动是为了能够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24]。Hans、Sten认为斯堪地纳维亚半岛国家的逆城市化也出现在1970年以后,除类似于德国将工业化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外,地方分权的政治制度还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繁荣兴旺[25]。Milbert提出二战后的德国在经历了城市化高峰后,于20世纪60—70年代将工业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伴随着产业的转移,农村出现了“非农业乡村居民点”,美丽乡村行动计划吸引更多的人口从城市迁徙至农村定居[26]。Roland、Löffler、Ernst Steinicke通过分析逆城市化在内华达山脉山区的社会经济效应影响中得出,旅游业是大都市区人口向高海拔地区扩散的最重要的推动力[27]。Bierens、Kontuly提出关于逆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对于乡村生活的生态经济因素的影响[28]。Irwin等通过回顾相关的农业经济文献得出,美国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是吸引城市居民返回农村的主要原因[29]。此外,发达国家农村地区持续上升的收入水平和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也是吸引城市居民逆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工业化吸引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形成了城市化,大城市的发展主要是以郊区和非都市地区的移民为代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开始离开城市,形成了郊区化,然后是逆城市化。这种移民流动是“生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主要动机的结果。然而,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研究显示出截然相反的经验,Gkartzios、Scott和Grimsrud认为逆城市化为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其中涉及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只是中产阶级),且与乡村田园式的建筑无关[30-31]。
四是其他方面,如新的区位选择、生活成本、犯罪、自然环境等。城市生活成本偏高导致人口向外流动。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年轻人由于职业选择、婚姻、育儿和退休等生命周期的变化会选择新的区域进行新的生活,房地产开发商为满足这种情况,会在周围地域开发房地产。从而促使一部分人在城市周围生活。在英国,长期和持续的逆城市化通常是与农村的殖民统治相联系的,这一现象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居民在农村生活[32]。另一方面是传媒时代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等导致中心城外围的增长和中心城城市化的衰落。Stark、Taylor则认为劳动力回流与城市的吸引力不足有关,城市工作获取相对艰难、生活成本偏高以及家庭生存风险较大等原因致使农民工家庭作出了回乡的理性选择[33]。Ladanyi、Szelenyi认为由于失业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城市人口逐渐向外流动[23]。Joony-Hwan O H研究1980—1990年期间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和郊区人口的动态变化过程,结果表明大城市地区人口的变动受犯罪和就业机会的双重影响[34]。因居民收入增加、通勤时间和成本降低、种族矛盾及犯罪率增加,居民居住郊区化,此外,城市中心环境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导致的产业郊区化成为城市郊区化的主要原因[35]。在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由于各种生活成本和沟通成本之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许多城市向外围扩展,出现了郊区化和城市之间人口密度平坦化的现象[36]。
3 逆城市化的研究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1980—2002年,萌芽期。在这一阶段,以Berry为代表对逆城市化的概念和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并采用人口流动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在此时期内,国外学者对逆城市化文献研究较少,究其原因是将逆城市化称为“反城市化”,视作与城市化相对立的一种发展阶段,或是一种城市蔓延的方式,一种“坏”的发展方式,很多学者不接受这种城市发展方式。第二阶段:2003—2008年,成长期。这一时期以Mitchell为代表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逆城市化进行界定和分析。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城市体系的发展方向,运用地理学方法对人口流动和城市空间布局等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此能够较好地验证城市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爆发期。以Feinerman为代表的研究者着手研究逆城市化与乡村复兴、农村发展等多方面,并从人们对农村生活方式、生活偏好,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方面进行研究。
3.1 逆城市化的内容分类
根据研究内容的集中性,可总结为三大类:第一,逆城市化内涵是研究逆城市化问题的基础;第二,人口组群是逆城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三,多中心主义是逆城市化的空间布局形式。
第一,逆城市化内涵界定。Berry最早根据Tisdale所提出城市化概念的基础上推理出逆城市化的概念,并指出逆城市化是人口由集聚状态转向分散状态的过程。此后很多学者也一直沿用这个概念。到20世纪末,Arroyo、Panebianco and Kiehl和Fielding等学者提出,逆城市化是大都市地区人口的重新布局,大量人口由城市向乡村流动,城市等级层次发生转变,人口空间布局的重新分配导致中小城镇发展加速[5-6]。城市经济增长点不再单单是城市中心,而逐渐向郊区和小城镇分散。因而,逆城市化是实现乡村复兴的一种方式,不仅提高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可以带动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二,人口重新组群是逆城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城市化集聚时期,城市吸引力较强,大多数人口不断向市中心集聚,形成人口向心集聚的现象。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病”问题凸显,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拥挤等,人们更意愿向往郊区或是乡村等环境优美的地方。企业为降低成本也向郊区或农村搬迁,部分劳动力为就业而选择去郊区上班,在一定程度上疏散了一部分市中心人口。此时,房地产业寻求契机,增加房地产的投资和建设,以较低的价格吸引房客入住,部分人口选择在郊区居住。这样,原有人口在市中心集聚转而向城市外围的地区集聚,实现人口的重新组群。
第三,多中心性是逆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形式。城市化的发展正是由于资本、资源和技术对某一地区产生本地化效应,从而使得这一地区成为集聚中心,并且通过道路沿线对周围腹地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促使周围贫穷地区的大量劳动力向中心地区集聚,以此,该中心地区成为主要的创新和增长中心,而周围地区只为其中心地区提供必要的需求而得以生存。随着创新的不断发展,这种中心城市的核心力量已经解体。由于运输方式和新的交流方式的改善打破了这种模式。经济增长区域不再是集中于同一个市中心,而是形成在郊区、非大都市地区和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等多个地区。城市空间格局由单中心的城市中心逐渐向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转变。
3.2 逆城市化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
21世纪初,学者开始意识到逆城市化与乡村复兴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由于城市地区现有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比如污染、犯罪和种族主义等,这种种原因导致了人口逐渐向小型居住点和环境质量更好的农村地区迁移[2-7]。由于技术进步、通信的改善及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加快等,农村人口增加,为农村的发展带来生机。这将进一步促使农村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Berry、Vining、Kontuly及Fielding指出城市的衰落将标志着大都市区的未来,就像过去城市增长一样[5-6]。Cloke从农村的角度对逆城市化进行了解释,他认为逆城市化就是农村复兴[37]。Grimes研究了多尼戈尔、利特里姆和斯莱戈等传统上为农村和落后的西部县城的非农就业增长情况,发现其出现一个双重过程,即成年人迁回农村,而青年人迁移出农村[38]。Brady、Gillmor 和Jeffers认为农村复兴与逆城市化有关。Brady发现都柏林市中心人口出现下降,人口迁移至郊区及郊区的农村地区[39]。Gillmor、Jeffers研究发现在1961年至1981年期间,由于移民返回,劳斯县小村庄人口增加及经济增长[40]。Coward和Cawley通过研究1970年至1986年的人口趋势,认为在此期间,农村和郊区具有很大增长,而相较于传统上繁荣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相对增长趋势[41-42]。Champion、Watkins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人们逐渐从城市向乡村迁移,这也是英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后阶段[43]。Hourihan研究表明,爱尔兰的三个主要城市都柏林、科克和利默里克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人口急剧下降,而迁移出的人口促进了郊区的发展[44]。Phillips将逆城市化研究集中在农村地区,即在人口流动中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如何与他们的等级和身份联系在一起的[45]。Mitchell认为逆城市化模式就是在大城市中克服传统的工业城市化和集中的模式,并与后工业化的城市发展和农村城市化有关[2]。Feinerman等基于以色列农村的数据发现,逆城市化的结果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口规模达到最优水平,并且增加了农村居民人均福利水平[3]。一些农村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关注逆城市化的经济解释。Moseley、Owen和Bosworth认为逆城市化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并且可以提供重要的地方公共服务[46-47]。
3.3 逆城市化的影响或结果
对于逆城市化问题研究结果多样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逆城市化对于城市发展具有有利影响。逆城市化可以疏解核心区过密的人口,使人口分布趋于合理;同时核心区产业外迁,尤其是污染型工业的外迁等,可降低城市中心区的环境污染,同时腾出的土地可用于绿化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另一方面,逆城市化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逆城市化发展导致人口外流,城市市中心人口减少,降低市中心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逆城市化导致城市管理混乱,大量人口户籍在城市而居住在郊区,存在人户分离现象,从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对于人口的管理难度。同时,农村的规划政策不能及时跟进,导致出现乱开发、乱开采现象,进一步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Boyle等主要针对研究逆城市化地理选择特征,及其与国际上的逆城市化经验相关的社会空间系统的多样性问题(包括对多种社会文化建设成果和对农村管理的不同态度)[48]。从对农村居民的角度看,Stockdale指出逆城市化不仅增加了大量的农村人口数量,也通过将城市要素流入农村的方式,如企业在农村办厂,可以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49]。Hofmann、Steinicke证实了逆城市化进程正在进行中,不仅导致了横向发展,而且也导致了纵向的扩建[50]。逆城市化的政策影响被广泛探讨,如规划和住房政策[51-52]、关于社区权利的关系和农村发展的主要转变问题等[53]。虽然逆城市化能够实现经济发展[54-55],但是其同时也存在着流离失所、社会排斥和住房无法承受的问题[56]。
4 总结与启示
逆城市化问题已是当今城市的热点问题,正确认识和理解逆城市化是城市能够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国外城市发展速度比国内快,其逆城市化发展阶段也早于中国。国外学者对于逆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和理解也较为深刻。通过梳理以上关于逆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逆城市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城市衰落,而是一种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市扩张,更是一种城乡关系的转变过程,是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方式,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方式方法。当然,各个国家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基础和背景不同,国外文献可以为中国学者研究逆城市化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而不是一味对于国外相关观点的认同,也不是认同逆城市化导致的城市衰败。对于中国而言,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逆城市化进行了研究,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7—2000年,萌芽期。在这一阶段,国内学者首先对国外有关逆城市化问题进行转述,大多包括对国外文献的介绍,对于国内大城市地区或是大城市进行逆城市化研究较少,并且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发展阶段还未进入逆城市化时期。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是张善余、周一星、闫小培等,研究的内容主要以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类型以及逆城市化概念探讨等为主[57-59]。第二阶段:2001—2009年,成长期。在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开始着重探讨和分析逆城市化现象,并对中国城市是否进入逆城市化阶段进行研究。这一时期以王旭、孙群郎、邱国盛、陈伯君为主要代表人物,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逆城市化的现象、实质以及与郊区化的关系等[60-63]。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持续增长时期。在这一阶段,逆城市化问题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包括研究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致力于将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共同推进城市发展,未来关于逆城镇化的文献将会越来越多。在这一阶段,文献数量增长速度很快。在此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主题也发生了变化,学者开始关注国内城市发展中的逆城市化问题,尤其是大城市地区,并将其与农村发展、农民工迁移、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等相结合。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逆城镇化发展更利于理解现阶段的城市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与国家战略政策相吻合,对于促进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主要以沈东、张强、李培林、李铁等为代表,其研究主题包括非转农、城市空间布局、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等[64-67]。
逆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依然是一个学术挑战。它影响着农村发展、城市发展乃至区域的协调发展政策,对于未来农村发展规划具有潜在的关系。然而,国内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理论基础还很薄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基础背景,且对于逆城市化的内涵界定、概念理解模糊不清。大多数学者只是就逆城市化(逆城镇化)而研究逆城市化(逆城镇化),或是单一地运用地理学方法进行案例或经验式分析。这从根本上无法厘清逆城市化的本质。当然,其中的原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中国对于城市边界的划分、对于大城市地区城市中心、郊区等没有科学的界定;学者对数据没有进行详细划分,而数据是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68-69]。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围。本文认为,逆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措施。在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注意中国已经出现的城市扩散现象,因势利导地发挥逆城市化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