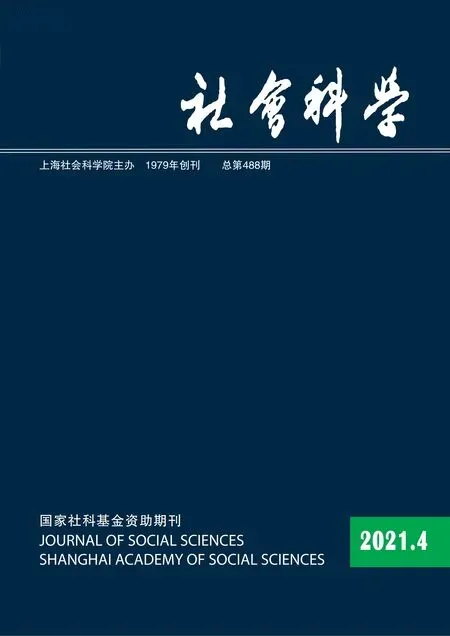新媒体语境下的舆论外交:弱者传播与数据新闻
2021-11-24曾庆香
曾庆香
认知政治,奉行认知即为真实,具体来说,现实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怎样看待现实,“如果能让足够多的人认为某件事是真实,那么它就是真实”(1)[日]近藤诚一:《日美舆论战》,刘莉生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认知政治认为,塑造人类“脑海中的图像”(2)[美]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1页。即舆论,比认知客观现实更重要,从而导致美国奉行“舆论外交”(3)[日]近藤诚一:《日美舆论战》,刘莉生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舆论外交英文是public diplomacy,国内翻译为公共外交。由于公共外交内涵太广,本文采用《日美舆论战》的翻译,更具针对性。,即主权国家及其专门的外交机构,通过影响或操纵本国、他国甚至全球的舆论,以“达成协议或约定,处理国家间关系、实施对外政策、维护本国利益”(4)陆佳怡:《媒体外交:一种传播学视角的解读》,《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4期。。
一、镜像神经元与舆论定律:弱者传播与情感叙事
2020年5月25日,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无法呼吸而死亡,引发了全美的游行示威,以抗议种族歧视。这一舆论大火迅速蔓延至欧洲,导致欧洲部分国家也出现骚乱。但同样在2020年,美国因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高达10万(5月)、20万(9月)、30万(12月)都未引发美国人的抗议。两相对比,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实世界揭示了舆论世界的深层定律:弱者传播(5)邹振东:《弱传播》,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情感叙事和个人呈现。
舆论,即公众意见,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针对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以言语、情感、行为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大体一致的信念和态度。(6)曾庆香:《对“舆论”定义的商榷》,《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因此,舆论的地基是认同。但无关注就无认同。关注向度包括对己和对他。对于普通人而言,对己,一种是一切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件均能引发关注;另一种是与自身利益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联系的、与自己社会、国家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权力、公共危机、社会道德等有关的公共事件(7)公共事件,有的从事件属性来界定,有的从是否舆论热点来界定,笔者赞同前者。,能最广泛、迅速地聚集注意力,如“华南虎事件”“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江歌事件”等。对己的关注是满足自身利益的需求。对他,通常也包括两种关注:一种是具有认知震撼、道德震撼的事件,它们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传奇、荒诞色彩,这种事件满足了自己的猎奇心理;一种是包括个人名声、心情、生活、工作处于不正常甚至极度状态的事件,这种关注通常是为了满足自己同情、佩服等各种心理。第一种关注,只有事件所牵涉个人的数量足够大,或者事件本身具有奇特性质或处于极度状态从而转变成第三、四种关注,才能引发舆论;第二、三、四种关注较易引发舆论。
认同通常是鉴别与认可与己具有同一性的人。在现实世界,强者总是少数,弱者总是多数。因此面对着强弱冲突,舆论主体通常认同与己相同的弱者,这促成了舆论的弱者传播定律,也促成了强者在舆论世界的不被认同。基于此,现实世界的强者和弱者在舆论世界常发生翻转,即现实中的弱者成为舆论的强者,而现实中的强者则成为舆论的弱者。(8)邹振东:《弱传播》,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但这只是表面的、社会的原因,深层的、生理的原因在于人类头脑中具有内隐的、映射他人动作与情态功能的镜像神经元,使人类面对别人的动作或情绪时会感同身受,即会产生自己做出同样动作或经历同样情感时的神经反应,从而产生共情能力。正是这种镜像神经元的存在使人类具有天生的同情弱者心理,这进一步加剧了舆论世界的弱者传播效果。湖北宜昌老奶奶冒雨拿现金交医保被工作人员拒收的事件,老奶奶的弱者身份加上无助表情,瞬间激起网民同情,从而成为舆论强者。更能证明舆论的弱者传播定律的是,现实世界的弱者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通过谩骂、行凶、恐吓而变成强者,如果这一事件转化为舆论热点,他反而变成人们谴责的对象,成为舆论世界的弱者,如老人在地铁或公交车上因未有年轻乘客让座而发飙怒骂反被广大网友指责,便是弱者在现实世界转变为强者而变成舆论的弱者。舆论的弱者传播定律可谓抓住了“我看见的你就是我自己”(9)[意]贾科莫·里佐拉蒂、安东尼奥·尼奥利:《我看见的你就是我自己》,孙阳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媒体等于真实生活”(10)Reeves,Byron & Nass,Clifford. The Media Equation.转引自[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84页。的真谛。
由于人们(包括传者和受者)获取信息受到交往、机会、时间、注意力、速度、词语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导致舆论并非建立在真相和理性之上。(11)[美]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因算法推荐而形成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壁,加剧了舆论偏离真相与理性。同时,舆论建立在广泛、快速传播的基础上,而广泛、快速传播的达成依赖于裹挟着简洁凝练的信息之情感、情绪的迅速感染,而非条分缕析的摆事实讲道理,因为道理激活不了使人类具有感同身受的镜像神经元,难以调动人们的情绪,也就难以在空间流动。因此,同样由于镜像神经元的模拟功能,导致非理性与情感化成为舆论的底色,这成为舆论的另一条定律。(12)邹振东:《弱传播》,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自媒体时代让舆论的情感律清晰可见: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舆论主体因尽情发泄情感而造就舆论,情感在舆论中的关键作用和所占比重,以往处于隐约的黑洞之中,如今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从而促成了“后真相”概念的盛行。舆论的情感律在新媒体时代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与运用,以致社会运动由以往的资源动员为主转变为现在的情感动员为主,而网络事件则完全由情感动员所促成。(13)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总第9期。
情感寄生于事件,而事件最有效的表达是故事。虽然文字最早记载的不一定是故事,但叙事是人类最早的思维模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几乎人类所有文明最早的都是故事。“故事之于人类,正如水之于鱼。”(14)[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许雅淑、李宗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前言。在漫长的故事与人类共生的过程中,故事沉淀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以致人在出生时自带着“故事软件”,所以“人类的心灵对于沉迷于故事显得毫无招架之力”(15)[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许雅淑、李宗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5页。。人们每晚梦中内容都是一个个或完整或片段的故事就是明证,因此梦被称作“栩栩如生而且不间断的故事”。(16)[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许雅淑、李宗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96页。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尤瓦列·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将人类社会的维系归功于虚构的故事。(17)[以]尤瓦列·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99页。因为故事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人类对故事情有独钟,无怪乎为寻求关注与认同的人们采取故事模式来传递信息和携带情感,即情感叙事。情感叙事有两种表现:一是直接诉求情感,即在标题或正文中直接召唤情感,如“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太心酸!老奶奶冒雨去交医保遭拒,只因办事窗口不收现金……”二是间接诉求情感,即通过叙述事件来唤醒某种情感,如胡戈的《馒头》,主要通过戏仿来唤起观众厌恶的情感。间接诉求的文本能达成“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奇效。因此,故事叙述成为舆论的底层逻辑。故事意味着有主角,意味着呈现了清晰可见的个人,而不是混沌模糊的群体,无论他是英雄,还是混蛋;是悲伤,还是快乐。
“弗洛伊德说:‘我们不是纯粹的智慧、纯粹的灵魂,而是一个冲动的集合。’而镜像神经元就是这个冲动集合的‘开关’”(18)诸神的恩宠:《镜像神经元为你做了这么多,是该和它说谢谢的时候了!》,https://www.jianshu.com/p/84ccbeb7446f。。正是借助这个开关,人们才被动员起来,弱者传播、情感叙事、个人呈现才成为舆论的定律。
至此,黑人乔治·弗洛伊德1人之死和10万、20万、30万人之死,前者解锁了全美抗议而后者未能解锁的原因为:前者有强弱的冲突和叙事(即视频),作为个体的弱者的悲情清晰可见,能迅速激活公众的镜像神经元,调动他们的情感。而后者因为疫情中并无明显的强弱冲突,虽有弱者但无故事叙述,没有主角,没有情感诉求,人们的镜像神经元的开关未被打开。
二、西方媒体对华舆论战:认知政治与强弱传播
任何文化体系背后都蕴涵了一些基本预设,存在着一些基本共识。(19)李金铨:《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西方媒体虽常常自诩客观、公正、平衡,以揭露真相为使命,但这种新闻专业主义标准只在报道有争议的事件和问题时才得以实践。面对具有社会共识的报道对象与问题时,西方媒体只是权力部门“球场的啦啦队”和“探戈的共舞者”。针对中国,出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基因等等共谋,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基督教为文化背景、以资本主义民主为政治体制的西方国家始终存在着基本预设和基本共识,其经典表述是美国权力集团所建构的全球道德阶梯:天国的上帝处在道德最顶层,美国处于紧邻天堂的道德第二层,代表着“善”;第三层乃是美国盟友,即西方民主资本主义阵列;第四层乃是道德边缘位置,由对它不构成威胁的第三世界国家所占据;而居于道德失序位置的第五层则是像中国之类的放弃“资本主义、上帝和选举”的国家;处于最底层则是恶魔撒旦。(20)赵月枝:《意识形态的再次终结》,载《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因此,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着“中国是与他们对立的极权、专制、独裁、黑暗、邪恶的国度”的扭曲认知,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成为他们的终极目标。这种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导致西方媒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配合其国家进行舆论外交,罔顾中国客观现实,建构虚假的认知真实。
综观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为协助政府的舆论外交,其战略是将中国政府(偶尔也包括中国人民,主要是汉族人民)建构为舆论世界的强者。为吸引全球民众的眼球,对于中国这一“他者”,西方媒体只能诉诸于上述第三、四种关注,即报道具有认知震撼、道德震撼的事件和处于非正常状态甚至极端状态的事件,因此,一桩桩莫须有、耸人听闻的事件被西方媒体制造出来。为吸引眼球、引发舆论而诉求认知震撼、道德震撼的事件,导致中国这一强者形象具有所谓的“邪恶”特质。
西方媒体无法直接塑造中国政府的强者形象,于是他们便通过形塑一个个弱者形象来间接揭示中国政府的所谓“恶行”,“7·5”事件外媒摆拍的“维族妇女‘单枪匹马’面对武警”新闻图片便是经典。外媒要么选择一个个冲突场景作为自己的战场,但在中国,冲突通常只在极端宗教分子的恐怖活动等现场才出现,因此在任何社会都被谴责的、现实生活中的“强者”:恐怖分子、邪教分子、分裂分子在遭遇中国政府时却被翻转为奋起反抗的弱者;要么选择极少数出于种种原因、种种目的宣称遭受过中国政府所谓“虐待”的个人来讲述自己的悲情故事,充分运用弱者传播、情感叙事和个人呈现等舆论定律。因此西方媒体是通过弱者传播来将中国政府转变为舆论战场上的强者,且是具有所谓“恶魔”特质的强者,即西方媒体的强者传播是通过弱者传播来实现的。质言之,西方媒体并非真正关心他们眼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祖国分裂者、邪教者、极端宗教者,也并非真心同情中国的弱者,他们只不过关心自己的舆论战目标能否实现而已,他们关注、报道这些“弱者”只因能妖魔化中国政府,因此西方媒体笔下的弱者只不过是他们攻击中国的一枚枚炮弹。
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进行强者传播、对暴徒进行弱者传播战略的完美诠释是英国网站“怪物和评论家”(monstersandcritics)对“7·5”事件的24张图片报道:其中13张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5张是抗议和哭泣的少数民族,其中多张是妇女和儿童;汉人带着防身器具上街游行的有4张;维吾尔族人看被推翻的汽车以及走过被汉人破坏的餐馆各1张。(21)王西:《西方媒体刻意歪曲“7·5”事件纪实》,《环球时报》2009年7月14日,转引自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7/14/content_18134200.htm。笔者所搜集的全球8家主要西方媒体推特账号(《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BBC、《泰晤士报》、《卫报》、法新社、“德国之声”)2018至2020年的新疆报道也大体如此。
为了让新闻呈现客观真实,让舆论战具有正义感,西方媒体既会采取“明枪”战术,又会采取“暗箭”战术。前者有:①张冠李戴,如2009年新疆“7·5”事件,西方媒体将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武警维持秩序的图片歪曲报道为乌鲁木齐军队镇压维族民众,将杭州车祸现场说成是“7·5”事件受害者的证据。(22)王西:《西方媒体刻意歪曲“7·5”事件纪实》,《环球时报》2009年7月14日,转引自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7/14/content_18134200.htm。②颠倒黑白,又如“7·5”事件中,英国《伦敦晚报》官网将两位被暴徒袭击后满是鲜血的少女互相拥抱说成是被警察攻击后互相安慰。2008年西藏“3·14”事件,德国《柏林晨报》网站18日将西藏武警解救被暴徒袭击的汉人的图片报道为抓捕藏人。③夸大其词,如“3·14”事件中有的西方媒体说伤亡人数达到了60多人,有的则说超过了80人,还有的说超过了100人,有的甚至说超过了300人。(23)盛沛林、郭星:《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军事记者》2008年第5期。④无中生有,通过摆拍、合成等方式进行弄虚作假,如“7·5”事件,法新社发布的“维族妇女‘单枪匹马’面对武警”新闻摄影,网友根据其他媒体发表的同一场景报道显示图片是照片中的维吾尔族妇女与外媒摄影记者“联手合作摆拍”的结果。⑤一面之词,西方媒体关于中国许多报道的消息来源多是在政治上具有反华甚至极端反华倾向的人物,如藏独的达赖,疆独的热比娅,港独的黄之锋、林朗彦、周庭,反中祸港的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何俊仁,反华的吴弘达、魏京生,等等。这五种战术由于较易被人发现并更正,因而较易拆解。
西方媒体采取的“暗箭”战术有:①出场与缺席,在冲突中,施暴者本是恐怖分子或反华分子,但却通过句子某些成分的出场与缺席将暴力行为转嫁给中国警方,如《纽约时报》针对“3·14”事件的报道《中国承认打伤4名藏族示威者》指出:“西藏人权组织说,警察镇压时,拉萨有几十个人被杀死;四川、青海和甘肃也有不少人被害和受伤。”(24)曾庆香:《西方某些媒体“3·14”报道的话语分析》,《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通过句子的行动元的缺席和状态元的出场,将暴力行为转嫁给警察。②偷换概念与二元对立,在藏族、维吾尔族人中,本只有达赖集团(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热比娅集团(即所谓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才反对中国政府,但西方媒体把达赖集团偷换为藏族人,把所谓的“世维会”偷换为维吾尔族人,从而变成整个藏族人、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或中国政府存在对立。③话轮与话语权的转换,西方媒体通过进攻防守式话轮转换、围追堵截式话轮转换来消解中方的立场,突显反中方的观点。前者是中方立场只要一提出,就被反驳,最后以反对中方立场的观点来结束;后者是中方立场出现后,马上涌出N个反对中方的观点。④模糊化与合理化,即借助时间、地点、身份、背景等因素,来淡化、模糊化或合理化暴恐行为的事件,如《纽约时报》推特报道“香港老伯被烧伤”事件,先叙述同一天发生且已被报道的“警察向抗议者开枪”之事,再轻描淡写“一位与抗议者争吵的男子被点火”,然后点评“两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如此行文,既淡化了暴徒的残忍和凶狠,又合理化了这一暴行:因为警察开枪导致两男子争吵,其中一位被浇油点火。这四种战术只有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对事件较了解的人才易察觉。
总之,上述种种战术都是为了将中国政府歪曲为具有“恶魔”特征的“强者”,将中国政府的反对者或恐怖分子建构为受迫害的无辜者或奋勇反抗的“弱者”。
在新媒体语境下,由于媒体的推特、脸书等账号突破了版面、时间的限制,导致许多外媒把最符合他们对中国的想象与价值观念的新闻进行违反新闻专业主义的多次重复推送,如《纽约时报》推特账号2020年7月7日和2018年11月15日出现了同一张新闻图片。不过,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社交媒体时代,他们对华的舆论战略目标基本没变,如所谓的“犯人器官买卖”“种族灭绝”“汉藏和汉维民族冲突”等话题已经被西方媒体使用了几十年。正因如此,卡弗蒂才误以为中国人“基本上和50年前一样,是一帮暴民和匪徒”。
美国的全球道德阶梯显示,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就是“原罪”,这一认知导致他们长期对华进行舆论炮轰,且报道主题几十年未变,采取各种战术不遗余力地建构虚假的认知真实;更导致他们既看不见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看不见中国民众(包括藏族、维吾尔族、香港同胞)团结一心,只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所建构的中国图景之中。正是这种沉浸使他们戴上有色眼镜,导致经常双标而不自知,《纽约时报》于2020年3月8日相隔仅20分钟分别推文报道意大利封城是“为遏制新冠病毒爆发而冒着经济风险保全欧洲”,而中国封城则是“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巨大损失”。他们的双标行为是因为错误认知遮蔽了视线。
三、反制西方的舆论策略:弱者传播、认知转译与数据新闻
弱者传播作为舆论定律,中国媒体较少运用,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往往把整个国家看作一个大家庭,中国人往往以家庭道德、家庭感情为社会母本,这种观念推导出官员是“父母官”,百姓是“子民”,朋友、熟人是“兄弟姊妹”的仿家族和准血缘的社会关系。这种家国观导致我国媒体往往注重救灾而不是报道灾难本身。同时,救灾也符合我国“人定胜天”的观念。救灾报道观念与实践直接导致我国媒体不注重弱者传播,而注重强者传播。这种强者传播反应在恐怖事件中便是报道反恐而不是恐怖事件本身;表现在贫困人民脱贫中则是多报道官方的扶贫举措与行为,而不是处在贫困民众的生活窘状。2019年香港“反修例”骚乱中,在笔者所统计的6月1日至11月1日的推文报道中,“人民日报”推特账号@PDChina主要报道中国官方的言语谴责和抓捕行为,在295条中占55.3%;而“纽约时报”推特账号@nytimes则重点报道抗议者和普通民众被逼抗议,在350条中占55.4%。又如关于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我国媒体主要报道抓捕暴恐分子,而非被暴恐分子伤害的平民百姓。
我国少数新闻也会讲述受害者的悲情故事,但往往是通过别人(主要是官方)之口来讲述,而不是直接陈述,即我国媒体偏向言语型报道而非事件型报道。相比之下,西方更倾向于事件型报道,如香港“反修例”骚乱报道,“人民日报”推特报道展示人物言语占58.3%,叙述事件仅占27.5%;“纽约时报”推文叙述事件占49.5%,展示人物言语占27.1%。
这种抗暴、反恐的强者报道,对国内非常有必要也很合时宜,因为既具有威慑力,又大快人心。但对国外却似有不妥,因为西方国家本就认为恐怖分子、分裂分子是奋起反抗的“弱者”,歪曲中国政府是专制、独裁、侵犯人权的“强者”,这种强者报道无疑印证、强化了他们对中国的认知真实。正如曾对20世纪6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过友好客观报道的英国记者费里克斯·格林对我国外宣工作者所提出: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作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文化不同,不仅意味着价值观念不同,而且意味着表达方式、思维模式相异,如中国的思维是统观性的,而西方则是分析性的,这分别促成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又如中国的时间观是过去导向型,而美国则是将来取向型,这导致中国电影电视偏爱历史剧,新闻喜欢报道老人,而美国电影电视则偏爱科幻片,新闻喜欢报道小孩。既然人类大脑之间并无中央交换器,也没有无线接触,人们的交流不能像机器传输数据那样互相传递,所以我国对外舆论战既要符合舆论规律,也需采用一些西方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模式来表达我们的价值观念。因此我国外宣首先要改变强者传播这一既难唤起认同,又易遭致误读的战略,而应采取弱者传播战略,突显暴恐分子、极端分子、分裂分子的暴行及受害者的痛苦,即更应拍摄新疆极端宗教分子的恐怖活动,讲述一个个受害者的情感故事。其次要改变叙述方式,要由中国官方转述受害者的故事,转换为直接呈现受害者的情感。
不过,最重要的是抢先用西方的认知体系或者说文化基因来讲述我们的故事,譬如“南京大屠杀”,在对日本讲述时,我国对外传播可说成是“广岛原子弹爆炸”;针对今年我国武汉封城及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和其他国家,报道可将其界定为“诺曼底登陆”。针对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总理设计的请柬:“请你欣赏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人们在认知异国他乡的经验时,通常都存在认知转译与认知搭桥,如他们将新疆的教培中心歪曲成所谓的“集中营”,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是“马歇尔计划”,将中国复兴强大后的中美关系看作是“修昔底德陷阱”,等等,都是将中国的实践、现象转变为他们的认知经验、认知体系。文化基因是人出生后文化给人们安装的一系列“软件”“代码”,因此要让异国他乡的人们解码我们的经验,必须要在电脑上安装他们的软件、代码,如同要想让电脑识别PDF文档,我们的电脑必须先安装PDF软件一样。
目前,西方对华舆论战虽充分利用了推特等网络新媒体平台,但其武器仍是传统媒体时代的传统武器,即通过报道一个个故事来攻击我国,却未采用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概念武器”,那就是数据新闻、VR与AR新闻、新闻游戏等。如果说弱者故事是“子弹”或“炮弹”的话,那么数据新闻如果用在攻击上就是“原子弹”,用在防御上则是天罗地网,VR与AR新闻则是“导弹”,新闻游戏则是“糖衣炮弹”。
“子弹”或“炮弹”可通过辟谣来“躲避”,如一位叫阿德里安·泽茨(Adrian Zenz)的学者讲述了三位叫扎米拉·达武特、米赫里古尔·图尔松和图尔苏尼·齐纳夫丁的妇女被所谓“强制绝育”的故事来攻击中国政府莫须有的“种族灭绝”。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通过找出这三位妇女并通过“人民日报”推特账号在2020年8月30日进行报道予以澄清。但西方媒体常借美籍中国人之口来攻击中国,如“纽约时报”推特账号2018年10月23日报道一位名叫如尚·阿巴斯(Rushan Abbas)的美籍维吾尔族妇女,声称她的姐姐和姑姑无缘无故被抓进所谓的“集中营”,这种“子弹”显然难以“躲避”。
针对这种西方媒体时不时冷不丁发射过来的一枚枚“炮弹”,我国不如直接通过大数据,制作数据新闻,织就天罗地网进行防御,如将1272万维吾尔族人按照家庭人口情况利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做成数据新闻,可回击一切关于“种族灭绝”“强制绝育”等恶意攻击。而针对西方对新疆教培中心的指责,可通过VR新闻,如有必要可加上直播来展示,这种透明性新闻无疑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可信度,从而戳破他们的谎言、谣言。针对西方对我国实施教培项目的质疑,在利用新疆恐怖活动的大数据做一则“新疆的每例恐怖事件”的数据新闻基础上,再通过新闻游戏的报道方式来让全球网络用户认识到教培项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和为贵”的认知体系和高语境的含蓄表达,导致我国尽量总是避免对立,被动防御。但舆论战既然是一种战争,我国不能只是防御,忙于救火,也应抓住时机主动出击,设置议题。防御如同踢足球总在自己球门前踢,这样球极易被踢进,即我国极易被舆论伤害。主动出击如同在对方球门前踢,不但确保自己球门无虞,还易把球踢进对方球门,如2020年11月30日赵立坚在推特上推送一幅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战场所施恶行的漫画,就让澳大利亚应付得手忙脚乱,并引发全球舆论。不过,这一推文效果也与运用了西方所青睐的政治漫画有关。针对西方媒体污蔑我国少数民族政策,我国可就美国印第安人做一则数据新闻,展现美国政治的虚伪与霸权。
四、消解西方的虚拟现实:定义自己与言行并肩
媒体是有国界的,新闻是有立场的,舆论中的世界是被政治家们精心定义的,远离了现实中的世界。政治上的认知真实在媒体的“枪林弹雨”下转变成普通民众头脑中的现实图像,即虚拟现实,因为“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25)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7页。
为挑战西方对我国的虚拟现实,我国需在国际上自己定义自己。而要定义自己,我国对外传播须实施上述的舆论策略:采用对方的认知体系,遵循舆论战弱者传播、情感叙事、个人呈现的规则和定律,充分利用新媒体提供的数据新闻、VR/AR新闻、新闻游戏等新战略。但更重要的的是需先抛弃“沉默是金”“行胜于言”“用事实说话”的观念,转为遵循“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按我们说的去做,但别按我们做的去做”(即“言胜于行”)(26)李希光:《美国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上),《科技潮》1996年第10期。的美国认知观念。因为在舆论战中,中国的“行胜于言”类似于只是在中国的战场后方进行生产,但西方发射过来的一枚枚“炸弹”时不时地炸掉我们的“庄稼”和“工厂”,即通过舆论毁掉我们的成果,让我们不停地“抗议”“谴责”以修补形象,并且出现“做得越多,被攻击的次数也越多”的现象。
很重要的“言”,除了“怎么言”,“什么时候言”也很重要。美国通常“在决定决策之初,就已经考虑什么样的政策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向国民传达才最有效果的方案”。将政策制定和实施与信息发布(尤其对外发布)联系起来考虑,造就了美国政治的表演性,甚至达到“只听到吱吱的烤肉声,却没有烤肉可出售”的程度。(27)[日]近藤诚一:《日美舆论战》,刘莉生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3页。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在政府言行被无数或隐藏或公开的摄像头三百六十度聚焦的今天,人人被迫进入“楚门的世界”,我国政府也应言行并肩,甚至言先于行,增加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色彩:“吱吱烤肉声”和“一盘盘烤肉”同时在场。
总之,为消解西方所塑造的虚拟现实,需将舆论战当作一场真正的战争,应有总体规划:未雨绸缪和斗而铸兵、防御战和进攻战、定点攻击与防御和全面进攻与防御,传统武器和新概念武器都要兼具。《孙子兵法》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