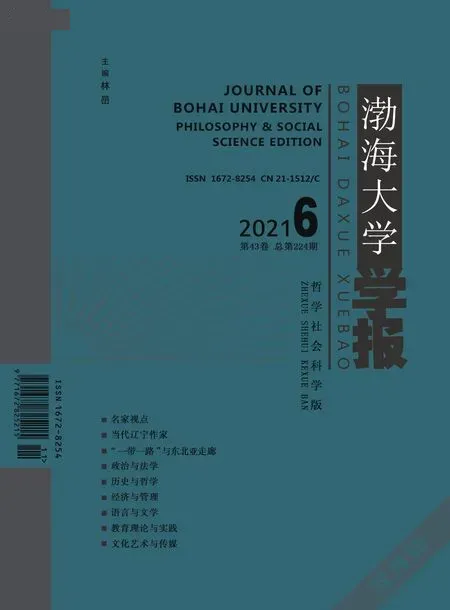如果我们这样谈论军旅文学
——与作家马晓丽的对话
2021-11-24马晓丽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锦州03原沈阳军区创作室辽宁沈阳0044
林 喦 马晓丽(.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锦州03;.原沈阳军区创作室,辽宁沈阳0044)
辽宁军旅作家马晓丽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楚河汉界》获第二届全国女性文学奖、第十届全军一等奖、第六届辽宁省曹雪芹文学奖;长篇传记《光魂》获第四届全军二等奖;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获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白楼》获首届辽宁文学奖;短篇小说《舵链》获第六届全军一等奖。在马晓丽的军旅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真实地感觉到,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其以实际的军旅生活体验和细腻而平实的女性视角深度审视了军旅生活和军旅实际,基于文学创作而深度思考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对军旅文学文体的理解,并用小说作品进行了实践性的阐释,在这一点上是难能可贵的。同时,马晓丽在创作中也充分地展现出一位作家的个性化风格和写作技巧。
林 喦:马老师您好,第一次阅读您的小说是在2011年的《作家》上,小说的题目是《杀猪的女兵》。对于军旅文学,我已经有关注,但对您的作品是第一次,面对这篇小说时,感觉眼前一亮。小说中女兵“她”的形象改变了以往军旅文学中女性对男性英雄的被动依附叙事惯性,完全从女性的主体情感和精神意识流动来创设文本,给予了读者阅读期待达成之外的精神满足。其实,这种写作意识您在1987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夜》中已有所显露,您在2006年发表的《云端》中更为鲜明。小说中的云端与洪潮两个女性人物既是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文化象征,亦是特殊时代女兵这一群体的两幅精神面孔,暗含着浓烈的身份、身体、心灵与直觉的冲突与拷问。时隔5年,在《杀猪的女兵》中我能感受到您艺术创作的一种清醒和机警,您重组了性别意识在叙事中的分量,而不是毫无节制地沉潜于此。您在一篇访谈中说《云端》是您最喜欢的作品,那么,您是怎么评价《杀猪的女兵》这篇作品的呢?
马晓丽:军队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特殊群体,我15 岁入伍,对女兵在这个群体中的处境有着切身的感受,无法不关注她们的际遇和命运。其实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无论是《云端》还是《杀猪的女兵》,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女军人还是和平时期的女军人,她们的处境往往会折射出许许多多同时代女人的处境。只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雄性的军队中,她们更需要放弃自己的性别认同,经受更多的身体、情感和精神的磨砺,所以她们的精神面孔常常呈现出更多的相貌。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总是能不断地与她们不期而遇。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间,她们那沉浮不定的女性身影总会令我心动,令我产生走近她们、理解她们、表达她们的冲动。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从这个角度上说,《云端》和《杀猪的女兵》都是我的一种表达,也是我对不同时期女性境遇的一种关切。
林 喦:如果说《云端》和《杀猪的女兵》让读者感受的是在不同时代个体情感安放与自我拯救的悲剧性命运的话,那么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就在搭建以离休将军周汉家庭为主体的红色家族叙事伦理框架。我认为小说中的父子伦理是聚焦点,它上可追溯到君臣、家国的象征意义,下可延伸至和平年代较为单向的家庭伦理关系。周南征、周东进与周和平这三个人物对待国家、军人、父亲的价值判断迥然相异,在完成了审父、寻父的生命体验后,周东进面对半截汉阳造理解并认同了父亲,周和平貌似与这个革命家庭决裂得最彻底最猛烈,然而他的商业项目是否成功仍取决于父亲手里的那只“鲁格08”。请问您设置周汉这位革命家庭的缔造者是什么意图?他是被质疑、被反叛、被放逐的孤独的长者,还是一种现代人建构自我的精神参照符号?
马晓丽:您很敏锐地捕捉到了《楚河汉界》中的伦理焦点。没错,革命的集体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冲突,也许是促使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最直接的内心冲动。《楚河汉界》中写了三次伦理困境:第一次是战争年代团长负伤自杀,周汉在集体伦理的说服下没有说出实情,导致油娃子被诬陷而遭活埋;第二次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周东进指挥失误使连队过早暴露伤亡近半,由于他坚持说出事实,导致部队得不到嘉奖,个人被调离野战军;第三次是周东进的边防团巡线兵偏离线路造成伤亡事故,如实上报就会断送边防团十年无事故的荣誉及周东进的升迁,所有人因此陷入了伦理困境。这三次伦理冲突发生的年代和故事虽然不尽相同,但所表达的内核都是一样的,都是人们直面现实时,在谎言与事实、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组织伦理与个体人性伦理间的矛盾纠葛和艰难选择。我很困惑,从历史追溯到今天,我们总会不断地遭遇这样的伦理困境。这道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无解题,似乎是人类文明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我曾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去追随周东进,希望能看到周东进发出人文道德的光亮,但周东进的路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最关键的是,我也常常会对周东进的孤军奋战产生怀疑。我知道,事实上选择牺牲局部来成全整体,一直都是人类甚至是所有生物进化过程中默认的规律。所以,我担心自己对被牺牲的个体有切肤之感,而对公众利益和宏观大局缺乏足够认识,担心良知的天平过于向个体生命倾斜。但是作为作家,我无法不关注那些被牺牲的局部,无法不关注和重视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无法不担心抉择权若操纵在道德亏欠的政治之手,会给个体生命带来无辜的伤害。所以我愿意继续追随周东进,愿意相信拒绝异化的人类良知,愿意看到社会环境中有更多的人文气象。
林 喦:同样是写父亲,您在2007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散文《阅读父亲》中以儿媳的视角,在充满深情的表述中,在自传、战地日记、家书中复原了军队高级指挥官蔡正国这一革命烈士形象。您能谈谈这篇作品中的父亲吗?
马晓丽:这本书之所以以《阅读父亲》命名,就是因为我先生出生才40 多天,父亲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他从没见过父亲。所以我们对父亲的认识大多是从阅读历史文件中获得的,当然还有一些是从长辈们的讲述中得到的。
最初,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我们找到了父亲的档案,档案里的干部履历表是父亲在牺牲前一个月填写的,上面这样记载着:蔡正国,1909年10月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车田村,1929年参加苏维埃土地革命,担任过苏维埃工会主任及少年先锋队长。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之后则是父亲从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步一步成为将军的详细履历。
父亲是个战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父亲历经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参加或指挥过的战斗、战役多达几十次。抗美援朝汉江阻击战时,上级起初只要求父亲坚守阵地一个星期,后来情况发生变化,首长问父亲能守多久,父亲当即回答:需要守多久我们就守多久!结果父亲亲临一线指挥,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率领部队足足守了两个月。辽沈战役中,由于父亲的师表现突出,曾被毛泽东亲点入京,从傅作义手中接收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
但在母亲和父亲的战友们的讲述中,父亲全然不似李云龙、石光荣类的鲁莽军人,而是个沉稳严谨、果敢坚定、仁义平和的军事指挥将领。父亲话少,从不轻易发脾气,也不骂人,实在生气了也只是说一句:乱弹琴!但在军中父亲不怒自威,麾下几位性格刚烈、打仗勇猛谁也不服的师、团长都对父亲十分敬重、信服,愿意听从父亲的指挥。
父亲对下级十分爱护,南下时,父亲的车从行军的队伍旁经过,看到队伍中有一部下怀孕的妻子,立刻停车让她乘坐自己的车。一位曾是父亲老部下的将军,还坦诚地讲述自己当年犯过严重错误,讲父亲是怎样狠狠地批评他,最终又出手挽救了他的过程,讲得声泪俱下。
阅读父亲的过程,就是通过各种文字、照片、实物和不同人的讲述,把碎片化的父亲重新组合复原,与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对话、了解、亲近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逐渐还原了一位与通常的概念化描述完全不同的戎马将军。
林 喦:除了父子伦理,《楚河汉界》还直面了职业军人许多无法回避、甚至略显沉重的话题,比如升迁、嘉奖、退伍、转业等。我认为,在军队特定体制所形成的职场氛围中,您小说中观照军人的个人前途和职业命运的笔墨很重,尤其在周东进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得更为显著。小说的叙事线索之一便是他与魏明坤的职场升迁和个人进步的明争暗斗。周东进既有高干子弟对革命浪漫主义的纯粹想象,又有作为人的独立个体性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在小说结尾处,您写道:“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他知道从前的一切都永远地过去了。”这是一种告别,又仿佛是一种新生。1998年您发表的小说《白楼》也在思索同样的命题。您20世纪70年代入伍,对部队的生活非常熟悉,您认为在战争缺席的背景下,军人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在文学的表达中应该如何实现呢?
马晓丽:一直以来,我们对军事文学多有误解,总以为军事文学是个特殊的文学门类,有着特殊的使命,需要承担特殊的非文学功用。所以常有人形容军事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于是,我们就煞有介事地按照想象出来的军事文学模样,自我背负起镣铐进行文学创作。
记得是多年前一个阳光稀薄的下午,我懵懵懂懂地在一个文学活动现场,忽然听到徐怀中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把军事文学当作军事文学来写。彼时,我浑身猛地一震,有如醍醐灌顶般一下子被点醒了,忽然感觉心里困惑已久的某个结似乎松动了,长期缚在躯体内被规训的那个魂似乎被呼唤了出来。也许就是从那个阳光稀薄的下午开始,我逐渐脱离了规训,挣脱了束缚,找到了自我。多年以后,我才逐渐体会到,这样的精神挣脱,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后来我读了巴别尔的《骑兵军》。《骑兵军》完全颠覆了我那点可怜的军事文学阅读经验,让我十分震撼。我不记得有谁能像巴别尔这样,用一本仅有13 万字的小书,令我长久地惊悸不安。为什么巴别尔会令我如此不安?我想是真实,是弥漫在书中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真实。巴别尔似乎没有刻意表现英雄的意图,他只真实地讲述战争中的人,讲述在战争极端环境下人的境遇和命运,让你身不由己地被这些人所感染,为这些人而动心。
如此说来,军事文学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定要承担理想主义和英雄情怀。或者说,军事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情怀,并不一定只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一种表达。事实上,许多优秀作家都涉猎过军事题材,海明威的《士兵之家》、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蒂姆·奥布莱恩的《士兵的重负》,这些作品中的军人形象,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战后的和平时期,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见,无论有无战争背景,军事文学面对的都是人,也只能是人。是人的理想和情怀,人的选择和精神追求,人的困境和痛苦,人的得失和欢乐。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抛却凌空蹈虚的拔高,带着敬畏真实地表达。而真实,是需要有勇气去面对、用心灵去感知的。你的心灵有多大的容量,就能感受到多大的真实;你的心灵有多重的质地,就能感受到多重的真实。这其间的差别恐怕不在于运气,更不在于技巧,而在于眼光、在于境界、在于隐在眼光和境界后面的那个主宰着你的心灵。既然如此,作家的自我修炼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林 喦:我也注意到,《楚河汉界》这部小说您叙事策略的建构。整部小说的叙事者是重病昏迷中的周汉,这让我想到20世纪80年代谌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二者都是架空了物质化的肉体,将灵魂视角成为勾连历史与现实的触发器。在这之上,您又设置了周汉与油娃子的对话,在斗争策略、道德底线等问题上呈现出历史的诡谲与无常。结合您的小说创作,能为我们谈谈小说家是如何建构一篇作品的吗?
马晓丽:我其实是没有底气谈论小说结构和技巧的。我不是一个对小说技巧谙熟,对结构和叙述策略有设想的作家。我的写作很随意,也可以说是很缺乏技巧意识。写《楚河汉界》时我只是想,用什么办法能更舒服地把这些内容装进去,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些内容装得更巧妙更好看一些,结果就自然出现了两条线并行的结构。这也许说明,我更倾向于根据内容寻找与之匹配的形式,更习惯从素材里自然生长出相适应的技巧吧。
林 喦:看了您和舒晋瑜的访谈,您说《楚河汉界》让您很受挫,并重新认识了文学是怎么样一回事。您在2007年《我的楚河汉界——关于军事文学的断想》中也说道:要功利还是要真诚,是您作为作家的“楚河汉界”,您现在对文学的理解是什么?
马晓丽:谈到功利写作,这个概念有时显得很模糊。当然,从宏观上讲,无功利的写作是不存在的,任何写作都带有很明显的功利目的。无论你是从个体出发还是从人类整体出发,无论你是从物质需要出发还是从精神追求出发。但功利也是有大小高下之分、也是有狭隘宽广之别的。在创作之初,激发我们创作热情的通常都是很单纯的功利目的,满足自身对文学的热爱,向往文学带给我们的名利,这都没有错。当我们在文学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之后,我们还会逐渐接受一些更宽广的功利观念,比如社会功利主义,比如人类功利主义,等等。可见,功利其实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写作,始终影响着我们的写作。
问题是,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功利写作,我们怎样才能不断地从狭隘的功利写作中超拔出来,进入更高一层的写作境界。这其实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需要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写作者毕生都要面临的问题。而决定高下的,往往是对文学的理解。
我喜欢的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说,多数人只是对发表作品感兴趣,如果可以,他们更想一夜暴富。他们渴望成为一个“作家”,而非渴望写作。而奥康纳认为,艺术的基础是真理,无论作为其方法还是作为其雏形。她认为作家是探寻艺术的人,而一个在作品中探寻艺术的人,其实就是在探寻真理,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是在想象的领域探寻。
林 喦:现在我们谈谈2012年发表的《俄罗斯陆军腰带》,这篇小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2011—2012 双年奖和第十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学新作品一等奖。我很喜欢这篇作品,觉得《俄罗斯陆军腰带》在表达一种超越战争、国家、信仰之外的人性力量,秦冲、鲍里斯身上因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军事传统带来的差异并不能影响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一条腰带充满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您是否通过这部小说尝试着对军旅文学创作进行着一种有效的突破性探索?
马晓丽:说实话,我写《俄罗斯陆军腰带》还真没有突破什么的想法。回想起来,促使我写这篇小说最直接的动因,可能还是我有机会参加了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之后,对我们以往的文化传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对于两支不同国别的队伍而言,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他们在队伍管理、日常训练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还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包括对个体生命的认知也是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化传统对个体生命的认知与重视是不足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极其缺乏人的意识。如王安忆所说:“在我们几千年历史里,你检测不出丝毫的关于人的概念,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没有人在意我们的生死,包括我们自己。”
这些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也在反思,这也是我创作了这篇小说的直接动因。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提升,包括国家的强大,都使我们在对待个体生命的尊严、价值上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每当看到那些为了寻找本国失踪在海外的一个国民、或一具遗骸、或营救因战乱而困顿在海外的相关人员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国家行为,我都会被深深地触动。
林 喦:2005年,您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将门风云》开播,2016年您的中篇小说《催眠》被改编为同名话剧,登陆人艺实验剧场,在信息媒体时代,这是否意味着您的作品与大众读者的链接方式更多样化了呢?
马晓丽:不瞒您说,我至今也没看过《将门风云》这部电视剧。我对小说改编多少有点非理性的排斥。当初制片方曾把改编的电视剧本发给我看,我没打开看就删掉了。记得郑晓龙问我为什么不看?我说,小说和电视剧不是一种东西,你改编成精品我看了也会受刺激,之后再拿我的感受去刺激你,还是免了这个过程别互相刺激吧。
北京人艺请我去看《催眠》首演,当时我也很犹豫。后来勉强去看了,结果发现人艺真把这个话剧做得很好。现在这个剧已经是人艺的保留剧目,每年都要轮演,而且演出期间场场爆满。但这似乎也不能说明我的作品与大众读者的链接方式多样化了。我想,有些东西不是作者能把控的,也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作为写作者,我只用心做我该做的就是了。
林 喦:您在2021年《满族文学》第2 期发表了一篇《午后的细节》,我被您简省而富有节奏感的语言打动,小说对吴八佬、瓷瓶儿、豆包的描摹很有乡土文学的味道,您是怎样看待这篇新作的?
马晓丽:《午后的细节》与我以往的军事题材小说不太一样,对主题意味和主要人物的表达更加淡化了,但语言和感觉的灵动感增强了。这篇小说我写得很随意,写作过程因此比较轻松且有趣味。我希望能在较短的篇幅中蕴含更丰富的、不确定性的内容,希望能用轻松的表达透出内里的沉重。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但我可能会继续进行这样的尝试。
林 喦:除了小说、传记,我还注意到您尝试写作散文,于2020年发表了《福清月照人》。您说写完《楚河汉界》再也不碰长篇了,那么散文会是您新的创作领地吗?
马晓丽:我不碰长篇是因为自知能力不足而不敢碰。长篇小说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以我现在的哲学观照能力、新的发现能力及内容与形式的突破能力,都无力构建一部像样的长篇小说。当然也存在体力问题,写长篇小说是需要体力支持的。
散文我其实一直有写,但很随性,只是偶尔为之,没有当作创作方向,也没有创作计划,所以也谈不上是新的创作领地。不过今年《鸭绿江》杂志在刁斗主持的《重现的镜子》栏目里,发表了一篇对我散文的评论文章,对我有些触动。现在您也这样问,看来我似乎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散文的写作了。
林 喦:感谢马老师,并祝您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