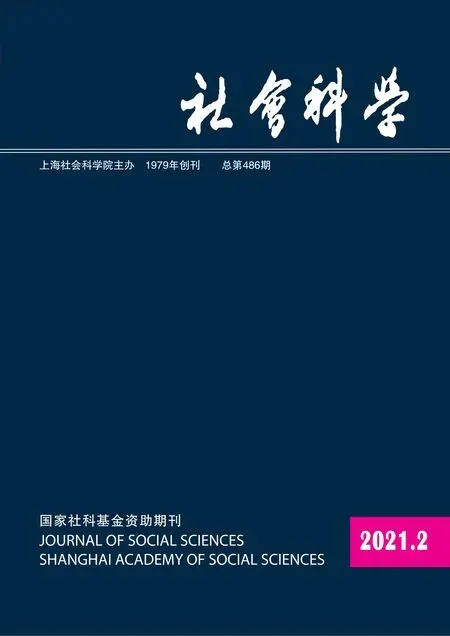“政治战”视域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特点、影响和内在机制
2021-11-23倪建平
倪建平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我国锁定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战略界、安全界、政界、学界、思想库和媒体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政治战”上(1)CNAS Report, “Protracted Greatk-Power War,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Feb., 2020.。近三年来,特朗普总统无缝整合美国国家权力的多个要素(外交、信息、经贸、金融、情报、执法和军事),推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朝着“纵向升级”的遏制方向演变(2)CSBA Report, “Forging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2020.。其中,美国战略界、安全界和智库以中国“影响力行动”为主旨框架,先后发表了20余份研究报告,对中国十八大以来为提升国际影响力所做的各种努力横加指责,发起了包括信息战在内的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攻势。特别是2020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更以美国大选为契机,凸显“政治战”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5月20日,白宫公布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首次将“价值观挑战”与“经济挑战”“安全挑战”并列为中国对美国的三大威胁,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展开进一步的政治动员(3)https://translations.state.gov/2020/05/20/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本文以美欧智库聚焦中国影响力行动的研究报告为依据,以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政治战”为研究出发点,阐述特朗普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政治战”的特点、影响和内在机制,以期更深入地追踪和研究日趋严重的中美意识形态冲突,有效应对美国对华的“政治战”攻势,努力改善我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处境和安全环境。
一、“政治战”:冷战史视角的基本涵义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整体战的逐步展开,“政治战”也逐渐进入美中两国智库和学界的研究话语,并日益得到关注(4)唐健:《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国政治战》,《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5期;王鸿刚:《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治战》,http://www.crntt.com/doc/1059/1/8/3/105918322.html?docid=105918322; Seth G.Jones, “The Return of Political Warfare”,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turn-political-warfare; Rand Report, “Modern Political Warfare, Current Practices and Possible Responses”,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772.html; Hal Brands and Toshi Yoshihara, “How to Wage Political Warfare”。。但是,这也难免会出现“谁也说不清,大家都在用”的情况,其概念的界定和涵盖的现象比较宽泛和极不明确,带来的问题是两国政策层面以及学界对“政治战”的讨论趋于表面化和缺乏完整性。面对美国对华发起的日益咄咄逼人的“政治战”攻势,有必要充分把握“政治战”的内涵和外延。冷战时期美国“政治战”计划的历史为我们理解什么是“政治战”以及采取什么应对形式提供了例证,也指出了美国今天对华发动“政治战”的可能手段。以史为鉴,厘清概念。中美有关冷战史的研究成果更能启迪我们对“政治战”这一概念内涵的提炼和阐释。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实施了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的“政治战”。美国与苏联在政治、军事、外交、思想和文化领域进行了除直接战争以外的全方位竞争,采取了向苏联集团广播、秘密和准军事行动、经济脱钩政策、人权运动等一系列措施,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推广西方制度模式,竭力抵制和削弱苏联在欧洲和更广泛的“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舆论攻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援与美国友好的“第三世界”政权,作为防止苏联影响力扩张的途径,对那些他们认为有可能受到共产主义夺权的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的干预。时任美国国务院第一位政策规划司主任、美国遏制战略的设计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就大力倡导美国对苏联战略中发挥“有组织的政治战”的重要作用。他对“政治战”的定义依然是目前最常引用的定义之一:
“政治战”是克劳塞维茨的原则在和平时期的逻辑应用。从广义的定义来说,“政治战”是指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利用一国统领下的所有手段来实现其国家目标。“政治战”的行动既公开又秘密,包括政治联盟、经济措施(如“马歇尔计划”)和“白色”宣传之类的公开行动,还有秘密支持外国“友好”团体、针对敌对国家施行的“黑色”心理战甚至鼓励地下等隐蔽行动(5)CSBA, “Forging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2020.。它可以包括像公共广播这样的公开行动和像心理战这样的秘密行动,以及对地下抵抗组织的支持(6)George F.Kennan, “Organizing Political Warfare”,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April 30, 1948,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4320.pdf?v=944c40c2ed95dc52d2d6966ce7666f90.。
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战也是一种“政治战”,其目标包括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军队、私营部门和普罗大众。无论是为了影响舆论或迫使决策者采取某种行动而攻击政府机构、政治领导或新闻媒体,信息战的最终目标都是人的认知。因此,信息战有时被称为劝说或影响力行动,甚至是心理战(7)CRS, “Information Warfare: Issues for Congress”, Mar.5, 2018.。单从字面上看,凯南的定义暗示了“政治战”可以涵盖广泛的行动范围。正如凯南在1949年指出的,“政治战”的两个目标是“凝结我们的自由世界,增加苏联集团的离心力”(8)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对他而言,“政治战”在当时就是美国应该在冷战中采用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免受热战一样的危害,这也就难以区分和平时期作为整体的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了。因此,近期就有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专家学者对凯南的这一定义加以提炼,指出“政治战,作为一种广泛的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就是使用除战争以外的各种措施来增加自身的影响力,损害对手的国家利益,使其社会陷于动乱并严重削弱其竞争力”(9)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显然,这个概念更清晰地强调了对特定对手或敌人施展的“政治战”举措是展开大国竞争的一部分,也排除了诸如人道主义干预、气候变化外交以及普通的外交政策倡议等国家的外交战略基本目标。当然,这些外交举措绝不是当年凯南称之为“政治战”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三位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政治战”就反映了凯南提出的“有组织的政治战”的内涵范围,这一时期(1947年至1956年)也是美国“政治战”勃兴的第一阶段。从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的冷战中期,这一时期见证了美国“政治战”攻势的相对衰退。美国“政治战”勃兴的第二阶段是卡特和里根政府时期,特别是里根总统在冷战的最后十年复兴了美国的“政治战”。1983年,里根总统颁布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 77),把国际信息、国际政治和国际广播活动重新整合到“公共外交”的概念中,强调实施针对苏联的“真相(宣传)计划”,要求动员美国社会全部力量,推动他国民主政治机制的构建和其他民主实践,反击苏联及其代理人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侵略性政治行动。1985年,里根又颁布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159号文件,要求使用包括秘密战在内的所有适当手段来反击敌对力量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10)于群、白玉平:《冷战时期美国的心理战和宣传战》,载沈志华等《冷战启示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页。。这些手段包括宣传,经济政策,外交和政治援助、政治行动,准军事活动和情报援助等在内的秘密行动,它是冷战期间美国“政治战”的关键要素和有效工具。
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发动了防御性的“政治战”,旨在挫败苏联的“政治战”倡议,保护美国社会及其盟国免受“恶的影响”(Malign Influence)。早在1948年,美国就通过经济援助,支持外国友好的政治家、工会和政党,公共外交以及其它秘密行动,减少共产党在意大利和法国上台的可能性。“马歇尔计划”提供了130亿美元以振兴西欧经济,这在当时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运用经济政策以实现美国战略目标的计划,它成功制止了西欧国家亲苏政治力量的兴起。依据国际开发总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统计,“马歇尔计划”主要参与国家及份额为英国(24.7%)、法国(21%)、意大利(11.7%)、德国(10.8%)等。从援助的形式上看,主要包括美元援助、技术协助、担保金以及对等基金等。科技上对苏联封锁,遏制其经济发展,也提升了美国防御性“政治战”的成效。凯南认为,尽管苏联可以输出意识形态,但却无法形成有效的经济出口。如果西方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政权遏制10年到15年,将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1949年,美国召集17个西方发达国家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和贸易限制。在美国,根据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制订了《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武器出口控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AECA)《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等法律法规,阻止苏联获得西方高新技术和武器装备,使其不断丧失经济活力和军事优势。值得指出的是里根总统在1980年代的对苏政策中,也强调利用美国的非对称经济优势,拒绝苏联获得美国高新技术。随着信息技术在冷战期间的发展,这在当时成为美国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战”工具。美国以苏联卫星国经济为目标的种种制裁,以及拒绝修建跨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的做法,使得已经过度扩张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里根政府“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成了苏联经济被彻底拖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防御性“政治战”方面,美国随着冷战的发展还对苏联发起了信息战攻势。这主要是通过采取反情报措施和协调机制,政府跨部门全力应对苏联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来增强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里根总统于1981年成立的积极措施工作小组(AMWG),帮助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即苏联虚假信息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威胁。这个跨部门的工作组包括中情局、美国新闻署、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局、国防部和司法部,致力于发现苏联的影响力行动,并将其向美国公众公开。积极措施工作小组通过发表公开年度报告——《苏联影响力行动:对积极措施和宣传的报告,1986-1987》,宣传苏联的虚假信息活动,增加了苏联制作虚假信息的声誉成本,并最终说服了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接受虚假信息对推进苏联目标难以奏效这一事实。当时,在美国自由规范的推动下,活跃的美欧国家的新闻界在无美国政府协调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共外交的信息战活动,着力揭露苏联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苏联政府控制的虚假言论和政治压制。他们的高专业水准也证明了反对苏联虚假信息的壁垒,针对那些制造虚假故事的手段,“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11)CSBA, “Forging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2020.。
冷战期间,美国还实施了旨在重创苏联的进攻性“政治战”,通过颠覆苏联集团的统治政权、增加其发展经济的成本以及其它方面,破坏其与美国竞争的能力。美国当时采取广泛的手段来增加苏联集团的离心力,包括支持这些国家的秘密抵抗行动、信息战、经济脱钩政策、人权外交以及其它的意识形态压力。然而,美国当时切中苏联统治集团软肋的进攻性“政治战”倡议也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激烈反弹,致使苏联动辄镇压其势力范围内发生的反苏政治动乱。1953年6月17日,当时的驻德苏军出动坦克上街,镇压了发生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场工人运动。另外,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在匈牙利的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事件也被迅速平息。为此,即使处于冷战高潮时期的1950年代,美国官方也决然排除那些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选项,以免引发不必要的、难以收拾的流血冲突。美国冷战后期发动的进攻性“政治战”都不得不考虑其它的目的和力量因素(12)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
冷战时期,在对苏联的进攻性“政治战”中,美国通过秘密情报活动开展“黑色宣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拆除了欧洲和“第三世界”的苏联政治联盟。里根政府还通过秘密行动,成功侵蚀苏联的政治影响力,并将苏联的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紧迫和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之间。例如,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致使苏联的政治意愿和财政资源都大为削弱,这被证明是美国“政治战”非常成功的工具。据不完全统计,美国高层批准的、主要由中央情报局实施的大型秘密行动,杜鲁门政府有81项,艾森豪威尔政府有170项,肯尼迪政府有163项,约翰逊政府(截至1967年)有142项。到了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时期,由于中情局被迫面对国会质询,并对“政治战”进行重新定位,一部分秘密行动项目被中止,一部分项目被打上“绝密”标签,迄今没有解密,还有一部分项目却由秘密转向公开。以中央情报局1951年在亚洲开始实施的代号为“DTPILLAR”的大型秘密行动项目为例,其主要目标就是在亚洲成立一个秘密机构,“团结亚洲‘自由’国家的人民,共同反击共产主义对‘自由’以及其他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挑战”。该项目实际上就是其后数十年间在亚洲文化和教育援助领域发挥巨大影响力的亚洲基金会(原名自由亚洲委员会)。亚洲数所大学(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数十个“现代”专业方向的发展、无数大学生和“青年领袖”的培养、十多个刊物的创建、数个影业公司的实际投资,还有亚洲各图书馆中难以计数的捐赠图书,都与该机构有关。1967年,亚洲基金会是中央情报局前线机构的事实被美国媒体曝光后,其身份转为公开并直接接受美国国会的拨款(13)于群、白玉平:《冷战时期美国的心理战和宣传战》,载沈志华等《冷战启示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101页。。
美国对苏联的进攻性“政治战”,采取“黑色宣传”的秘密行动,还包括中情局利用美国的文化影响力在整个“第三世界”引发亲美情绪。例如,1950年,中央情报局(当时的OPC)秘密组织并资助了文化自由大会(CCF),该大会召集了来自西方各地的知识分子来反对共产主义,鼎盛时期在35个国家/地区设有办事处,雇佣了数十名人员,并出版了20多个著名杂志。它举办了艺术展览,拥有新闻和专题报道服务,组织了备受瞩目的国际会议,并向音乐家和艺术家提供奖励。中情局还秘密实施了“学说宣传项目”,对该项目的功能定位是发挥“冲锋在前”的作用,对于所有相关行动都会给予优先支持。图书出版则是中情局“学说宣传项目”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中情局的策划之下,美国总计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发放了1000万册图书和其他出版物,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由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以及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迅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冷战时期一场意识形态斗争的风暴。在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文件中,曾经这样评价中情局在图书传播方面的作用:这个项目在直接接触专业技术精英方面十分有效,通过该项目,加强了对文化自由的态度和倾向,以及对独裁的不满。
冷战时期,美国进攻性的“政治战”也是以“白色宣传”的公开信息战来实施的。1946年3月5日,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铁幕”演说,正式开启美苏冷战的序幕;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就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发表演说;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站在柏林墙的西德一侧发表被“视为冷战的转折点”的演说,呼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官方公开的、系统的破坏性宣传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开展信息战的重头戏。不同于三位前任总统尼克松、福特和卡特,里根总统的“政治战”策略解除了缓和“苏联用来追求自己目标的单行道”,强化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开展公开的信息战,除了美国之音连篇累牍地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还有为了配合匈牙利的“自由运动”,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在东欧剧变期间充分利用富布莱特项目的运作机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对波兰团结工会和公民社团的支持,资助和推进这些国家的自由化运动项目。美国认为,在与莫斯科开展全球的意识形态竞争中,毫不畏惧地支持民主价值观本身对苏联就是一种压力,可以通过捍卫美国的外交传统和价值观来赢得竞争优势。如果说“政治战”的一个关键目标是要利用竞争者体制的软肋,那么,公开或直接瞄准其最糟糕的发展趋势就是非常强有力的,它们还有助于避免秘密倡议不断陷于被揭露或公开,以及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14)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
正如美国外交政策的大多数方面,美国“政治战”一般都是由政府部门或准政府机构实施的,包括中情局、国务院和国家民主基金会。但美国进攻性的“政治战”也得益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网络,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建立有利于美国目标的信息环境。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等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通常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1963年至1966年间,美国向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10000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有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15)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读书》2002年第5期。。卡特总统时期,1978年成立的赫尔辛基观察组织(“人权观察”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前身)就是设在纽约的一个美国非政府组织,其成立是为了调查苏联对1975年签署的确保欧洲国家自决权以及政治和领土主权的《赫尔辛基协定》的遵守情况。在冷战的最后十年,美国劳联-产联积极支持和贯彻美国统治集团以反共和反苏为核心的“政治战”战略,积极充当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和渗透、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最为著名的案例是劳联-产联选择了波兰“具有西方倾向”和“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团结工会,对其政治上大力支持,经济上鼎力资助。劳联-产联还在美国政府资助的促进世界“民主化”的“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中起着主要作用,该基金会在五年时间里先后资助波兰团结工会370万美元。1989年1月,劳联-产联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时,特意邀请了波兰、匈牙利、捷克和苏联“独立工会”领导人,同加拿大、法国、奥地利、联邦德国等国的工会代表一起参加大会。布什总统亲临大会,这是1971年以来第一个参加这种大会的共和党总统。他对“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工会领导人第一次参加美国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激动不已”(16)吕其昌:《美国劳联-产联是搞和平演变的急先锋》,《国际研究参考》1990年第9期。。
以上有关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开展“政治战”的经验做法,有助于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更好地理解美国“政治战”的内涵,也有助于我们洞察美国对华施展“政治战”的策略和手段。其一,对冷战历史的回顾表明,“政治战”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多种政策选择,既可以补充也可以取代军事行动,还可以适用于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以及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美国对苏联“政治战”的措施也是在不断调整的,如积极措施工作小组只是在冷战的最后阶段才出现,旨在集中火力与苏联打一场同军事和经济竞争同等重要的“观念战争”。这不仅是为了守住美国防御型“政治战”的底线,也是对苏联集团进行极限施压,是按照美国方式来结束冷战的前奏。其二,信息战是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政治战”致使东欧转型和苏联解体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政治战”的一种形式,信息战是美国实现战略目标和推进外交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更是最大限度追求对苏竞争优势的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充分发挥公共外交中信息战的“意识形态攻势”,并有意忽视或中断双方的文化交流。其三,在美国对苏联的缓慢绞杀过程中,经济方面利用贸易管制、经济制裁和拉拢盟友的方式,阻碍苏联贸易发展,断绝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技术领域,联手西方国家实施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的管制政策;此外,美国根据苏联是粮食进口大国以及对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苏联经济贸易的痛点及弱点进行突破(17)叶桢:《以史为鉴:冷战时期的大国经济博弈》,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8-10-19/doc-ifxeuwws5864890.shtml。。但美国对苏“经济战”措施被证明是有争议的,无论是卡特政府还是里根政府,都很难采用“经济战”来对付苏联。当下所有主要经济强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是与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相接轨的,以至于这次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许多欧洲国家始终没有与美国保持同步。这也是冷战时期从未有过的。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战”的特点和影响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通过2017年12月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8月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逐渐确定了对华开展全面战略竞争的基调和手段。过去两年多来,除了贸易争端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热点,美国政府还动员和整合所有战略资源(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法律、文化和军事),采用冷战时期应对苏联战略竞争的模板来塑造当前的对华竞争战略,其行动、布局呈现越来越强烈的“有组织的政治战”特征。在这场新一轮的对华“有组织的政治战”中,特朗普不仅开启了“史诗级”的中美贸易争端,还纠集美国国内的建制派精英、反华极端派以及“五眼联盟”的反华势力,将对华实施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等内容全面导入其中。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政治战”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意识形态攻势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疫情打击和经济不振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对抗成为特朗普对华“政治战”的重要战略资产。2020年5月20日,白宫公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称,“北京显然自以为正与西方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竞争”,并首次将“价值观挑战”与“经济挑战”“安全挑战”并列为中国对美国的三大威胁。国务卿蓬佩奥还在该方针发表当天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这一事实”。7月23日,蓬佩奥又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提到了美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不同,这不是他第一次强调美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自2019年以来,他就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刻意区分“中共/中国政府”与“中国/中国人民”。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攻势的一个特点。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界人士强调,“美中冲突只是美国与中共的冲突”,宣扬西方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甚至还公开挑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6月26日发表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讲话中也承认,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之前没有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指出,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已经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一国的“防御型”意识形态努力被另一方视为“攻击型”的意识形态行动(或是意识形态的输出),从而触发另一国的反应,导致竞争升级(18)VOA中文网,2020年7月24日。。
在这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中,美国政界、战略界、思想界还刻意打造两个妖魔化中国的标识性概念,即“国家资本主义”和“儒家重商威权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推出再次表明,中美战略竞争已向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方向扩散和蔓延,这使中美战略竞争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冷战涵义。近几年来,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方式与美国和西方所奉行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完全不同,如果西方无法与这种模式抗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在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北,最终就连西方信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将受到颠覆(19)倪峰:《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若干特征》,http://www.cpifa.org/cms/item/view?table=book&id=135。。他们警告称,“儒家重商威权主义”正在击败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早已对西方打响“经济战”,通过输出过剩产能等方式摧毁西方国家的工业能力,导致美欧中产阶层日益穷困。他们认为,现在美欧的民粹主义者已经觉醒,将从根本上改变面对中国时的软弱和被动,他们还号召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中国。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防部中国事务官员的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日前在《国会山报》(TheHill)撰文指出,“美中对抗的意识形态本质,最终使其成为一场关于生存的斗争,因为两位参赛者争夺的是自我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在争夺暂时的地缘政治优势,而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治理理念和价值体系在冲突中争夺永久的文明优势地位”(20)https://www.voachinese.com/a/defense-china-biden/5700496.html.。
第二,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先后推出“全政府”和“全社会”的组织动员概念,以此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华“政治战”中凝聚起强烈的社会共识。美国战略界通过研究认为,需要更新和提升西方国家的“政治战”组织能力,尤其是政府能力,这样才能应对中国的举国体制。为此,他们从美国与苏联的冷战经验中提取出“全政府”这样一个所谓的新概念,旨在改变过去出现的“政出多头”乱象,整合打造官方各部门一致的对华战略行动。这一概念已被特朗普政府采用,并正式写入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美国在2020年5月公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中,正式确立美中两国的竞争关系,其结果是美国开始了一种动员“全政府”的对华战略,并向更深更广的全社会方向发展,对中国进行制衡,美国政府称之为“全政府模式”(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该指针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竞争性”的方针有两大目标:一是“提升美国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应变能力,以期在面临中国挑战时占据优势”;二是“迫使中国停止或减少从事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重大国家利益的行动”(21)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p.1.。
美国对华“全政府”战略不仅体现在两党的反华共识、行政与立法机构的配合上,还体现在行政部门对“全政府”对华战略的贯彻与执行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自2017年8月上任以来,始终将中国视为“美国全社会的威胁”。美国司法部长巴尔2020年7月16日在密西根州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博物馆的一场演讲中呼吁,“自由世界拥有一个‘自己的全社会方式’,让公共和私营部门在保持必要分工的同时能够共同合作来抵制控制,赢得掌握全球经济制高点的竞争”(22)VOA中文网,2020年7月18日。。美国国务院利用各种外交场合,不断攻击抹黑中国。2019年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欧洲五国期间对这些国家施压,阻挠其使用华为5G技术,声称“美国有义务警告其他国家用中国电信巨头的设备建立网络的危险”(23)侯海丽、倪峰:《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探析》,《当代世界》2019年第7期。。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7月8日的演讲中,也强调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认为,中共“正在不择手段地钻我们开放制度的空子,同时利用它自己封闭制度的优势”(24)VOA中文网,2020年7月24日。。雷还表示,“我们将中国的威胁视为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威胁,应当采取全社会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威胁”(25)Michal Kranz, “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ys 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Threat to the US and Americans must Step up as a Society to Defend Themselves”, https://www.thisisinsider.com/chinathreat-to-america-fbi-director-warns-2018-2.。受此影响,2018年,共有30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教授、学术机构负责人以及政府政策研究专家的访美签证被吊销,或开始行政复审,其中包括知名学者(26)VOA中文网,2019年4月14日。。这给中美正常的学术交流蒙上了阴影。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的意识形态攻势正在形成国内舆论与国际盟友两相夹攻的局面。美国战略界认为,正如美国计划者在冷战时期所发现的那样,发展和维持民众对与中国长期竞争的支持至关重要,这种竞争既涉及和平时期,也涉及长期冲突的可能性,这样的评估是基于考察美国和中国在竞争的社会维度上的优势和劣势。因此,首要任务应该是为美国人民确定一个合适的社会叙述(Narrative),以及旨在支持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的民众支持的叙述。一方面,通过宣传手段使美国民众视政府的一切战备与战争行为为遏制国际规则破坏者的正义行为,并力争获得首战胜利,鼓舞国内士气,坚定必胜信心。另一方面,美国争取盟友国家民众支持的重点是为了降低中国全面“政治战”胁迫的风险,努力与世界各地盟友达成合作协议,共同结成信息战的群体网络。但是,西方国家采取适当的防御性和进攻性对策的组织障碍也相当高,美国和盟国必须充分加强政府机构之间卓有成效的协调,相关协调机构必须在打击这种威胁方面发挥超常作用,即使这要求它们承担额外负担并在传统责任领域之外进行运作(27)Thomas G.Mahnken, Ross Babbage and Toshi Yoshihara, “Countering Comprehensive Coercion on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gainst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Warfare”, CSBA Report, 2018, 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Countering _Comprehensive _Coercion% 2C_May _2018.Pdf.。
第四,保守派思想库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中发挥急先锋的作用。特朗普上台之后,在掀起中美贸易争端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防范也在进一步增强,保守派思想库继续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者和竞争对手,将中国正常的对外交往行为贴上“锐实力”和“海外干涉”等标签,积极推动美国在行政和立法层面展开行动,酝酿出台多个反华措施。与特朗普白宫团队核心成员纳瓦罗有密切联系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于2018年6月出台《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干涉行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的报告,在梳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干涉行动”的基础上,就全球民主国家如何予以反击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应该牵头成立“全政府”的项目来调查中共的干涉和影响情况,确定反情报和执法之间的界限,以及立法和公民社会倡议之间的界限;二是国会应该就此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增强透明度和公共监督,公民社会、智库、中国问题学者和记者应该联合起来,建立“统战追踪机制”;三是建立“国际民主国家统一战线”,采取为全球媒体和教育以及中文研究和中国研究提供更多独立资金来削弱孔子学院的吸引力等反制措施(28)Hudson Institute Repo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June, 2018.。此后,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中国正在使用全政府的途径,使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宣传工具来提升自身影响力,获取在美国的利益”。哈德逊的研究报告还认为,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行动”“模糊了传统间谍、秘密行动和扩大影响力的界限,并以民主的脆弱之处作为攻击目标,因此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危害”(29)Hudson Institute Repo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June, 2018.。保守派思想库的研究报告还无一例外地提出了反制中国海外“影响力行动”的建议,这些建议已经有相当大部分被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所接受,并在其他一些欧美国家引起了强烈共鸣,客观上助推了美国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
综合2017年以来美国思想库特别是保守派思想库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发布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根据他们的分析建议和对华强硬态度,以及与白宫的频繁互动,不难发现,他们保守的对华政策主张对白宫对华关系方针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化起到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第一,发达世界正在迅速且全面地形成一个反华阵线,在各方面支持和同情中国的重要国家正在显著减少。自提出“印太战略”以来,美国不断推动完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协调机制,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推出“对印太地区经济前景的构想”和安全合作倡议,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在支持地区基础设施、能源安全、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等方面采取联动举措,不断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推进构建“印太民主十国联盟”,甚至是“印太十国军事同盟”,同中国进行所谓较量,争取阻绝或减少中国的意识形态影响。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海洋发达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在战略和以高科技为内涵的高端经济上,与美国的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在如新冠肺炎疫情来源,香港、台湾、边疆问题,高科技脱钩以及军备控制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基本与美国一致,有些稍微保持一点距离(30)《对话时殷弘:近乎全面的西方联合反华阵营正在浮现》,http://net.blogchina.com/blog/article/570578562。。2020年12月初,欧盟委员会在其发布的《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中也表示,欧盟已做好准备,在当选总统拜登提议的民主峰会中发挥充分作用,就打击集权主义、侵犯人权和腐败的抬头作出共同承诺(31)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joint-communication-eu-us-agenda_en.pdf.。可以说,近乎全面的西方联合反华阵营正在浮现。
第二,特朗普政府将对华人文、教育和卫生议题高度政治化,对中国在美媒体及文化机构的发展与合作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和压制。这不仅恶化了中国文化和媒体机构在美欧国家的运营环境,也使得美中两国的民众对对方的负面看法均创下新高。2020年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五家中国主流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3月2日,又宣布对中国驻美五家官媒机构实行人员的限制;后又宣布拒绝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在以上这番政治操弄下,两国民众对于对方观感进一步走低。2020年7月30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受调查的美国民众对中国(中共)持“无好感”(Unfavourable)态度的比率上升到73%。这是皮尤中心2005年开展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点。该比率比中美2018年贸易争端时猛升了26个百分点(32)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12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终止五项美中交流计划,并指出这些计划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工具。美国同时宣布制裁积极参与中共中央统战部事务的官员及个人,拒绝他们申请入境签证。被终止的五个美中交流计划,包括“政策制定者中国行教育项目”“美中友好项目”“美中领导力交流项目”“美中跨太平洋交流项目”“香港教育文化项目”。这些计划是根据美国1961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法》,容许美国政府雇员接受外国政府资助出行。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还发布了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的规定,将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直系亲属B1/B2访问签证的最长有效期从10年缩短为一个月(33)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5206235.。甚至在抗疫这个需要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上,特朗普却不断“追责”中国造成大流行,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充当中国的牵线木偶,并以此转移美国国内对疫情恶化和种族矛盾激化的视线,使得中美两国几乎没有合作的可能。
第三,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问题高度政治化,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为由,对中国在美企业发展和运营设置障碍和进行打压。2020年2月以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相继出台多项措施应对“中共威胁”,包括特朗普总统11月颁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理由是这类投资会为中国的军事野心提供资源,名单目前包含中国铁建、中国中车、中芯国际、海康威视和华为等35家中国企业,另外,开展“干净网络”行动。12月15日,MSCI明晟指数也表示,从2021年1月15日起,将把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七家中国公司的股票从其指数中剔除。纳斯达克、标普和道琼斯指数公司此前已宣布将采取类似行动。2020年6月底,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正式将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通讯设备企业列入国家安全威胁名单,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联邦资金购买他们的设备和服务。此前,特朗普政府还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美国应用商店下架中国手机应用程序TikTok(抖音海外版)和WeChat(微信),并要求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TikTok在美所有资产。2020年5月,美国商务部切断了对中国华为公司的芯片供应,并扩大了对使用美国技术的限制,还宣布有意限制中国电信运营商和云服务供应商,限制中国开发商进入美国移动应用商店(34)https://www.voachinese.com/a/Who-is-abusing-national-security-20201216/5701648.html.。
三、美国实施“政治战”的内在机制
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发动的进攻性“政治战”是多层面的,能够对苏联发动多线攻击。1961年,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提出“两个半战争”理论,这一战略目标虽然在冷战结束后趋于“收缩”,但美国从未放弃过同时赢得两场战争的实力和准备。美国攻防型“政治战”也强调战略的多边性,尽可能利用与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合作。美国还注重在总统的统一指挥下,由政府各部门协调实施,避免了过于刺激苏联而产生负面后果。总之,美国相对完善的“政治战”内在运作机制,保证了其冷战以来无论是遂行非常规的军事行动,还是执行秘密政治行动,抑或是履行海外外交行动的长期性和有效性。
(一)美国“有组织的政治战”拥有顶层设计的组织和立法保证
“政治战”是冷战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以及军方着眼于战争需求,在“政治战”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非常完备的决策程序。美国历届政府都成立了专门机构来负责“政治战”的制定和实施,另有专门委员会考察、评估、提供政策指南和监督。1961年,美国国会颁布《教育及文化平等交流法》(又称《富布莱特法》),成立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主管学术、文化、体育和专业等方面的国际交流,推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利用可以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领导地位并为美国提供诸多利益的交流项目,率先开展国务院的公共外交外联工作。1999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秘密的68号总统决策指令(PDD-68),它是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77)的替代性指令,该总统令由国际公共信息委员会(IPI)负责,在于“诱导国外民众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抵消美国敌人的宣传”。直到今天,美国国务院还在继续履行主管和统筹“政治战”的职能,下辖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人权、民主、劳工办公室,给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和平队等机构拨款。2008年9月11日,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K.Glassman)在伦敦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讲话时透露,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意识形态的较量——思想战(Ideological Engagement),区别于用炸弹和子弹进行的战争。负责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身兼两职,除了负责属于国务院的公共外交工作,他同时还按照总统的指令,主导整个政府范围内有关思想战的工作,包括统筹与国防部、情报界、其他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的协作(35)http://www.america.gov/st/peacesec-chinese/2008/September/20080912112648eaifas0.8478968.html.。
国会为美国应对中国“影响力行动”提供了立法保障、经费支持,并进行有效监督。2019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对抗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的行动法案》,该法案责成国务卿应与所有相关联邦机构共同制定一项应对中国影响力的长期战略,除了要加强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台湾地区和蒙古的合作与协调,有效对抗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和美国的“锐实力”政治影响力行动,还要确保美国公民、普通华裔美国人以及经常成为“恶势力”政治影响行动的受害者和主要目标的华人受到保护。该法案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立一个常设机构,监视和应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行动”(36)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181.。此前2月13日,参议院也通过了《应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法案》,该法案聚焦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行动”,认为中国“协调一致、经常隐蔽地运用虚假信息、操纵媒体、经济胁迫、有针对性的投资、腐败或学术审查。这种努力通常是为了胁迫和腐蚀美国的利益、价值观、机构或个人,为了在美国培养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态度、行为、决定或结果”,要求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协调联邦相关机构来制定一项长期战略,有效地对抗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和美国的“锐实力”政治影响力行动(37)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480.。2019年2月27日,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发布《中国对美教育系统影响》调查报告,认为孔子学院在美运营信息披露不公开,且美方类似教育机构在华未得到互惠待遇。2月28日,该小组委员会就该份调查报告举行听证会。会上,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代理主任贾森·拜尔(Jason Bair)在证词中表示,与中国大学合作在华建立学位授予机构的美国大学强调学术自由,但面临互联网审查和自我审查等因素的约束。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郭瑾(Jennifer Zimdahl Galt)在证词中指出,与孔子学院相关的K-12教学问题丛生,在两起查办案件中,私营部门交流办与领事事务局密切合作,合理撤销了已进入美国教学但不是通过交流访问者项目中教学类别指定的赞助商而获取资格的中方交流访问者的签证(38)参见https://www.rollcall.com/2019/03/01/china-is-building-soft-power-in-u-s-schools-senate-report-warns以及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与参考》2019年第7期。。
(二)政府和民间机构紧密合作机制的有序运行
近几年来,美国思想库和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有关信息战报告和文件都强调,要加强与美国社会中私人机构的合作,特别是大学、基金会、政治团体和媒体。在公共外交领域,美国政府、私人基金会和大学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机制,各自责任明确,构筑了“三位一体”的行动网络,甚至形成一种特殊关系下的利益共同体。美国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中,更是与权力部门相互策应、密切配合。从2017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发布《锐实力:崛起的极权主义影响》研究报告,到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中国简报》中陆续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影响力行动的初步调查》系列报告,再到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北京的全球扬声器——2017年以来中共媒体影响力的扩张》报告,这些反华基金会不仅担心中国威权“软实力”所带来的更复杂的挑战,还分析民主社会中非自由主义精英的言论,并强调中国这样的威权政权为了促进自身利益而试图传播的意识形态概念(39)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Jamestown Foundation,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CP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Japan, Singapore and Hong Kang”; Freedom House, “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Influence Since 2017”.。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随着特朗普本人的玩忽职守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全国性混乱,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高潮和失业人口的叠加效应,他急于“甩锅”世卫组织和中国,“中国责任论”在他的政纲及正式言论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少非政府组织也指责中国有关抗疫的宣传报道为“虚假信息”,煽动西方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不满。美国捍卫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负责人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就在《外交事务》网站上撰文称,“随着疫情开始在本国境内得到控制,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强势的外部信息宣传活动,旨在引发全球对其应对疫情方式的讨论。这场运动有着明确的目标:转移对北京自身抗疫失败的指责,并强调其他国家政府的失误,同时把中国描绘成其他国家的榜样和首要合作伙伴”(40)《外交事务》网站,2020年4月22日。。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大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美国政府也鼓励非政府组织在从事自身活动的同时,能够承担政府不能够开展的部分公共外交事务。美国国务院早在2006年12月公布的《对待非政府组织的指导原则》第六条中就规定,应允许非政府组织为从事和平活动而寻求、接受、管理和支配来自国内、国外和国际组织的财务支援。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每年都投入数亿美元用于公共外交,其中大部分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经费流入了非政府组织,由非政府组织出面提供经费及通过其它资助方式,借由文化交流来影响目标国国内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人士,包括教育工作者、新闻记者、妇女领袖、商界精英、工会领导、政治人物、科学家、军界人士以及青年学生等。美国私人基金会基于非政府的角色,借助公共外交的“柔性介入”方式,不仅比较容易回避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还有利于扮演某种客观、公正和中立的角色,从而使公共外交活动更具合法性的表象。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相互借重、各谋其利、互相依存而又保持距离,形成了一种微妙而特殊的关系。就政府间的文化外交而言,囿于意识形态差别及主权意识,美国官方对华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公共外交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这些问题在基金会活动中却可以适当避免,因为基金会往往不会像跨国公司那样追求利润,不涉及“赚钱”的问题,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某些价值观念,因而给人以单纯和公允的印象。这些独特功能是美国任何官方机构推行对华外交时所无法企及的,私人基金会往往凭借自身优势,能够在政治敏感地区发挥特殊功能,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特别是美国的基金会能极方便地深入到中国民众当中,这种草根化的表象使它们不仅容易取得普通民众的支持,还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民众的思想。另外,草根化的特点又使得它们在获取第一手信息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这些基金会能够在一些政治环境不同的非西方教育机构如大学中开展工作,途径之一就是在政治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间推动各个层面的学者交流。
(三)“旋转门”机制助推保守派思想库发挥重要影响力
美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决策咨询制度,尤其是“旋转门”机制,为保守派思想库设定美国对华政策议程、引领公众讨论并传递相关信息提供了充分条件。“旋转门”提供了参与对华政策决策的双行道:保守派思想库专家成为官员后进入美国外交决策层的核心,成为对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思想库专家和政府官员角色的“旋转”也增加了其在大众媒体的曝光率,形成了对华议题强有力的公共传播网络。保守派思想库通过与美国各种涉华政治机构、商界、非营利组织、学界以及媒体的沟通,实现特定议程设置;在某个涉华议题受到关注后,继而引领相关讨论,包括接触特定的决策者(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以及社会精英,在媒体发表美中关系的文章后,接受采访并举行主旨演讲。这些保守派智库还经常派专家去国会听证会,提供中国问题的证词。布什政府时期提出的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和胡佛研究所等提出的“遏制+接触”的政策咨询建议,他们主张,通过“接触”保持与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促使中国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推动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合作性民主大国,同时利用“遏制”减缓中国崛起进程,预防中国崛起后挑战美国国际地位和利益。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保守派思想库与特朗普鹰派团队的成员一拍即合,频繁互动,他们的研究实力和综合影响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据报道,彭斯副总统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的讲话稿,就是由特朗普的“权威中国通”顾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撰写的。彭斯在演说中还特别提及白邦瑞的观点,“中国反对美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实际上,中国正在与美国的盟友和敌人建立关系,这与建立任何和平及高效的中美关系的意图相矛盾”。这一观点即出自于白邦瑞2015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的秘密战略》。白邦瑞本人新近担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这一身份注定让他不只是一位简单的保守派思想库中国问题专家,而是今后美国军方对华战略的谋划者。美国保守派思想库的很多专家学者有在政府任职的职业经验,这也成为他们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据统计,保守派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有18名研究员先后进入奥巴马政府任职,部分成员还直接进入美国外交决策的核心圈。例如,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任常务副国务卿、莱恩(Willam Lynn)任国防部副部长、苏珊·赖斯(Susan Rice)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坎贝尔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尔(Dennis Blair)任国家情报总监等。这使得新美国安全中心异军突起,成为华府地区一家影响着美国军事发展战略的顶尖智库。
(四)“政治战”的催化性策略和侵蚀性策略的灵活运用
美国在冷战时期发动“政治战”,最惊奇的策略固然是催化性的(Catalytic),用来引发一些戏剧性的近期变化。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将有民主化进程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视为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该国的扩张。1954年,美国通过两次秘密行动,采取外交压力和心理战相结合的手段,最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民选政府,这也成为美国后来在拉丁美洲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种模式和手段。这一行动是由中央情报局负责策划和实施的。中央情报局自1947年成立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秘密行动”是1953年推翻伊朗摩萨台的“阿贾克斯”(TPAJAX)行动,而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则是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政权的“胜利”(PBSUCCESS)行动(41)贾力:《美国中情局在危地马拉的心理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4期。。此外,冷战时期美国的宣传计划也具有同样的动机。为了加强对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广播宣传,美国之音先后播出了“揭露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弱点和邪恶”的《政治的卡巴莱》、“揭露共产主义所标榜的更好的生活的虚假”的《共产主义伊甸乐园》和《铁幕后的生活》,以及回顾苏联扩张的历史,“使人们想起苏联政权想要抹掉或歪曲的事件和声明”的《你——记得这些时刻吗》等一系列专题节目。1953年,美国之音不断广播东德骚乱的报道,希望“推回”苏联的宣传攻势,鼓舞东德民众抗议苏联的统治。中情局还向东欧广播发表了赫鲁晓夫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秘密讲话,它后来确实引发了震动苏联集团的抗议活动。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称之为“保持沸腾”的行动(42)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任期是美国对苏东国家冷战宣传发展的重要时期,将“全社会”的“心理因素”融合进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各个方面。不仅美国的政府官员,而且美国的民众也卷入到国家的冷战宣传中去。美国冷战宣传政策、宣传机构建制和具体的宣传运动逐渐向长期、渐进和隐蔽的方式发展。在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和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的冷战宣传发展到高峰,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也迈向成熟(43)郭又新:《穿越“铁幕”: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冷战宣传(1945-1963)》,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冷战时期,美国最成功的“政治战”更多地是侵蚀性的(Corrosive)。这些“政治战”计划聚焦推高苏联集团的对抗和竞争成本,而不是政权的彻底更迭。美国国际广播在国内和全球听众面前,宣传共产主义势力的失败,其目标就是促使苏联集团内部不满的爆发,增加这些共产党执政政府长期的压力。此类经典案例就是自由欧洲和自由无线电台,通过长期播送苏联集团内部的弊病和失败,从而增加它们向更开放社会渐变的机会。成功的“政治战”不必刺激彻底的反抗,它只需要追求逐渐地、累积地侵蚀根基并打击敌对统治的竞争潜力(44)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年中以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等美国政府重量级官员,分别就意识形态、经济和间谍等议题发表涉华长篇主题演讲,他们纷纷为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中心的“7·23演讲”预热。有美国的中国观察家指出,由于美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处于螺旋式上升的状态,中国对威权体制的支持确实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理念——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对此,蓬佩奥的讲话如同发表了新铁幕宣言,开启了一场类似于美苏之间的新冷战(45)VOA中文网,2020年7月24日。。
结 语
冷战时期,美国曾利用多种方式对苏联发动“政治战”,包括在苏联内部制造混乱、削弱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合法性、与苏联围绕第三方展开竞争等。美国从未忘记强调与其对手之间意识形态差异的重要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一系列“颜色革命”,从中都能看到美国意识形态攻势发挥的颠覆性作用。美国拥有长期积累的意识形态“政治战”资源和经验,不仅具有非常强大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还将长期存在。特朗普总统自上台以来,希图恢复美国的竞争优势,在美国国务院的统筹和协调下,再次把思想和价值观的冲突放在对华关系的中心位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愈演愈烈。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呈加剧趋势。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意识形态安全关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前途命运,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及其变动在当今国际安全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科学决策与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需要我们对美国的“政治战”策略有更深刻的把握。毕竟,中美两个大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不仅是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角逐,更是对中国战略能力、战略经验、战略资源、战略耐力、战略定力的大检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无论如何既要增强自身的“四个自信”,又要有效应对美国的“政治战”攻势,努力改善我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处境和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