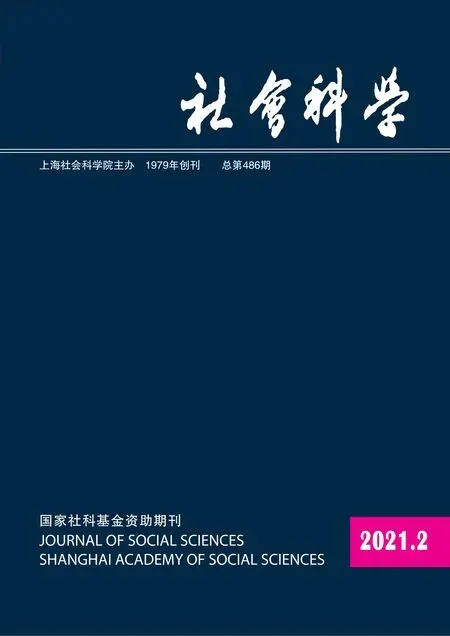事件思想的七种新走向:演进逻辑与文学效应*
2021-11-23刘阳
刘 阳
“事件这一范畴已经成为当代大陆思想的主要关注。”(1)François Raffoul, Thinking the Event,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0, p.6.2020年问世的国际新著《思考事件》如是指出。确实,作为思想方法的事件,在一种新的动态机制中自觉地破除形而上学预设,实现富于独异性的意义创造,迄今已形成涵盖欧陆内外的深广谱系。这一谱系,也正逐渐引起我国文论界将其引入文学研究的兴趣。在这里同样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活跃于晚近学术前沿的事件思想,陆续出现了七种具备内在演进逻辑的新走向,为推进事件研究提供了可及时追踪摄取的学理生长点。
本文将循序描述这七种新走向,以此尽可能清晰地图绘事件研究在晚近的最新面貌。对每种走向在学理叙述中的评析,对不同走向在信息与文献线索上的取舍和勾连,很自然地都会反映出我们自己对这一演进逻辑的看法与反思。而唯当客观还原出这些新走向(我们认为这对国内相关研究而言应属首要之务)以及它们之间的演进逻辑(这在形式上已体现于以下各小标题)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来总结其文学效应,估计其现实意义以及判别其得失的契机。
一、时间加速对空间的取代及其事件性分形
事件是超越形而上学预设并重构因果关系,在动变中生成的独异性。这一谱系共识,在晚近得到持续的进展。法国著名思想家保罗·维利里奥的事件思想对此作出了深化。出版于1996年的《事件景观》(英译本于2000年推出),推进了他1988年问世的《视觉机器》中有关“光线时间的频率已经成为事件的相对主义统觉的决定因素”的论断,(2)[法]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认为在时间加速的当今,空间本身被时间吞噬而变成了时间,这使事件概念具有了数学维度,根据概率论可以计算出其任何一种发生的可能性。
作为一位具有建筑学背景的人文学者,维利里奥感兴趣的是,时间的加速导致事件来自大量的碰撞,每次碰撞都由媒体政治、社会与技术加以转播,展示其不协调向量以及意外性。这样,时间战胜了空间而成为我们的主要感知方式。在这种感知中,一方面,任何事情似乎都无法再从其它的事情中继续下去,而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又仿佛什么事情都还并未结束。现在的持续时间,限制了历史的循环与重复。这的确是事件的真实体验。他提醒道,由于世界普遍的时间在重要性上正加速超越过去的、地方性的时间,这就需要我们超越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迫切地改革一般历史的整体维度,以便为虽然有限、但能精确定位的事件的“分形”(fractal)(3)Paul Virilio, A Landscape of Events,London: The MIT Press, 2000, xi.,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让路。这里有一个记忆与遗忘的张力结构问题,维利里奥称之为“事件景观”。他不无感慨地指出,对上帝来说,历史是事件的风景,没有什么事情是按顺序进行的,因为一切都是同时存在的。这是一种允诺并列的空间性感喟。与这种极端情形不同,现实生活的常态则是把空间变成了时间,社会已完全变成了时间的一种功能,持续的时间实际上是同时性的结合,后者却被不动声色地替代为前者了。
时间的加速取代了空间感,以至于“速度将视觉视同第一物质”(4)[法]保罗·维利里奥:《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成为事件的景观。这是一种独特而有趣的“速度-空间”观察视角。(5)[英]伊恩·詹姆斯:《导读维利里奥》,清宁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时间与空间的传统协调性,(6)参见刘阳《理论之外:后理论取径与中国接受变异》,《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是维利里奥试图打破的东西,他代之以裂变:时间的加速挤兑着空间的感觉。这才是事件。两相比较,维利里奥有意将时空协调关系错乱化,在表明事件的反常规、反惯习这一点上自有其独得之秘,是吸收了德勒兹虚拟概念的产物。晚近学者们引用他发表于2012年的《速度的革命》一文中的观点:“今天,在我们遨游的这个虚无缥缈的世界里,虚拟战胜了现实……对表征来说也是如此:虚拟映像比实际映像更具有实时性。”(7)Birgit Mara Kaiser, Singularity Transnational Poetics,New York: Routledge,2015, p.84.时间加速带给事件的分形,即虚拟化对事件的积极造就,它与文学在现代以来对各种时间形态的先锋性改造与创造性变革,比如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作品,正在取得不断趋深的联结点。从这一角度来探测,事件思想确实同时运作着文学机理。
占据着空间的,是具备广延的物(以及广义的自然)。时间的加速取代空间,产生事件性分形,这进而意味着“物”这个概念需从事件角度得到新的把握。
二、空间的物与自然由此作为事件得到把握
对物与事件的关系研究,伴随物质文化研究在晚近的发展而被推向新视野。西班牙巴斯克大学教授迈克尔·马德2009年出版《物的事件:德里达的后解构现实主义》,标示了思路。
从书名可见,马德的论述关键是物(thing)与事件的关系。他继承了事件思想谱系中不少前人的成果,同样首先认为人们对物、对物性存在着一种初始意义上的不知道,这种未知性促成了逃避认知与概念识别机制的事件,后者从命名它的哲学谱系每个阶段逃脱,而将自身表达为物的事件,其逃避因而并非消极,而具有生成与丰富性:“物指的是本质被剥夺的前本体论的形象,并在它所接受的、欢迎的、受苦的、经历的、经验的一切事物中,为这种剥夺的事件作准备。”(8)Michael Marder, The Event of the Thing: Derrida’s Post-Deconstructive Realism,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p.18.简言之,物是事件的准备。马德区分对象与物,认为前者是与主词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后者则意味着非对立的差异性。为论证这一点,他祭出的主要理论参照系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他意识到,解构主义是一种只出现在物的“撤退”中的理论主张,因为它旨在从它所给予的东西中减去它自己(这的确是解构的要义:“它自己”就是“在场”),去除包括空间与时间在内的现象学过程,因为后者每每呈现为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物自身的例行程序。这确实避开了对物的概念把握以及任何将物聚集为一个整体的企图。事实上,物本身不受分析、综合等知识秩序的影响,在不受束缚中才向事件敞开。马德注意到自柏拉图以来,从有限中提取无限、以物自身的特性取代其独异性,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拜物教,即利用物被提取的自身特性来抽象其社会意义,将其限制在价值规律内牟利,把商品作为非感觉的客体物加以利用,而在虚拟性操作中客观化了物。与之异趣,他挑明“也许”“是的”这类高频词在物实现为事件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微妙虚拟作用,指出“也许”这个词似乎加强着原先的物,实际上却呈现为一种被召唤的中断以及重新开始呼吸的过程。因为这种重复性的反符号将物重新具体化,使之转化为原物的可能性条件,而在重复中成为“双重肯定”(double affirmative)。“物的经验”从而蕴含一种持久的模糊性,因为它既表明了人体验物的方式,也表明物本身的经验只能从它自己的角度获得,而引出着在虚拟中生成自身可能性的事件。因此,物是一个受到差异影响并居于其中的折叠体,不同的、延迟的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使它与自身始终保持非同一性与差异性。
广义的物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然。像避免令物对象化那样不使自然僵固,以顺合自然的方式还原其作为事件的生命,是事件思想相应的发展动向。美国学者迪迪埃·德拜在2017年出版《自然即事件:可能性的诱惑》,接续了上述主题。
我们知道,“自然”是诗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它不仅早在古希腊即已作为摹仿论的目标而受到重视,即使到近代浪漫派兴起后,也仍是表现论谈论诗学主张时常用的一个概念,像雪莱与赫兹里特等著名的浪漫派作家便屡屡表示,心灵是对自然的表现,因为在他们看来,心灵集中了人的天性,而人的天性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理性主义哲学逐渐消解着这一传统。德拜的问题意识是,今天对自然的各种谈论,本身就充满了反自然的色彩,即并没有将自然当作其多样性得到了重视的事件。“如何给予自然中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以应有的重视?”(9)Didier Debaise, Nature as Event: The Lure of the Possible,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他发现,我们今天运用的抽象概念,包括思维模式都已不再能加深或发展对自然的体验,相反模糊了自然的本义。他倡导重新点燃怀特海哲学中的某些命题,来描画一种思考自然的不同方式,走向“普遍的特殊习惯”(universal mannerism)。由此既论证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不体现任何真正的本体论地位,质疑其是否每每将一种特定的自然观念强加给自然,也藉此表明克服上述行动所造成的限制的方法,认为自然的存在与我们对它的态度是相互交织的,与我们体验、感受、理解它以及赋予它重要性的方式一样多。“普遍的特殊习惯”因而便是将我们对自然的种种作为也融入自然本身的样态中,不产生基于理性认知冲动的距离。从中可见,还原和激扬出自然的存在多样性,便进入了对象与主体相同一的事件中,马德所倡导的“物的事件”,被德拜用“多样性”予以继承,两者的事件思想均指向了文学场域,因为文学植根于与虚拟体验相接近的虚构。
在提出者德勒兹这里,虚拟理论旨在建构一种基于差异性重复的本体论。对多样化虚拟的上述确证与深化,由此使事件进一步在本体论意义上得到新的阐扬。
三、事件由此获得本体论解释学意义
承接上面的脉络,马德的合作者、巴塞罗那大学教授圣地亚哥·扎巴拉,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让·格朗丹在2014年出版了《动摇:本体论与事件》一书,引人注目地揭示了本体论解释学事件思想与长期以来注重变异的事件思想之别。
扎巴拉充分意识到,对存在的形而上学解释排除了事件的到来,因为后者既不可预见,也无法被简化为因果关系或数学公式。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每每呈现为系统的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神话的晦涩反映,排斥事件的干扰,意在安抚我们内心的恐惧,即当我们说出或听到“为什么”时,内心希望用一个“因为”来满足自己幼稚的好奇心而平息不安,我们提问是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要符合我们的期望。与之不同,扎巴拉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与创伤、震惊有关的经验。他举例道,假如笛卡尔烤火,这位坐得舒舒服服的哲学家会不会怀疑自己的存在呢?如果他把手伸得远些,在感觉到火的难以忍受的热度之际被它烫伤,冥想的稳定性将如何面对那展开冥想的物理环境呢?对哲学史上这一重要事件的此种假设,有助于我们对存在的可变性产生新理解,即倘若笛卡尔燃烧自己,他会得出“我在痛若中,因此我在(我的有限性中,在非存在的边缘)”这样的结论。推而广之,那些常处于战争、饥饿、身体或心理创伤的人,在遭逢经验的极限突发事件时也是一样的,这些边缘事件不应被忽视。不应将这种边缘经验理解为无根据的经验,那不仅会导致虚无主义,而且会再度返归把它压倒的形而上学。扎巴拉联系列维纳斯的异在与他者哲学,认为他者性并不是一种安全的基础,相反激发了我们说话的可能性。被人质疑,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询问世界的意义,从已成为对方目标的一方立场来思考存在的意义,即不再以一种主权的、自主的、主动的方式,而是以带着极大被动性的方式,进行在别处产生的询问。扎巴拉觉得,以打破传统为旨归的当代分析哲学恰恰落入了这个虚无的陷阱中。与之不同,基于他者性的事件是被苦难召唤而存在的,它决不再回到神话的起源,而是要大声质问当代世界的荒谬。
沿此,扎巴拉用“动摇”(shaken)描述事件的性质,不仅与巴迪欧等人以“溢出”界说事件形成了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更为清晰地强调了“动摇”的两个原发点:一是面对形而上学本体论而动摇;二是不让这种动摇滑向无根据的经验,而在动摇中动摇,最终走向存在。当主体从自满的昏睡中被摇醒,或在极端情况下受到威胁时,主体已远非自主的主体,而是决定了主体的存在。他由此表示感觉不同于经验,(10)Michael Marder & Santiago Zabala, Being Shaken: Ontology and the Event,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9.后者才是面向苦难和荒谬的。
作为本体论动摇之动摇的事件,得到了多位学者的赞许。如若认定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预测而无从解释,格朗丹紧接着说道,这不啻意味着我们同时建立了一种有关什么是规范的前提性观念,而那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做法。格朗丹由此相信,事件的不确定性,不应成为欺骗我们的一种伪装。这也再次回到了他同样处身于其中的解释学原则:此在的存在即历史性本身。这展示了解释学事件论与晚近各种强调非理性色彩的事件论的差别。
这种差别在于,存在的事件是一个机会而非一种威胁,后者是许多非理性主义者所乐于采取的思路。扎巴拉清楚指出:“解释学本体论对事件的兴趣不是简单地由它的无政府起源或生成目标所驱动的,而是由缺乏事件所造成的紧急状态所驱动的。”(11)Michael Marder,Santiago Zabala, Being Shaken: Ontology and the Event,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78.它具有相对确定的指向,而不像一些非理性事件观那样追求完全不可知的异质性力量。这对我们研究事件思想谱系的整体发展面貌颇有裨益,促使我们意识到这一谱系内不同观点、立场之间的必要分野,而不至于迷失于形形色色看似旨归一致的说法中。扎巴拉对事件思想的贡献,是强调事件的召唤并非澄清存在,而是产生存在,它作为一种变革性的思想,不是要去战胜与克服形而上学,而是要去超越形而上学,因为如果形而上学能被完全克服,就不会出现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而只会重演单一的范式。尽管本体论解释学通过违反现存的秩序来促进存在的产生,仿佛旨在克服存在,但这种存在不重蹈框架思维,而呈现为广大的、松散的和不可预测的事件。这也就是本体论动摇及其不断继续动摇的意思所在。这因而既带有富于启迪的总结色彩,也锚定了往前谈论事件的文学起点:苦难和荒谬,不正是文学着力聚焦的现代生存困境吗?
获得了本体论解释学意义的事件,将现实与虚拟性有机融合于一身,触及了生存始终在稳定中被建构的真相,相应地出示了事件在审美中同时贯通政治的议题。
四、事件由此在被建构的意义上贯通审美与政治
在这点上提供了前沿学理的,是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学家布莱恩·马苏米。他的基本观点是:在生活中发生的情感,不可避免地伴随“活力的过度影响”,其一方面形成模糊的情感感知,另一方面又总是由于对过度的意识,而同时展开着把“生命力强度转换为可重新计算、可编码或可形式化的内容”的过程,(12)Brian Massumi, Semblance and Event: Activist Philosophy and the Occurrent Arts,London: The MIT Press, 2011, p.153.这一过程即政治,审美政治从而即事件。这在马苏米出版于2019年的新著《无法预见的建筑:突发艺术论文集》中得到了接续。
这部著作围绕当代建筑艺术,对事件在统一两种看似异质的要素这点上的身体性特征进行了探讨,重申了审美政治在事件中依靠虚拟获得统一性这一原理。马苏米发现,在同一虚拟空隙中的连续性原子,由于缺乏规模或位置,严格而言在空间上无法区分,我们得到的图像,是在虚拟叠加(virtual superposition)状态下不断区分连续性原子的产物。从与主体意识的关系角度来看,意识在事件上述虚拟叠加的连续性中减弱,替代它的意识上升后,会发生一小部分的中断,导致缝隙中发生的微小事件不会被自觉地记录下来,看似盲视的这一过程,会对发生的事情作出一种定位。他以林恩(Greg Lynn)的建筑作品为例。在通常的理解中,建筑典型地体现了内部与外部的分割。但马苏米指出,林恩将建筑描述为无止境的运动,建筑的“内部性”概念,被林恩落实在可操作的、与“外部性”(技术、历史、社会、个体等)的连续性关系中,虚拟是贯穿它们的一切。当所有这些元素被有效融合为一个运行中的事件后,所谓的持续时间便是新出现的虚拟运行的同义语,建筑本身也由此呈现为一种虚拟技术。马苏米尤其感到,光学效果在林恩建筑中的出现是个事件,它激活了建筑,也使看似偶然的因素克服了传统框架的装饰物-结构二分法,呈现出统一的突出效果。到这一步,建筑便成为了一个“身体事件”(body-event),其自身具有动态形式,所有形成自身的相关因素获得了协调,其特征是“真实而抽象”(13)Brian Massumi, Architectures of the Unforeseen: Essays in the Occurrent Art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9, p.93.。这一来,折叠成强烈的情感内容的事件便以身体为自己的有效生命:“身体是事件的生命。”(14)Brian Massumi, Architectures of the Unforeseen: Essays in the Occurrent Art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9, p.94.建筑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用身体事件阐释建筑的性质,给人审美的感觉多一些,审美因素作为在事件的各个维度之间瞬间扫过的一种动态文化行为形式,在马苏米看来充满了真实而纯粹的潜力。这种审美性会不会消解建筑作为艺术的政治性呢?这是马苏米紧接着摆出的议题。他设问道,在这种拓扑式的建筑设计过程中,政治作为形成因素进入了哪里?其能否不以外部框架的形式约束性地施加给过程,而成为过程固有的主动性?尽管林恩本人对这个问题保持了沉默,但马苏米认为,其对身体的看法孕育了答案的方向,那就是“身体事件永远不会中立”(15)Brian Massumi, Architectures of the Unforeseen: Essays in the Occurrent Art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9, p.76.。其论证要点是:身体事件产生出的影响力,在由隔膜引起的拉力场中分布不均匀,设计过程的吸引力与排斥力之间的差异,随着经济与文化差异而以不同的方式进一步传递后续效果(这一点触及了政治的关键:话语区分及其文化政治后果),设计的情感力消失在一个复杂的景观中,在整个景观中,其影响是不均匀分布的,并在质量上有所不同,转导过程只能在这个政治层面上继续下去而反复进行。因此“身体事件是人类身体的端口。参政。这是个可以重新受到政治欢迎的政治起点”(16)Brian Massumi, Architectures of the Unforeseen: Essays in the Occurrent Art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9, p.76.。这样,马苏米的事件思想围绕作为事件的审美政治而层层推进,而且愈往后愈自觉地从思维方式的根基上深化这条主线,成功地将德勒兹等欧陆思想家的事件论拓展到了英美学界,在一个具备经验论优势的传统中接续和扩展了事件研究的魅力。尽管受到后现代惯习影响而以建筑为探讨核心,事件的上述身体政治性质,也是旨在创造出切身场面的文学的基点所在。因为在身体的感受与体验中打开政治维度,同样氤氲出了文学的当代意义。
连续意味着情境,审美与政治在身体中的事件性统一,于是进一步提出了事件的情境性问题。对情境的建构一般来说是语言论出现后的自然议题,符号在此的建构力量把诗学引向政治的一面,身体事件的出现则有望补充政治这一面,而深化情境的完整面。
五、事件由此情境化
事件的情境化阐释,较早发生在晚近人类学领域。出版于2015年的《在事件中:走向普通时刻的人类学》中,两位编者、分别系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文化与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的洛特·梅内特与布鲁斯·卡弗雷尔,集中讨论了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从情境(situation)角度对事件的研究成果。
两位学者试图超越以格尔茨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方法,把事件视为人类学分析的中心而非一种社会概念,作为一种力量的独异性来探索,探索其中社会文化存在的关键维度如何揭示出正在形成的社会文化现实的新潜力,从而超越将事件看成社会中某种代表的传统观点,而把它把握为对潜能的肯定与实现。这个方向与编者们信赖的后结构主义者,主要是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思路一致,后者强调社会是在多重转移与实现过程中的虚拟。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不是一种封闭整体,如同以康德先验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涂尔干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展示的那样,而是一股超越其所能表达的范围的力量。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事件转向,是由以马克斯·格卢克曼等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发起的,它“远远超出了仅仅将事件作为已知事物的例证或说明来对待的范围”(17)Lotte Meinert,Bruce Kapferer, In the Even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Generic Moments,New York: Berghahn, 2015, p.16.,不再仅仅被视为必然支持一般民族志叙述的例子,相反被视为独异性以及关键的民族志时刻。在此,事件作为一个特定的强度平台,使事物通过事件本身的实现而有效地变得可知,后者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迄今尚未实现的潜力的创造性熔炉。其中,伴随着虚拟过程的冲突与紧张的事件,并不能被视为功能失调或病态,而应被积极地视为对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定义,它推动着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打破过去的模式而产生了最初的制度秩序,表达了社会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不可通约性。
在这样理解事件时,格卢克曼既强调经验主义的重要性,同时避免经验主义。后者表现为,情境分析需要抽象地列出理解所涉及的步骤;前者则表现为,情境分析更需要描述事件所包含的动态过程。这种做法被人们概括为“抽象经验主义”,并被两位学者拿来与格尔茨的“厚描述”概念作比较,他们将事件方法定位于人类现实不断变化这一点上,认为变化而非停滞才是人类学研究的环境,人类不以一个连贯的整体生活于他们的世界,而总是在多个维度上不断成为历史形态的各个方面或时刻,这得发展出相应的“事件社会学”(sociology of events)。(18)Lotte Meinert,Bruce Kapferer, In the Even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Generic Moments,New York: Berghahn, 2015, p.11。美国学者休厄尔(William H.Sewell JR)是事件社会学的倡导者,可参见William H.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81-123。例如马歇尔·萨林斯主张在人类学研究中,为事件的动力学增加另一个文化价值的维度,以抵消事件分析中可能存在的还原论因素。他举例道,库克的谋杀诞生于当时的情感紊乱与紧张局势中,这在人类学事件中被创造性地重建为一种有意的牺牲行为,并由此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所以,这一事件影响了后来的行动神话。这些情况为人类学研究——当然也应包括审美(艺术)人类学等分支——注入了新的活力。
有趣的是,论及事件的这种能量时,人类学家们还联系“后人类时代”(19)Lotte Meinert,Bruce Kapferer, In the Even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Generic Moments,New York: Berghahn, 2015, p.19.,指出对事件思想的研究应选择建构主义路径,以回应后结构主义转向影响之下的反建构主义方向。曼彻斯特学派认为,由此形成的方法,值得推广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自然也包括文学。
如同符号所处的符号关系通常被称为语境一样,对情境的建构意识,主要来自从福柯的话语权力到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建构主义)这一脉语言论学理。上述事件人类学与社会学在此基础上的重要贡献,是将不断多维变化的因素引入情境建构,既保证了变化的经验性,也始终将变化涵摄于界限这一超越经验的轮廓线中,认为这才是面向未来、富于意义的情境。那么,事件的情境建构是靠怎样的建构者、也就是主体来完成的呢?
六、事件由此形成情境建构的主体机制
事件的主体机制,在美国学者罗宾·瓦格纳-帕西菲奇出版于2017年的《什么是事件》中可窥线索。帕西菲奇借助保罗·利科等学者有关历史叙事中事件的作用的论述,认为既然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包含开始、中间与结尾,那么,需要探讨事件是如何扮演造就现在、中止过去与改变未来的重要角色的。他由此反对记忆研究。许多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都假设被记忆的事件已经结束,因此记忆本身错过着事件。帕西菲奇认为,社会学中的记忆研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分析在时空中固定事件的物体——纪念性的石头、废墟、纪念碑、审讯听证会与各种纪念活动等来进行的。但“纪念物、演讲、石头与博物馆只是事件本身暂时凝固的时刻”(20)Robin Wagner-Pacifici, What is an Event,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6。另参见同书第135页对“事件空间”的论述:“这里提出的方法设想了一些空间——包括但不限于传统的事件空间,如纪念馆——在这些空间中,事件仍然存在。在这个愿景中,事件被理解为从这些空间、个人、机构与集体的经验、界限和使用方式中汲取生命。”,会导致“事件的理论化”而石化(petrify)事件。
虽然事件因此难以普遍化,但帕西菲奇又认为,这不妨碍对事件可以作理论分析与研究。因为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对比结构与能动性的词汇的做法变得流行起来,其致力于解释社会生活如何既具有约束性又具有重力性,在这个框架中,事件被帕西菲奇看作是“通过活动动摇结构的一种铰链元素”(21)Robin Wagner-Pacifici, What is an Event,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8.。和格卢克曼一样,他也举了人类学与历史学领域的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元素的勃兴。人类学家萨林斯反对结构与事件之间被夸大的对立,而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提出了“连接性结构”这个显得有点矛盾的概念来缓和结构/事件的区别。历史学家威廉·休厄尔也把事件定义为相对罕见的偶然事件的子类,充分顾及结构的转变。受到这些近期研究成果的鼓舞,帕西菲奇认为可以尝试走出传统二元性词汇表的含糊性,以更具生产性的姿态来正视事件的形式与流变,动态化地进入事件。这便需要掌握事件的形式与流变动态,“比喻性地思考它”(22)Robin Wagner-Pacifici, What is an Event,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11.。他援引法国哲学家拉图尔的一段阐释文字为证。拉图尔质疑社会科学中描述与解释的区别,认为对一个事件的解释仿佛接力棒,不应当突然跳转至一个仿佛能解释穷尽与彻底的整体性虚拟框架中,任何这样的虚拟,只是比赛的不断继续而已,有意义的是拒绝转向任何超验结构,以免暴露存在的巨大缺口。这便需要来重构事件的主体,不再将其关联于超验性力量。据此,帕西菲奇从一个独特角度——政治符号化(Political Semiosis),解说了事件的主体机制。
这一主体机制是:事件的所有过程都由政治符号学的三个要素来同时完成,即述行(performative)、指示(demonstrative)与表征(representation)。(23)Robin Wagner-Pacifici, What is an Event,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p.19-20.奥斯汀所发现的述行情形,被帕西菲奇认为对身份影响最为明显与直接,而身份的发现与事件密切相关。他以“九一一”事件为例指出,导致一些人对这个突发事件感到进退两难的,是在世界贸易中心发生这个不确定事件后一小时左右时间里,一个目击者在确定自我的身份这点上陷入了困境:我是旁观者还是证人?抑或只是受害者?这种身份的转换或许用时很长,但可以肯定,作为身份转换实质的言语行为,是影响这种转换的关键时刻。换言之,事件是这种身份识别工作的集中。签名、声明与命令等,都属于明显的述行要素。事件的多变性,与这种身份认同上的不确定性有关。帕西菲奇认为,这便需要在对事件的解释中,动态地开辟允诺偶然性的空间,它同时依赖于指示与表征这两个事件的其它功能。指示性,维系于事件的情境性,因为任何事件都无法发生于上下文之外,上下文本身在不断变化,进行着扩展、收缩、合并与排除,尤其是指示词主动地重新配置着上下文,借助焦点、姿势与手势等变更着情境中的方向。因而,活动参与者和观众,在关系与身份转换过程中,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确定前方与后方是什么、哪些因素仍在进行中、哪些已完成、哪些是近距离的因素、哪些则遥远、何为中心何为边缘等,这些体现着事件在动变中的指示性要素。帕西菲奇由此给出一种独特的分析:“如果没有副本,任何事件的生存时间都不会超过一瞬间,也不会有事件的表征性转换的逃逸。这是因为每一个拷贝都呈现出新的东西,不管这种新的东西是它在一个系列中的位置、它与新背景的关系、不断变化的复制技术,还是别的什么。”(24)Robin Wagner-Pacifici, What is an Event,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26.“副本”即帕西菲奇所说的表征性。
仍以一场灾难性事件为例。其“副本”可能包括当地的报道、政府要员的定性与自己的事后判断等一系列渐进、反复的表征,它们复杂地交缠于对事件的理解中,实际上也是事件之所以为自己的题中之义。不难感知到,身份也就是这种表征性副本的产物。帕西菲奇在这里强调,体裁对于政治符号化的表征性尤为重要,小说、戏剧、诗歌、绘画与照片之类体裁,都形成并移动着事件,大众媒介传播中对突发新闻的标题处理,便体现了体裁对事件框架的意义赋予。当所有的政治符号系统协调起来并构成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事件,其转折点遂避免了永久性的固化倾向。事件独异性的动力也维系于各种现实条件,而不像法国事件论那样,每每以死亡、战争等为极端驱动力。这种显得更为平和的走向不仅值得重视,而且明确地将作为事件主体性动力的“副本”维系于文学等体裁,让我们看清了文学力量对事件的支撑。
既然事件中的主体已非某个特定的人,而是基于语言论精神的政治符号学建构力量,这就最终指示了事件思想的伦理走向。因为一个符号在符号关系中才存在并获得意义,始终受关系性语境的制约而相应地具备限度,语言的差异性“揭开着理解的限度本性(limited nature)”(25)Ilai Rowner, The Event: Literature and Theory,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5, p.109.,使伦理的实现必然与语言的创造有关,那是一种对主体脆弱性的深刻时代认知。
七、事件由此展开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好客伦理
事件的主体超越自我而涉及他者,这种基于好客与想象的事件伦理,是晚近学者们对德里达事件思想的深化。德里达认为事件不可预见,主体面对不可预见的事件不是被动麻木地应承,而恰恰获得了责任的起点,即以好客的姿态去迎接它。这种好客并非来自主体设定的某些条件,而是由另一个人的事件产生的,此即事件的伦理——无条件的好客。在作为到达者的事件到来之前,主体无能为力,当事件尚未发生,主体措手不及,暴露出绝对的弱点、脆弱性与无力感。唯有在这种主体觉得没有能力接待他者的情况下,到达者的到来才会构成一个事件。在《友爱的政治学》中,德里达认为“我们永远首先是通过应答、当面对(自我、自我的意图、行为、言论)负责。其中应答这种方式更本源、更根本和更无条件”(26)[法]雅克·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胡继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页。。在此,责任已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权力设定,而是与一种开放的、无法预估的未来有关,是对不可预测的事件——因而也即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事件——的反应,它总是突破了充分理由的框架设定。可见,围绕事件的伦理性,德里达实际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将传统意义上每每显得强势的“责任”观念改造为弱势的;二是相信弱势者才更具备对责任意识的敏感。
这两点在更为年轻的事件论者手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美国学者约翰·卡普托2006年从神学诠释学角度对事件与名称的关系进行研究,表明当事件发生时,它独立于我而产生并降临到我身上,是来拜访我的,这种拜访是我必须处理的,无论我是否喜欢,它超出了康德意义上的可能经验的条件,而构成了不可能的经验,成为“放大了的超现实主义事件”(27)John D.Caputo, The Weakness of God: A Theology of the Event,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1.。那么,如何理解事件神学是如卡普托所说的“超现实主义”呢?另一位美国学者克莱顿·克罗克特出版于2018年的新著《书写终结后的德里达:政治神学与新唯物主义》,对此及时作出了阐释。克罗克特分析指出,卡普托对事件的这些界说,受到了德里达后期思想对宗教与神学问题的重视的影响。卡普托早期的作品是关于托马斯·阿奎那、海德格尔与埃克哈特的,其1978年出版的《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秘元素》一书展示了海德格尔哲学与埃克哈特的密切关系,但嗣后卡氏转向激进的解释学研究,借鉴德里达而开始发出自己的哲学声音。在此基础上,克罗克特呼吁将解构作为一种激情来对待,激情是一种证明语言、写作与说话的他者性的力量,其召唤超出了写作者的预估,成为一种对不可能的祈祷,解构主义由此致力于解决的事情,就既是可能也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不能认为解构主义关注的只是我们在认识与渴望方面的可能性,相反,不可能性才是它应正视的目标。这里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关注可能性的解构操作会倾向于一种差异性结果与产物,尽管有差异,差异在获得确定性这点上却不至于引起怀疑;关注不可能性的解构操作,则主张不把差异视为一种可被构造的、实质性的东西,因为那样做的实质是赋予事件一种从外部加上去的强大逻辑——或拯救,或复活,相反,视之为不简单以字面方式发生、却始终正在发生的东西,承认“事件是一种独异性,它是一种造成差异的差异,是一种情况的根本转变或变形”(28)Clayton Crockett, Derrida After the End of Writing: Political Theology and New Materialism,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00.。这也即事件在克罗克特看来超现实的缘由。以超现实为前提,责任的弱势以及相应的好客伦理才都有了原动力。
接续了这种好客伦理的,是韩裔德籍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他用“他者的消失”来命名自己的书,认为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正在变得高度同质化的时代,同质化带来了他者的不断消失,在形成“同者”之间的结合——荒淫的同时,营造出了充盈的空虚,在这种空虚里,原本应当作为他者深深刺激我们的引诱力消失了,这就是思考及其事件后果的不幸式微:“思考可以通往全然他者,它会使同者中断。其中蕴藏着它的事件属性。与此相反,计算则是同者的无尽重复。与思考截然不同,计算无法产生新的状态。计算看不见事件的存在,而真正的思考却是事件性的。”(29)[德]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6-7页。韩炳哲相信,正是这种同质化造就了恐怖主义,因为它是拒绝对话的、极端非理性的。他用相对于启蒙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一词概括这种非理性情形,认为剥削不再以异化的面貌出现,而是披上了自由与自我实现的外衣,它被韩炳哲描述为自恋。自恋而不愿去接纳异质的他者并与之对话,是他所指出的逐渐失去独异性——从而失去了事件——的现状。既然这是一种主动的异化,根据韩炳哲的分析,他者的上述消失趋势便每每是以对真实性的追求为外衣的。这又仍是新自由主义生产自我的基本方式:我把自己当货物,在生产与展示自己的信念驱动下,实则营销着自己。这个过程是在与他者的持续比较下进行的,在比较中,他者不断地被转换为同者(同质),而遗忘了“他者首先以抵抗姿态报到”这一点。(30)[德]韩炳哲:《暴力拓扑学》,安妮、马琰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页。韩炳哲由此借用德里达的好客理论,指出康德对永久和平的启蒙式倡导,是旨在以一种无条件的、最大限度的热情好客姿态来实现其主张的理性,与常见的党同伐异现象相反,这种基于理性的强制主张的好客,允诺了一种敞开怀抱的他者性友善和权利,成为普遍理性的最高表达。这便将独异性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于理性,与德里达等学者从不可能性来谈论事件与他者,显示出了联系中的异趣,也更为中肯地拈出了好客伦理的对话性要义。
作为限度意识的伦理,在事件的好客中由此得以充分展开。它源自事件的政治符号运作,以语言符号为主体,显示了伦理、事件与语言的内在统一。而这三者的结合点,显然即文学的发展前景所系。从这个意义上不妨承认,事件思想确实是与文学运作方式有关的一种思想。
结语:意义与局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七种事件思想新走向尽管具备开阔的涵盖性,似乎不专为文学而发,但细究其间的学理脉络以及触点,又每每让人感到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了文学。对此,我们可以在上述每部分最后一段过渡性小结的基础上再集中加以深化。
倘若承认贯穿这些新走向的精神是从“物”向“事”的转化,以及在转化中对各种因果预设的自觉超越,那么应该看到,事件的实质被前沿学者们继续把握为叙述与所叙述之事之间并不平行对等、相反总是拉开着张力的叙述学本体问题,它本质上是文学问题。美国学者拉里·格里芬在探讨历史社会学对事件进行结构分析的方法时,不仅对事件作出“在有限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的界定,而且接着指出“对事实的解释意味着对未发生的事情的解释”(31)Larry J.Griffin, Narrative, Event-Structure Analysis, and Causal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hicago: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5,No.5, pp.1094-1133.。正如其所言,叙事本质上是时间性的,但在实际处理中,它常常被从因果性角度加以利用。他由此发现,在时间性与因果性之间取得平衡,是值得历史社会学研究追求的方法论目标。这不难得到推演。因果性是把对象视作物、从而作抽象逻辑概括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它来自视点的相对性,视点克服自身相对性后的敞开,意味着走出物化的对象性思路而融合其与周遭的生存亲缘,这个自分而合的过程,是激发出叙述与所叙述之事的张力、而非让前者去垄断后者的文学智慧的运作。以此观照,上述诸家让时间产生分形而引出事件,克制时间的因果化趋向而积极使之创造出可能性,从事件角度理解物以及自然而还其广义,从物化的变异中回到生存本体,持守主客交融的情境,在自身视点中平等兼容他者视点,这诸般努力的共同旨归,确乎是一种文学效应。事件思想的深层文学机理正在这里。
从这一文学效应出发,对以上新走向的现实意义,可以看得更为分明。鉴于事件的实质维系于叙述与所叙述之事的张力,我们在包括上述各家在内的谱系中,不断领略到事件思想的四方面主要现实意义:(1)让事件的发生和对事件的描述,努力实现为不隔的一者;(2)分割形而上学思想强度;(3)介入他者;(4)虚拟折返。这四点显然都在某种程度上植根于文学,属于文学的独特优势。它们使事件思想理所当然地激活着今天的艺术创作活动,(32)Jack Richadson,Sydney Walker, The Event of Making Art,Reston: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Vol.53, No.1,2011, pp.6-19.乃至教学活动。(33)Charles R.Garoian, In “the Event” That Art and Teaching Encounter,Reston: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Vol.56, No.1,2014, pp.384-396.而贯穿这四点并将它们推向高潮的,则是伦理意义在事件思想中的凸显。按上述走向,事件伦理只能展开于不适宜性中,如《思考事件》一书在以“事件的伦理”为题的结语中所道出的那样:“伦理就是对存在的事件的不适宜性(inappropriability)或秘密的‘承载’。”(34)François Raffoul, Thinking the Event,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0, p.311.这种伦理意义同样顺应文学的现代嬗变。如果说传统观念对文学是否必然承载伦理使命这一点有所争议,进入现代以后这种争议则逐渐消弭,海登·怀特便把“历史叙事的道德化功能”作为立论基石,指出“叙事完全可以凭借其关于道德智慧的教导,或关于在文化而非自然条件下存在的不可还原的道德主义的教导,宣称具有认知权威”(35)Hayden White, The Narrativization of Real Events,Chicago: Critical Inquiry, Vol.7,No.4, pp.793-798.。在此语境下,融渗于新走向及其文学效应中的伦理,便构成事件思想在今天得到持续研究的严肃意义。
诚然,事件的初衷是超越各种被预设的形而上学前提所决定的思路框架,摆脱例证地位而获得独异性,深入冲击传统形而上学大厦,这却也或多或少滑向了某种非理性境地,比如强调事件中绝对的差异及其不可能的经验后果。从历史上看,尼采等开启的事件思想谱系,确乎从一开始便与“非理性转向”联系在一起,它伴随着差不多同时兴起的“语言论转向”,因为语言被有力证明为是不具备实质性的符号系统,其性质是任意性(arbitrariness),任意的,自然首先是非理性的。但这不表示思想史由此走向了相对主义,相反,非理性中孕育着更高的理性智慧,如同明确提出“事件化”概念的福柯及时澄清的那样,“这个程序依赖于比它们的直接实施更为普遍的理性形式。”(36)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 Peter Miller,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80.所以,事件的非理性特征其实包含着两种情况:一种是语言论意义上的非理性,它仍创造着意义而具有建构性,如同当代事件思想前半阶段不少论者所做的那样,本文论及的事件的本体论解释学化趋向,也是此意的表达;另一种则是进而不满于语言论对差异原则的持守,认为那有可能再度凝固起某种安稳、武断的形而上学实体,而在对语言论原理流露出某种怀疑的前提下反对理性,以致走向无法言说的神秘与虚无。后者作为发展至今的事件思想的局限,呼唤着我们实事求是地对之加以客观的审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