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尽的恐惧
2021-11-22青丝
青丝
普鲁斯特说过一句非常沮丧的话,认为自己可能今生都写不出想写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每一个从事文字写作的人,是否都有过类似的念头,但可以肯定,每一个从事文字写作的人都考虑过才思枯竭的问题。曹禺晚年就公开谈论过写不出作品的内心痛苦,余华也表示这辈子就算往死里写,也写不出像《活着》这么受欢迎的书了……
文字创造力是造化赋予写作者的一项卓越天资,写作者具有这一禀赋之后,便再也无法接受自己有一天会失去这种能力。江郎才尽的担忧,会像梦魇一样,时刻萦绕在每一个写作者的心头。然而,如同江淹在梦里被郭璞索回五色笔,从此诗作再无佳句的例子比比皆是。
曾为英国文学偶像、引领先锋主义的王尔德,人生后期落魄到熟人一看见他就躲,喝酒都要赊账的地步。他于困厄中写信告诉朋友,做梦死后去到天堂,天使抱着一大摞书拦在门口问他,王尔德先生,你还有这么多书没写,怎么就来了?其实他不是不想写,而是这时候,他除了偶尔还能说一两句俏皮话博人一粲,再也写不出任何有分量的作品了。
写作者的才华穷尽,除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创作巅峰已过,也因为人的成熟世故、老练稳重,与想象力是无法共存的天敌。人对于世界的感知,是各自的大脑对于外界环境的间接还原,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思维多标新立异,性情更为怪诞冲动,有助于发掘创造力的潜能。很多人年轻时写作,想到什么写什么,不拘章法,亦无所畏惧,敢于把各种古怪的想法与现实结合到一起,激情与自我就是创意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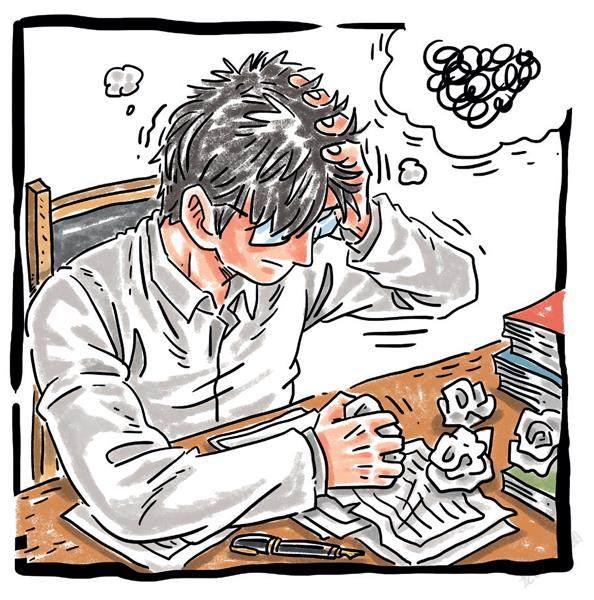
但是写到了一定的阶段,作者对社会、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多的掌握,思考加深,就会逐渐发现之前作品的幼稚和不足,对于自我创作有了更高的要求,不敢再在离经叛道的界线上游走,也不再依赖过去对世界的直觉性认识。如以“纳什均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纳什,一生为精神病症所困,他自述回归到理智“不完全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思考的理性将限制强加于人,制约了人们对自己和宇宙之间的可能性”。
很多写作者就是陷入到這样的怪圈中,从傲视一切到磨平棱角,文字由直抒胸臆到玩弄各种技巧,写作的野心大了,诚意却少了,逐渐丢失了最初的激情与灵气,作品由此不再动人。我看过不止一个作家回忆早年的创作历程,坦承自己都不知道过去是怎么写出那些作品的,放到现在就再也写不出来了——人的困扰往往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而是出自人对事物看法的改变。
才思与灵感有时就像一种随机的奖励,遽然而来,又翩然而去,但越是难以捉摸,给写作者带来的情绪反应也越强烈,不论是欣喜还是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