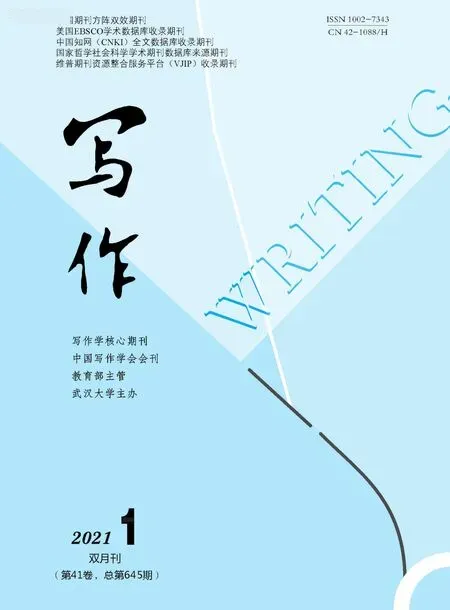创意写作的类型路径
——以电视剧《三叉戟》为例
2021-11-22谢尚发
谢尚发
有研究者指出:“文学作品以族群也就是以类型的方式而生存,乃是文学史的一个客观事实。”①石昌渝:《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这所描述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存在的样态,实际上通过这样的样态描述,所指向的乃是创作者内在的创作路径。所谓的“族群”“类型”在最初并不一定以类型成规的方式存在,只是在作品创作与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被总结出来。一俟类型成规被总结出来,反而逐渐被接受为文学作品存在的样式,并通过“影响的焦虑”传递给后来的创作者,从而成为其创作的出发点与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研究者们声称:“成规不是创新的敌人,恰恰相反,它是创新路标。没有成规,创新不可想象;找不到成规,创新就找不到落脚点和方向,盲目创新,或者自以为是的创新,其实是真正的陈词滥调。”②葛红兵、许道军:《创意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这需要辨析的恰恰是创意写作与叙事成规之间的关系。
2020 年5 月31 日,由刘海波导演,沈嵘和吕铮编剧,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三叉戟》首播,获得一致好评。这部改编自吕铮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剧之所以获得好评,在于它改变了观众的审美习惯,以类型片作为创新导向,并基于人物塑造的逆向思维,从而产生了别致的审美趣味。这其实正是创意写作在类型叙事成规基础之上所结出的硕果,于此也能透析创意写作的类型路径。
一、创意写作与类型成规
以《故事形态学》驰名世界的普罗普,曾在他的《神奇故事的衍化》一文中,阐述他把运用于植物学和骨骼学的“形态学”一词引入到“神奇故事”研究领域的理由:“故事研究在很多方面可以与自然界有机物的研究进行比较。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民间文学专家,都要与同质现象的诸多种类和变体打交道。……无论在自然王国还是在我们的领域,现象的相似性并未得到准确客观和绝对令人信服的直接解释,它依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可能会有两种观点:或者认为两种表面没有关联也不会有关联的现象的内部相似并没有共同的遗传根源——这是物种独立产生论;或者认为这种形态相似是某种遗传关系的结果——这是认为相似是经由有这样那样起因的变形和衍化途径而产生的起源理论。”①[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2页。在前文的“中译本代序”中,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涅赫留多夫引用这一文章时,翻译稍有不同,但似乎更容易理解。“无论在此或在彼,都可能会有两种观点:或者认为两种表面没有关联也不会有关联的现象的内部相似并没有共同的遗传根源——这是物种独立产生论,或者认为这种形态相似是某种遗传联系的结果——这是源于或此或彼原因而发生变形和衍化的起源论。”参见该书第4页。这段话既是他为自己所开创的“故事形态学”研究的可行性所做的辩解,也同时指出了他研究的核心价值和意义,以及所关注的对象所具有的内在肌理。“物种独立产生论”与“物种起源论”都是对物种所具有的“种类”和“变体”进行的概括与研究,将之置于神奇故事的研究正是因为普罗普看到了这种“种类”和“变体”广泛存在于许多领域。可以说,《故事形态学》所提出的理论正是奠基于“物种起源论”的观点,尝试从类型学的角度来切入,剖析“种类”的特征与共性。与此同时,创意写作强调独创性,与“物种独立产生论”颇为契合,但是所谓独创性的起源问题,与故事形态学所处理的类型成规密切相关,它又某种程度上是“物种起源论”的。
从万千民间故事入手,以形态学的研究方式关注其类型成规,把种类作为研究对象,最终抽象出“普罗普公式”②这一提法是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涅赫留多夫在“代序”中指认的,也是对普罗普研究的一个十分精准的概括。参见[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这是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研究的思路。在某种程度而言,创意写作实际上是走了与“普罗普公式”恰好相反的路径,即从类型成规的规约起步,熟知类型故事的叙事模式,并进而在成规中容许变化的部分加入新鲜的要素,从而实现“由种类到变体”的质的升华,以此实现创意的目的。对于创意写作而言,类型成规并非是束缚手脚的障碍,而是其合理的出发点,因为它不但有约束性、协调性,还有生成性。③相关论述和提法,参见葛红兵、许道军:《创意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9页。因此,在看到因为类型成规的存在而导致的“相似性”④普罗普正是看到了民间故事的这种“相似性”具有植物学、骨骼学的“种类”特征,才将形态学引入到故事类型的研究之中。参见[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2-153页。当代诸多文学批评也在指认同样的类同化、同质化现象的存在,尤其是在网络写作、青年写作中。参见谢尚发:《80后写作:器物、性事与现代性——以〈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为中心的分析》,《当代文坛》2016年第6期。、类同化、同质化的同时,还应看到类型成规存在本身作为一种基础所能提供的创生空间。甚至可以说,类型成规是创意写作的出发点,也指认了任何创新都是在既定叙事成规的基础之上展开的人类思维的最新进展。如果说类型成规、叙事成规⑤关于类型成规、叙事成规、成规、类型等概念,这里需要做一下界定。类型成规主要就写作的内容而言,从内容上来划分作品的叙事模型,最早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有论述,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等的划分就是依据类型成规来完成的。相应地,类型成规就意味着抽取故事形态学那种“普罗普公式”,可以规约这一类型叙事的基本框架。叙事成规主要就写作的文体而言,注重在形式上进行文体写作训练的规约,尤其是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这样的大类文体规约上,最为突出。这里所谓成规,实际上是指作品的内容或形式上长久以来而形成的固定叙述格式、样态,这一意义上,成规与类型是同义的,但成规更偏重于叙述意义上的,类型更偏重于叙事意义上的,即前者注重对文体的规约,着重于在语言上、叙述上定型某一类叙事文本,后者则注重对内容上的规约,着重于情节、叙事链条、故事类型等的定型。是创意写作起先最该掌握的规矩,那么作为起步阶段的基本功,它就不再是限定创新的条款,反而是促成创意产生的前提。这尤其体现在应用文体的写作上,但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
作为出发点的类型对于创意写作而言是必经之路,在文学史的长河中,类型成规、叙事成规是不少作家创意生发的基础。且不说如纳博科夫《微暗的火》容纳了诗歌、小说、评论于一炉,从而在既定的叙事成规的文体基础之上,创造了全新的小说样式,即便是莫言的《蛙》,书信、戏剧、小说等通通服务于小说本身,在看似陈旧的文体叙事成规上创造了全然一新的文学文本。这些都是成功的例子,也恰好证明了以类型成规、叙事成规作为基础所能够进行的巨大创意。非但如此,类型成规的巨大开掘潜力也呼唤着创意写作的青睐,尤其是近年来各种写作高手对内容进行跨类的改造与提升,使得探索创意写作与类型叙事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网络小说从最初的创作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类型成规,而后逐渐开始在类型成规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写作者也开始对类型成规进行改造。非但此,影视剧的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对类型成规进行改造、重组的道路。
一般而言,类型成规作为基础,其提供的创意写作实践的方向是丰富的,有研究者就直接总结为“类型写作的四大方向”,即类型化写作方向、反类型创作方向、兼类型写作方向与超类型写作方向①具体论述,参见葛红兵、许道军:《创意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2-611页。类似的研究还有张永禄、葛红兵:《类型学视野下小说类型的正体与变体》,《当代文坛》2017 年第5 期;许道军:《“作家如何被培养”——作为教学法的创意写作工作坊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其它还有类似的探索,但就类型成规而言,大体上体现为这些方向。。所谓“类型化写作方向”,是指在类型成规内部不违反规则的情况下,依靠着成规线条本身的创新来实现对类型成规的丰富、提升或深化。比如同为家族叙事,《红楼梦》所开创的线索是继承《金瓶梅》而来,却又有着向前的巨大推进;巴金的《家》则因为新时代因素的加入而呈现出新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差异,实现了创新;张炜的《家族》同样属于家族叙事,因为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对历史的复归等,获得了新鲜的品质而实现了创新。任何一种类型成规都不可能穷尽所有故事,只能是在成规的指导下发现、创造更多的故事。所谓“反类型创作方向”,指的是对既定类型成规的反叛,在看似反类型的叙事中体现着类型规约的弹性与张力。比如金庸的《鹿鼎记》所塑造的韦小宝,把英雄叙事的凛然大义、道德光辉等抹去,取而代之的是贪财好色、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等,但一以贯之的英雄大义、家国情怀等,却始终并未改变。在具体的行事风格上看似反类型的写作,实际上是从类型成规的对立面来确认类型成规的存在。所谓“兼类型写作方向”,指的是同时将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类型成规综合在一个故事类型中,使得同一个类型成规的规定性变得模糊起来,且因为其它类型成规的加入而获得了创新的品格,但故事类型本身又不因众多叙事成规的加进来而陷入混乱,反而能拥有较为明显的个体类型标志,从而实现创新目的。上面列举的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莫言的《蛙》便是叙事成规上兼类型写作的成功范例,而这里要分析的电视剧《三叉戟》也是兼类型成规叙事的例子。比较难以理解和把握的是“超类型写作方向”,它指的是将类型成规、叙事成规乃至于所有已经存在的成规与类型作为创作基础,从这些成规与类型出发又不拘泥于此的创作路径。也就是说,“超类型写作方向”是要站在既有人类写作的基础之上,融会贯通后实现真正的超越与自由,达成从必然王国跃向自由王国的目的,从接受成规与类型的束缚并适应这种束缚最终彻底摆脱这种束缚。人类文明史上一切卓然独立的创作都可以算是超类型写作,他们或者奠定了类型成规的基础,或者开创了新的类型成规,又或者将某一类型成规推向极致并奠定其最终形态。另外一种情况则是,站在所有类型成规与叙事成规的基础上,自由运用叙事成规于特定的类型成规,从而达到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契合。
四种类型的创意写作方向,从根本上而言仍然是奠基于普罗普所说的“物种独立产生论”与“物种起源论”两种认识论的倾向上。不管从众多的作品中寻找到那个决定种类成为种类的“普罗普公式”,还是从这个公式出发创造出更多的全新作品,根本上而言它们仍然存在着现象内部的相似性。从这个内部的相似性出发,独立产生论也好,物种起源论也罢,这个核心就能够生发出千变万化的成果来。这一如人类的存在,作为生命他们基本上是一样,但每一个人又都是独立的个体,既不能用“人的概念”来一笔抹杀“每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但“每一个人”也都无法逃脱“人的概念”的规约。知乎此,创意写作的类型路径,也就十分清楚了。
二、混杂类型的故事
因为存在着跨类、兼类的创意可能性,近些年来,甚至一直以来,都很少有作家纯粹地坚持一种典型的类型成规,而是旁涉多种,以求创新目的之实现。对于作家而言,创意不仅仅意味着开创一种全新的类型成规,也在于对类型成规的熟悉与自由运用。辗转腾挪间,作家熟练地操作着类型成规,令人耳目一新的结果也就很快诞生了。作家的创作如果说还有更为复杂的元素,网络小说与电视剧则更容易被观察出来,这一者是因为作家的独创性与市场接受度的差异,二者也是因为网络小说与电视剧本身的特质所决定,即作品的长度、题材开掘的丰富程度等。在创意写作与类型成规的视野下来观察《三叉戟》这部电视剧,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实践的可操作的例子,也能看出其间的成败得失。
《三叉戟》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混杂类型的故事”,在类型成规的运用上以兼类、跨类为特征的综合性类型叙事,成了它区别于其它同类电视剧的亮点。就这部电视剧的故事讲述来看,它至少存在着四种类型成规,即警匪故事类型、都市情感类型、成长故事类型和家庭伦理类型。《三叉戟》的核心部分是警匪故事类型,以崔铁军、徐国柱和潘江海为首的警察与以黄有发、小青为首的黑恶团伙之间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较量,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最终以罪恶团伙的全部覆灭、绳之以法落幕。故事随着情节的发展,又被分为两个有机构成部分,分别涉及刑侦和经侦,并由此构成、推进整个电视剧情节的发展。电视剧开头,即将退休的老夏惨遭匪徒的杀害,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并与犯罪团伙周旋始终,构成了前半段的刑侦故事。这其中不仅有匪徒的奸诈狡猾,也有警察内部的各种规定的掣肘等,以致于让故事处于未完待续的状态,并进而演化为经侦故事,让匪徒们的犯罪变得更加复杂,警察的智慧与果敢得到进一步的呈现。小人物纷纷出场,构成了故事的复杂网络,不但有匪徒所牵连着的许多周边人物,也有警察们的子女、亲人被裹挟进入,剧情瞬间充满了张力,错综复杂的布局关系、线索百出的侦破难题、经验老到的警察,以及无辜被牵连进去的普通老百姓、现代高科技设置的重重迷障……所有这些都充分将警匪故事类型叙事中双线并进、你来我往的紧张斗争包含其中,论者所指出的“彰显英雄崇拜、探讨人性的复杂阴暗、揭发社会体制的缺陷、展现暴力美学等”①论者所依据的对象主要是香港警匪片,这与大陆警匪片又有着不同之处。相关论述参见崔墒烈:《当下国产警匪电影的类型叙事——以〈烈日灼心〉为中心的考察》,《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8期。几乎一个不少地给带出来。三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所携带着的正义、法治气质,钱权交易的内幕故事情节、匪徒阴暗的心理和复杂的人性、执法过程中上演的器械或徒手搏斗……将这些叙事要素一一展示出来,可见《三叉戟》的完整警匪故事类型的架构。
如果单纯地把警匪故事类型如此编织起来,把相关叙事链条扩展、丰富,作为一个纯粹类型成规的电视剧,《三叉戟》无疑也可以成立。但要获得一定的创新,甚至说要获得口碑与收视率,它就需要加入新鲜的创意。考虑到观众接受的程度、影视审查的相关要素,稳妥起见,编创人员并未对之进行反类型化的叙事,而是选择了兼类和跨类的方式,在警匪故事类型中加入了都市情感类型、成长故事类型、家庭伦理类型,既调节了警匪故事类型的紧张的叙事节奏,也丰富了这一故事类型。都市情感类型的叙事,主要集中在崔铁军之子崔斌与同事老夏之女夏静怡、徐国柱与花姐的故事上。年轻人的故事,在现代都市的情感故事类型中,一般会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崔斌与夏静怡也不例外。他们从最初的相互熟悉,到一步步地牵手走到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述链条。虽然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但其间的坎坷曲折恰好来自于警匪故事类型的牵扯,使之与主要故事类型完美融合。徐国柱与花姐的故事,则是与年轻人的故事形成对比。作为经过了年月风霜的人,他们的爱情纠结着过去,尤其是“类匪徒”的董虎加入其中,又增添了故事的曲折性。他们爱情的若即若离,直到最后团圆收尾,因为徐国柱警察的身份与“主类型”故事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长故事类型主要围绕三个年轻人来展开:作为刚入警察行业不久的新人,小吕努力向三位老警察学习办案经验,这其间充满了各种挑战与危机,在应对挑战、化解危机的过程中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心思缜密的警察。崔斌的父亲尽管是警察,但他却尝试着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其中隐含着“成长与弑父情节”的影子。作为新新人类,崔斌投入到角色扮演的新行业,通过直播售卖道具获得经济收入。这条叙事链条新颖之处在于,始终存在着成长道路上“父子之争”的线索,一方面是父亲对儿子的逐渐理解儿子的成长,另一方面则是儿子用成长的实际来完成对父亲的脱离。夏静怡的成长故事又补充了成长故事类型的其他元素,即成长中的陷阱、困境与负面,战胜这些就意味着成长。夏静怡一不小心落入到匪徒设置的金融陷阱中,不但面临着自己身陷囹圄的困境,还连带着将周边亲人也裹挟进去,被以金融诈骗的罪名置入人生的负面。也正是如此,成长故事搭线并揉搓进警匪故事类型之中。三个人的成长故事,连同“类匪徒”董虎女儿的成长故事一起,构成了一个成长故事的群像,把这一叙事类型的要素带入其中。家庭伦理类型的叙事,在电视剧中相对而言所占份额较少,但却是有机构成部分,且与主类型故事若即若离,其存续关系全靠两个警察崔铁军和潘江海来维持。围绕着孩子的成长而发生的崔铁军与妻子之间的各种故事,既彰显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一面,也把夫妻之间的温情、小冲突、日常琐事等都代入其中,父子、夫妻、母子,这些家庭关系融入在一个故事框架内,把老百姓的小日子端出来,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与温馨亲情,作为类型规约被呈现出来。家庭伦理类型叙事中,还有一个侧面就是“灾难降临叙事”——各种家庭变故、内部争斗等将家庭陷入困境之中。这一类型规约被潘江海的故事所承担。一直试图下海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警察,随时准备赚取更多的钱,但天降灾难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女儿罹患重病,搅乱了他的平静生活。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一个人承担下所有的苦难,警察局了解详情后募捐了有限的资金,也让这个家庭暂时走出困境。也还是因为他的职业受到了奖励,深陷困境的家庭才被解救,这个解救的过程也是他警察事业的成功过程。
“主类型”与“辅类型”分工明确,且互为因果,纠缠交织在一起,让《三叉戟》的故事讲述既丰富又平衡。不过跨类、兼类的创意写作路径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即多线条的类型规约会彼此影响、削弱,从而导致故事的拖沓、繁琐,降低故事讲述的有效性。尽管都市情感类型、成长故事类型和家庭伦理类型都以某种方式被搭入到警匪故事类型上,甚至被揉搓进去,形成一个整体,但过多的笔墨也冲淡、分散了主类型叙事的集中性,让辅类型的叙事显得多余又不能自成系统,构成电视剧叙述的独立单元。完美地将主类型与辅类型融为一体,确实考验着叙述者的高超写作技艺与高瞻远瞩、超视建瓴的眼光。
三、反流行类型的人物
对于电视剧而言,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是提升收视率的重要手段。固定的类型故事同样有着固定的人设成规,他是有效保证类型故事向前推进且凸显类型特征的重要部分,与故事讲述本身密切相关。在普罗普的研究中,类型叙事本身有着不变的功能项与功能项的顺序性排列,而人物身上所携带的诸种外在症候,却是这种类型故事中可变因素,也因为这些差异而导致了故事的无限增长。“角色的名称和标志是故事的可变因素。我们所说的标志指的是人物所有外部特点的总和:他们的年龄、性别、状况、外貌、外貌的特征等等。这些标志赋予故事以鲜明的色彩、美和魅力。”①[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2页。对于固定的类型叙事来说,功能②在普罗普的研究中,所谓的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功能本身规定着角色的固定性,而角色的固定性同样推衍出固定的功能项。相关论述参见[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项是一定的,它的排列组合也是一定的,促成功能项落实的角色同样也是固定的,尽管对于这些角色来说,外在的标志不停地改变。因此,作为可变因素,这些外在标志或名称改变着不同故事脚本讲述的新鲜性,而不变的角色预设则是作为类型故事的特定规约。普罗普把俄罗斯神奇故事的角色界定为七个:对头(加害者)、赠与者(提供者)、相助者、公主(要找的人物)及其父王、派遣者、主人公和假冒主人公③相关论述可参见[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4页。。有了这些固定的角色,角色推衍出的固定的行动,组成了类型成规的功能项,角色按照类型故事成规的秩序逐个展开功能项便构成了类型叙事文本。对于类型成规而言,必须将角色固定,才能有推动者将类型行为付诸行动。创意写作的类型路径从这里展开,便是要明确角色的稳固特征与可变特征,既将之作为基础,又在可变因素上下足功夫,从而获得创新的可能性。
从类型成规出发,《三叉戟》的混杂类型叙事本身,包含着更为丰富的人设布局。其中,警匪故事类型中始终存在着对头或坏人(小青、黄有发)、警察(三叉戟与小吕以及全体破案民警)、受害者(夏静怡与小雪)、辅助者(董虎以及各种提供线索的线人)、相关者或见证者(家庭里的其他成员)等;而就都市情感类型而言,应该存在着男主人公(崔斌与徐国柱)、女主人公(夏静怡与花儿)、破坏者或搅局者(赵总与董虎)、亲友团或父母与朋友(崔斌母亲等)、相助者(化解危机的帮手)等;家庭伦理类型至少有父辈(崔铁军、潘江海、董虎)、子辈(崔斌、婷婷、小雪)、诱惑者(彪子、疾病或角色扮演行当)等;成长故事类型则包括主人公(崔斌与肖静怡)、施害者(黄有发、赵总)、辅助者(三叉戟或父辈)、伙伴(创业路上的合伙人)、指点者或高人(崔铁军)等。从这种人设布局来说,他们互相之间重叠交织,在承担功能项上却并不重复,反而一个人物角色常常能同时客串在不同的类型成规中且互不影响又勾连一起。恰是这种人物结构,保证了剧情的丰富性、吸引性以及主类型故事的多面性,也让辅类型故事既保持着存在的价值也少有喧宾夺主的场面。
按照类型成规的分析来看,《三叉戟》确实保持着固定叙事框架的严谨性,但既要创新,就需要保持可变因素的时刻存在,且能抓住时代的理解面。在普罗普看来,类型成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同一类型故事有着不可改变的“稳定因素”,而它们又有着丰富存在的原因则是因为众多“可变因素”的加入。他举例说:“派遣与出去寻找是稳定因素。派遣者和出发者、派遣的缘由之类是可变因素。”④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神奇故事的衍化》一文中,参见[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53页。就影视剧而言,类型成规中的人设同样如此。作为《三叉戟》的主类型,警匪故事类型是其重头戏,在保持类型人物的主要功能项上并未做出太大改变,这是稳定因素。但在可变因素上这部剧作可谓下足了功夫,尤其是对主人公标志的期待,几乎与类型成规的预设是相反的,可以看作是“反类型写作方向”的人物塑造方式。一般而言,警匪片中警察都是超级英雄,有着非凡的能力,他们年轻健壮、足智多谋又能随机应变地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哪怕是出格的行动。但在《三叉戟》中,三位警察主人公则是年老力衰、即将退休的状态,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超级英雄的伟力,更不用说以高超的武艺令人信服地制服坏人。所谓的足智多谋、机智过人,也只不过是年轻时练就的江湖套路、甚至是下三滥的把戏,纯粹靠着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从心理摸排探案线索,从而侦破案件。他们年轻时冲动犯错,年老了也仍然与江湖混混脱不清干系,现代科技在他们身上几乎毫无用处,多少年积累起来的江湖道义却成了他们破案的重要帮手。从警察的职业道德来看,这甚至是违反规定的。职业能力的下降与超级英雄的想象相违背,江湖义气成为侦查手段,英雄的风头被无情的现实所限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起来,对类型成规的背离,甚至是反类型的设定,都让这部以警匪故事为主类型的电视剧显得与众不同。
不唯此,人物角色的可变因素丰富类型成规的同时,也与时下流行的人设观念有着背离与调和。在“小鲜肉”时代,“老戏骨”成了一种反衬——在电视剧的预设中,与流行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拨正是其诉求,但也并不拒斥。老演员们贡献演技,显得从容、顺畅,但剧中的年轻人小吕、崔斌等也都是一干小鲜肉。在价值观念的传递上,使用老戏骨对小鲜肉的同性恋怀疑的桥段,巧妙地讽刺了当下流行文化中的性别倾向,却也用了父子的和解与老一辈的观念转变化解了这一对立与矛盾。尽管这样有圆滑与价值观含混的弊病,但却用人设的布局与故事的推进,化解了小鲜肉与老戏骨之间的尴尬,甚至价值对抗。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三叉戟》的人物角色搭配与故意的反类型化,实际有着两种考量:其一,对类型的角色的稳固因素进行保留,但在角色的标志等可变因素上进行大胆变革,甚至以反类型的写作方式来归入到类型成规之中;其二,对流行的人设类型观念进行背离,却又将之整合起来,以实现与时代的应和,同时在价值的设定上既是一种矫正,也是在矫正的基础上进行理解与价值观的重塑。反类型的叙事并非要背离类型本身,只是以通常方式的反面出现而已。
四、结语:创意写作的类型路径
什克洛夫斯基曾就文学的陌生化指出:“创新是对它之前包括创作模式、创作框架在内的成规的陌生化,新形式的出现不是为了表达新的内容,而是为了取代已失去自身的艺术性的旧形式。”①转引自葛红兵、许道军:《创意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他注重的自然是“形式主义”的侧面,但也明确了对创作模式、创作框架等的陌生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陌生化的工作不是偏离类型成规,而是以之为基础的再出发。因此,从成规来创新,已经成了创意写作的一个重要共识②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葛红兵、许道军主编的大学《创意写作教程》中,甚至可以说,这本书的基础观点既是从成规出发,开始创意写作的各种训练。因此该书的开头除了突破障碍、激发潜能外,第三个起步阶段的重要工作就是“从成规上路”,此后所论述的基本上是创意写作的实训。。抛开作为文体规约的叙事成规不说,因为文体训练是创意写作训练的基础,从文体的特定规约开始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基础性的,单说类型成规,从之出发来进行创意写作的训练,既能知晓类型故事的特点从而避免出现雷同、撞车现象,也能很好地从类型出发进行创新,在稳固因素与可变因素之间寻求平衡。一般而言,创意对类型成规的利用有两种,一个是突破,即创造新的叙事成规;另一个则是整合,即在既有类型成规的基础上来求取创新。只是不管是突破还是整合,二者都要求谙熟类型成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创意写作的类型路径,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其一,对类型成规的重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其叙事模式的探究;其二,在稳定要素与可变要素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平衡既是对创新的追求,也是遵循成规的前提;其三,类型成规通于人类的思维模式,创建新的类型成规或归入既定成规,都是对人类思维模式的深入探究;其四,在创意写作与类型成规之间,知晓其中互相生成与转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在《文学理论》一书中,韦勒克、沃伦指出:“优秀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类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展它。总的说来,伟大的作家很少是类型的发明者,……他们都是在别人创立的类型里创作出自己的作品。”③[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创意写作的类型路径,所指的正是在类型成规内部进行创新的探索与尝试。因此,从类型成规内部如何进行独创性作品的建基活动,也就成了写作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事情。按照普罗普的解释,功能是构成故事类型的基础,按照类型成规的约定,任何类型都存在一个功能排列的叙事链条,从此可以归纳出类型故事的公式;角色是类型成规的稳定要素,他们使功能获得实现,或者说他们推动了功能的产生,促成了类型故事的完成。如何写出鲜明、典型的角色,本身就考验着创作者的写作才智,再加上角色标志物、外在特征与内在气质等的可变要素,这一创意写作的类型路径就已经彰昭出来了。功能本身以及叙事链条同样是基本规约,作为稳定要素不可改变,但功能项的重复、复杂与扩展,则又是可变要素,同样指明了创意写作的方向。稳定因素构成类型的基础也同样提供了创意写作可资继续前行的资本,可变因素又能成为创意写作挥洒才华的领域,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三叉戟》正是在类型规约上严格遵循警匪故事类型的叙事模式,使得它基本的面目很清晰,又因为对基本叙事的调整、扩充甚至是背离,以及对可变因素的最大化改造,而获得了独创性的品质。
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并未停留于“普罗普公式”,而是推向更为深层的对神奇故事历史根源的探讨。因为在他看来,故事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并进而反映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最终与人类思维模式勾连起来①相关论述可参见[俄]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8-22 页。尤其是其论述的“故事与原始思维”,更彰显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来说,类型成规的形成,是人类思维模式作为基础而形成的对世界的认知与解释,因此对类型成规的把握实则是对人类思维的探究。创意写作根植于人类的独特思维,也以这种思维作为创新的依据,更是在这种思维的基础上前行。文学创作是对人类思维的最佳呈现方式之一,它理应承担起这个责任。从类型出发,沿着类型成规的道路前进,并最终回到类型规约上来,这已经超离了形式与内容的契合问题,而是呈现为创意写作从理念生发、构思框架、落笔成文、修改校订等,自觉地对人类思想进行不懈的探究。创新之所来便是如何更好地领悟、探究人类思想,类型规约只是作为这种领悟和研究的载体与表达罢了。因此,所谓创意写作的类型路径,不仅仅在于类型成规提供了创意写作的出发之路与依傍之途,给初学者甚至是创造者带来前行的资鉴,还在于它能够从人类思维模式出发,去提升创意写作对人性、人类思想的更深的开掘与深挖②当然,从这一点来看,《三叉戟》并没有太大的创新与掘进,仍然流落在收视率与商业思维的窠臼之中。但作为一部有所追求的电视剧,它在可变因素与类型成规的创新上,着实也走出了一条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