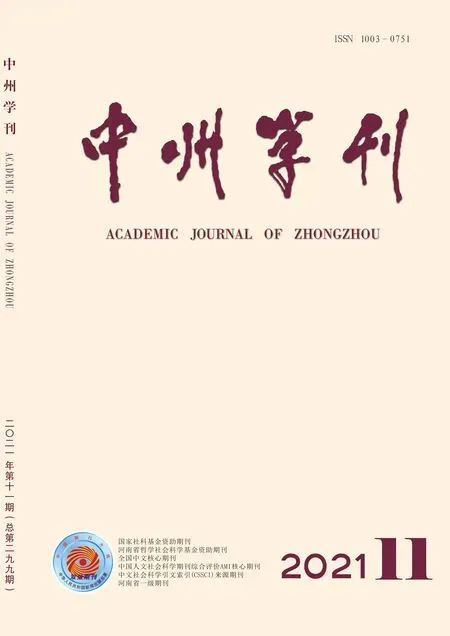康有为“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说论辩述评*
2021-11-21姜广辉肖永贵
姜 广 辉 肖 永 贵
“壁中书”系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主阵地,是破解汉代经今、古文之争这一学术公案的关键。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付梓,将《史记》《汉书》所载“壁中书”事全归刘歆伪窜,全力以今文经学非难古文经学,直接引发了晚清、民国对汉代经今、古文的再争论、再认识。其时,学界围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命题展开激烈论辩,其“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论更是成为争论的焦点。既有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疑古派”学者大力推崇和阐扬康说,也有洪良品、朱一新、符定一、钱穆等驳正者从康说的立论依据、论证逻辑以及具体论据,驳正其谬误,瓦解其论说。双方的激烈论辩,在晚清、民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推崇与阐扬者无非是为康氏摇旗呐喊,驳正者虽然对康说进行了严正驳斥,但仍待进一步完善,方可宣告康有为“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说谬误的终结。故此,本文立足康氏“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说,梳理晚清、民国学界对康氏的推阐与驳正,评述其中是非,弥补学界对康氏“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说及其论辩缺乏全面梳理的缺憾①,为破解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学术公案提供裨益。
一、康有为所谓“壁中书”及其真伪论辩
《伪经考》中“壁中书”仅出现七次,康氏论说仅三次,另四次是其辨伪对象。据此,“壁中书”似乎不是康氏“新学伪经”说的重心。但细读全书,“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实为康氏力证“古文经典系刘歆伪窜”的核心。所以,须弄清“壁中书”的初始概念与内涵,对比康氏所谓刘歆伪造的“壁中书”,分梳晚清、民国对此形成的论辩,述评其得失。
1.“壁中书”的初始概念与内涵
“壁中书”首见《说文解字·叙》。许慎说:“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②所谓“古文”,是相对于秦汉流行的“今文”字体而言的。秦汉流行的“今文”字体是隶书,而“古文”乃是曾经流行于六国的篆体文字,孔子旧宅壁中所出之《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皆用此种文字书写。这些经典不仅书写字体不同,篇章内容也有差异。许慎编撰《说文解字》,曾从这些书中选择文字材料,列举古代篆书、籀文的写法。
唐代的颜师古注《汉书》,两次提到“壁中书”。一是注“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时说:“壁中《书》者,多以考见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③此“壁中书”专指孔安国所得孔壁古文《尚书》,属经学体系。二是注“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时说:“古文,谓孔子壁中书。”④与许慎所说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称“孔子壁中书”是一种独特的书体,既不同于秦汉流行的隶书,也不同于时人曾见的缪篆和秦小篆,故笼统称之为“古文”。当时学人所谓“古文”,其意是较“篆书”和“缪篆”更古老的文字,甚至以为是仓颉最初所造的书体,如《晋书》卷六十《索靖传》载:“(索靖)作《草书状》,其辞曰:‘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蝌蚪鸟篆,类物象形。’”⑤“古文”又被称为“科斗文”或“蝌蚪文”,因其书体中时见蝌蚪状笔法而得名。孔安国古文《尚书序》称:“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⑥《后汉书》卷九十四《卢植传》载卢植上书有云:“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形似科斗,因以为名。”⑦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叙及晋太康元年发现的《汲冢竹书》时说:“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⑧古代谈论“科斗文”的学者中,杜预曾亲见“科斗文”的实物,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古文”或“科斗文”并非空穴来风。由于孔子旧宅古书及《汲冢竹书》后皆失传,后世学人包括康有为皆无由得见“古文”(或“科斗文”)书体,因此转而怀疑“古文”(“科斗文”)文献之有无。
关于“古文”(“科斗文”)书体,直到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图版公布,学术界才重见这一书体。原来许多字今日楷书写成横与竖或捺的结合,此种书体则写成大圆点与竖或捺的结合,这样便满篇多见“小蝌蚪”了,“科斗文”之名当是由此而得。宋代朱长文《墨池编》说:“蝌蚪篆者,其流出于《古文尚书序》,费氏注云:‘书有二十法,蝌蚪书是其一法,以其小尾伏头似虾蟆子,故谓之蝌蚪。’昔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宫室,得蝌蚪《尚书》。又《礼记》《论语》足数十篇,皆蝌蚪文字。”⑨《墨池编》所谓“费氏注”,概指南朝梁国子助教费甝,费甝曾撰《尚书义疏》十卷,其书今不传。“虾蟆”,今人称为“蛤蟆”;“虾蟆子”即俗所谓“蛤蟆骨朵”。实际上这是一种曾经流行于六国的篆书文字。当时汉代诸儒所称之“古文”经典,多由此种书体书写。
“壁中书”史实载于《汉书·艺文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⑩《汉志》进一步明确恭王坏宅所得,有“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可以实证汉晋时代所出之古书确曾有不同于隶书、缪篆和秦小篆的“古文”书体,《汉书》所记并非虚构。而刘歆责让今文博士,主要并非强调此种书体的特异之处,而是强调“壁中书”的经学价值,以期立古文经博士,辟今文经学之弊端。
2.康有为所谓刘歆伪造的“壁中书”及其真伪
康氏认为刘歆伪造的“壁中书”包括三类:一是古文《尚书》,含伏生所藏、孔壁所藏、河间献王所得;二是壁中古文经典,即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三是“古文字”材料“壁中书”。康氏《伪经考》将三者全力证成伪经,激起晚清、民国最激烈的论辩。
首先,孔壁古文《尚书》。康说:“《汉·志》所谓鲁共王坏壁所得之《书》也,《史记》于《鲁共王世家》何以无之?且其时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同异若何?史公于《河间世家》何以无之?”继而论证《汉书·艺文志》所载鲁恭王坏壁得《书》事是刘歆为了伪乱《尚书》而窜入,并引刘逢禄说:“盖此十六篇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刘歆辈增设之以抑今文博士耳。”钱玄同认为,“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经之事”是《伪经考》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康氏甚至怀疑伏生壁中《书》,“考六经之传,有书本,有口说……伏生于《尚书》是其专门,即有百篇,皆所熟诵”,《诗》与《春秋》等篇幅较长的都可依赖口传保存,伏生又是秦博士,其《尚书》本没有被烧,为何非要依赖壁藏?于是得出“壁藏亡失之说更不待攻”的结论。
壁中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是否刘歆伪造?经符定一考证,《孟子·万章》《孟子·尽心》《礼记·缁衣》《尚书大传》《史记·殷本纪》《汉书·律历志》等文献皆曾引此十六篇中之事。符定一说:“总核诸证,知十六篇中已有十一篇见于经典,足以征其不伪矣。”今文经学家认可的《孟子》引《伊训》《武成》,《礼记·缁衣》引《尹吉(告)》,《尚书大传》引《九共》,《殷本纪》言“作《汤诰》”“作《伊训》”“作《典宝》”“作《原命》”,都是“康不能诬为歆窜、歆窃,亦莫由诋为歆造、歆绐者”。足见今、古文经学家都认可十六篇古文《尚书》。清前期考证学家阎若璩在其《尚书古文疏证》第八卷第一百一十三条明言:“予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康有为对这一重要考证结论故意视而不见,否认历史上曾有真《古文尚书》十六篇出现。
这里,我们认为还有两个关键人物:鲁恭王刘余和河间献王刘德,需要略做介绍。汉景帝共有十四子,鲁恭王刘余为汉景帝第四子,河间献王刘德为汉景帝第二子。两人都是汉武帝的庶母兄长。司马迁与汉武帝、鲁恭王、河间献王是同时代人而略晚,因他为李陵辩解而遭受宫刑,其后发愤著《史记》。虽身为史官,但著《史记》之事并非受命于上,而是出自其私人意愿。由于当时的遭遇,对当朝之事无论从资讯来源或形势避忌方面,多有掣肘之处,难免有详古而略今的不得已难处。因而他记叙汉景帝十三子之事极其简略,只记叙“景十三王”的爱好和世次,寥寥数语带过。即便如此,司马迁还是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提及:“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此处记载正同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之事相应。司马迁惜墨如金,既然在《儒林列传》中提及此事,又何必在《鲁共王世家》中再提此事?正因为《鲁共王世家》没有重提此事,康有为便断言这条是刘歆窜入《史记·儒林列传》的。康氏不能自圆其说的是,刘歆既然能窜入《儒林列传》,为杜绝世人怀疑,再窜入《鲁共王世家》应该也不难。所以,康有为这种说法较为牵强。另外,康氏由当时经师能背诵《诗三百》使《诗经》得以传世,推论伏生也能背诵《尚书》之文,不必依靠壁藏之《书》传世。从学术规范来说,这不过是一种推论而已。其实《诗经》诸诗都是有韵之文,便于背诵,且传习甚广。《尚书》乃是上古官方的政治档案,佶屈聱牙,本不便于记诵;且古字古音,一字之差,谬以千里。若无文本,如何传习?即使秦博士所职之书可以不烧,秦末兵荒马乱之际,秦博士们逃难四方,谁会带着许多竹书逃难呢?
其次,壁中古文经典。在《汉书艺文志辨伪》上、下篇中,康氏先说刘歆乱《史记·儒林传》,以便坐实伏生壁中藏《书》,得出“壁中古文之事,其伪凡十”,以证壁中古文《尚书》皆为刘歆伪托。进而将《礼》《记》《论语》《孝经》全归刘歆伪造,分述于“礼记”“论语”“孝经”类,强调“刘歆为《七略》、修《汉书》,于是杂窜古文诸经于《艺文志》《河间献王鲁共王传》中”。
古文经典是否刘歆伪造?洪良品对比《汉书·王莽传》《西京杂记》《史通》,驳正“刘歆伪造古文经典”并无实据,因《汉书》载刘歆“颠倒五经”而非伪造。《王莽传》载公孙禄说:“太傅平化侯(唐尊)饰虚伪以偷名位……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公孙禄说唐尊“饰虚伪”与刘歆“颠倒五经”,明显不同。因为“‘颠倒’二字,训诂不作‘造窜’解,于是非则曰‘颠倒’……若‘造窜’,则当论有无,不必计是非也”。公孙禄指责刘歆“颠倒五经”,主要针对其想立古文经学。符定一、钱穆专门寻找证据阐明《周礼》《左传》早在刘歆前已有之,故必非刘歆伪造。第一,《周礼》行于周、秦、汉。符氏找到《周礼》行于周之证十四条,行于汉之证十条。第二,刘歆之前已有人引《左传》,分别为子夏、荀卿、刘向、翟方进(刘歆师)、班彪诸人,以及《孟子·万章下》《韩诗外传》《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左上》诸书,尤其是汉代今文学家和汉朝礼制都有引《左传》。钱穆也认为:“路温舒、张敞等引《左氏》尤在前,而方进之传《左氏》,则有明证矣。”
我们知道,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久已不传。古文《礼经》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今文《仪礼》十七篇相同,多出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康氏并未见到其书,不知何以便断定其为刘歆伪作?《论语》《孝经》既有今文本,也有古文本,内容上的差异本不很大,姑置不论。至于《礼记》只有古文本,并无今文本。《礼记》各篇明显非成于一人之手,前人推断是七十子之徒散佚之作,汉儒将其汇编成一书。其中《大学》《中庸》《礼运》之篇为儒学的经典文献,康有为所作《中庸注》《大同书》依托的就是后二篇。他虽然没有关于《大学》的专门著作,但在其著述的其他地方有不少论述。康有为在《伪经考》中将《礼记》定为刘歆伪作,自相矛盾,康氏何以自圆其说?
最后,古文字材料“壁中书”。在《汉书艺文志辨伪》下篇中,康氏将涉及古文字的所有材料都归于刘歆伪造,不仅这些用古文书写的经典版本是刘歆伪造的,这些“古文字体”也是刘歆伪造的,为的是要推行“小学”。
古文字是否刘歆伪造?钱穆认为,康氏对《史记》所载古文字“均诋为刘歆所窜改”,而对《汉书·地理志》载十一次“古文字”、三十八次“禹贡字”,“则一字不提及”,因后者属今文经学,“不但证明有古文《尚书》,且证明有《周官》……且证明有《左传》矣”。符定一以《史记》《中庸》载“书同文”和琅玡台石刻为据,认为“孔子书六经,势不能不用古文”。逐一辨证《说文》有古文、有今文,还有古今共用之字,“用之于今文经不伪,用之于古文经则诋为伪,岂理也哉?”古文、小篆、今文一贯,“小篆与今文经字不伪,则古文亦不伪”,并且《说文》所载古文、籀文、小篆,符合文字发展的繁简演变规律和原则,足证古文字不伪。
钱穆、符定一所言甚是。汉晋以后学者虽然未曾见到这种“古文”字体,但都相信它是历史存在,很少有人存疑。康有为勇于疑古,断然否定它是历史存在,认为一切所谓古文经典连同它的文字载体全都是刘歆伪造的。这种做法实在鲁莽,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传播极为有害。
二、康有为推论“刘歆伪造壁中书”及其论辩
康有为以为,刘歆作伪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他善于制造和利用伪经前提、佐证,并且他有伪经的能力、能量和凭依。为了证明“壁中书”都是刘歆伪造,康有为还有一套自己的论证体系,晚清、民国学界就此也形成了激烈的论辩。
首先,康有为认为,“秦焚书”是刘歆窜乱诸经的前提。《伪经考》载:
(刘)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一则曰“书缺简脱”,一则曰“学残文缺”,又曰“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又曰“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学者习而熟之,以为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说之是非,故其伪经得乘虚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书之权为之也。
将《史记》载“秦焚书,书散亡益多”视作刘歆“乘虚而入”、伪窜六经的窜入之地。据此,刘歆才能冠汉代学术以“书缺简脱”“学残文缺”,以便“假校书之权”,全面伪经,推行古文经学。其实,这里有一个秦焚书对文化破坏程度的评估问题。康有为的潜台词是,虽然有秦焚书在先,但秦博士所藏图书依然完整,不存在“书缺简脱”“学残文缺”的问题。所以“书缺简脱”“学残文缺”云云,都是刘歆人为制造伪经的借口。
其次,康有为认为,刘歆乱《史记》、撰《汉书》,为伪造古文诸经做铺垫。对于后世学者而言,有关汉代的背景材料,只有记载国史的《史记》《汉书》为人信据。康推测刘歆的心理:刘歆为了兜售古文经典使人相信,先在《史记》《汉书》上下功夫,有意在司马迁《史记》中窜入了古文经之事。在康有为看来,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古文经之事,所谓古文经之事纯粹是刘歆制造出来,加入历史中来的。而《汉书》中记载古文经的材料非常之多,所以康有为破天荒提出“《汉书》为(刘)歆所作”而非班固所作。
《史记》《汉书》所记之言、所记之事,晋代以后之人已不能尽明,因而有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司马贞的《史记索引》,以及唐代颜师古的《汉书注》等。诸人皆为一流的学问家,皆不曾言及刘歆伪窜《史记》、亲撰《汉书》。况且与《史记》《汉书》时代相近的文献资料甚少,像刘歆伪窜《史记》、亲撰《汉书》这类议题本无资料加以证实,康有为以臆断式的推论来立论,是欺世人难以证伪其说。然而,与康有为同时代的洪良品即起而反驳,他根据《史记》《汉书》记载,结合《史通》《二十二史札记》等后人考证,论证刘歆曾续撰《史记》,而非窜乱《史记》;《汉书》作者确系班彪、班固父子,而非刘歆。
在我们看来,康有为为证刘歆伪经,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这样说的结果,却间接把刘歆塑造成了文化巨人。你看,以刘歆一人之力,能够伪造多种古文经典,能够创造出一套系统的“古文”字体,能够编撰出前四史之一的《汉书》来。若非文化巨人,谁能有如此宏大的文化成就?以至章太炎说:“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这是不是对康有为的反讽呢?
最后,康氏为了证明刘歆的能力和能量,论证刘歆凭其家学渊源与绝人之才,借王莽之权与私人、私党、故智之力“倾售”伪经。刘歆“上承名父之业,加以绝人之才,故能遍伪诸经”。刘歆、王莽互相利用,“歆既奖成莽之篡汉”“莽又奖成歆之篡孔”。康氏推论,两汉倡导和推行古文经学的,都是刘歆的私党、私人、故智,私人百数、故智千数。“私党”主要是与刘歆同事一朝者。歆为国师,受莽尊信,故《说文序》列“爰礼、杨雄、甄丰皆其私党”。“私人”,即“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此百数人被征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伪古文、奇字之学者也”。“故智”乃王莽所征通古文经者。因“刘歆工于作伪,故散之于私人……如古文经传,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征天下通《逸礼》、古《书》《毛诗》《周官》……诣公车,至者千数,皆其故智也”。
就此,洪良品、符定一、钱穆三人直言,汉代今、古文经学之间如冰炭般互不相容,今文家何以不直指刘歆伪经?洪良品认为,刘歆责让的太常博士为何只说刘歆“非毁先帝所立”经典,对康氏所谓刘歆“私改诏书”之罪,夏侯胜、师丹等对刘歆“怀恨怨怒”之人,“何不发其增改诏书之罪,甘受其责”。符定一也说:“太常为大庭广众之地,歆即胆大妄为,决不能向太常博士任意虚构,将无说有,假使捏造事实,而博士怨恨,三公大怒,岂有不指摘其作伪者。”就康氏所谓刘歆“预布”售书之人,钱穆指出:“此数千人者遍于国中四方,何无一人泄其诈?”尤其是与刘向、刘歆父子同校书的尹咸、班斿、苏竟、校书天禄阁的扬雄,桓谭、杜林,以及师丹、公孙禄、范升等深抑古文诸经者,既无一人说刘歆伪经,也无人发现其伪经迹象。且“《伪经考》谓所征通小学者皆歆伪遣,又谓(扬)雄从歆学,则奇字亦出歆手,(刘)棻何忘其家丘而转学从雄?”
我们以为,如果真如康有为所说那般,王莽、刘歆互相利用,刘歆能量巨大。为什么王莽不久败亡,遭到清算,而刘歆却没有遭到清算,他所倡导的古文经学反而在东汉时期如日中天一般发展起来,涌现出如郑兴、郑众、贾逵、许慎、马融、郑玄、服虔等著名古文经学家,难道他们都是误信刘歆伪经的受骗者吗?可见,康有为为了使今文经学发皇光大,向古文经学发起疯狂的挑战,并且造成巨大的文化影响。应该说他借助了晚清社会要求变革的时势力量,不能说他手里掌握了真理。
三、关于康有为坐实“刘歆伪造壁中书”及其论辩
如何坐实刘歆伪造“壁中书”?康有为有其论证的逻辑起点、论证原则。然而,其逻辑起点和论证原则都不能成立,而且自相矛盾。
第一,逻辑起点——“秦焚书未尝亡缺”。康氏先认定秦虽有焚书之令,“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继以《史记·儒林列传》为基础,定“六经”未曾亡缺,故后世新出古文就是伪作。他还先假定“刘歆伪作诸经”。《伪经考》开篇就说,“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后汉之时,学分今、古,既托于孔壁,自以古为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伪者也”。后又力证“西汉新学皆系于伪”。
其实,康有为这一逻辑起点并不能确立。先不说“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是否事实,即便如此,也不能预判古文经典一定不会问世。国家秘府所藏,一部典籍就可能有多种写本,而有秘府校书确立定本的事务。而一经校订成为定本,便以今文——隶书的形式在社会上传写流布。此后,由于各种因缘,原来藏在山岩屋壁的六国时期的简帛文献写本就有可能陆续出现,因为文字书体与今文不同,而被称为“古文”经典,它不仅文字书体不同,篇章内容也有所不同。汉代已是“尊经”时代,“古文”经典因为距孔子时代更近,更接近孔子原意,所以受到热爱古文经学的学者的重视和推崇。这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康有为认定“六经”未曾亡缺,后出古文经典皆是伪作,这种推论是相当武断的。
第二,论证原则——凡《史记》《汉书》记载不同,全从《史记》,以“史迁不载”为金科玉律,力证《汉书·艺文志》所载壁中古文为刘歆伪造。一是不容司马迁有失,其未见、未说的,都不足信。康氏认为,史迁曾亲登孔子堂,“未尝言及孔庙所藏之六经有缺脱而叹息痛恨之”。迁既亲见,“若少有缺失,宁能不言邪?”更有甚者,“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不容不见矣”。二是对比“壁中书”与今文经,史迁不载,即为伪经。他说:“(《诗》)三家之外,史公无一字。”“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其传经,安有不叙?”足见康氏以《史记》为辨伪的根本参照,将《汉书·儒林传》所涉古文旧事,如“缀周之礼”“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中的“为之传”“六学从此缺矣”,视作刘歆“增窜”“暗窜”“复窜”,得出“《史记》不著,盖出刘歆之所伪”的结论。对此,赞同者如顾颉刚认为:“我们可以用康长素先生的方法,拿《史记》《汉书》的两篇《共王传》来比较……这真奇怪:为什么《汉书》全钞《史记》,却多了‘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经传’的一事呢?”足见其不仅赞同康说,更推崇其对读比较的方法。顾颉刚将康氏所谓刘歆“征天下异能之士”以售经视为“毒辣”,说:“这件事情,手段非常毒辣,一方面把古文学的种子散播到民间,一方面又令今文学增加许多敌人,凡古文学家的眼光中感到的‘乖谬’和‘异说’都扫空了。”痛恨之情可见一斑。
反对者则竭力驳正康氏《史记》《汉书》对勘法。因为,康氏既认定《史记》是刘歆伪窜之书,又在《史记》《汉书》比勘中唯《史记》是从,以伪证伪,实难令人信服。《史记》是否刘歆伪窜,朱一新认为:“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符定一则认为,《史记》不止一人一家,“歆何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遍改民间所有之《史记》?”
比勘《史记》《汉书》,唯《史记》是从,康氏论证谬误有二。其一,朱一新、洪良品都认为康氏对于《史记》所载“合己意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故康氏以《史记·儒林传》立论,却有意无视《史记》所载“孔氏古文逸《书》十余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起其家”。其二,康氏以其所谓刘歆伪窜之《史记》证刘歆撰作之《汉书》,谬误更甚。故洪良品对梁启超说:“信如尊言,则《史记》为窜乱不可辨之书矣。何以贵师(康有为)必专据此书,但于其中有合己意者,则曰铁案不可动摇;有不合己意者,则以为刘歆所窜入。”批判康氏对《史记》的取舍,态度极不客观。符定一也认为:“康(有为)谓《史记》(刘)歆窜,《汉书》(刘)歆撰,焉用引之;《别录》(刘)歆依托,焉用援之。既张其盾,复建其矛,以矛攻盾,遁词知其所穷矣。”更有甚者,“《西京杂记》为伪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辨之已详”,康氏大量引用姚说,又以姚氏所辨“伪书以攻人之伪,谬妄实甚”。
汉初推行黄老之学,直到汉武帝时才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言。这时朝廷所能做的,只是网罗儒学耆旧,对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才刚刚启动和展开。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人,所以《史记》中只有《儒林列传》,专注于当时传经之儒的记叙,而没有如《汉书·艺文志》那样的篇章,详述典籍的汇集和概述。以《史记》所未载断言后世文献皆伪作,那《汉书·艺文志》所载,岂不全是伪书!康氏这个论证原则显然是说不通的。
四、结论
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将汉代所出古文经典,关系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核心内容——“壁中书”全归刘歆伪造,实际是为其倡导变法的政治目的张本。就此而言,康有为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其政治目的。在今人看来,康有为倡导变法的政治目的是正当的,因而对其《新学伪经考》中武断的学术见解多持一种宽宥的态度。但是我们更欣赏马克思的观点,一个正当的目的,不能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因为“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因此,我们并不应当宽宥康有为的这一思想方法。
也有学者提出康有为所使用的“疑古辨伪”的考证方法,对“古史辨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的确是一个事实。现代“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就特别推崇《新学伪经考》考辨古史的方法。“古史辨派”冲击并矫正了盲目信古的史学痼疾,对于科学研究古史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古史辨派”的过分疑古,也对史学研究产生了负面作用。这是学术界所应认真反省和检讨的。
从经学历史的实际情况和康有为的论证来看,康有为的“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之说,既不符合经学历史的实际情况,在论证过程中又存在主观臆断、牵强附会、自相矛盾等种种错谬,自然会激起晚清、民国关于经今、古文全面之争的激烈论辩,促成晚清、民国的经今、古文之争。其实,中国传统典籍和历史中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变革思想可供倡导社会改革之用,康有为未能从传统经典中吸收这些养分,殊为可惜!而其随意借用经今、古文之争的历史倡导变法,以致故意迂回曲折地歪曲史实,则是吾辈学人应当引为鉴戒的教训。
注释
①现有关于《新学伪经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来源、初刊、古籍辨伪价值、论说逻辑、反响、禁毁、康有为今文经学与晚清政局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新学伪经考》的重新审视等方面,主要成果有:李耀仙:《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5期;胡建华:《首请禁毁〈新学伪经考〉者非安维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陈占标:《〈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朱维铮:《重评〈新学伪经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1期;贾小叶:《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於梅舫:《以董生正宋儒:朱一新品析〈新学伪经考〉旨趣》,《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孟永林:《安维峻首请禁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补正》,《文史档案》2014年第3期;张欣:《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与晚清变局》,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6月;李少波:《〈新学伪经考〉古籍辨伪平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黄开国、黄子鉴:《〈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比较》,《孔学堂》2017年第2期;於梅舫:《〈新学伪经考〉的论说逻辑与多歧反响》,《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5期;申海涛:《求真与致用:〈新学伪经考〉的重新审视》,《理论月刊》2019年第11期;皮迷迷:《以“今古之辨”解“汉宋之争”:一个考察〈新学伪经考〉的视角》,《人文杂志》2020年第5期。对康有为以今文经学非难古文经学的核心——“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的论辩,则几无论及。②〔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315页。③④⑩〔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7、1722、1969、212页。⑤〔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9页。⑥〔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15页。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116页。⑧〔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897页。⑨〔唐〕朱长文:《墨池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八一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5页。〔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6页。按,《汉书·艺文志》作“《礼记》”,但段玉裁结合《汉志》《说文解字》记载,认为是《礼》《记》,并说:“所谓《礼》者,礼古经也……《记》者,谓《礼》之记也。”《汉书》,第1318页。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2012年,第31、57、391、29—30、30、55、71、5、47、60、143、111、103、103、5、2、3、10、19、19、22、38、127、36页。符定一:《新学伪经考驳谊》,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8—19、19、55、2、65、64、10、5、1、7页。〔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附古文尚书冤词》(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02页。〔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25页。〔清〕洪良品:《洪右丞给谏〈答梁启超论学书〉》,叶德辉编:《翼教丛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57、51、53页。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1、8、2、108、48页。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1页。顾颉刚:《古史辨序》,《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页。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32页。〔清〕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二书》,叶德辉编:《翼教丛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4页。马克思的德文原话为:“Wenn der Zweck die Mittel heiligt, dann ist der Zweck unheilig.”又翻译成“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或者“用不正当手段达到的目的,不是正当的目的”。参见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