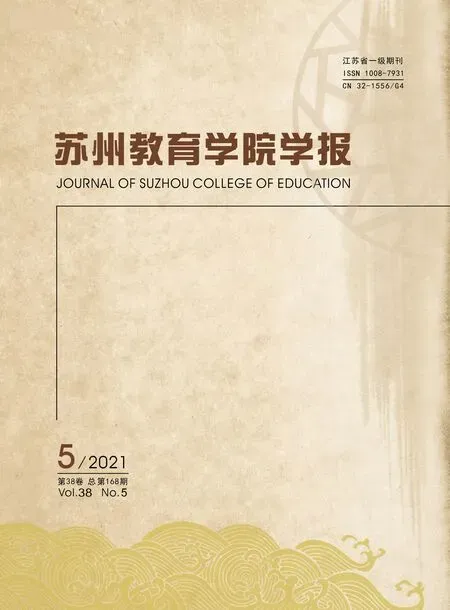再论东晋时期浔阳陶氏的阶层升降
——以乡品考察为中心
2021-11-16胡伟
胡 伟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3)
关于东晋时期的浔阳陶氏,魏斌《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一文曾对其发展历程予以考察[1],指出其在东晋经历了从武到文、从军功走向隐逸的变迁,对于这一结论,笔者基本赞同,然对于浔阳陶氏在东晋门阀社会中的阶层升降,仍有可讨论之处,本文即从陶氏家族相关成员的乡品与仕宦入手,试图勾勒其政治发展的脉络,以期对前人的研究作一点补论。
一
关于浔阳陶氏家族最早的记载为陶侃之父陶丹,《晋书》卷六六《陶侃传》:“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2]1768西晋平吴,陶侃一家身为孙吴旧臣,由鄱阳迁至浔阳。简括史料,孙吴时期曾担任扬武将军者还有全绪、钟离牧、陆式、吴景、张休、朱异,分析几人出身,全绪、吴景与朱异皆因对外作战获得军功,如全绪,《三国志》卷六○《吴书·全琮传》裴注引《吴书》:“琮长子绪,幼知名,奉朝请,出授兵,稍迁扬武将军、牛渚督。孙亮即位,迁镇北将军。东关之役,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以破魏军。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3]1383吴景,《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传》:“景常随坚征伐有功,拜骑都尉。袁术上景领丹杨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孙策与孙河、吕范依景。……衔命南行,表景为扬武将军,领郡如故。”[3]1195-1196朱异,《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恒传》:“异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钦七屯,斩首数百,迁扬武将军。权与论攻战,辞对称意。……评曰:……吕据、朱异、施绩,咸有将领之才,克绍堂构。若范、桓之越隘,得以吉终。”[3]1315-1316钟离牧则镇压孙吴内部五溪蛮与山越叛乱,如《三国志》卷六○《吴书·钟离牧传》载:“会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骑校尉。……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纯等散,五溪平。”[3]1393-1394陆式与张休没有武功,由于出身吴郡大姓陆氏和张氏,可对陶丹获任扬武将军略作推论。唐长孺认为:“孙吴的建国乃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对于另外各个宗族集团即宗部的胜利。”[4]据此可知,陶氏家族应是孙吴时期鄱阳地方的土著豪族,支撑了孙吴建国工作。如依陈寅恪推论陶侃出自溪族[5],则陶氏家族便是早期实现了“归化”的宗部。至于浔阳陶氏的地方豪族的族风,从陶侃之母湛氏身上也可窥见一斑,《晋书》卷九六《列女传》: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氏每纺绩资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坩鲊遗母。湛氏封鲊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鄱阳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时大雪,湛氏乃撤所卧新荐,自剉给其马,又密截发卖与邻人,供肴馔。逵闻之,叹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显。[2]2512
陶侃母所属的豫章湛氏,为豫章五姓之一,据魏斌文[6],史籍中豫章湛氏在东晋南朝时期人物不显,但经历了南朝时期地方土豪的发展与寒人的崛起,最终在唐代被被确认进入《氏族志》,其在地方上的势力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与其相似的便是陶氏家族亦被确认为浔阳三姓之一[1],在孙吴时期便联姻的陶、湛二族地位相当,都属于孙吴的地方土豪,《列女传》记载的湛氏不受官物、撤席喂马、卖发供肴的事迹,亦是地方豪强任侠的表现。
二
在确认陶侃出身的浔阳陶氏家族属于孙吴的基层武力豪强阶层之后,那么陶侃在东晋时期的仕宦经历便可以理解了。宫崎市定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政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门阀政治(贵族制),在贵族社会中,门第的高低首先体现在贵族子弟任官之际。最初被任以官职称作“起家”“释褐”或“初仕”,起家时的官职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以后的升迁。东晋继承曹魏以来的九品官人法,贵族子弟由其籍贯所在地的中正官授予乡品,而贵族子弟在什么官职上起家,这与乡品的高低密切相关。然而,这种制度进入东晋以后已变得有名无实,完全固化。高门贵族全都被授予乡品二品,于是,二品之家的子弟通常都从六品官起家。[7]60-67因此,这里首先对陶侃的起家官与乡品进行探讨,以观陶氏家族这一时期的发展。关于陶侃早期的仕宦经历,《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有以下三则:
侃与敏同郡,又同岁举吏,或有间侃者,弘不疑之。[2]1767
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2]1768
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晫曰:“《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书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武库令黄庆进侃于广。人或非之,庆曰:“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庆后为吏部令史,举侃补武冈令。与太守吕岳有嫌,弃官归,为郡小中正。[2]1768-1769
关于陶侃的乡品,首先看其作为起家官的县吏。唐长孺曾针对孙坚少为县吏时的情况指出:“孙氏皇室是富春的豪族,却不是高门。吴志卷一孙坚传说他少为县吏,陈寿评说他孤微发际。我们知道东汉时的县吏已不像西汉时期一样受人尊重了,高门子弟固然不屑为之,连非高门的名士也不肯屈就。可是县中的土豪却依然多据其职。”[4]17孙坚起家县吏,其孤微发际与非高门的情况与陶侃几乎无异,似可以之推断陶侃起家县吏的寒微身份。
其次可从与其一同举吏的陈敏身上再进一步推断,《晋书》卷一○○《陈敏传》:“陈敏字令通,庐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东海王军谘祭酒华谭闻敏自相署置,而顾荣等并江东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遗荣等书曰:……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欲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2]2614-2617对于陈敏“七第顽冗,六品下才”,阎步克认为其中“七第”当作“九第”,代表仓部令史的官品为九品,陈敏的中正品(即乡品)即为六品。[8]因此,一同被举为县吏的陶侃的乡品,应与陈敏相近,不登二品,而这里陶侃仕宦无门的窘境也可印证这一点。
最后,陶侃因“寒宦”就任了被“中华士人”所不齿的孙秀的掾属。西晋平吴后,虽然对于吴、蜀旧国人士仍有防范,但政府仍然施行笼络为主的政策,如《晋书》卷五二《华谭传》:“谭至洛阳,武帝亲策之曰……又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对曰:‘……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2]1449-1450政府在取士上虽然表面对江东士人予以优待,然而“中华士人”(即北人)则对南边的“亡国之余”有所偏见,并在日常交往中加以轻视与羞辱,如《晋书》卷五四《陆机传》:“超领万人为小都督,未战,纵兵大掠。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2]1480陆机被孟超呼为“貉奴”。陶侃虽然获得了乡望杨晫与同为“亡国之余”的顾荣等人的称赞,但仍被北人直斥为“小人”,遭到弃嫌。对此,赵翼即有评论:“六朝最重世族,已见丛考前编。其时有所谓旧门、次门、后门、勋门、役门之类,以士庶之别,为贵贱之分,积习相沿,遂成定制。”[9]再结合前述陶侃早期仕宦无门、以“寒宦”身份担任孙秀舍人等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出陶侃身为“寒人”,不登二品的身份。但其乡品并未因此而固定,随着陶侃逐渐得到乡望杨晫及顾荣、黄庆等人的相继点评与赏识,名声大振,乡品便随之获得晋级。《九家旧晋书辑本•王隐晋书》卷七:
后为十郡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10]
而随着陶侃建立勋业,政治地位逐步提升,其乡品也就必然在二品位置固定下来。《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
太兴初,进号平南将军,寻加都督交州军事。及王敦举兵反,诏侃以本官领江州刺史,寻转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复本职,加散骑常侍。时交州刺史王谅为贼梁硕所陷,侃遣将高宝进击平之。以侃领交州刺史。录前后功,封次子夏为都亭侯,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王敦平,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余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2]1773
平定王敦之乱后,陶侃的军功及仕宦之途达到了高峰,成为东晋政权炙手可热的当权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其成功,说明此时的陶侃已然成为荆楚地区乡望的代表。伴随着陶侃本人上升进程的陶氏家族的发展状况,可以通过陶侃诸子的官职来展现。
三
《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并不显。”[2]1779其诸子的生平与任官情况均载于《陶侃传》中,此处不再标注,相关信息魏斌已有整理[1],见表1:

表1 陶侃诸子生平仕宦
表1中陶洪、陶瞻二人任官可藉补充,《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
会刘弘为荆州刺史……陈敏之乱,弘以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侃出兵御之。随郡内史扈瑰间侃于弘曰:“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侃潜闻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2]1769
王敦深忌侃功。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廙为荆州。侃之佐吏将士诣敦请留侃。敦怒,不许。侃将郑攀、苏温、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于是设盛馔以饯之。侃便夜发。敦引其子赡为参军。侃既达豫章,见周访,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进至始兴。[2]1772-1773
这里陶洪与陶瞻二人分别被刘弘与王敦引为参军,虽然其实质是作为政治交换的质子,但也说明当时其各自都在陶侃身边,并未出官,可以认为两人的起家官即参军。参军原是由中央派遣至地方军府以参与军事的官员,随着东晋以后地方军府的发展,参军逐渐成为府主僚属,可以自行板授。关于参军的地位,宫崎市定据《通典•魏晋官品表》整理魏晋间公府、将军府僚属官品如表2[7]137。

表2 魏晋公府僚属官品表
参军的等第大致处于七品与八品之间,然而东晋、南朝时期,地方王国、军府的僚属类官,其实际地位的高下并不是依照纸上记载的规定,而是随具体的政治情势而变动,主要根据王国诸侯与军府府主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在地方州郡的地位而确定。东晋为了抵抗来自北方的重压而在地方设立军镇,保持严密的战时体制,其中最为重要的军镇即设于荆州,以应对来自北方长安的压力。引陶洪为参军的刘弘当时即为荆州刺史,先前便引用陶侃为长史,补选其为府行司马,后更引为江夏太守,委任讨伐陈敏叛乱,可以说是总襄荆州军政。 而引陶瞻为参军的王敦,《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详载其仕履曰:“侃之灭弢也,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敦始自选置,兼统州郡焉。”[2]2554据前引史料,陶侃灭杜弢后,王敦忌其功,予以压制,将其贬至广州,远离权力核心,引陶瞻为参军即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王敦有四种官职,即“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2]2554都可单独开府,作为时局中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甚至可以在不知会中央的情况下直接将陶侃左迁广州,其府中参军的实际地位也不应低于七品。同时,在同一府内参军随其负责的不同诸曹地位也不同,这里因材料有限,无法对两人所任具体的参军职务展开探讨。考虑到这一时期行参军屡屡作为起家官,且当时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的名族也有成员获此官职(见表3[7]140),可以认为陶侃二子起家参军,实际上是获得了乡品二品。

表3 行参军起家表[7]140
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时期陶氏家族的发展呢?这里可以参考胡宝国关于世族与势族的相关论述:“所谓势族,乃是指现实有势力的家族,即那些魏晋政权中的公侯与当涂者。这些人中固然也有两汉以来的著姓、大族,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河内司马氏、河东裴氏等等,但也有像石苞、邓艾、石鉴这样一些出自寒微者。他们显然不能以世族目之。固然势族只要稳定地、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终有一天会演变为世族,但那毕竟是以后的事,在魏晋时期,势族不等于世族。势族的地位也井不十分稳固。在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中,一些势族衰落了,一些人又上升为势族,虽然势族垄断了上品,但他们当中具体的家族由于现实政治地位不稳固,品也不稳定。”[11]胡论内容可概括为两点:第一,势族是因掌握政治权势而生,会因失势而门第失坠;第二,势族通过保持权势可以逐步转化为经久不衰的世族。据此,因陶侃本人的得势,其诸子中出现了乡品二品的获得者,仕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此时的陶氏家族便成为了显赫的政治家族,即势族。
然而得势后的陶氏家族,仍未摆脱其武力强宗的色彩,逐步实现世族化。《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
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末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皆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2]1773-1774
陶侃本人强烈的军功色彩,在吏职上的精明干练以及与士族社会清谈氛围的格格不入,使其始终不被高等士族真正接纳认可。陶侃诸子亦多为武人,如陶夏、陶斌拥兵相图,斌为夏所杀,陶旗性甚凶暴,陶称性虓勇不伦、与诸弟不协,陶臻有勇略智谋,陶舆果烈善战,以功累迁武威将军,陶氏家族这些人在史传中颇为知名,连逐渐有士人化倾向的陶范,也不脱蛮武风气,《晋书》卷九二《文苑传》:
袁宏,字彦伯,……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宏赋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尝于曲室抽刃问宏曰:“家公勋迹如此,君赋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无?”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2]2391-2392
胡奴为陶范小字,尽管陶范竭力向士族社会靠拢,但仍不被接纳,《世说新语•方正》:“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12]360-361王修龄对陶范的拒绝,恰如其父陶侃微时与顾荣同载而被温雅斥为“小人”,其中隐含着的仍是严格的士庶区分,正如余嘉锡所言:“侃《别传》及今《晋书》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议,致修龄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其子夏、斌复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修龄羞与范为伍。于此固见晋人流品之严,而寒士欲立门户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12]360-361
综上可知,东晋浔阳陶氏,因陶侃一人之力曾实现了由地方豪族向当朝势族的突破,但在陶侃死后,余力不继,未能完成向文化世族的转变而进一步提升在东晋贵族社会中的地位。此后史料记载的主要人物陶淡、陶潜皆入“隐逸”,标志着陶氏家族重新沦为地方寒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