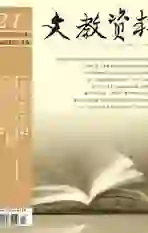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儿童视角叙事小说创作原因探析
2021-11-15于静静张晓瑜
于静静 张晓瑜
摘 要:儿童视角叙事是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叙事策略,《饲育》《感化院的少年》等是早期作品中使用儿童视角叙事的代表作。以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叙事为中心,从童年经验、作家个人气质及山村“童子”传说三个方面可以探究大江健三郎儿童视角小说创作的原因。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儿童视角叙事 创作原因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他的文学走出了国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受到了世界读者的青睐,成为享誉全球的著名作家。他是一位才学兼备的作家,不仅在文学创作领域大放异彩,在文学理论方面也可谓独树一帜,创作了《小说的方法》等具有大江创作特色的方法论作品。由此可见,大江是一位讲求创作手法、注重创作艺术的小说家。
儿童视角叙事是大江早期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叙事手法,《饲育》《感化院的少年》等作为其早期使用儿童视角叙事手法的代表作,使大江在日本文坛大放异彩、声名鹊起。本文着眼于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叙事作品,探究大江健三郎创作儿童视角小说的原因。
所谓儿童视角,是指“小说借助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的儿童叙事角度”[1]。大江是一个惯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家,早期的几部儿童叙事视角小说毫无例外地使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进行叙事“,我”是《饲育》里给黑人士兵送饭、抬粪便的少年,也是《感化院的少年》里由于手持利刃刺杀同学而被送入感化院的少年。虽然主人公的身份不尽相同,但是皆为处于边缘位置的少年角色,大江通过他们的视角演绎了一部部深入人心的故事。儿童视角叙事给大江的文学作品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探究其因对于理解大江早期文学乃至文学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童年经验
童庆炳指出:“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现代心理学一般把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称为‘儿童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2]并进一步提出“完整的童年经验并不仅仅是指原本的童年生活的记录,还包括活动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2]。每个人都有童年经历,在跨越童年之后的青年、中年及老年的每个人生阶段里,人们都会对自己的童年有着不同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是作家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以下分别从两方面探究童年经验对大江健三郎早期儿童视角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一)大江儿时被排挤和欺凌的经历
大江出生于日本四国岛北部的爱媛县大濑村,当时的大濑村是一个被森林包围的封闭村落,仅凭一条狭窄的公路与地方城市相连接,经济不发达。虽地处农村,但其实大江家并不是农民,其祖上为武士阶层,大江父亲继承产业,以收购山货为生,大江家在当地算是富裕家庭,但是大江也因此受到其他孩子们的排挤。在内子高中时因不堪不良少年的欺凌,他毅然转学至松子高中。十八九岁的时候大江离开了家乡,赴东京求学,但是他察觉到了自己与城市之间的隔阂,感觉自己被纯正的东京人拒绝。总之,他孩童时期的经历坎坷,但是这种饱尝艰辛的体验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在许多作家那里,童年经验以作品的生活原型和题材直接进入创作之中。”[2]大江的初期小说《饲育》里的主人公 “我”就生活在一個“古老却未壮大”的开拓村里,本就封闭的村庄恰逢战争期间,便与镇上彻底隔绝了。黑人士兵的到来 打乱了一向平静的村庄,为了汇报此事,父亲被指派前往镇上,我也一同随去“,一到‘镇上,我便把肩膀靠在父亲高高 的腰际旁走着,不理会街上孩子们的挑衅。如果父亲不在, 这些孩子会向我投以嘲讽与石块吧”[3]。小说中的“我”出生 于偏远的乡村,随父亲到镇上时遭受了镇上孩子们的挑衅, 仰仗父亲在旁“,我”才幸免于他们的嘲讽和欺凌。这一点和 大江小时候的经历不谋而合。可以说,小说中的“我”的原型 是大江本人,他将自己童年时被排挤被欺凌的经历复制到了 主人公身上,透过“我”这一儿童视角观察世界。
(二)大江儿时失去父亲的经历
大江九岁时丧父,年幼时父亲的突然离开使大江失去了安全感,虽然母亲也给予了他很多的鼓励和关怀,但父亲的缺失终归给幼小的大江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他的作品中不乏“父亲”形象的登场,可见父亲在他心中的分量之重。以下结合大江早期儿童视角小说中对父亲形象的塑造窥探童年经验对其作品创作的影响。
在大江早期儿童视角小说《饲育》中,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同时在家庭里拥有绝对权威。小说中有一段描写父亲的猎枪的文字“:父亲的那杆猎枪,枪筒自不必言,就连那油亮的枪托也变得像铁似的,发出暗淡之光,开枪时震得手发麻。它为我们贫寒的住所带来了方向感。”[3]通过对父亲的猎枪的描写折射出拥有权威性的父亲力量。可以说,这些都符合我们对父亲形象的一贯印象,但是在小说结尾,我被黑人士兵劫持“,父亲提着柴刀走出人群。我看见父亲的眼睛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仿佛狗眼般热辣辣的”[3]。父亲以牺 牲“我”的性命为代价,向敌人挥刀砍下,颠覆了父亲是“我” 的保护人的形象。在小说《感化院的少年》中“,我”由于身负劣迹被感化院收留,正值战争末期,感化院决定疏散“,我”期待父亲接走自己的希望落空,等来的却是父亲顺带把弟弟一同放在感化院的结果。从大江的以上两部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其对父亲形象的矛盾处理,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处理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童庆炳认为“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般来说,作家面对生活时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他的先在意向结构。对作家而言,所谓先在意向,就是他创作前的意向性准备,也可理解为他写作的心理定势”[2]。其中,父亲意向是先在意向结构中对作家创作影响很大的因素之一“,在儿童的心目中,父亲是威严的象征,他和理性、责任、能力、纪律、遵从、功利、刻苦、奋斗、冒险、秩序、权威等字眼连在一起”[2]“。父亲的原则是要把孩子引上社会,适应社会的规范,成为社会的人。这样泯灭童心和诗心是符合父亲的原则的”[2]。综上所述,父亲对孩子童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作为家庭中的权威,父亲是孩子的定海神针;另一方面,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领路人,父亲以原则约束孩子,促进孩子成长。
大江幼年失去父亲,在他人生最需要父爱的时候未能享受父爱,由此造成了人生中的重要缺失,但父亲意向作为先在意向对其创作的影响是依然存在的,或许可以说以一种更复杂的形式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童年时期父亲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家对父亲的印象产生矛盾感,即两面态度。具体而言,一方面,大江在《饲育》中塑造了一个富有责任心、拥有权威性的父亲形象,是对父亲威严性的肯定,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恋父情结”。父亲的过早离开,并未动摇其先前在家庭中“权威性”的地位,反而更激起作家对“父亲”这一权威形象的向往,进而反映在作品之中。另一方面,《饲育》结尾处舍弃儿子性命暴打黑人士兵、《感化院的少年》中无情地将儿子留在感化院的父亲形象则体现了其对父亲“原则性”的质疑。通过小说主人公对“父亲”代表的大人们的“异常”行为的谴责,表达出了作者对战争这一外在因素的控诉。作家着力塑造父亲形象,而非设置在母亲形象上,是基于父亲引导孩子成长之路的重要作用而考量的,父亲“脱轨”的做法正是作者想要营造一种反差,这种反差起到了深化小说主题的作用。
总而言之,童年经验是大江文学创作的本源,在他早期儿童视角叙事的代表作品中总能捕捉到童年的身影,加之这些作品往往采用少年的第一人称叙事,让我们很容易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大江自身的童年经验联系起来,进而理解作品视角选取背后所隐藏的秘密。
二、作家个性气质
关于文艺家的个性气质,张佐邦在《文艺心理学》中提出“:所谓个性气质,主要是指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特点在行为方式上的表现,它是个人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这些动力特征主要表现在心理活动过程的强度、速度、稳定性和指向性上。人的情绪体验的强弱、意志力的大小、知觉和思维的快慢、注意集中的长短、注意转移的难易及心理活动是倾向于外部事物还是倾向于自身内部等,都是个性气质的表现。”[4]根据张佐邦对“个性气质”的定义,作家的作品是作家个人气质输出的表现,个性气质因人而异,将决定作家作品风格的呈现。
个性气质作为一种个性心理结构,是促使作家创作活动发生的元结构,蕴含了作家创作的全部奥秘。张佐邦进一步指出“:正是这個元结构,才是一个文艺家之所以成为文艺家的决定性因素,是文艺家生成的根基和策源地。”[4]由此可见,作家的个性气质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纵然大江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主题不尽相同,但是决定其文学基调的作家个人气质从未改变,并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初期作品中的儿童视角小说的诞生与作家个性气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艺家个性气质的生成受遗传、环境、实践活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大江来说,童年的坎坷经历造就了其纯洁、敏感的个性气质,日本文艺评论家川本三郎曾直言“大江在我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一个大幼儿”,并将他身上的这种气质概括为“它是和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及支配社会整体的规范意识无缘的,一种类似婴儿特有的纯洁的感觉”[5]。
关于大江的个人气质与其儿童视角叙事小说创作的联系,我们试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解读。第一,大江是一个富有 童心的作家,他将这种童心附身于早期小说中的少年“我”这 一角色之中。在《饲育》中,很多个性鲜明的句子出自“我”之口,例如“弟弟像幸福的野兽“”他们那臃肿的飞行服上沾满 了枞树花,这使他们看上去好像一只只冬眠前的肥松鼠吧” “桥上走来一位脖颈如小鸟般清爽的少年”等,充满新奇感、富于童趣的比喻句俯拾皆是。如前文所述,大江的童年是在 被森林包围的山村度过的,童话般的森林世界必定是孩子们 捡拾快乐的源泉。从这些比喻句的喻体大都是动物和植物 这点,不难看出童年时期森林峡谷山村的生活环境给了幼年 大江宝贵的生活体验,孕育出了“纯洁”的个性气质特征。大 江的儿童视角小说自带“陌生化”滤镜,给读者带来一次次妙 趣横生的阅读体验。可以说,唯有拥有一颗未泯的童心,才 能创作如此富有童话诗意的语句。
第二,大江作为作家具有与儿童相似的心理构造,他的“童心”与儿童的赤子之心相通,真实地揭露社会,观照复杂的人生。《饲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山村里,仿佛与世隔绝,外部的战事给山村带来的唯一影响就是黑人士兵的到来,人们由恐怖到放下戒心,与黑人士兵化干戈为玉帛,孩子们和黑人士兵一同于河中沐浴、嬉笑,封闭的山村呈现神话色彩。在《感化院的少年》中,村庄的人们为了逃避疫情深夜不告而别,孩子们“小鬼当家”,在古老的村庄中上演了一部“雪祭”,乌托邦式的氛围洋溢在大人“失踪”的日子里。身为主角的孩子们脱离大人视野的“狂欢”是两部小说在情节设置上的相似之处,但这绝非偶然。具有神话般色彩的故事情节设置其实包含了大江影射残酷现实、向往和平的“赤子之心”,是大江身为一个作家永葆童心、不忘初衷的体现。虽身处繁杂的社会之中,但他依然顽强地保留纯洁独特的艺术视野,以此为阵地,为世界发声,为人类发声。
三、山村“童子”传说的影响
山村“童子”传说源于大江故乡的森林文化。大江出生于靠近四国山脉中央部、被森林包围的小村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以说森林孕育了生命,也孕育了他的文学“。森林” 成为大江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大江文学作品又传递了日本独特的森林文化。
“森林,是包孕山村人的灵魂之地。在日本文化中,森林有着镇守魂灵的作用。”[6]大江童年时就从祖母口中听到了关于森林与灵魂的传说:一个人死后,自己的灵魂会螺旋式盘升至森林里,寄居于某棵树上。当山村中有孩子出生时,灵魂又会回归,进入其体内。据说孩子最好不要进入森林,因为孩子在那里不知如何跟“自己”打招呼。山村“童子” 传说和这个森林与灵魂传说可以说一脉相承。据说村庄曾发生过农民暴动,每当农民暴动遇到困难、举步维艰之时,一个孩子便不知从何而降,告知农民他的锦囊妙计,然后消失于森林高处。由此可见“,童子”被赋予某种神性“,他”如天使般存在,救人们于水火之中,解人们燃眉之急。据说幼时的大江对“童子”传说深信不疑。纵观大江初登文坛时的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主人公大都为纯真无垢的儿童,或许与幼年时祖母口述的“童子”故事不无关系。
《饲育》中,在以“我”为首的孩子们的眼眸中没有大人间的敌我概念,将朝夕相处的黑人士兵视作伙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化解了大人们之间的敌意,给战时的动荡局势带来了一抹柔情,人性找到了落脚点。
在《感化院的少年》中“,我”作为感化院少年中的队长,在大人们逃避的日子里带领少年们进行尸体埋葬、雪祭等活动。当大人们回归村庄,企图对“我们”封口之时“,我”又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冲破他们的底线,踏上为自由、为未来披荆斩棘的前路“。我”如黑夜的一道亮光,用尽全力照耀星空。
此外,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弟弟”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弟弟是被父亲以无法找到疏散地为由送入感化院的,与其他成员不同的身份让他在感化院的生活中与众不同,当遭遇外界嘲讽的眼神时,弟弟是唯一一个敢于正面与对方进行眼神交流的孩子。由此可见,弟弟的到来扭转了“我们”面对嘲讽无力抵抗的局面,为昏暗卑微的感化院生活带来了一丝光明。另外,弟弟的存在成为鞭策“我”成长的一股动力。投靠哥哥的弟弟在感化院的生活中慢慢适应,期间还抱养了一只小狗,并把它当做自己亲爱的伙伴朝夕相处。不幸的是,在小狗成为咬伤女孩的重点嫌疑对象后,作为哥 哥的“我”保护不利,小狗惨遭打死,弟弟伤心欲绝,一气之下 离开了“我”,下落不明。弟弟的离场是我最终彻底反抗村民 的催化剂,是刺痛我心扉的一把利剑,某种程度上成就了 “我”的勇敢。
综上所述,无论是《饲育》中的成长中的少年,还是《感化院的少年》中的勇敢少年们,他们身上有着共同之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皆为山村传说中的“童子”的化身。《饲育》中的少年是降临在初陷战争旋涡中的村庄里缓解“敌我对立”紧张、给人们带来和平之光的“童子”,《感化院的少年》中的少年是降临在被村民抛弃的村庄里抗争歧视、披荆斩棘争取光明的“童子”,他们纯洁无瑕, 犹如黑暗中的灯塔,照亮天际,指引前路;亦如炎炎夏日的暴雨,洗涤污秽,涤荡人心。
四、结语
儿童视角叙事作为大江早期文学作品中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出现在其初登文坛时的多部作品之中,成为其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叙事策略,这绝非偶然。作家创作作品视角的选取与人生经历、个人气质等有着很大的关联性。本文以大江健三郎初期代表作《饲育》及《感化院的少年》为例,从童年经验、作家个人气质及山村“童子”传说三个方面探讨了大江健三郎儿童视角小说创作的原因。大江坎坷的童年、獨特的个人气质及古老村庄的传说故事成为其文学视角选取的动因,是探究作家创作背后秘密的钥匙,是使其小说散发出独特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吴晓东,倪文尖,罗岗. 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1).
[2]童庆炳. 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 文学评论,1993(4).
[3]大江健三郎. 个人的体验[M]. 王中忱,邱雅芬,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4]张佐邦. 文艺心理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川本三郎. 大江健三郎——根源的な無垢[J]. 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79(2).
[6]林啸轩. 大江健三郎文学论:立足边缘,走向共生[D]. 济南:山东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