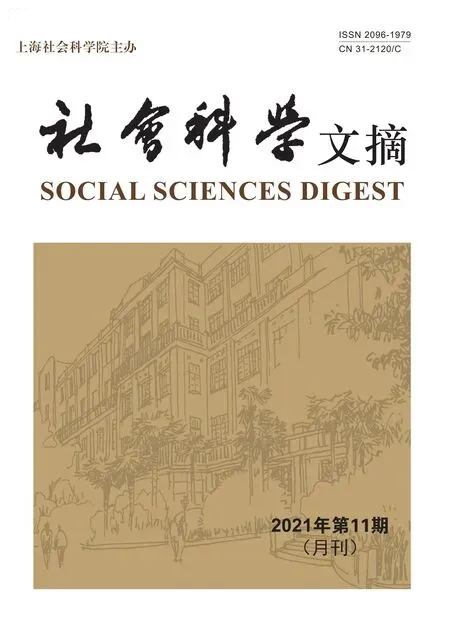观念史视域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2021-11-15孙晓春
文/孙晓春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摘自《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3期)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整体把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我们在怎样的程度上理解了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能够达到怎样的境界。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和主张构成的,不过,我们不能仅仅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看作是历史上思想家的言论记录,思想史研究不仅仅是要弄清以往时代的思想家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说了些什么话,提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们民族观念演变的历史,它反映的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方式和理解水平,记录着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价值观念。
从很早的时候起,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优良的,如何使我们的群体生活来得正当,便成为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有能力反省自己的社会生活的那一刻。
我之所以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源头应该追溯至我们的祖先有能力反省社会生活的那一刻,是因为,从那一刻起,人们便形成了一种道德自觉,这个自觉一直持续到今天。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之所以能按照其自身的逻辑演进,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从野蛮状态摆脱出来并且不断地走向文明,在根本上说是由于思想家的道德自觉。
不过,由于社会历史条件、认识能力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尽管历史时期的人们与我们一样有着对优良的政治生活的追求,但是,究竟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是不好的政治,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由于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一样,也就有了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念,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体现的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
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在观念的支配下运行的。对于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来说,人们在怎样的程度上理解了社会政治生活,对应然的政治生活做出了什么样的判断,也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质量。或许有人对这一说法持有异议。一直以来,我们是习惯于用经济的观点解释历史的,按照常识性教科书的说法,思想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又在根本上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确实地说,这种解释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它可以使我们看到其他分析模式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在这一视角下,我们也可能忽略了某些东西。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群体生活也是在观念的支配下运行的,用近代思想家的话说,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所在,就在于人们不仅能够为自己的社会生活规定一个目的,而且也能为自己规定用来约束社会生活的法则。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拥有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人们在观念上认可的生活。
人类思想进步的历史亦即观念演变的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按照近代以来流行的文明史观,我们通常把思想史理解为文明史的一部分,并且认为思想史是从属于社会生活史的,甚至在根本上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决定的。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思想史与物质生活的历史虽然有联系,但是,思想史的进程并不是由物质生活的历史决定的,这是因为,思想的进步是在每一历史时代的人们的思维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在生产活动中实现的。在有些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家想到的问题,可能会超出他们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思想家所关注的思想主题很可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历代思想家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讨论,大都是围绕着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统治者应该如何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统治者应该如何治理国家,亦即国家应该如何对待社会大众这些主题展开的。传统儒家素有经学的思想方式,特别是两汉以后,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往往从诠释儒家经典开始。但是,如果深入解读秦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就不难发现,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即使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都在诠释儒家经典,但是解读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儒学才有了汉代经学、宋明理学等不同的学术形态。可以说,每一历史时期的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历史时期的人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思考,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与观念的进步。
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的序言中曾经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思想史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从观念演进与传承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确实概括了思想史的本质。对于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来说,之所以要不断地与历史上的思想家对话: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说了一些富有哲理的话,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约束和规范了传统中国的政治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在更抽象的层次看,古代思想家所曾讨论过的许多思想主题,是人类永远面对的主题。对于这些主题,历史上的思想家曾经做过回答,但时至今日,仍然需要我们做出回答。在这一点上,刘泽华先生说得很对,思想史就是历史的存在,历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表达的是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因为他们在观念上认定了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因此,他们也就拥有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至于当代中国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却需要根据我们的理性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这是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我们民族历史上那些最聪明的人,在任何时候,与聪明人对话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他们曾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但每个思想家也不过是思想史上的过客,思想史之所以成为思想史,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谁能够垄断知识和智慧,没有谁能够道出万古不变的真理。对于古往今来的人们面对的那些共同的思想主题,没有谁有能力代替后来的人们做出回答。所以,无论历史上的思想家曾经说过多么富有哲理的话,作为研究主体,我们都是在与他们平等对话,切不可把思想史研究看作是向前人学习的过程。
在观念史的视域下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把思想史研究看作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那么,价值判断就是思想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是每一个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人无可逃脱的责任。在这一问题上,我不赞同近年来政治学研究所呈现出的技术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有些学者热衷于讨论宋代的乡规民约,管子的使四民分居的思想,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能纳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也不是说这些研究没有任何价值,但就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来说,这些肯定不是需要我们优先讨论的问题。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绝不能走技术性的道路。如果离开了价值判断的前提,技术性研究的意义只能无限趋近于零。
做好今人与古人的对话,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说到这一点,无法回避的是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作为政治学的重要分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肯定是与现实政治分不开的,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关系就是“为政治服务”。不过,即使是说政治思想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这个“服务”也不可以简单地理解。我们不是要到历史上找到以往思想家说过的经典语句,用来说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是否正确;也不是捡回以往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某些思想主张,用来解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更不是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中发现某些原则来指导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
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发现意义的工作,我们要通过与历代思想家的对话,唤醒那些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仍有意义的思想主题,通过对这些思想主题的认识和理解,构建属于我们的时代的价值体系,从而在根本上提高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