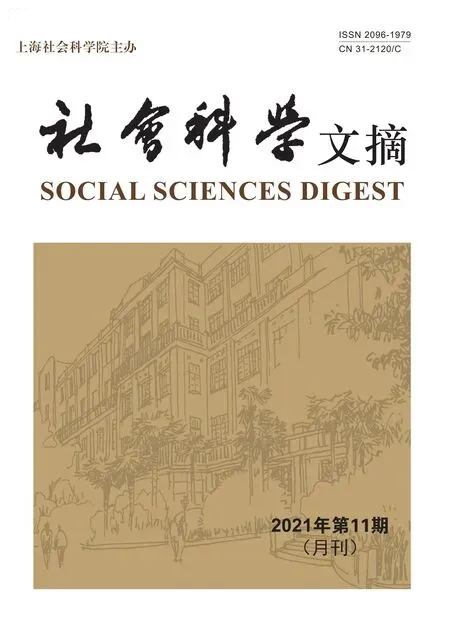十年“新子学”:从学术构想到文化引领
2021-11-15曾建华苏诗悦
文/曾建华 苏诗悦
(作者单位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摘自《管子学刊》2021年第4期;原题为《古今学问事,十年“新子学”:从学术构想到文化引领》)
通常学界认为子学即诸子之学。狭义的子学乃指著书立说自成一家的原创性学术;广义的子学则将后人对历代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也纳入子学系统中。就文献层面看,子学是相对于四部分类中的经学、史学与集部之学而言;就思想层面看,子学乃是士人对其所处时代困境的反思与争鸣,是超越于元经学思想的知识体系和学术理念,也是士人观念得以确定和发展的内在力量。而当前所谓“新子学”,主要是指基于传统“子学”与现代“西学”所提出的新的学术理念、方法路径和文化观念,乃是作为一种多元、开放的“新国学”构想,试图打破经学(儒学)主导下所造成的中西对立的“旧国学”观念而出场。然而,由于“新子学”尚未建构出“新”(有别于传统学术)的思想体系和方法理论,因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不断徘徊于“新国学”与“新哲学”的两端。故此,笔者于“新子学”十年创构之际,再度梳理“新子学”之发生理路,并尝试将“新子学”构思为一个反思传统学术、实现文化引领的新型知识谱系。
从争论走向共识
2012年,方勇先生终于向学界抛出酝酿已久的“新子学构想”。其认为,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并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具有与时俱进的革新品质,比之经学更具有开放、多元、平等的现代性意义。因此,方勇先生希望借助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诠释,不断从元典中摄取创生性、开放性、多元性和对话性的学术思想,以逐步破除经学思想所主导的封闭、专制的旧国学理念,从而为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最终为中华之崛起提供思想资源。正是从这一刻起,方勇先生骤然以“庄学专家”的身份,开启了心之所向的学术“通人”的理想之途,由此引发了文史哲诸多领域的广泛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双棣便强调,新子学要着眼于创新,广泛借鉴杂家宽容平等、兼收并蓄的思想理念,发展诸子多元的思想观念;厦门大学新传学院谢清果则认为,新子学之“新”在于子学对“礼崩乐坏”时代问题的回应意识,其既回应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提升文化自信的需要,又回应了中国向世界贡献建构和谐世界思想资源的使命;东南大学哲学系许建良则进一步将“新子学构想”解读为一种思想认识的革命,而将儒家回归为诸子百家之一,以期突破偏重儒家的现实局限,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学术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宋洪兵则着眼于未来中国信仰体系的多元、包容、平等、对话的新趋势,力陈“新子学”构想在未来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各家之言各有偏重,然而均基本认同“诸子学”作为国学之主体,具有多元、开放与包容的学术精神,因此,其本质便是与时俱进、日用而日新的“新子学”,必然在未来中国学术文化的构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随着探讨的深入,“新子学”到底新不新,其理路是否正确、是否重要已不言而喻。而学者们关心的话题也从对“新子学”现实作用的宏大构想,转向其本质属性的诠释与切实可行的理论创构。比如,华中师范大学高华平便将诠释的重点从“新子学”之“新”,转向了“新子学”之“子”,认为“新子学”之“子”即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而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就是所谓“新子学”。其时笔者也有类似的思考,认为“新子学”务必将子学研究与士人传统进行合理的关联,并通过对子学发生、发展及其文化建构与士人传统之变迁的复杂关系的考察,进一步揭示子学向“新子学”化生的内在动力,从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法性和超越于个案研究的有效路径。
不过,“新子学”最初的“构想”虽称宏大,但多着重于概念框架的设置而缺乏思想史的梳理,因而很难深入到子学发生、演化及其文化创生的层面,更难从本质上区分新、旧子学之渊薮,进而明确“新子学”的理论构建与方法路径。因此,“新子学”只有对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给出建设性的具体方案,才能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开创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这一系列的问题,逐渐引发了笔者对传统中国学术之弊的进一步反思。
中国传统学术之弊
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即渴望一种基于权力关系而形成的观念秩序,“经学化”的儒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应运而生的。于是,本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而存在的“三纲五常”,便逐渐被汉儒内化为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精神秩序与观念结构,进而确立为儒术独尊的思想格局,由此主宰了古代中国人几乎全部的精神生活、礼仪规范与学术传统。哪怕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长达百年的现代性启蒙,其依然顽固地存在于国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在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发挥着“经学”的主导作用,这便是“新子学”所指斥的“经学思维”。
经学主导的时代容不得新锐的思想,从而阻断了中国社会的科技创新与良性循环。而“经学思维”的核心特征乃是强调永恒的中心与不变的秩序,由此营造出一个极具优越性的“自我”,并试图以这个“自我”的意志去主导社会、政治和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而当下中国已然处于一个科学、民主、平等、公正、开放、多元、包容、进步的全球化格局之中,并对未来世界之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再以经学化的儒家思想去接洽当下的世界,抑或试图以此去建构当下的学术生态,进而期求借助这一学术生态去解决未来世界的相关问题,其结果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吊诡的是,当今学界(本文所涉及的“学界”与学科仅指人文学科领域)虽已广泛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和学科专业的分工,但由于经学思维的根深蒂固,而趋于不同程度的偏执、僵化、封闭甚至内卷,其直接表现便是学术的圈层分化与学者的代际割裂。
所谓圈层分化,主要是指不同学科以及同一学科的不同方向,由于问题导向与视野差异而产生的学术分化与话语阻隔,从而使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碎片化、项目化与烦琐化倾向。尤其是项目化,本是为了促进学术繁荣,但却迫使学术研究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行政性、应时性与依附性的特征。所幸,面对传统人文学术愈演愈烈的“精耕细作”式研究,学界已有较为客观的认知与反思,一些前沿学者甚至已经尝试提出某些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早在2005年,葛兆光、杨念群等人文学者,便开始积极寻求突破传统人文研究范式的良性发展之路。2020年11月22日,张江、周宪、朱立元、丁帆、邓安庆、曾军、成祖明、李红岩等人文社科的知名学者,更纷纷呼吁以当代阐释学理论破除学科藩篱,进而建构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和跨学科的学术范式。这次论坛的召开,对于反思当下学界之弊端,重构人文学术之使命无疑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指导意义,对我们“新子学”之未来发展自然也就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
至于学者的代际割裂则主要是指,学者从事学术工作的方法、思维与问题随时代变革而出现代际性错位,由此造成了主观、僵化、封闭与悖谬的倾向。经学思维主导下学者所面临的代际割裂,难以借助传统学术的方法、理论去维系,因此现代学术的代际延展,只能借助学术圈层的大循环才能规避可能出现的学术内卷化倾向,否则很难从根源上切除经学思维的毒瘤。因为,经学思维强调基于经学文本所构建的师承、门户与问题意识,所以它既不强调学者的独立性与创新意识,更不在意千差万别、与时俱进的现实问题,而是试图以一套自以为完美的理论体系——经学模型去建构和规范现实秩序。这必然导致学者在自以为清醒、独立的情况下出现思想的僵化与空悬,日益步入逻辑的怪圈,造成荒谬的代际割裂。以当下最为主流的“(新)古典学派”(以现代“史料”派为主流)为例,此派学者多注重对知识材料的整理和完善,主张以经典文本作为知识材料,追求知识材料的“原始”性,同时有意识地排斥宏观、化约的理论建构,且往往以占尽资源的“知识贵族”的高傲姿态,睥睨通俗的知识传播或“空疏”的理论建构。于是,传统文化便成了圈子内的文化,而不同圈层又容易形成某种荒谬而隐形的鄙视链,使学科交叉的诉求成为叶公好龙式的、不切实际的口号。
有鉴于斯的“新子学”,乃力求破除中心、僵化与封闭,强调多元对话与观念的嬗变,要求将儒家经学文本还原为子学的有机构成,建构一个兼容并包的子学文本体系,进而从历代诸子的观念中抽离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知识、范畴、方法和理论,以此作为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和知识谱系的基本信息库。进一步以此为内核形成一个多元对等的思想体系,最终在现代价值与文化身份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按照“新子学”的此种构想,我们确有可能从思想根源上破除经学思维,从而改变古典学术因圈层分化与代际割裂而日益内卷化的倾向。然而,在“新子学”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考虑“新子学”自身的“国学”属性以及对新的“诸子”的培养。这就要求“新子学”不能只是一味强调其“新”,而应切实地创造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话语,应对新的问题,进而以全新的学术范式推动整个文化事业的返本开新,以独立的姿态,去担负通过学术文化之重构,以实现参与时代进程、链接世界文明的使命。
文化引领的可能进路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类知识信息的沟通与传递能力正在经历指数级的增长,而人类大脑的功能则越来被超级计算机所取代。面对席卷全球的数字革命浪潮,人文学术的发展存在着困惑。也即,面对“超级智能”这一全新“宗教”所建构起来的虚拟“幻象”,我们的人文学术究竟该何去何从?是积极应对去寻求“预流”之途,还是坐视“人文”的枯竭而接受文化消解的命运呢?如果存在“预流”的可能,那么我们古老的“诸子”是否仍能提供某种新创性的思想资源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又将如何在古老的“诸子”中获取应对困境的知识与智慧呢?对此,“新子学”势必给出具有哲学方法论性质的预判和应对方案,以哲学的高度去思考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现实问题与相应的学术构建,这就必须提及当下方兴未艾的数字人文思潮。
所谓“数字人文”,乃是以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文献为基础的横跨人文社科与自然科技领域的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更多涉及电子信息的调查研究、分析、综合与表达,同时指向人文主义的思维与价值。因此,“新子学”首先要思考的就是,在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存在形态、传播路向、接受方式与创作研究等相关问题及其所引发的知识谱系与思维方式的重要变革,尤其是古典学在数字化时代的知识重构与文化塑造等问题。
对此,笔者不得不重申从“新子学”到“新古典学”的建构路径:观念—方法—话语—知识谱系。借助大数据分析,从传统经典文本中提炼出核心语词范畴,并对其进行观念史的梳理与现代性阐释,从而超脱历史时空所带来的思维局限,最终将古典文本从沉寂、封闭、僵化的经学阐释中唤醒,赋予其鲜活的历时性意义。基于一系列观念链条的通道,我们便可着手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直到形成完整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文化的知识谱系——包括新观念、新方法、新理论和新话语体系的古典知识谱系。“新子学”视域下的古典学研究,并非要从经典中获得指导当下生活的准则,更不是通过古典的研究来寻求预测未来的“智慧”,而是试图通过尽可能精确地了解我们的古典世界,从而跳出当下生活的局限,尤其是观念上的局限,最终促使我们得以确立某种既具有中国文化特质,又面向现代文明的适时、多元、开放的话语体系、精神诉求和思维方式。
当然在此建构过程中,我们须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以解决相应的技术难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技术而进行的传统文化反思与对现实的人文关怀。首先,要合理借鉴数字人文理论,构建专业的学术数据库系统,这或许是实现传统“子学”甚至是整个古典学转型和持续发展的必然进路,同时也是避免重复研究和碎片化研究的最优选择。其次,要基于准确周备的数据网络与观念体系,让学者超出单一文本和学科藩篱所造成的片面、主观、僵化、滞后与封闭的碎片化认知,逐步形成适时互动与集体协作的学术生态,最终构建一个生发、流变、融通的新古典学的“知识谱系”。对此,陈成吒先生基于“新子学”视域所进行的“小说观念”探索无疑具有典范性的实践意义。其指出,过去经学思维主导下所建构的中国学术文化生态是人为修饰的秩序井然的花园幻象,而“新子学”所展开的则是一个全新又原生态的学术文化森林,诸子及其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小说家”也在其中,而且“小说”理念不断走向通俗、潮流的特征正是子学开放性、大众化这一根本特质最集中、最前沿的呈现。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多元、并包的“诸子”话语谱系打破学科专业的瓶颈,去全面观照我们的中华文化,比如在“新子学”的视野下,李贽、唐甄、袁枚等离经叛道者,不再为文学、哲学或历史研究所局限,而是传统思想脉络中一个个独具创新意义的“新子”,是当代思想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源。由此,修修补补的饾饤之学,自然就升级为既深入传统又关怀当下且能面向未来的经世致用之学,此方为当代学术之大视野、大格局、大趋势与大气象。
总之,“新子学”十年的探索,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必须以有机的观念结构为脉络,对诸子文本进行跨学科的系统研究,在整个世界的文明谱系中观照先秦诸子这些最具原创性与思想性的经典文本,从而真正实现文化与文本的返本开新、当代转化与世界链接,进而为培养新时期的“诸子”与“元话语”性质的知识信仰建构一个相对坚实的、具备现实性与操作性的学术范式,最终开创一个真正具有中国话语特色与理论深度的学术新时代。与此同时,“新子学”还需要抚今追昔,实现文理交融,即立足当下生活,合理利用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以跨学科、跨文化的方式,重新审视古代经典及其学术,最终建构一个价值性、功能性、科学性、身份性的“新古典学”。而这样一种基于道义与牺牲精神的“新古典学”,或许可以被人类赋予“超级智能”的未来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