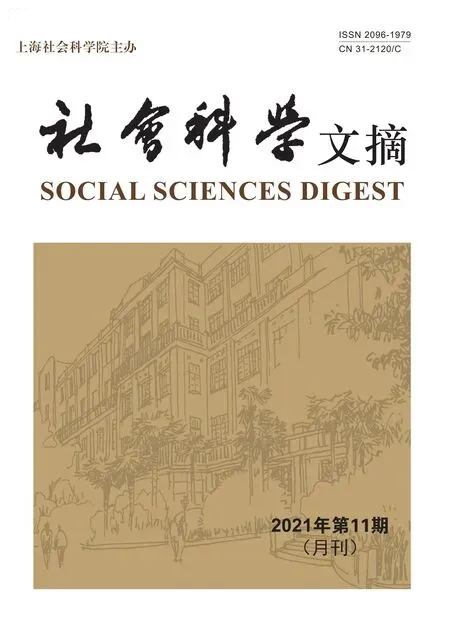冷战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一项理论评析
2021-11-15尹继武
文/尹继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摘自《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经典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聚焦领导人的人格与认知等传统心理学变量,以外交决策作为核心命题,契合美国外交及美苏核威慑等冷战时期的战略环境,探讨领导人政治心理的国际政治影响。随着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以及政治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当前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已出现了系列的理论进展,体现为经典命题的深化、研究议题的扩散、微观战略心理命题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演进和不同地区经验的重视等。
领导人政治心理学:人格、认知与情感
二战结束后,随着欧美国际关系学界逐步开展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早期的经典研究已形成了三个流派。人格分析流派聚焦领导人的人格特质与结构的分析;二战后领导人政治心理学的认知偏差研究,成为国际政治心理学早期研究的主流范式;在领导人情感与情绪的早期研究中,较多学者认为情绪是理性的一种损害因素,无助于领导人外交决策中的正确判断、认知与决策。
(一)领导人的人格分析
乔治(Alexander George)夫妇关于威尔逊总统的人格精神分析似乎奠定了这一传统经典研究方法的标准。冷战期间,在理论探讨上,格林斯坦(Fred I.Greenstein)从行为体必需和行为必需等角度论证领导人及其人格特质是否重要,关于领导人人格分析的相关方法,尤其定量的内容文本分析技术,开始在赫尔曼(Margaret G.Herrman)等学者的推动下得以系统化运用。
第一,研究对象的扩散。经典的领导人人格分析主要聚焦的领导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总统,有单个案例的人格分析,也有系统性的总统性格类型学分析;另一类是其他一些国家有着较为独特个性、对相关国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国家领导人或民族领袖,经典研究对印度甘地、德国希特勒的性格与人格探析较多。冷战结束后,领导人人格的研究对象聚焦美国及相关国家最新的国家领导人,比如克林顿、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等成为重点人物,尤其是特朗普的独特人格特质引发了关于美国总统人格分析的热潮。相关研究聚焦他超级自恋的性格特质,以及不羁善变的核心特质等维度。另外,由于冷战后恐怖主义的兴起,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关于本·拉登等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分析,也成为当下领导人人格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研究方法的多元。早期关于领导人人格特质的分析,主要运用精神分析学说以及相关定性分析框架。随着人格心理学的方法,以及政治心理学关于领导人人格分析方法的创新,一些定量的分析方法得到推广和使用。一方面,以赫尔曼等为代表的早期学者,结合政治情境,提炼出领导人人格特质分析的相关维度,比如权力、控制感、信任感、群体偏见等,进而提炼出人格特质分析的“远距离文本分析”方法。近期,美国心理学家运用精神分析的深层心理和动机剖析,提炼出特朗普的核心和主要性格特点,即超级自恋,但主流的领导人人格特质测试仍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或采用专家测试方法。比如,美国心理学家关于特朗普、拜登等人的人格特质的文本内容测试受到广泛关注;尹继武等人通过美国问题专家的系统化问卷测试,也提炼出特朗普的五个人格特质维度,并指出不羁善变是其最为核心的特质,而拜登的最大性格特点是对于环境压力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第三,研究主题的变化。传统领导人人格分析集中于“是什么”的描述性层面,即所研究的领导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大的性格特质是什么?更进一步,国际政治分析中必须揭示相关领导人性格特质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机制。冷战后的领导人人格研究,在传统的人格稳定性基础上,出现侧重于领导人人格变化性的研究,即在什么情况下,领导人的人格特质会发生变化,尤其是产生负面的决策、政治后果?另一方面,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在于差异性,因此,在传统的五大人格等经典人格维度的基础上,当前有研究聚焦在战略决策情境中,领导人人格特质的差异性及其国际战略后果,比如,领导人的“自我控制”(selfˉmonitoring)信念的差异,会产生不同领导人对于外部声誉压力的追求与敏感性差异。
(二)领导人的认知分析
以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代表的认知学派重点探究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领导人的认知局限及其偏差,并讨论了其可能的形成机制与来源。后续的讨论多聚焦于杰维斯所总结的认知偏差在美苏冷战起源、战争历史类比等重大决策中的作用。
第一,新的认知偏差及其来源。新时期认知偏差研究的进展体现为,在有限理性的限定下,探究领导人认知偏差的新类型及其外交决策与国际政治后果。这些认知偏差类型,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借鉴行为经济学的重要行为心理学成果、以前景理论为代表的相关认知心理学最新成果,在国际危机、战争决策等国际政治研究中受到重视。在此基础上,人类决策的两种系统——理性系统和直觉系统也得到关注,在多元启发决策理论中有较好的应用。此外,受中国战略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启发,有相关研究探讨中国在处理争端、解决双边关系矛盾中出现的一种新型错误知觉类型——单边默契,这是一种基于各自不同理解和预期的错误知觉,即一种虚幻的默契。
第二,认知偏差的理性功能。杰维斯确立了国际政治认知偏差分析的基本范式之后,关于错误知觉的战略功能便以其负面的效应为主。但是,仍有部分学者关注认知偏差所可能具有的理性功能。比如,在特定条件与问题领域,错误知觉与国际合作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如果行为体彼此忽视对方的非合作信号、意愿,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美丽的”错误知觉而形成合作。如果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关于战争、博弈等“积极的幻觉”,很可能会对领导人的战争中止、合作形成等意愿产生促进作用。如果领导人在特定问题上形成了虚假的单边默契,至少在短期内,将会激发领导人达成短期合作的愿望,从而促进双边关系的进展,将争议问题搁置一边。
(三)领导人的情感分析
在早期关于情感与情绪的讨论中,更多将领导人自身的情感作为有限理性的一种来源,或者是“受驱动的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背后原因和机制。勒博(Richard Ned Lebow)在关于国际危机的经典研究中总结出,领导人自身的情感、政治需求以及愿望对错误知觉的形成有重要驱动作用。
第一,作为战略工具的情感。领导人的情感与情绪,对于他的政治需求与判断会产生扭曲作用。这种研究路径仍将领导人的情绪与情感看作一种干扰与非理性要素,而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界,越来越强调领导人或国家的情感与情绪实际上能够发挥理性的战略功能。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相比,情感外交手段通过领导人和国家的情感表演传递相关战略信息与目标,这些战略信息包括战略决心、敏感性、战略意图等重要的国家间博弈信息。一方面,即使国家面对信息对称的情境,仍会产生错误知觉;另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情感的表演来表达相关的战略信息,从而博弈双方形成在特定议题上的战略敏感性、原则底线共识。郝拓德(Todd H.Hall)的研究遵循此种理性主义的逻辑。遵循理性主义的路径,相关研究突出国家可能对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利用,以此作为国家处理外交争端的一种谈判工具。与此相反,也有相关学者持情感本体论世界观,认为特定的民族主义与社会认同情感,是相关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民众构建“我们是谁”这种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要素。
第二,作为理性必要的情感。基于情感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国际政治心理学界逐步接受了情感对于理性的重要重构作用这一观点。以达马西奥(Antonio G.Damasio)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家在系列的临床观察中发现,如果一个病人由于生理病变,从而丧失了相关的情绪与情感能力,那么,这是一种符合“理想类型”的“理性人”的自然实验场景;然而,如果病人丧失了情绪与情感能力,那么,他的理性决策能力将受到极大的损害。基于此,情感神经科学家提出了重构情感与情绪的理性基础的命题。这为国际政治和外交决策中重新思考情感的理性价值带来了基础性的理论支持。
受此影响,关于领导人情感与情绪的理性本质分析,成为近年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界有关情感研究的前沿。受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相关研究的启发,比如镜像神经元的发现,重新揭示了人际信任、共情中面对面交流机制的重要性,相关学者探究了面对面外交对于领导人建立初步信任感、发出昂贵成本的信号(比如签订约束双方的协定)的重要性。面对面外交是领导人之间意图领会、建立信任的重要渠道,而情感的神经科学研究为此提供了微观的心理学机制。
战略互动的政治心理学:微观命题的深化
除了外交决策之外,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更多聚焦战略互动,比如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过程,包括信息传递、意图辨析、偏好塑造、承诺策略、声誉逻辑等环节。基于此,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在战略互动研究领域的外交信号、战略心理等命题上,深入推进理论与经验研究。
第一,外交信号的理论研究。自杰维斯具有开创性的理性主义研究之后,外交信号的理论研究遵循两种基本的路径,即理性主义和社会心理路径。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外交信号的可信性在于其所承载的代价或者成本的展现,这种成本必须具有不可逆性,或者体现为如果违反则会带来较大的代价。成本信号或昂贵信号,成为理性主义者观察外交信号可信的重要基础,其成本来源于两种方式:其一是自我约束的“自缚手脚”,其二是不断投入的沉没成本。在经验分析中,观众成本往往成为领导人确立外交信号可信的成本方式之一,尤其在民主政治国家。
社会心理学路径关于外交信号可信的分析逻辑,着重强调一些非昂贵成本的信号表达方式、信号载体等,也能达到增强可信性的目的。这些非昂贵成本的信号确立方式有很多,典型的如面对面外交、内部协调与协商、隐蔽行动等。比如,面对面外交在传统的外交方式中并不受到重视,因为其具有欺骗性、秘密性等特点,这导致面对面外交更容易被看作一种廉价外交方式。然而,郝拓德等学者的研究表明,面对面外交实际上能够确立领导人之间的初步情感联系和信任,正是这些信任情感使得领导人对于彼此的意图,尤其是合作意图,有着较为确定的把握,从而能够从各自的合作利益出发,签订具有较高代价的合作协议。
第二,战略心理的微观研究。战略决心成为近些年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重点理论研究命题。相关研究重点提炼了领导人判断、观察与知觉对手决心的基本理论依据,比如理性主义的成本代价论、声誉论的过去行为论、基于实力基础的物质主义论等。也有研究从决心声明的解读入手,系统性批判传统的行为论、声誉论等存在的不足,从而提炼了一种领导人观察对手的决心声明是否可信的理论依据,重要的一点在于对手是否有着坚决贯彻执行决心的相关外交行动能力,这种能力既有客观的国家军事与战略能力,也包括能否克服国内否决者的压力等。也有相关研究探究了决心的认知偏差所造成的冲突效应,这种低估冲突决心的认知偏差,与传统的错误知觉理论以及理性主义冲突起源论均有所不同,而且如果把战略决心看作自变量,那么,战略决心是动态演变的,受到外部环境和领导人自身人格特质的影响。
自默瑟(Jonathan Mercer)开创性探究了声誉形成的悖论之后,关于战略与安全研究中的声誉逻辑讨论,已形成了诸多理论流派,比如过去行为论、行为体的执行能力论等。在声誉的形成逻辑中,乐观主义者坚持认为,从行为塑造开始,增强声誉兑现的能力及其执行决心,都可以保持较好的声誉记录。但悲观主义者则认为,领导人或国家追求盟友的声誉很多可能是徒劳的,只会增加国家间冲突。关于声誉形成的动力与来源问题,不同学者的看法存在差异,比如,唐世平坚持结构主义解释,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本质,造成国家间关于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从而国家间声誉的形成和维系是艰难的。微观论者则关注领导人的内在特质差异,比如,不同领导人对于“自我控制”信念的程度不同,从而造成不同领导人对于外部声誉的敏感性差异。
第三,战略文化的特质研究。战略文化的传统研究聚焦美苏等大国的战略竞争议题,分析苏联领导人的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以及大国关于攻防的战略思维及其手段选择,进一步形成了关于进攻性还是防御性战略文化的争辩。
冷战期间,关于中国战略文化及其与武力使用关系的讨论,大多数路径持中国进攻性战略文化的分析,而中国文化路径学者提炼出较为独特的文明型国家形态,以及中国外交中关于面子、等级秩序、天下秩序等世界观想象。冷战结束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进入更为实证化的阶段,并形成了进攻性与防御性战略思维的争辩。一方面,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在《文化现实主义》中系统论证了中国“未雨绸缪”式的战略思维;王元纲在汲取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基于明代等相关的战略实践分析认为,中国在权力对比、实力对比中的优势与劣势位置,实际上决定了中国是否采取武力等进攻性战略手段。另一方面,关于中国防御性战略文化的研究也得到较多支持,典型如冯惠云等人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操作码分析,较为系统地描绘了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世界观,体现出较为强烈的防御性战略文化特质。
为了超越上述关于防御性还是进攻性战略思维的传统争辩,有研究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领土边界争端问题上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处理相关领土等主权争端的“搁置”思维。这实际上是一种为了解决问题,在无法形成真正共识的情况下,追求单边默契与共识的特定战略思维——单边默契战略思维。
在理解中国的战略思维方面,也有研究将分析单位聚焦特定的领导人,比如分析中国不同代际领导人的人格特点,辨析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在外交事务兴趣、信息开放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辨析其对待国际社会的不同态度。另一方面,在宏观思维层面,文化特质成为理解中国国家形式、对外关系决策方式、中国国际关系及其秩序观的基础,基于心理人类学的视角,中国的国际关系观有着自身的文化理性,区别于西方的国家理性特质,比如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形式、集体主义式理性以及天下秩序观等。
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政治心理学在经历冷战时期的经典与传统研究阶段之后,理论与经验研究进一步进入学科的成熟发展阶段,这直接表现为研究议题的细致与深化,从探究政治心理要素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定性判断,到进一步提炼影响机制与作用条件。在领导人的人格、认知与情感研究路径中,探究新的案例、政治心理类型以及作用机制。同时,在研究议题上也结合了传统的安全与战略研究,以及新时期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关系现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