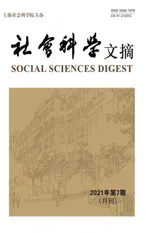司马迁“行国”史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2021-11-15樊丽沙杨富学
文/樊丽沙 杨富学
以司马迁著《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部“正史”,差不多都对中原王朝四邻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有所描述。《史记》对西域民族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大宛列传》中,该传也被视为历代正史“西域撰述”之开端。在论及月氏、乌孙等河西牧业民族时,司马迁用同俗类比的方式以“行国”冠之,将这些影响较小的牧业民族与影响巨大的匈奴一样视为游牧民族,后世历代史学家多奉为圭臬,遂逐步形成中原史家书写牧业民族的一贯传统,以致影响于今。如何看待司马迁之“行国”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准确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牧业经济,不无积极学术意义,故而特撰此文,提出一己之见,望方家雅正。
司马迁对西域认知的局限
在《大宛列传》中,司马迁依据张骞西行归来的上奏报告,对当时西域诸国做了详细描述:
1.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城郭屋室。”
2.乌孙:“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
3.康居:“行国,与月氏大同俗。”
4.奄蔡:“行国,与康居大同俗。”
5.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6.安息:“其俗土著,耕田。”
7.条枝:“耕田,田稻。”
8.大夏:“其俗土著,有城屋。”
揆诸以上记载,不难见太史公对西域诸国生业方式的了解程度,大体依据“随畜”和“土著、耕田”与否,将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称之为“行国”。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行国就是不土著”,大宛、安息、条枝和大夏等因有耕田和城屋遂被视为“土著”。其实,这种对西域诸国社会经济方式的认知存在着历史惯性和地理局限性。司马迁对西域的叙述主要取材之于张骞的西行报告,据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其中,张骞在匈奴中逗留十余年,在大月氏中留年余,掌握信息情报最多的即是二者,尤以匈奴为最。司马迁所言“乌孙与匈奴同俗”“康居与大月氏同俗”“大月氏与匈奴同俗”,大体不出这种认知。在太史公笔下,匈奴风俗如下:“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
看来,在太史公眼中,匈奴、乌孙、大月氏等“行国”是以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的,以“不土著”和“随畜移徙”为特征。由于当时汉朝对西域尤其是河西走廊的熟悉程度不高,司马迁将原先活动于河西地区的大月氏、乌孙等民族采用“与匈奴同俗”的类比推理,界定为“行国”。这种某国与某国同俗的记载在《史记》中比比皆是,乃司马迁对西域诸国生业特点的总结评判,就其认知而言,西域诸国大体是同俗的。司马迁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中国观之下,认为匈奴是逐水草迁徙的“行国”,无城郭、非定居、不稼穑,且“毋文书”“不知礼义”,将匈奴视为纯粹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并以此推之乌孙、大月氏等河西牧业民族,显然失之偏颇。事实上,匈奴并非是单一的游牧生业方式,考古资料表明,匈奴帝国存在着半定居性的居所和城塞建筑物,不仅有城池,而且有一定的农耕业,在其活动故地更有大批墓葬群被发现,说明真实的匈奴社会经济模式并非司马迁所记完全“不土著”。但总体来说,匈奴是以“不土著”为特征的,就此而言,太史公对匈奴的认识是准确的,但因其对河西走廊地理环境了解有限,以“与匈奴同俗”之类比法来记述乌孙、月氏等牧业民族,不免会让人将匈奴“行国”特点加诸乌孙、月氏之上。以司马迁的巨大影响力,其论断自然会被后代史家所承袭。
后世对司马迁述写模式的因袭
《史记》之后,历代正史对西域民族史的述写模式明显承袭于太史公风格,《史记》中对西域、河西牧业民族“随畜逐水草”的记载也被后世直接袭用,成为正史对牧业生活描述的固定模式。今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具体而言,婼羌“随畜逐水草,不田作”;鄯善国“民随率牧逐水草”;西夜国“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尉头国“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乌孙国“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在班固笔下,这些西域诸国都是“逐水草而居”的。出于放牧需要,“逐水草而居”是必要的,但需要考虑这种“逐水草”到底是设立一定居点、白天去放牧晚上回来,还是一去不回,还是根据季节不同而循环往复。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就应该看作是住牧,第二种情况才应是游牧,第三种情况那就应该是转场。转场的情况今天比较多见,但在古代,应以裕固族、青海藏族和哈萨克之先民较为典型。
汉代之后撰写的正史,大体都奉史班为圭臬,如《三国志·魏书》载:“赀虏,本匈奴也……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晋书·四夷传》载,吐谷浑“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宋书》载吐谷浑“逐水草,庐帐居”。《魏书·西域传》同载“遂水草,庐帐而居”,乌孙国“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小月氏国,“随畜牧移徙,亦类匈奴”;康国“迁徙无常”;嚈哒国“无城邑,依随水草”。诸如此类,不能一一例举。
后世史学家在描述西域牧业民族时,无一例外,皆沿用司马迁之语,按照与匈奴同俗的标准,多用“随畜牧逐水草”之类语言来概括。班固明确界定为“行国”的有大月氏和西夜国,其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太史公所记“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即“不土著”,颜师古也从之,认为“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随畜牧移徙也”。若以此为标准,则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中可归于“行国”者大体有十三个,即鄯善、小宛、戎卢、渠勒、西夜、乌秅、子合、蒲犁、依耐、无雷、捐毒、休循、若羌。然这些西域绿洲小王国大多分布在今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族别和语言皆不同,皆因其生产经营方式上有“随畜逐水草”的特点,均被冠以游牧民族论之。其实历史上如匈奴、鲜卑、铁勒诸部、斯基泰、突厥、蒙古、哈萨克等比较典型的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漠北、欧亚草原地区,在新疆天山南北、河西走廊、中亚、西亚等地以绿洲经济为特点的民族中,游牧是不现实的。游牧的特点在于游而不归,在绿洲地区很难做到这一点。
历代史家对牧业经济尤其是绿洲牧业民族的认知出现一定偏差,盖因承袭司马迁对“游牧”一词的误解而来。
司马迁对“游牧”的误解
农业和畜牧业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两种生业方式,而畜牧又分为游牧与住牧二种,介于游牧与住牧之间的当为转场。这是西方学术界普遍遵循的划分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划分原则。中原士人对我国北方牧业民族的最初了解大抵来源于以《史记》为代表的“正史”,对畜牧业的认知,大多局限于“逐水草而居”,认为匈奴、蒙古等典型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其生业方式适用于所有生态环境下的畜牧业经济形态。其实,并非所有畜牧业民族都是如此,游牧仅是畜牧生活的一种形态而已。当然,这里所说的“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游牧”为主,并不排除一定程度的“定居”的成分,纯粹的游牧社会(pure pastoralism society),即不存在农业种植的、完全以畜牧和游牧经济支撑的牧业社会在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河西走廊地形多样,“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养”,经济特征十分复杂,古往今来皆是月氏、乌孙、匈奴、回鹘及现在的裕固族、蒙古族、藏族等牧业民族的理想栖居地,元人曾美誉“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但囿于独特的地理面貌,河西走廊农牧间杂,代代沿袭,故而一直未能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游牧生业方式,此山间草原地貌被有些学者认为是“适于游牧生活”显然是不合适的。
河西走廊的西部也多有绿洲,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的畜牧大多只能是住牧,尽管不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成分。司马迁和班固等中原史学家将月氏和乌孙描述为“行国”“随畜移徙”“随畜逐水草”,很容易使读者得出月氏等为游牧民族的结论,这与考古所见河西史前畜牧业文明存在明显偏差。沙井文化(公元前1000年)与骟马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两者都属于牧业文化,分别与月氏和乌孙的活动地域重合。月氏、乌孙等民族的畜牧业属于住牧生业方式,有自己的活动中心与定居点,而且这些定居点都是长期的,是游牧民所完全不具备的。
月氏和乌孙的此类住牧经济方式被历代河西畜牧民族所沿袭。唐代的漠北回鹘、宋代的甘州回鹘、沙州回鹘都属于典型的住牧生业形态,都拥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及至明清,裕固族先民“黄番”继续繁衍生息于河西走廊一带,依然保持农牧兼营的生业方式。今天的裕固族在生产方式上与古代先民并无二致,以肃南大河乡为例,牧场转移依据山体的海拔高度来确定,夏季在海拔较高的地方放牧,冬季转入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放牧,这种生活方式属于“小游牧”类型,与蒙古高原之远距离游牧不可同日而语。可以看出,这种生业方式介乎游牧与住牧之间,以“转场”为其特色,应该称之为“四季轮牧”更为合适。裕固族与古时河西从事定居畜牧业的月氏、乌孙、回鹘、黄番在生业方式上近似,历千年而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实乃地理环境使然。因此,河西史前畜牧业,如果真有游牧存在,应该是以“大定居,小游牧”为特点的,并非是纯粹逐水草而居的“行国”生业方式。质言之,“畜牧”“游牧”和“农耕”属于三个不同的概念,是三种不同的生业形式,但太史公将“畜牧”和“游牧”混为一谈,以“土著”表示农业,自然无误,但以“不土著”表示畜牧业,就有违史实,因为畜牧业既可以“土著”,也可以“不土著”。是以,《史记》《汉书》等所见月氏、乌孙“随畜逐水草”之谓,不应解释为游牧,而应理解为住牧最为合适。
司马迁“行国”说对当今学术界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之先河,其《大宛列传》也被视为西域史志的滥觞,因此,“行国”说被历代史家奉为圭臬,对当今民族史、古代经济史、农牧交往史等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
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一般都没有明确界定“畜牧”和“游牧”的本质差异,很多学者论述的“游牧经济”概念实际上多是指“畜牧经济”。此种误解首先表现在翻译西方学术成果上,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中,有多处被误译,原译本中“pastoral race”或“nomades or pastors”表达很清楚是畜牧民族,结果国内多位学者无视畜牧和游牧的区别,皆译成“游牧民族”(nomades),显然是不合适的。
河西民族史研究领域中,“游牧”概念也时常被误解,受“行国”史观影响,不少学者将月氏、乌孙等河西牧业民族等同于游牧民族,在论述时出现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有学者意识到“像匈奴和月氏这样的游牧民族当时有没有农业,史书记载和实际情况不尽相符”,并依据沙井文化认为“史籍所谓‘无耕田之业’的匈奴和‘与匈奴同俗’的月氏,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农耕稼穑,文献与实物抵牾处,我们更相信地下发掘的材料”。这些说法都是将河西的这些先民冠名为“游牧民族”,却又言其过着定居的生活,实际上混淆了游牧与住牧的区别,显然是说不通的。
受此“行国”说影响,学界不少学者在论述西域、河西绿洲经济时会陷入困惑,如有学者认为对于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的记载“过于绝对”。还有学者依据司马迁认定“行国”的几大要素,将乌孙、大月氏、康居、西夜等西域牧业国家称之为“游牧行国”或“政治体”。位于甘青高原河谷的河湟一带牧业经济也经常被误认作游牧经济,如有学者认为河湟部落民众“基本上他们是行游牧的,但‘地少五谷’这样的陈述,似乎是在说他们并非绝无农业”,将河湟地区与蒙古草原、东北森林草原一并作为游牧经济的地理环境论述,显然是受传统“行国”史观影响,与前列几位学者一样,没有分清畜牧业与游牧的区别与联系,因而陷于窠臼,难以自圆其说。
西南民族史研究上也受此影响,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有学者以“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为据,将巂、昆明、徙、笮都等归入游牧民族,其实这些少数民族的经济特点与当今裕固族几无二致,当为“转场”而非“游牧”,有学者虽然认为此种经济模式“由于亩均产草量低而必须转场”,但却陷于旧论,习惯“用‘行国’与‘土著’”的标准来界定边疆民族文化类型。西南夷民族(herders)这种兼农牧而常移住处的生活方式不能简单等同于游牧民族,更不能用“逐水草而居”的“行国”观一概而论。
司马迁之“行国”说对学术界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也造成了极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畜牧部落”(一般指住牧者,德语“Hirtenstämme”),英译本中的“Pastoral tribe”被误译作“游牧部落”;恩格斯原文所说的“Hirtenvölker”“Hirtenleben”,本意为“牧业民族”和“畜牧生活”,却被误译作“游牧民族”和“游牧生活”。不少译者对“游牧”与“畜牧”者两种不同的生业方式不甚了解,认为“游牧”就是“畜牧”,反过来,“畜牧”就是“游牧”,把两种不同的生业方式混为一谈了。
新疆天山以南被沙漠环绕的绿洲地区,本身就不大,不可能存在游牧,受“行国”说影响,不少学者以“游牧”称之,如有用“南疆游牧文化”或“山麓草原游牧区”来指代天山以南绿洲畜牧业的情况。这种观念也深深影响了诸多民族学领域学者对牧业文化的认知,如有学者把乌孙、大月氏称为“原活动于今甘肃河西地区的游牧民族”,将定居的甘肃肃南裕固族文化视为游牧文化的代表,以定居游牧文化视角来研究新疆牧业民族,甚至也有学者把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陕西省北部的农牧兼营区域视为与蒙古草原一样的“适合游牧的地带”。以上论述显然不合适,皆是对牧业文化认知偏差所致。
结论
司马迁的“行国”史观出自农业民族士人对牧业民族生业方式的认知,由于受各种条件所限,未能准确区分西域、漠北、河西地区间牧业经济的区别,未能将游牧与定居的畜牧业区分开来。后世史家多承袭之,把具有“逐水草而居”特点的牧业民族统归入“行国”之列。这一史学传统一直得到延续,以至于对今天的相关研究造成影响,出现“事实上游牧民族也过着定居生活”之类的悖论。出现这种悖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我国学术界的史学观念中缺乏“畜牧”与“游牧”有别这一基本概念。这些是今后史学研究中应予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