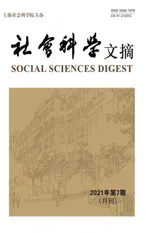生活儒学与“哲学训诂学”建构
2021-11-15张小星
文/张小星
儒学的现代转型必然蕴含着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但到目前为止,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的相关思想资源被建制化地划归入文学、史学等学科中,其现代转型并未真正实现。从学理上讲,彻底的现代转型必须深入到存在论(the theory of Being)层级,即揭示“经典诠释”作为前主体性、前存在者活动的意义。换言之,对于“经典诠释”相关问题的探讨必须纳入存在论层面才是透彻的。而这一转型的具体展开,既要有效吸纳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有益思想观念,又要充分考察中国本土的经典诠释传统,挖掘中国训诂学所蕴含的经典诠释资源。就此而论,生活儒学的“生活论诠释学”为我们提供了启示。本文意在从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出发,展开对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进而勾勒出一种新的诠释学形态:“哲学训诂学”(Philosophical Exegetics)。
“经典诠释学”评析
在“中国诠释学”建构思潮方兴未艾、各种诠释学形态不断涌现的当下,一些学者试图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尽管这些建构尝试是在梳理中国(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却各以西方某种诠释学历史形态作为其指向性目标,因而在理论旨趣上呈现出不同样态。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强调“中西之异”,旨在建构作为现代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经典诠释学,以景海峰的论述为代表。他认为,中国哲学经典诠释方法的现代转化,应当是从传统训诂学转为经典诠释学。在他看来,中西经典诠释传统具有明显差别。西方诠释学不仅有作为语言工具之技艺性层面的向度,而且有作为认知工具之哲学化向度;而中国训诂学则缺乏哲学之思辨性和认知功能上的独立性,而且随着中国学术范式的现代转型,尤其是传统经学的解体,原来附庸于经学、作为解经工具的“小学”现在被安顿于语言文字学之中,使得训诂学与作为精神性的哲学相去甚远,加之义理之学被归入哲学,这就导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建构在方法上依赖于西方。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诠释”的意义,通过打破传统训诂的界域,迈向新的经典诠释学,从而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奠定方法论基础。另外,吴根友的相关论述也可归属于这一类型,其具体做法分为两步:首先是以西方诠释学作为参照,通过阐述清儒戴震的经学解释实践原则,进而将其归结为一种“经学解释学”;然后再将此“经学解释学”思想泛化到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释过程中,从而将其提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代“经典诠释学”,在由训释文字、分析语言而到解读经典意义的过程中,实现认知水平与思想境界的双重扩充,从而为“当代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提供新方法与新视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经典诠释学”本身不仅未能提出具体而有效的方法,也未能从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形出发来探讨“经典诠释”作为方法论原则的合法性所在,于是成为一种抽象而空洞的口号,而缺乏应有的实质性内容。此外,就诠释学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方法论范式的诠释学形态已经因其内蕴着“认识论困境”而遭到解构,如果以此作为参照镜像,那么,这种“经典诠释学”本身将同样面临被解构的危机——“经典”的客观性意义何以可能?
另一种是强调“古今之变”,旨在作为建构理解理论的存在论基础的经典诠释学,以傅永军的论述为代表。与上述方法论向度形成对照、强调“中西之异”不同,傅永军主张由“古今之辨”转为“古今之变”,即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所应完成的基本任务应当是从“经典注释学”转型为“经典诠释学”。在他看来,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笼罩在文献学、语文学、历史学之下而缺乏哲学自觉意识,“经典诠释”主要被理解为一种解经的技艺学,表现为一种以文字训释和文本考据为中心的注疏之学。而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必须借重西方诠释学的刺激,实现从文献学—语文学—历史学到诠释学的现代转型,在中西经典诠释传统的对话中完成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诠释学转向,进而建构一种摆脱方法论定位而作为理解存在论的经典诠释学,也就是关于理解本性以及理解如何可能的理解理论,此乃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的优选路径。
显然,这种诠释学的问题意识源自海德格尔,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伽达默尔说:“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因此,伽达默尔事实上延续了海德格尔的矛盾:尽管“此在”被海德格尔认为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由此而获得突入存在本身的优先性,但“此在”依然属于某种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因此,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矛盾在于:既然“理解”不属于主体性的行为,那么其本身又何以成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呢?对于作为理解存在论的经典诠释学来说,“理解”依然属于一种主体性行为,而问题在于——这种主体性本身何以可能?
“生活论诠释学”思想
诠释学史表明,任何一种诠释学理论都必然奠基于某种存在论形态,而此诠释学理论出现问题则反映了为之奠基的存在论本身的困境,因而需要建构新的存在论,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诠释学理论。上述“经典诠释学”范式之所以不彻底,根本原因即在于为之奠基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彻底。这意味着,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首先需要一种更为透彻的存在论为之奠基。笔者以为,生活儒学提出的“生活存在论(Theory of Life as Being)”,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注生我经”为核心观念的“生活论诠释学”,为我们的思考与讨论提供了理论指引。
具体而言,这种“生活论诠释学”的建构内在地遵循了生活儒学“破解—回归—构造”的致思进路。
首先,所谓“破解”,是指一种在“破坏”中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通过“解开”而“释放”,即通过解构既有的诠释模式,进而释放出建构新的诠释学的可能。简而言之,这种既有的诠释模式就是“主体性诠释”,表现为作为主体的诠释者对于文本或经典的理解与解释,其实质上是一种以主体性预设为前提的诠释观念。上述“经典诠释学”亦属于这种诠释模式,它不仅长期主导着中国前现代的古典诠释观念,如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而且至今仍存在于诸如“中西比较”“对话伦理”“东亚儒学”等关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诠释经验中。这种诠释模式的问题在于,其内在前设的“主—客”思维架构难以避免胡塞尔所指出的“认识论困境”,也就是认识如何能够确定它与被认识的客体相一致、它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准确地切中它的客体的问题,这就导致“主体性诠释”本身面临追问:我们如何可能确证一个文本及其意义是客观实在的呢?我们如何可能通达、理解这个客观的文本及其客观的意义呢?进而言之,这种诠释模式本身难以阐明——诠释者的主体性、文本及其意义的客观性何以可能?
然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归”,即回溯到生活—存在视域,亦即“还原”诠释活动的“事情本身”。“生活存在论”认为:“生活”乃是一切的本源,而生活本身并非某种主体的生活,即并非海德格尔所谓“此在的生存”——“特殊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先行于任何主体性、任何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所谓存在”;生活本身作为“事情本身”,总是如此这般地显现为“有事无物”的生活情境,即无分别的“境遇”,而“境遇”正是一切作为存在者的“物”得以生成的本源;生活本身呈现为“在生活并且去生活”的结构,“在生活”表明生活本身作为“事情”总在发生着,而“去生活”则意味着生活本身总在超越着,“事情”本身总是蕴含着向前运动的可能。就诠释活动而言,所谓“注”亦即“诠释”正是生活本身所显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情境,尽管这种情境总是表现为主体在理解与注解文本,但其本身也同时在生成着新的主体性,以及新的文本客体。
最后,“破解”与“回归”的目的在于“构造”,即建构一种新的诠释学理论,来阐明“注”亦即“诠释”活动本身如何塑造着新的存在者。对此,生活儒学提出“由言而成”,即“言说”给出了新的存在者,此即儒家所讲的“不诚无物”,“诚”本身说的是一种本源性的言说,讲的是由“言”而成。存在者成为存在者,他们是怎么被给出的呢?由言而成。“注(註)”正是如此这般的“言说”活动,孔颖达《毛诗正义》讲“注者,著也,言为之解说,使其义著明也”,文义著明的过程同时亦是主体实现自我理解与自我解释的过程,新存在者就生成于这种“注(註)”之中。由此,生活儒学提出“注生我经”的诠释观念:“注”本身是生活的一种显现样式;所有实体性、存在者性质的东西,包括“我”“经”以及“主—客”思维架构,都是在此事情当中生成并显现出来,从而不断地展开并实现自身超越。
“哲学训诂学”构想
为此,在上述生活儒学“注生我经”观念的启发下,这里尝试提出“哲学训诂学”(Philosophical Exegetics)的理论构想。需要申明的是,所谓“哲学训诂学”并不是要建构一种有助于文本解释的方法论,即并非那种为哲学研究与哲学创作提供一种方法的所谓“训诂哲学”,而是一种存在论性质的研究,即通过揭示“训诂”的存在论意义,而探讨“训诂”活动如何生成新的意义世界的问题。
所谓“训诂”,最初指“解释古语”,如《说文解字》讲:“训,说教也。”段玉裁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说文解字》:“诂,训故言也。”段玉裁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随着后世语言研究的发展,凡是对古代典籍上的语言进行解释说明的活动,皆可称为“训诂”;而这种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可见“训诂”原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境遇”。按上文生活儒学存在论的观念,“训诂”活动可被视为生活—存在本身的一种显现情境。在此意义上,所谓“通之”便不是存在者层级上的主体在沟通“古今异辞”和“南北异言”,即孔颖达所谓“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而是生活—存在本身给出存在者,即训诂活动生成“古今”(时间)“南北”(空间)“注者”“物”等存在者观念的过程。
事实上,训诂本身也是一种“不诚无物”“由言而成”的过程。无论是孔颖达所谓“释”“通”“辨”,还是黄侃所谓“语言解释语言”,皆属于“言—说”活动。此“言—说”活动的发生,既确证了“言说者”自身之主体性,即“(我)言,故我在”,同时又生成了“被言说者”之对象性。在此意义上,所谓“通辞”“辨物”并不是对所谓文献词义、名物的训释与考证,而是“物”本身之生成(“人”本身亦归属于“物”),即“存在者”的生成,而作为“言—说”的“训诂”在此意义上即成为一种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活动。
“训诂”生成存在者的过程,也是一个构造新的意义世界的过程。尽管当下发生的训诂活动表现为主体对经典及其语词的训释与考证,但这种活动事实上却构造出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在此世界中,主体被赋予新的主体性,经典文本被赋予新的经典性。具体来说,由“言语不通”引起的理解障碍使得“训诂”成为必要,这种障碍表面上体现在语言文字方面,但实际上是作为主体观念中的事情而归属于“读者”自身,所以“训诂”实则是在消除主体之于文本意义所形成的“疑惑”,而扫除语言文字障碍的过程便展现为对主体自身之疑问的“疏释”过程;“训诂”完成即读者之“疑惑”得以“疏释”,使得读者自身实现了自我观念的更新,即实现了自我超越而赢获新的主体性,从而成为新的主体。与此同时,经典文本也被赋予新的意义,即读者经由“声训”“形训”“义训”等“疏释”方式而赋予经典以新的意义,亦即通过语言文字之意义的扩充,经典文本的面貌得以焕然一新,从而生成为新的经典。这就是说,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被历时性的“训诂”活动所塑造的,经典文本由此而不断获得“去存在”的可能性。
比如说,在当前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古代儒家经典之所以具有现代性意义,正是被当下的诠释活动所赋予的。例如,生活儒学对于《周易》经传的重新解读,并不只是使得“生活儒学”理论自身获得了新的充实,更为重要的在于赋予了《周易》经传本身以现代性意义,促进了易学哲学的现代转型,阐发出一种包含三个层级内容的现代性易学哲学形态。一是关于建构现代社会伦理和价值的形而下学,即以探讨社会制度规范赖以建构的正义原则为核心的正义论。黄玉顺认为,《易传》事实上提出了两条正义原则。第一是正当性原则,如:“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二是适宜性原则,如:“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二是关于绝对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即将“变易”视为形而上之本体的“变易本体论”。在黄玉顺看来,《易传》提出的作为本体的形而上者并非某种固定的实体,而是一种流动的“变易”,此即《易传》所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三是关于如何描述主体性得以可能的本源存在论,即《周易》古经之本源情感论。在黄玉顺看来,作为形而上者的“变易”本体源于阴阳交感观念,而这种阴阳交感的观念则是源于咸卦、观卦古歌所显现出的生活情感,其本身乃是生活感悟的存在者化、本体化、形而上学化的结果,所谓“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而这种“训诂”活动,亦即对于古代经典的解读与诠释,无疑归属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亦即当下生活的一种显现。
以上即“哲学训诂学”的初步构想,旨在立足于中国特有的训诂学思想资源,为中国(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探索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