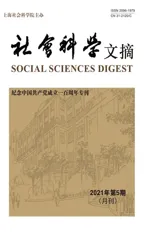从“主义”到“党”:政党观念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2021-11-15李里峰
文/李里峰
政党观念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党”的记载,“朋党”及“党争”也是传统士大夫政治论述中时常出现的字眼和主题。但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政党”概念出现于中国,无疑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知识交流的产物,经历了传统汉字词汇被赋予新意涵而成为一个现代概念(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过程。
在传统中国政治语境中,“党”总体上是一个具有显著贬义色彩的概念。《说文解字》释“党”为“尚黑”。《论语》云:“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北宋之际,“朋党”一度成为朝中政治论争的关键词。欧阳修呈送宋仁宗的《朋党论》一文,将朋党分为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呼吁君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尽管如此,“党”在传统思想脉络中的负面意涵并未真正改观。到了清代,雍正帝亲自撰写《御制朋党论》,严厉驳斥欧阳修的朋党论述,称“朋党之徒,挟偏私以惑主听,而人君或误用之,则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为至私之事”。
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党”(party)与“派系”(faction)长期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政党(political party)作为现代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则是因应18、19世纪代议制政府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普及而产生的。萨托利敏锐地抓住“政党”与“部分”的实质性关联,指出现代政党本质上是作为国家整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不同政党之间围绕权力争夺、利益整合、政策主张展开竞争与合作,正是现代代议政治的根本前提。及至十月革命爆发,苏俄政府成立,一种新型的政党登上了人类政治舞台,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为手段、作为国家整体的列宁主义政党。“作为部分的政党”和“作为整体的政党”,构成了20世纪政党的两种基本类型。
从甲午到辛亥的政党论述
19世纪后半期,具有现代意涵的政党概念逐渐传入中国。甲午战败对朝野上下形成的强烈刺激,是促使政党观念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的重要转折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政党的论述开始在各类中文报刊上广为流传,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难以尽述。从甲午到辛亥的十多年间,国人的政党论述主要涉及四个问题。
政党与朋党。朋党在国人观念中根深蒂固,西方政党概念传入中国后,通过与朋党相比较来界定政党之特质,自在情理之中。朋党为私而政党为公,朋党以人情相合而政党以政见相合,这样的比较,从根本上扭转了“党”在国人心中的道德形象。
政党与立宪。这一时期的政党论述,大多强调政党为民权政治、立宪政治之产物,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立。“政党之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两翼。非有立宪之政,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翼耳。”
政党与救国。甲午战败引发的国耻感和救亡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政党观念以探索救国之道的重要转折点,故政党与国家、与救国之关系,成为国人关注与讨论的焦点之一。“天下不能一日而无政,则天下不能一日而无党”,“今者中国之存亡,一系于政党发生与否,是政党问题者,实今日最重要之问题也”。
两党与多党。在认可政党为立宪之产物、救国之良方的基础上,时人多把英、美等国的两党制作为理想政党制度的范本,其理由大致在于两党相互均衡有助于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梁启超比较各国政党制度,认为“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杜亚泉则于辛亥前夕,冀望保守党与进步党相互扶助、相互制衡,造就中国的两党制。
这一时期,“政党”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广为传播,成为他们观察时局、表达政见的重要视点;另一方面不仅完全摆脱传统“朋党”的负面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和以武力颠覆政权的“革命党”区别开来,成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或立宪政治之政党的专用名称。
党派运动与国民运动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原则,是国家与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及利益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具有政治代表、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和聚合、社会化和政治动员、组建政府等政治功能。从甲午到辛亥前后的政党论述主要在民权政治、立宪政治的框架内展开,更多强调政党的代表功能、利益表达和聚合功能;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出现,知识精英的政党论述日益与“民众运动”“国民运动”联系起来,越来越多地强调政党的社会化和动员功能。而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看来,当日中国之政党在动员国民方面恰恰显得力不从心,从而难以担负救国之重任。
民国初年,李大钊即对政党和政党政治进行激烈批判,称民国政党不过“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唤汉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实则“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这和此前秦力山、梁启超等人视政党为救国之良方,形成了强烈反差。
1916年初,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撰写的新年寄语,集中表达了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政党观念。他将“党派运动”与“国民运动”、“政党政治”与“国民政治”相对立,认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陈独秀一方面分党派为“政府党”与“在野党”,而与其政策主张无关,事实上消解了原则或政见对于政党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将党派放在与国民对立的位置上,前者以夺取或行使权力为目的,后者则以社会进步为己任。在《吾人最后之觉悟》这篇名文中,陈独秀虽对共和宪政仍持肯定态度,却强调共和宪政不可得之于党派,只能出于多数之国民,立论重点实已由“立宪政治”转移到“国民政治”上,“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陈独秀此时已对以代议制和选举制为基础的西式政党政治产生怀疑和不满,不再强调现代政党的公共属性,转而将其与传统“朋党”“派系”概念中偏狭自私的消极意涵重新联系起来,批评政党缺乏公心与雅量而陷入党争;也不再把政党看作立宪政治的产物或前提,甚至不把立宪政治本身看作中国政治之理想;而是以“国民政治”为参照,主张由“党派运动”向“国民运动”转化。
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关注、介绍和宣传俄国革命的无疑是李大钊。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于1918年接连发表多篇介绍和评论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俄国革命则“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庶民的胜利》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BOLSHEVISM的胜利》介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其中,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关于现在的理论”和“关于将来的理论”,并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期专号并没有一味赞扬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确实将其当作一种“学说”加以“研究”,其中多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持有明显的批评立场。例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从经济论、唯物史观、政策论三个方面,逐一介绍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意见,并引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表达了不要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绝对真理的观点。因此,这期马克思研究专号还算不上《新青年》同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这一两年间,陈独秀一边宣告“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一边指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并预言“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
以俄为师的建党主张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一般性地介绍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到积极探索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理念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建党实践,大致发生在1920年春夏之际。在实践和组织层面,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分别开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在观念和宣传层面,则以1920年9月《新青年》的改版重刊和同年11月《共产党》月刊的出版最为重要。
《新青年》在1920年5月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后短暂休刊,至1920年9月1日重新刊行第八卷第一号,在封面设计和内容上都有显著变化,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宣传阵地,也成了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事实上的机关刊物。该期杂志增开《俄罗斯研究》专栏,至1921年4月第八卷第六号为止,共发表32篇与俄罗斯相关的译文。专栏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简史、政治结构、列宁生平、劳动组织、社会教育、经济政策、女工问题、军队问题、文艺问题、性别问题等,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引起陈望道、胡适等同人的不满及关于办刊宗旨的争论。
在《新青年》改版前后,蔡和森从法国致毛泽东两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国际的基本情况,并明确提出以俄为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的信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党”(另三种为工团、合作社、苏维埃),它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和“神经中枢”。他提出“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同年9月16日的信内容更丰富,包括以下要点:介绍布尔什维克的入党条件;简述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过,介绍俄共(布)的组织结构及党员绝对服从党组织等基本特征;介绍共产国际成立的基本情况;介绍美、英、法、德、西班牙、比利时等十余国家共产党的概况;以俄共为参照,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步骤。将两封信的内容与后来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和“二大”通过的章程相对照,不难发现它们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有显著的相似性。
由此可见,中共创建者们认识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各有特色的。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最为系统和深入,尤其侧重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陈独秀往往从时局观察入手,在国家、阶级、政党及国民运动的视野中表达马克思主义主张;至于在深入探究列宁主义建党思想与实践,并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案这一方面,蔡和森的贡献则更为显著。在很大程度上,这两封信应视为中共创建者们拓展政党观念、理解并效仿俄共组织结构的核心文本之一。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月刊。至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共刊出6期,发表文章一百余篇,主要包括三类:列宁著作及国际共运相关文献的翻译;关于列宁生平、俄国革命以及革命后苏联现状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介绍;对各国社会党、共产党及劳工运动的报道和评论。陈独秀为创刊号撰写的“短言”,概括出创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具备以下基本特征:俄国式的党(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社会主义的党(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的党(用革命的手段、阶级战争的手段);阶级专政的党(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反对民主政治、代议政治的党。此文仅数百字,但是作为中共创建者明确阐发政治主张并且公开发表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宣言的性质。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以及《新青年》的改版和《共产党》的创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已经实质性展开。有了这些最直接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便水到渠成。
结语:主义型政党的诞生
考察中国与西方政党观念的演变过程,大致都经历了基于利益的朋党(宗派)、基于原则的部分党(近代西方政党)、基于主义的整体党(列宁主义政党)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正是建党先驱们政党观念转型与政治实践探索相互激荡的结果。从19世纪后半期到十月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政党通常是指代议制的政党,理念上与共和、立宪相联,制度上与选举、国会相联,其核心特征是“部分”,即特定政党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共同推动政治运行,维系社会稳定。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准备。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共创建者们所接受、服膺并引为奥援的理论武器,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是具有鲜明俄国色彩、列宁色彩的“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后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的阐发与实践。中共创建者们由此实现了从作为部分的代议制政党向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观念转型,其建党实践也由此获得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
甲午战争之后的30年,见证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急剧变迁,政治观念转型的“主义时代”、政治主体转换的“群众时代”、政治实践革新的“运动时代”,都在这一时期联袂降临到近代中国。将这三者有机整合起来的,便是以“主义”为引领,以“群众”为基础,以“运动”为手段的新型政党。就其目标而言,它是革命型政党(在体制外以武力方式夺取政权)而非宪政型政党(在体制内以选举方式竞逐政权);就其功能而言,它是整合型政党(动员和教育群众而不仅是回应他们的要求)而非代表型政党(为获取选票而迎合民意);就其结构性特征而言,则是干部型政党(以受过训练的职业政治精英为中心)和群众型政党(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为中心)的结合。
思想史家敏锐地指出,“主义”与“组织”是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两个核心元素。观念上寻找一种“主义”,实践中寻找一个“组织”,可以说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然而,并非所有的“主义”都能引领时代潮流,更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只有将“主义”与“组织”有机结合起来,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方能成就近代知识精英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理想。如所周知,这种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