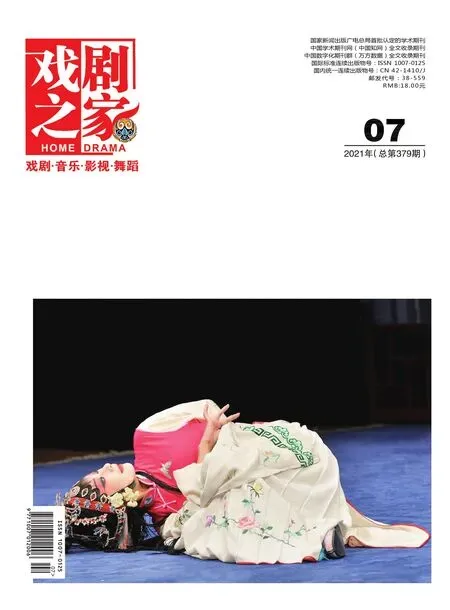丝路题材纪录片中河西走廊的区域形象研究
2021-11-14李敏,张茜
李 敏,张 茜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纵观历史长河,河西走廊一直是我国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商贾必行之路。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自身的非凡价值,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纽带。纪录片中的河西走廊形象有军事重地、商贸要道以及宗教文化汇聚的圣地等。纪录片在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显示出了新的价值和作用,成了民族价值观的重要载体。[1]摄影机视野下的《河西走廊》(2015年)记录了初通时使臣的身影,记录了繁荣时的贸易往来,以及河西走廊沉寂时的平淡样貌。在纪录片《丝路大遗址》(2017年)中,在摄影机的视角下和数字化的还原中,我们欣赏到了丝路遗址的历史样貌。在《河西走廊》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军事、商业、宗教文化相融相交的繁荣场景,在情景再现中更加直观地看到了河西走廊的人文物象。1980年播出的由日本放送局NHK及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联合制作的《丝绸之路》,记录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域遗址的历史和文化。自该片播出后,丝路题材的纪录片便大量涌入观众的视野中,各节点城市也在纪录片视野下再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面貌。
一、初具规模
这条通道的开启要追溯到张骞出使西域,他的出使对于打通河西走廊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张骞的西域之行可以看出汉武帝对于西域的向往之情,这条绵延在黄河以西的天然窄长通道在汉武帝拓展中国版图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军事意义上说,河西走廊是汉武帝进入西域完成中国版图设计的唯一通道;从商业意义上说,河西走廊是西域以及中原商贾来往贸易的唯一方式,也是中原与西域互通有无的天然通道。张骞出使归来对西域的一番描绘,使汉武帝想要打通这条通道的欲望成为了决心。如《探宝者·丝绸之路》(2012年)纪录片记录了探险家斯文·赫定跨越中亚边疆地带,只为寻找丝路城市。他不但成功开启了通往东方的探险之路,亦将中亚与丝绸之路重新绘入了世界地图。
在《丝路上的古城》(2019年)纪录片中也呈现了张骞出使西域以及霍去病率兵打通河西走廊的相关影像资料,在此之前河西走廊一直处于未知地理状态,大大地阻碍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纪录片《河西走廊》“使臣”与“通道”两集中,以大量情景再现的拍摄方式,高度还原了张骞出使西域以及霍去病率兵出击匈奴的场景。这两集纪录片从内容上来看可以看作连续的关系,“使臣”出使西域阻碍重重,而后坚定了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的决心,遂有骠骑将军攻入走廊之景。该纪录片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更直观地向观众展示了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过程以及意义。张骞出使归来不仅带回了大量的中国地理知识(《河西走廊》解说词:河西走廊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还打通了东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要道,中原的商业、文化等通过河西走廊开始向西域各国传播。
作为纪录片“情景再现”最常用的手法之一,人物扮演、剧情再现在纪录片《河西走廊》中被大量使用,共10集的正片中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人物引领历史故事的发展。[2]该纪录片再现了从汉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走廊”的繁荣、衰落与复兴,编年体史诗的形式以及叙事模式也暗示了河西走廊对于征服西域的战略意义。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使观众身临其境进入历史情境中,还能将逝去的历史再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该纪录片还让观众们看到了河西走廊初成规模的前因后果,无论是在军事安全方面还是在商业、文化交流方面,河西走廊的作用既是屏障也是纽带。纪录片《敦煌·探险者来了》中的镜头内容以史实为据,情景再现了斯坦因等人对河西走廊的“探索”,探险者们的到来也揭开了河西走廊神秘的面纱。初具规模的河西走廊积极融合来自各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以崭新的面貌欢迎来往的使臣、商贾,丝路上的驼铃自此开始响起。
二、繁荣盛景
在古今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可以看作是一条不可割舍的纽带。在商业往来中,盛唐时期是丝路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此时期,河西走廊上的商贸往来也是最为频繁的。从宗教文化方面来看,河西走廊也是东西宗教传法的唯一通道。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东段咽喉要道,西域佛教艺术在此与中原文化融合形成特有的“河西模式”。五凉后期,河西走廊上的佛教完成向中国南方和北方地区的转移。河西走廊上的天梯山、莫高山等石窟却为河西走廊以东石窟的开凿提供了范本。[3]在《河西走廊·造像》便记录了昙曜在天梯山建造的第一座佛像石窟。纪录片《鸠摩罗什》也曾记录高僧鸠摩罗什在后秦时期就已经受到多国君王的青睐,该纪录片同样以情景再现的拍摄手法记录了鸠摩罗什在后凉建国初年到达凉州,传扬佛法达十七年后入长安译经论传的故事。
《河西走廊》纪录片以时间为主线梳理并还原了汉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河西走廊的发展状况,又以情景再现的拍摄手法详细再现了河西走廊初通与繁荣的场面。从公元前138年的与匈奴之战、张骞通西域到儒家文化扎下根脉反哺中原;从魏晋时期佛教文化开启中国化的历程到隋唐时期敦煌艺术的辉煌和国际化的贸易中心;再从元明清的没落到新中国的资源基地和建设蓝图的关键一环。[4]《河西走廊》的镜头再现了往日的河西盛景,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四郡在盛唐时期都是见证河西走廊繁荣的都郡。纪录片《河西走廊·丝路》从军事、商业以及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立体介绍了隋唐时期河西走廊的繁荣景象,裴矩赴张掖疏通东西两方商贸往来也为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河西走廊·敦煌》中介绍了盛唐是丝路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敦煌艺术最辉煌的年代。长安艺术被工匠们带到敦煌再一次绽放光彩,本集以敦煌220号石窟为主进行讲述,敦煌石窟的壁画见证了丝路的繁华,同时也是大唐盛世的缩影。敦煌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最后一站,被汉武帝纳入河西四郡,宗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在这个地方大放异彩。镜头记录了敦煌莫高窟现下的壁画艺术的同时,加入了情景再现的表现手法,使本集纪录片形成古今对比,同时将更详细的文字以及画面符号内容传达给了受众。
纪录片《河西走廊》在重现历史繁荣景象的同时,以城市空间为背景,运用对比的手法展现了如今河西四郡的发展面貌。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展现,经济支柱命脉的发展,城市标志建立来塑造城市形象以及文化精神。[5]河西走廊的汉唐荣光不仅表现在纪录片的镜头中,更表现在河西四郡古城中。以敦煌莫高窟为例,盛唐时期建造的彩塑壁画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而莫高窟的作品中也记载了河西走廊商业贸易、使者往来的和谐景象。除此之外,《丝路大遗址·商贸繁盛》纪录片以数字化技术充分还原了河西走廊商业繁荣的盛景。摄影机无法还原的历史样貌,在数字化还原技术下使丝路上的商业贸易景象重现在观众视野中。此时,河西走廊更多地表现为丝绸之路上天然通道,往来使者驻足交流,商品交易频繁,俨然成为东西商业、宗教文化等交融发展的场所。
三、归于沉寂
从初具规模到繁荣盛景,时间的流逝使得河西走廊不再是往日景象,似乎是时代的和平将它推上了沉寂之路。河西走廊不再是兵家必争之地,也不再是商贾必经之道,如今的河西走廊似乎变得格外“安静”,没有了往日的“聒噪”。纪录片视野下的河西走廊多呈现开辟时的不易以及商贸、文化的繁荣发展,诠释沉寂时期的河西走廊的纪录片与其他时期相比更显稀少。
1980年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系列纪录片记录了八十年代的河西走廊样貌,摄制组重走河西走廊一千公里,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该纪录片主要拍摄沿线各个民族、不同地域的居民生活环境,以客观视角拍摄加解说的方式展现了河西的人文物象,观众能够从该纪录片中感受到浓厚的民族淳朴风情。该纪录片的价值不仅在于摄影机记录了河西走廊沿线一千公里的民族生活面貌,还在于它是记录八十年代河西走廊样貌的珍贵影像资料,片中记录了武威、张掖、嘉峪关等河西重镇的城市样貌。与今天的高楼大厦相比,八十年代的建筑有着独特的韵味,与过去的繁荣盛景相比,这里少了商贸来往的气息,多了一份寂寥。
如今掀起了重走“丝绸之路”的热潮,更多的丝路景象被数字化记录、被摄影机记录,保存为图片、影像等形式。“一带一路”政策的开展使得陆上丝绸之路重新被唤起,河西走廊仍是丝绸之路上的核心通道。
四、结语
纪录片视野下的河西走廊有初次开辟时的稚气,也有繁荣盛世的景象,镜头记录了河西走廊多变的一面,不同时期的它拥有不同的形象。而它并不拘泥于交易场所,无论是军事重地,还是商贸要道,河西走廊都是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通道。摄影机下的河西走廊完整地展现了它历代以来的成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