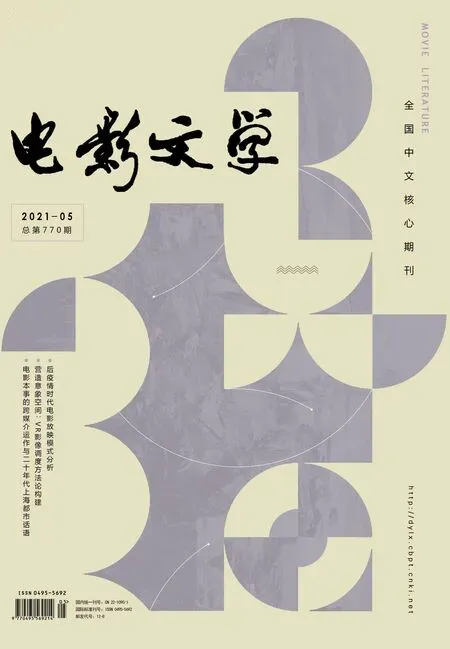《花木兰》的他者化想象和东方主义困境
2021-11-14刘泽溪邹韵婕LiuZeXiZouYunJie
刘泽溪 邹韵婕/Liu Ze Xi Zou Yun Jie
2020年9月11日,由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真人版剧情电影《花木兰》在中国内地上映,由美籍华裔演员刘亦菲饰演的“花木兰”、甄子丹饰演的汉军指挥官董将军、新加坡籍华裔演员李连杰饰演的皇帝、巩俐饰演的女巫,曾在电影上映前期被多次宣传,但是始终未呈现出庐山真面目。随着影片在全球上映,关于《花木兰》的文化争议也随之爆发。
一、西方主义视角下东方主义与东方化想象
对好莱坞、迪士尼电影中中国人形象呈现的研究早已有之。探究美国电影之旅,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电影历史几乎为好莱坞、迪士尼、FOX等影视制作公司垄断,透过影像文本追溯美国镜头下的华人形象与中国印象,并不只是《英雄》《神话》呈现的古风意韵、江湖快意恩仇,也有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还有西方中心主义之下的东方化想象。
(一)东方主义的历史渊源
“东方主义”由霍斯沃特在1769年首次提出,用来指称西方人对东方文化进行探索研究的各类学科。不同于传统学科以“-logy”结尾,东方学(Orientalism)以“-lism”结尾,使其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这意味着,东方学除了包括学科含义外,还包括了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
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将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或者将东方作为一种话语权力和思维方式,都表明了西方文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书写、研究与控制,即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流露的傲慢与偏见,其本质目的在于设置西方文明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和思想界限。
东方主义的兴起源于西方中心主义,但是东方主义思维下的文化产物却需要东方人的参与才能够获得存在合法性。《花木兰》中清一色的东方面孔以及无处不在的东方文化元素,是影片吸引中国受众走进电影院的重要原因。但影视文本呈现的东方形象和人物特征,依然隐含着浓烈的东方主义。即便是高度国际化的迪士尼,其文本生产也没有完全摆脱西方人对东方的类型化刻板印象,在真人版电影中,东方化的东方形式和内容依然存在。将文化间的差异构建为文化间区分的边界,并通过文本书写呈现出对异域文化的控制权。
(二)西方滤镜:他者想象的权力支配与自我满足
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者。美国影视制作公司对东方形象的认知,在无形中强调了一种权利支配关系,正因为这种认知框架,导致了影视文本中的异域社会沦为了被制作被驯化的想象存在。当然,电影文本中的东方也并非谎言或者虚构,也不是西方对东方的虚构和想象,而是一套基于西方自身需求和东方文化符号体系建构出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种文本渲染是在西方价值内核的基础上对东方文化符号进行机械化处理,在他者化的想象认知中构筑起的东方美学图示。
从《艺伎回忆录》到《战争与和平》,再到迪士尼的《花木兰》,由美国影视公司制作的外国经典,其艺术呈现有着鲜明的“西方滤镜”。从历史架构、背景设置到场景布局、服装道具,美国用一种自我构建的、服务于自身需求的文化印象取代已经发生或正在进行的文化经验。由于用文化置换历史,所以这些文本投射出的东方形象已经没有真正的历史性可言,它们的再现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再生产。
沃尔特·李普曼曾指出,刻板印象的形成有赖两个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承载刻板印象的象征符号(symbols),二是将这些象征符号植入人的观念的权威力量。
中国在西方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的截然相反的形象,伴随着西方社会的演化两种形象交互起落,从《中国佬的来信》到马可·波罗《东方游记》,从“黄祸论”到“赤色中国”,从《西行漫记》到“社会主义乌托邦”,从“中国威胁论”到“东方中心主义”,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长期处于一种焦灼矛盾的状态。
在西方构建的东方世界中,从国土疆域到人口分布,从历史根基到文化影响力,中国长期作为东方世界的代表,并且以神秘莫测却又相对固定的形象呈现在西方的东方化想象中。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存在意义并非地理分布上的明确主体,更倾向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虚构空间。在西方大众媒介中,中国永远不会是先于话语存在的政治实体,而是重视萨义德所言之的“想象中的地理概念”,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对异域文明的他者化想象产物。
二、《花木兰》的文本特征与叙事策略
在《花木兰》电影上映之前,西方对东方的他者化想象已经让欧美和亚洲之间意义差异固定化,在东西方的思维隔阂下,亚洲沦为落后、野蛮的代名词,真实的东方只能被隔离在想象的屏障之后,而对东方和东方人的想象、表述则成为西方的特权,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在东方化想象的认知框架下,一个复杂的东方在西方社会大众媒介上被呈现出来,大学东方学系的学术著作、《傅满洲》中的阴险傅博士、威廉二世赠予尼古拉二世的《黄祸图》,还有二战陆军司令部设计的反日海报,都是被西方东方化后的建构产物。
(一)话语:东方主义的古代中国叙事
《花木兰》真人版的制片方是迪士尼影视公司,尽管影片在全球范围上映,但在展示东方相异性时,参演演员、导演编剧以及主体观众基本是面对美国本土,从剧本撰写到镜头拍摄,都是以西方视角构建。作为一部西方人拍摄给全球受众观看的、呈现异域文化的电影,一些细节上的偏差并不会阻碍大部分观众的观看,正如詹姆斯·博拉迪内里所指出:大多数西方人并不知道细节上的差别,即便“花木兰”的人物源于中国古代诗歌集,但电影《花木兰》构建的故事以及呈现的人物形象,依然是基于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解读。人类社会的文化符号是不断被解构和建构的,任何相对固定的文化形态都会处于动态的演化,就古代东方主题的话语叙事中,迪士尼构建的《花木兰》也是经主观构建的影视形象。
电影《花木兰》的原型,关于花木兰的史料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陈《古今乐录》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辞》,根据历史学家考证,诗歌的故事发生于公元5世纪前中期,即南北朝时期北魏破柔然之战。
《木兰辞》记载: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历史背景则是“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家庭困境则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家庭成员结构意味着“从此替爷征”成为木兰尽孝的唯一途径。基于此背景,木兰选择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戎马生涯。随着《木兰辞》的流传唱诵,“花木兰”也以“忠孝节义的巾帼英雄”形象固定于文学、诗歌、戏剧、电影等历史文本中。
就故事整体而言,迪士尼塑造的花木兰有意淡化花木兰作为巾帼英雄的忠孝节义,而是借助花木兰的东方面孔和东方文化外壳凸显“女权主义”价值观。无论是离家从军还是战场搏杀,花木兰虽保家卫国、策勋饮至,但是剧情主线依然是花木兰的自我觉醒和命运抗争。尤其是和柔然大军搏杀过程中,花木兰在仙娘和凤凰的指引下触发雪崩、拯救魏军,也是典型的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叙事。
(二)文本架构:二元对立话语结构
将世界进行划分,并采用比较的方式描述世界,是西方哲学的悠久传统。古希腊与古罗马在和古代波斯的接触碰撞中,就构建了作为对立面的“东方”形象。《花木兰》延续了西方中心思想一贯的二元对立框架,尽管整篇故事都发生于东方,但在东方世界内部,依然存在的利益冲突主体。就故事背景来说,北魏王朝与柔然汗国长期的对抗、北魏男权思想与女巫身份的对立、柔然可汗与女巫的对立、木兰的婚姻自由与家族荣誉间的对立。
故事的宏观背景是北魏王朝与柔然汗国的长期积累的矛盾,从先秦时期到明朝中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长期持续,民族间的争斗、仇恨的累积,引发了公元5世纪前中期的“北魏破柔然之战”。北魏与柔然之间的二元对立,也是通篇故事剧情的主要脉络。
《花木兰》中人物命运的沉浮也是在各种独立中不断挣扎撕裂。作为家族长女,成年后的花木兰要履行婚约以完成家族使命,但是天性渴望自由的花木兰,拒绝成为“男性附庸”,为了反抗家庭规训,木兰女扮男装踏上从军之路。这种剧情设置淡化了传统文本中的“孝子典范”。参军的内核由“尽孝”转向了“女性独立”。
花木兰的征途也充斥着各种二元对立,以女子身份踏入军营,必须面对性别之间的二元对立,从晨起着装到夜间洗漱,从校场训练到营帐夜谈,木兰必须时刻警惕身份对立带来的不便。在北魏与柔然两军搏杀的场景中,木兰在追击柔然骑兵分队后与仙娘相遇,身世的揭露令木兰陷入身份定位的对立中,在认清自我返回战场并拯救全军后,木兰卸下重重伪装向队友坦白实情,标志着木兰以女子身份立于世间。
(三)符号:他者化想象的文化符号错位
《花木兰》中的场景布置与历史史实的文化错位,也是引起中国受众不满的重要原因。在东方学兴起之前,古希腊的哲学圣贤能够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审视异域文化,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既有对波斯专制制度的谴责,也有对古埃及文明文化的赞叹,并且能以他者为镜,审视希腊城邦制度的优劣。
随着时代变迁,西方人否定与贬低东方民族的思想也开始萌芽,但对于古代中国,欧洲上流社会长期存在着美好的遐想,渴望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经济与文化的突飞猛进,俯视东方文明的东方主义形成,“东方”“亚细亚”“中国”等地理名词成为丑陋、罪恶、愚昧和贫穷的代名词,东方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介话语中定格,形成了固态化叙事文本。
根据《木兰辞》“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的记载,木兰应居住于黄河流域,也就是中国北方,但是《花木兰》电影开篇的空镜头,却是典型的中国云贵地区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随着镜头前行呈现出花木兰家族的住宅——圆形土楼。《木兰辞》收于南朝陈《古今乐录》,故事发生时间在公元5世纪。但最早关于“土楼”的记载,也要追溯至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重修虔台志》载“福建永安县贼邓惠铨、邓兴祖、谢大髻……占据大、小淘水陆要道,筑二土楼,凿池竖栅自固”。一千一百多年的时代间隔、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空间阻隔令稍有中国地理常识的受众心生违和感。
高坐于龙椅上的帝王,留着浓密的八字须。对由新加坡籍华裔男演员李连杰饰演的皇帝,多以严肃威严的冷酷帝王形象呈现于镜头前,除了精致奢华的龙袍和华丽精美的盔甲,最显著的外部标志便是浓密的八字形胡须。八字胡须作为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符号,在《傅满洲》《陈查理》以及《加勒比海盗》等主流影视作品中皆有出现。
在18世纪,“八字胡须”是流行于欧洲的代表性“中国元素”,英国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绘制的,以清王朝统治阶层为主题的漫画,多次出现“八字胡须”。其作品《在北京皇宫接待大使和他的随从》,将清朝乾隆皇帝描绘为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拙态,配以宝塔帽、八字胡须、长烟管等符号,尽管大量文字图画史料可以证明,詹姆斯·吉尔雷笔下的清宫廷形象与历史史实大相径庭,但是詹姆斯·吉尔雷虚构的漫画以及漫画中的帝王形象被奇妙地历史化,甚至遍布整个欧洲,参与塑造19世纪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由巩俐饰演的女巫仙娘,从人物服饰、能力设定到出身背景,都呈现出浓烈的西方女巫元素。尽管先秦时期就有“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的记载,但东方语境下的“巫”,通常作为沟通人和天地鬼神的媒介,即“巫祝”,这一类人群通过特定仪式传达鬼神的意志,巫祝本身并不一定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仙娘穿戴黑衣的特征,海鸥瞬间变飞禽的技能,都与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巫祝”大相径庭,这些角色设定与技能特征更多源于西方的witch文化。
此外,对木兰的形象塑造也一反常态。花木兰虽替父从军,但《木兰辞》开篇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证明,花木兰的日常生活状态遵循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在电影中,饶雪晶饰演的童年花木兰却成为家族中的“混世魔童”,飞檐走壁、横冲直撞,致使楼院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这种形象建构延续了美国小妞电影的反传统叙事,赋予了花木兰顽皮好动却又热情勇敢的人物性格,与家族中恭良婉顺、恬静柔美的妹妹形成鲜明对比,为随后抗婚离家的剧情埋下伏笔。
木兰在接受军事训练过程中,甄子丹饰演的指挥官提到的“chi”,也令中国受众感到陌生和莫名其妙。关于“chi”的东方想象在《功夫熊猫》《尚气》均有出现,这种神秘的力量通常被认为来自中国古老的“气功”,即一种由身体迸发出的精神力量。但即便是东方文化语境中,所谓的“气”也只是一种想象物。
正是这些无所不在的想象权力,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框定在精神隔绝之中,无法超越,也难以超越。而在这话语框架和刻板印象背后,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东方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
三、西方异域叙事的东方主义困境
从《傅满洲》中的“满大人”到《加勒比海盗》中的“清夫人”“啸风”,西方文学作品或电影作品中呈现出的华人形象始终难以摆脱“西方文化中心”视野的审视与傲慢,文本中涉及东方文化和人物形象呈现,大多基于东方学的阐释方式,尽管表现了东方外壳,却彰显了西方意志。
(一)影像背后的意识形态博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国家掀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冲击了西方主义的霸权统治,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东西方权力交替中过时,为了弥合第三世界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崛起引发的文化裂缝,缓解竞争的焦虑,以异域文化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创作不断参与到文化支配地位的修复中,对西方文明之外的异域文明进行想象化建构。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东方社会,往往是经西方媒介话语过滤过的社会。对东方世界的他者化想象和西方中心视角下的东方化解读,共同构筑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东方形象。后殖民主义学者赛义德延续了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剖析并批判了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权力的“东方想象”,指出“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所谓的“东方”只是东方学对未知领域的妖魔化想象。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跨文化传播日益繁荣,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也日趋频繁,在此背景下,西方欧美国家的影视行业出于拓宽市场、开展文化交流等目的,大量发掘神秘的异域文化,以异域文化为故事背景的电影题材也日益盛行,由美国影视公司制作的《艺伎回忆录》《战争与和平》《罗马帝国》《摘金奇缘》《阿拉丁》,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于异域风情的讲述。
多元文明主体之间相互凝视与形象建构,是跨文化传播领域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一个文明对异域文明的媒介形象建构,关乎文明主体之间彼此了解的方式和角度,更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的人理解他者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来源。在众多大众媒介形态中,电影不仅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这种特定还被掩盖在其远高于其他媒介的娱乐性之下,这种隐性的价值传递和意识形态传播恰恰是西方维护自身文化自信所迫切需要的。
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也是一种文化艺术产品,电影文本的生产者通过场景布置、台词撰写、拍摄技巧、镜头拉伸等制作技艺,在影像文本中隐性传递创作者的意识。作为电影文本的主要创作者,导演在前期创作、中期拍摄和后期剪辑环节向观众传递“作者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观众认知、了解并记忆的故事剧情和内涵隐喻,是由电影创作者根据自身意志主观建构的虚拟世界。
(二)东方文化的西式拼凑
如果将《花木兰》所再现并传播的古代中国形象归咎于恶意丑化或者种族歧视,这种论断也是不客观的,从演员甄选到场景布置,从故事剧情到镜头画面,迪士尼影视公司竭尽全力打造出一场东方视听盛宴。
作为商业化影视公司,选择在中国市场投放的本意便是希望借助“花木兰”的人物形象和东方面孔迎合中国电影受众,进而开拓中国电影市场、兑现经济利益。无论是故事背景、场景布置、角色设定、服饰道具还是演员妆容,都是根据西方普遍观念中关于中国形象的话语操练结果。这样的叙事方式和影像文本,是迪士尼创作者根据多元受众群体的审美需求而做出的贴合,最终演变为西方凝视下的、想象中的“花木兰”。
从《傅满洲》到《摘金奇缘》,从《尚气》到《花木兰》,欧美影视企业一直积极致力于东方叙事以开拓全球市场,但是由美国影视公司制作的文本,虽然在国内大获成功,却无法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其中,《尚气》中的梁朝伟饰演的“满大人”更在中国引发种族歧视争议,尽管在《傅满洲的奸计》之后,欧美国家再也没有出现过极端丑化中国人的影视作品。无论是好莱坞还是迪士尼对异域文化的翻拍,都体现出了文化本质主义的傲慢。
在美国主流文化中,东方认知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有迹可寻的认知观念中,无论是拉马丁笔下的东方女郎,还是福楼拜《旅行漫记》中的妖艳舞女,都是经过历史演绎形成于西方社会文化认知的建构物,在建构的同时,媒介文本内容的生产者也融入了主观表述与想象,所谓的“东方世界”变成了一块斑驳的画布,等待着西方人的描绘和渲染。这种渲染从电影文化符号的拼凑上便能看出端倪,《花木兰》的故事发生于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但是在故事中却出现了明清时期的圆顶土楼和大红灯笼。史料记载花木兰居于黄河流域,但电影开篇却是云贵梯田和闽南建筑……迪士尼对古代中国产生的认识论基础首先是历史主义。普遍化的历史主义,是将文明主体或者文化主体置于时空的天平上进行考量,文化主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被置于循序渐进的时间系列中,成为不同节点。
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下,欧洲与美洲则是现代社会线性进步的起点,欧美模式更是当代社会的典范与缩影,在这种观念下,欧洲与美洲的文明成果成为孕育理性的繁衍之夜,东方的现实无法改变地蜕变成一种范式的风化。
为强化这种文化身份的优越感,西方世界以自身立场和文化需要构建了对东方的认知体系,即“东方主义”。这种“东方主义”既是一种想象依托,也是话语修辞,为西方语境中的认知提供了知识框架。尽管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文本建构呈现的是东方元素,但其建构模式却是西方视角,充斥着西方对东方的臆想与主观发挥,其存在目的是为迎合西方视域下的“东方化想象”。
这种被剥夺主体特性的呈现、认知随着西方文化的演化,渗透至各种文化文本中。文化的优越与先进不仅需要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维持,还需要强大的软实力和意识形态维护。在当今世界中,蕴含丰富文化符号的“东方”便成为西方文化优越感的投射对象。
在全球化语境中,影视作品的生产需要考虑多元文化受众冲突、兼并、融汇的复杂状态,这也令电影文本的创造者和鉴赏者双双陷入文化焦虑的境地。如何进行跨文化表述;在历史史料、艺术创作和个体经验之间应当如何取舍;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相同文化符号的不同理解应当如何中和……这些都是异域文化主题电影应当面对的问题。透过《花木兰》的影像呈现和形象建构,会发现基于西方中心视角的他者化想象已经深刻嵌入美国主流文化中,甚至泛化为文化文本中的思维定式和话语方式。
在西方眼中,东方是被观看、被研究、被书写、被表述的对象,活跃于好莱坞、迪士尼影视作品的中国人形象并没有权利或者能力表述自我,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中国人的形象建构,都是被表述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