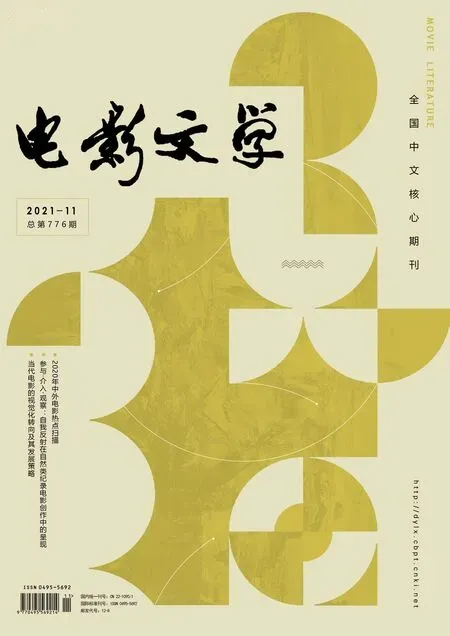“女人的哭泣”:刘冰鉴电影的性别隐喻和文化反思
2021-11-14朱柏成
朱柏成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目前在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网等国内大型文献服务平台搜索关键词“《哭泣的女人》”“《男男女女》”“《砚床》”“刘冰鉴”,发现当下的学者多把关注目光聚焦在其中的单一文本读解上,缺少深入的关联对比研究。此外,针对第六代导演刘冰鉴的研究也尚在少数,且主要集中在访谈录和创作风格两方面。
故本文力图深度解读刘冰鉴执导的《哭泣的女人》《砚床》《男男女女》中蕴含时代记忆的空间建构与性别隐喻,并以《找到你》《亲爱的》《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嘉年华》《狗十三》等近些年来女性题材电影为观察视点,回望刘冰鉴导演所塑造的女性角色,窥视电影银幕中的现代中国女性思想与处境的变迁图史。
一、底层场域:集体记忆的真实美学
《哭泣的女人》在美学层面上,延续了作者之前在《砚床》《男男女女》作品中所贯彻的纪实风格,正如导演自己所言:“我几乎是和我当下的所见所感来同步做我的电影。”刘冰鉴攫取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代记忆与人生感悟,描绘出彼时女人悲惨境遇的真实图景,其影像中的长镜头、大景别以及手持镜头所具有的纪实美学风格更来自导演对世界的观念转化成视觉表达的伟大尝试。
(一)长镜头:“钉在墙上的苍蝇”
正如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对长镜头的肯定:“长镜头的呈现能使观众保持在一个客观的地位,去观察持续性的空间原貌,以最接近现实世界的角度观察他们眼前的影像。”在《哭泣的女人》中,导演尊重时空的连贯性,多次采用了长达30秒以上的长镜头,来减少摄影机和创作者对事件的干预,营造了一种非强制性、开放型的完整式观影模式。如影片开头的第一幕画面就长达45秒:王桂香于清晨起床,准备出门卖碟赚钱,而同在枕边的丈夫不仅抱怨输了钱,而且仍昏睡在床上;王桂香和男友李友敏第一次去他人家中哭丧的片段,更是以一个长达两分钟的全景镜头予以呈现。这里的摄影机更像“钉在墙上的苍蝇”,冷静且极为客观地展现了一种底层群体的生活图景,给予受众充分思考的余地。
不仅是《哭泣的女人》,《砚床》《男男女女》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长镜头,如《砚床》中吴家少奶奶和阿根道别的场景,《男男女女》中青姐和阿梦同居的片段。这些长镜头的呈现符合摄影机复制生活真实的照相本性,再现导演记忆中女性的生活环境和角色特征,并展现被摄对象行动的全过程,给予观众一种正在处于某个特定环境中的真实质感。
(二)大景别:幕外空间的思考
景别作为完成电影、电视画面空间塑造的重要形式,也是导演美学风格建构的重要元素之一。刘冰鉴在其创作生涯中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摄影风格,《哭泣的女人》也不例外。该片中充斥着大量的远景和全景镜头,如王桂香为他人哭丧、王桂香嗓子难受卧床休息等等片段。
这些大景别表现开阔的空间格局和场景设计,配合长镜头,使观众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对画面的丰富信息做出反应,继而从画面中获得现象学派胡塞尔所称之的“心象”,即一种重现的记忆活动。相比于快节奏的特写和近景镜头,大景别的“心象”能够让受众从长时间且信息丰富的画面中联想到与自身经历相关的人生记忆,进而生成崭新的意念化产物。比如,有曾经参加过丧礼的观众,长时间地凝视王桂香为他人哭丧的场景时,可能会陷入曾经参加过丧礼的回忆之中,继而会结合影像情境,生成关于“死亡”“生存”等意象的新认知。
再者,大景别能够给予演员塑造角色的更多权力,交代丰富的环境信息,建构其空间关系以及影像美学的总体基调。在《哭泣的女人》中,王桂香的生活环境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原先王桂香和丈夫陈庚生活在繁华的北京都市中,但自身衣着以及居住环境的杂乱与都市景观格格不入,并不断受到城市人的“阻击”。然而,王桂香回归到农村后,衣着打扮仍受着老乡们的讥笑,所谓的“根”也不再包容和无私,而是裹挟了“羡慕”“计较”“鄙夷”等种种狭隘的思绪。刘冰鉴借助大景别,从多重角度交代人物关系和影像信息,建构出一种城乡对立的文化场域。
(三)手持镜头:浸入式的情感体验
论对手持摄影的偏爱,不得不提到第六代导演的娄烨,在他的《春风沉醉的夜晚》《浮城谜事》《推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作品中,无不都采用了“解放的摄影机”。在这种镜头运动中,画面内部元素具有不可预料的特征,晃动的画面充满着呼吸感,观众仿佛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介入剧情叙述情境之中。
同为第六代导演的刘冰鉴,在《男男女女》《哭泣的女人》中也采用了不稳定的手持镜头来强化故事的纪实质感和情感张力。《男男女女》中,小博被迫离开青姐家,到冲冲家暂住,此时画面便是由手持镜头捕捉了小博的背影,表现出一种不甘又无奈的情绪;《哭泣的女人》之中,王桂香和李友敏在网吧门前争吵时,导演同样利用手持摄影机的长镜头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两人复杂的心境:一面是李友敏想劝阻王桂香放弃解救陈庚的私欲,一面是王桂香想坚守“妇道”的执念,由此受众能够清晰地感受两个人物的情绪碰撞以及内心挣扎。
刘冰鉴影像作品中所采用的晃动镜头虽然会使得画面失去了一定的信息完整性,但它带来的情感张力却是其他镜头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当受众在观看手持镜头捕捉的女性形象时,摇晃不定的画面和真实质感的声音同时占据观众的视听感觉器官,两者共同作用,受众在心理上能够更快地接受镜头所提供的信息,也更容易被女性人物流露的细腻心情与复杂思绪所渗透。
二、物语隐喻:彼时女性的悲惨图景
处于 20 世纪末期和 21 世纪初期的中国女性远没有西方女性那样幸运,受到思想解放浪潮的洗礼,彼时的她们仍深受着中国封建性别文化的影响,背负着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和物质负担。刘冰鉴尤为关注彼时底层女性的现实遭际,在《砚床》《男男女女》《哭泣的女人》这“三部曲”中,通过书写多重残酷物语展现她们的生存逻辑、精神世界、感情生活以及生命体验。
(一)性欲错乱:以“身”卫“纲”
性欲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但中国的性动机受限于传统伦理文化的束缚,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尤其是女性的性欲行为。然而,在刘冰鉴的作品中,女性的性欲行为表现得极为混乱,但究其本质仍是为了守护封建文化的“夫为妻纲”。《砚床》中的少奶奶和少爷在多次“房事”后无果,在父母的“生子接代”传统观念施压之下,少爷竟劝妻子出卖身体与仆人结合,来获得“种子”;《男男女女》里的青姐发觉自己喜欢上了小博后,迫于丈夫的存在不得不打消追求真爱的想法;《哭泣的女人》中的王桂香在丈夫被送进牢中后,竟愿与监狱长肉欲结合来寻求拯救丈夫的机会。从这些女性肉体或精神的出走意义而言,“妇女只有按照宗法制度和世俗男性所期待的样式塑造自己,才能适应社会和家庭的规范”,男性对于物欲、情欲、思欲的渴望程度,往往会导致女性产生错误的性欲观念或行为。
如同朱迪斯·巴特勒所持有的观点:性别,“它具有意图同时也是操演性质的,而操演意味着戏剧化地因应历史情境的改变所做的意义建构”。在刘冰鉴的电影作品中,女性性欲的背后往往有着男性身影,他们的背叛、救赎以及欲求改变着女人们的未来行为与内在信念,也正是导演对于两性肉体的铭刻考量了彼时男性权力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地位,借以引发大众对传统性别文化的沉思。
(二)人格面具:空洞的情感容器
刘冰鉴影片中所塑造的女性人物深受家庭道德、社会舆论、文化思想等多种文化观念的压迫,她们被迫戴上“人格面具”,“用来平衡无意识领域的欲望与外界现实之间的关系”。《砚床》中的吴家少奶奶与男仆人交合后,对他产生了莫名的情愫,然后碍于丈夫的存在,不得不隐藏潜在的想法;《男男女女》里的青姐和丈夫本没有了感情,但由于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仍在一起居住;《哭泣的女人》中的王桂香丈夫入狱后,使她颠沛流离,又对情人产生依赖,但出于婚姻的责任,不得不通过哭丧挣钱来保释丈夫。可以发现,这些人物的遭际都展现出彼时女性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桎梏,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抉择、观念以及心绪都受男性的牵制,时刻伪装自己的情感流露、人生追求以及多重欲望,自身仿佛一具空壳的皮囊。
《哭泣的女人》中提及的哭丧文化,是中国落后地区长久延存的一种地域风俗,本质是一种后辈追悼先辈的仪式,借以表达对逝者的内心不舍和崇高敬意。而在该片中,这种数千年沿袭的传统却成为一种另类的表演和生意,血脉之间真情荡然无存。王桂香作为哭丧人,在不同人的丧礼上用戏曲式的舞蹈表演来替他人祭奠前人,且从未哭泣,而小女孩津津一直都在哭泣。恰恰她跟丈夫、跟情人的关系完全崩溃,对生活的追求陷入绝望时,却流下了眼泪。可见,她之前哭丧时所戴的“人格面具”是受他人所迫,虽然具有现实的外在表征,但内在情感却是空洞的。当“虚伪的面具”被现实因素所碾碎时,挂着眼泪的脸庞完整且真实地暴露无遗。另外,极具思辨性的地方是,影片中逝世的人都是男人,唯独一位年迈的女性,其三个儿子在生前格外不孝顺,死后还道貌岸然地宣称“要给母亲办全城最风光的葬礼”,彼时男性面具之下的“丑陋人格”被导演揭露了出来。
(三)多重规训:男权社会的“失语者”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性理应遵守妇道,在家服侍男性,照顾孩子和父母,没有权力去寻求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地位。这一思想是在数千年的男性话语权力的多重规训下所生成的,其手段及过程在刘冰鉴的电影中也被多次描写。
刘冰鉴的电影作品之中,男性的话语权的获得及阐释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段:言说与暴力。在《哭泣的女人》里,男性角色多是公职机关人员,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和维权者,而作为底层女性的王桂香多次受到“规矩”的惩罚。比如,没收了王桂香碟片的男城管,没有主动充公,而是欣喜地准备“分赃”;王桂香试图把丈夫赎出去,监狱长先是暗示五千块钱不够,后又与王桂香行了“苟且之事”;在丈夫陈庚被击毙后,男警员面无表情地握着王桂香的手胁迫她按手印,不给她任何说话的余地。再者,影片中王桂香在情感生活中深受男性言语的欺骗和压榨,他们极其无能和懦弱:陈庚无能还好赌,软弱没主见,进了监狱后还对前来探监的王桂香哭诉监狱生活的难熬,求她早点把自己赎出去;李友敏享受着王桂香的肉体带来的乐趣,但当妻子与她争吵时,却像孩子一样不敢吱声,不愿意对其负责。与之相反,刘冰鉴片中女性往往是社会的底层群体,与生俱来就遭受着被社会嫌弃的悲惨命运。比如,《哭泣的女人》中三岁的津津因是女孩被父母抛弃,由王桂香收养,而王桂香也没有任何亲戚,始终是孤身一人;《砚床》中少奶奶在年轻时,自身的情感需求无人重视,只是被当成一个“生育机器”,年老时,又因身体不佳,被家人与外人所嫌弃。
刘冰鉴通过描绘男性在身体、言语以及思想上对女性的“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把“丑陋的男性”塑造成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监督者、维护者和裁决者,展现出彼时女性在社会环境、家庭生活、精神世界的无奈与凄惨。
三、借鉴与思考:反观近年来女性题材电影的成长之路
纵观刘冰鉴影像作品中吴家少奶奶、王桂香、青姐等女性形象的遭际,不难发现她们的意志、思想以及行为多是由男性所决定,这也反映出处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时中国女性的弱势地位。但伴随中国的经济、教育、法律和文化快速发展,原先封建的性别思想禁锢也日渐式微。据2019年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的报告显示:相比于2005年,历届女性人大代表的数量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女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明显减少,女性是家庭户口中户主身份的比重也得到提高。此种女性赋权的现实境况在当下的电影银幕中,逐渐呈现出一种别致的景观。
近年来,《找到你》《亲爱的》《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嘉年华》等国产女性题材电影不仅沿袭了刘冰鉴犀利的现实主义写实风格,更是利用剧情结构、人物设置、视听语言等多重手段来讽刺和抨击封建的性别文化,挥舞起男女平权的思想旗帜。这些影片中女性不只限于乡村村姑、家庭主妇、务工妇女等底层群体,也涵盖现代都市生活中律师、白领、学生等高中阶层群体,她们所面临的境遇已与《红高粱》《菊豆》《哭泣的女人》等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作品中所描绘的女性命运大不相同,展现了当下不同群体女性的生命遭遇、情感生活以及思想作风。比如,《找到你》中律师李捷的离婚原因不是家庭暴力、性欲不满、移情别恋等传统女性容易面临的问题,而是没有共同语言;《七月与安生》中的李安生不再是受父权随意宰制的少女,她放浪不羁爱自由,打破传统伦理的束缚,和多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少年的你》中的魏莱虽然是女性,但凭借出身卓越以及跋扈性格,成为学校的“校霸”,肆意欺凌他人。
可见,当下国产女性题材电影凸显出中国女性在政治权力、社会地位、思想风气等多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她们拥有的一切与男性所享受的多种“特权”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依然会受到男性的欺压而质疑作为“女性”的身份价值。《找到你》中的保姆孙芳饱受丈夫施加的家暴,迫于残酷的窘迫境遇,她偷走了雇主家李捷的孩子;《亲爱的》里的李红琴是一位不能生育的农村妇女,错信丈夫的话,认为孩子是在深圳捡来的,为此与田文军、鲁晓娟两人争夺儿子;《少年的你》中陈念和董小蝶长期受到校霸们欺凌,前者误杀了魏莱,后者则自闭到跳楼自杀;《嘉年华》中的小文被男官员玷污后,不仅无人帮助她,而且社会和家庭又变相来对她施暴。这些女性的凄惨遭际无疑揭露出当下社会中的一种残酷现实境况:“社会留给女性的选择,还是相对少”,“对女性的要求,还是相对多”,“中国女性生活幸福度很低”。
综上所述,相比于刘冰鉴作品中的女性命运,近年来的女性题材的电影仍裹挟着明确的性别立场,呈现了当下社会幽暗角落中女性的悲惨窘状。值得指出的是,这类影片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凸显出现代女性的开放思想和主权愿望——寻找在两性对话中的平等地位。但纵观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市场可以发现,坚持现实主义阵地的女性电影在数量上还是寥若晨星,规模及投入仍无法与悬疑片、喜剧片、动作片等泛娱乐化的类型电影相当。
结 语
刘冰鉴导演用纪实质感的镜头语言倾诉出带有时代记忆和家乡意蕴的女性故事,把底层女人的“哭泣”谱写成一种讽刺男权的“寓言故事”,隐喻着女性精神家园的颓废与凋零,以及女人对男性特权的憧憬。从历史纵向的维度,审视当下的女性题材电影中的个体命运,不难发现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镜头下女性形象已悄然位移,现代女性对物质生活、情感品质以及人生理想等多方面需求已经透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在社会权力、财富收益、家庭地位、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女性仍与男性有着不小的差距,这也意味着谋求性别平权的“呐喊声”正亟待借助更多具有现实批判性的女性题材电影之力来予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