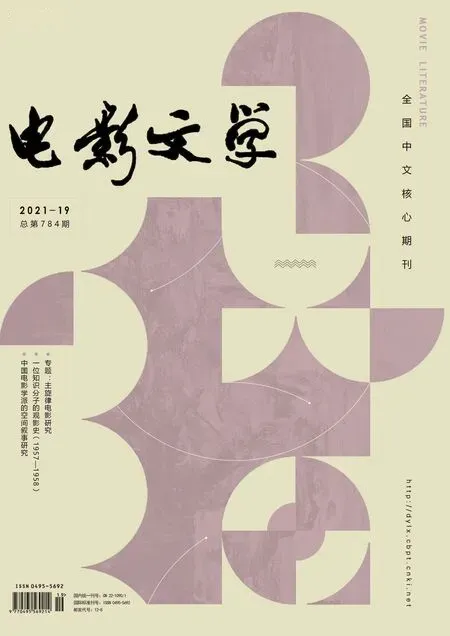租界文化语境下中国早期电影的生态图景与风貌格调
2021-11-14王侠
王 侠
(1.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0065;2.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北京 100029)
中国早期电影在上海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因此研究这时期的中国电影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而彼时的上海又是因租界而兴起的城市。因租界的开辟,上海从一个小县城一跃成为号称“东方巴黎”“东方纽约”的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电影繁荣兴盛发展的土壤。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诞生,但形成“生产—发行—放映”的完整电影工业体系,创建独特的中国民族电影业却是在上海完成的。因此上海电影也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代表。以往的电影史多从海派文化、都市文化角度诠释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状况,却忽略了租界文化之于上海的意义以及对早期电影的生发意义。“租界语境下的上海文化,很难用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准确全面地指称,脱离‘租界’这个根元素,海派文化、都市文化难以解说清楚……以‘租界文化’来指称现代上海的城市文化特性,或许,它更贴近上海的文化个性。”特殊而稳定的租界环境,商业主义与娱乐消费文化的并重。众多而稠密的人口、人际关系疏远的移民城市、中西兼容的文化姿态都为电影在上海的成长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租界文化与早期中国电影具有同源同构同质的特性。租界文化是西方殖民化的产物,电影被引进中国伴随着殖民入侵这一过程。电影是一种商业化的艺术品,而租界恰恰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繁荣提供了生机蓬勃的市场环境。租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平台,同时作为中国电影人发挥才干的舞台,无疑是中国早期电影成长的息壤。
上海租界从1843年开辟到1945年收回中间有一百年多年的跨度,在上海这座都市建构了与中国传统城市截然不同的市政制度、文化形态、城市景观、审美趋向。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为经,以殖民化、商业化的特质为纬,形成独属于特定的文化形态,李永东先生称其为租界文化,“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它主要有三大特征:中西文化的杂糅、商业文化与娱乐消费文化的交错共融、殖民性与民族性的交织。这些特征在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中打上了或深或浅的烙印。
一、租界中西杂糅文化在早期电影中的彰显
租界作为一个强势的文化场规约着上海城市的精神气韵。生活在租界的文化空间中,并学习着欧美电影的表现形式与艺术技巧走向电影创作的中国电影人,不自觉地会将他们所感受到的这种亦中亦西的文化特质呈现在电影中。中国电影人独立制作的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阎瑞生》(1921)、《红粉骷髅》(1922)、《海誓》(1922)都呈现了中西杂糅文化的特质。
影片《阎瑞生》的取材就来源于租界上海的一则新闻,讲的是洋行买办出身阎瑞生,为了贪图钱财谋害了已经从良的妓女王莲英的故事。洋行买办这一人物身份是租界社会的产物。其对弱小女子的欺负,也隐约透露出裹挟在西方殖民文化中的极端腐朽堕落的品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影片的拍摄方式与表达技巧模仿美国侦探片,迎合了生活在租界中的上海市民的观影需求,获得了理想的票房收入。与此同时,管海峰编导的《红粉骷髅》,将中国自古就有的武打和言情情节披上美国武打片的布景设置,在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穿插进洋人律师破案的情节,“是一部‘有侦探、有冒险、有武术、有言情、有滑稽’的影片,凑集了一切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货色”,《中国电影发展史》因此称之为“是十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上海租界洋场文化的产物”。直陈了影片受租界中西文化杂糅的影响特质。
除此之外,立足上海租界电影市场的但杜宇以“一女二男”的三角恋爱为故事,编导了影片《海誓》。由“号F·F(Foreign Fashion),蛮靴卷发,有西方美人风味”的殷明珠饰演女主角,颠覆了中国温婉、娴熟的传统女性形象。以时髦小姐的身份呈现在银幕上,引起了上海社会的一时轰动。浸染着租界文化的但杜宇,也通过这部影片显示了他对租界杂糅文化的认同。影片中的中国人穿西装、在花园中求爱、在草地上吃西餐、在教堂中举办婚礼,完全是租界开辟后,西方文化植入中国文化所带来的结果。为了营造这种“西化”特质,影片甚至不惜损坏真实性,如让仆人也西装笔挺,让穷困不堪的画家也“住着一间西式的洋房,家里摆设着铜床、地毯、西式椅子和大大小小的花瓶”。但是影片“西化”特质十足的同时,又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如影片中的字幕又都是用古雅的文言文写成。程季华等人分析“字幕的‘古雅’和画面场景的欧化,就构成了这部影片形式的不古不今、非中非西、杂乱混合的特点”。而这正是租界中西杂糅文化的直接体现。
继此三部长片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影戏部也拍摄了长故事片,依然显示出租界中西杂糅文化对其的影响,如1923年拍摄的《孝妇羹》《荒山得金》《莲花落》,虽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但布景道具、人物服装造型皆具欧化倾向。1924年先后推出的《大义灭亲》《好兄弟》等影片皆因是中国化的故事披上西方化的外衣而遭时人诟病,《大义灭亲》中的女主角梅丽兰:“颇有欧美侍女之风”,其“举动言笑,吾敢谓同化于西洋式中,已及于炉火纯青之境欤”。《好兄弟》中的布景道具设计及人物的生活方式,同样遭人指责:“台上陈设俱系西式,各人以巾围身,如吃西餐,而所进菜肴,又系中国式,不伦不类。”商务印书馆作为宣扬先进思想文化的阵地,曾出版了《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等期刊,在电影如火如荼地在上海放映时,商务印书馆成立影戏部拍摄影片,目的是“借以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表彰吾国文化,稍减外人轻视之心”。然而与这种初衷相违背的是,他们在租界土壤中摄制出的电影,依然难以摆脱被“租界化”的命运。
1926年“大中华”“百合”合并成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刻意走“西化”之路,拍摄了大量以租界都市生活为题材的电影,更是租界文化的中西杂糅在电影中呈现的集大成者。在《小厂主》(1925)、《透明的上海》(1926)、《探亲家》(1926)、《王氏四侠》(1927)等诸多影片中,无论从道具安排、环境营造、故事内容上,还是从人物形象、生活方式、思想倾向、价值判断,都有着“欧化”倾向。这是租界亦中亦西混合文化在影片中的投射。为了能在上海电影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博得租界华人和洋人的好奇,上海的各电影公司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竞相“掀起了不伦不类的古装片竞摄风潮”。在这股浪潮下拍摄的《红楼梦》电影,竟然让人物都穿上时装,让“林黛玉穿着一件像舞裙一样的长衫,足蹬高跟鞋”,“布景则是雕龙柱与西式吊灯并列,太师椅与沙发共陈。”极尽之能事地彰显了租界文化对这部电影创作的影响。另外,从1928年到1931年间,各大电影公司拍摄的大量取材中国武侠小说的武侠片,其中的主角也因“穿着美国西部与墨西哥式的cowboy服装,头穿阔边尖顶的牧者呢帽,身穿骑马式的衬衣”而显得不伦不类、亦中亦西,遭人诟病。
早期中国电影创作中所呈现的租界文化的中西杂糅特征,是租界社会的一个表现。租界特有的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也影响了他们对电影艺术的感知。租界自由、开明、包容、新奇、多样的文化氛围让他们大胆创造电影,希冀既能获得国人的认可,又能博取洋人的眼球。中西文化的杂糅正是他们在电影反复利用的表现方式,在其中混合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时髦的丰富讯息,显得多姿多彩却又不伦不类。
二、租界文化的商业娱乐性使早期电影的选材充满投机意味
租界开辟后所形成的以商业为重镇的上海,使得商业文化成为该城市的主导气质。外商携带着电影到上海放映,是看上了上海这块肥沃的风水宝地有着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在攫取丰厚利润的推动下,他们在人流密集的租界区投资建造了大量电影院和电影公司,聘请中国商人加盟合作拍摄电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成长的中国电影本身就有着商业利润至上的引导。再加上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中国,工商业十分不景气,中国商人在多方投资失败的情况下,有一部分商人转向了投资方兴未艾的电影业。因此,选取什么样的电影题材,拍什么类型的影片以及何种影片能获得丰厚收入成为这些商人首当其冲的考虑之处。
在充满投机思想的引领下,早期中国电影的取材主要是根据观众的喜好而来。比如影片《黑籍冤魂》(1916),“就是根据当时新舞台几经演出、卖座不衰的文明戏《黑籍冤魂》改编而成”。《阎瑞生》(1921)影片产生的原因也是从“演出半年之久,卖座始终不衰”的文明戏中得来的灵感。从《黑籍冤魂》中尝到甜头的管海峰,创作《红粉骷髅》的动机同样是出于讨好观众的投机心理,他后来回忆说“拍什么片子,剧情的选择十分重要,因为,剧本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和利润。根据上海人的心理、口味,当时最受欢迎的,也就是剧院最卖座的一些武侠情节的戏剧。因此,我决定从这方面来选择剧情”。
从交易所投机失败的张石川、郑正秋等人投资明星公司的初衷,同样认为电影业是有利可图的大事业。在“处处惟兴趣是尚”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明星”仅一年内就拍摄了《滑稽大王游华记》(1922)、《掷果缘》(1922)、《大闹怪剧场》(1922)、《张欣生》(1922),前三部受观众喜爱的美国喜剧片的影响,以多吸引观众为宗旨,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电影的“娱乐”功能。《张欣生》与《阎瑞生》的创作动机一样,都是根据在上海轰动一时的文明戏改编。1923年《孤儿救祖记》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明星”于是接连拍了一系列此类题材的影片,如《苦儿弱女》(1924)、《好哥哥》(1924)、《上海一妇人》(1925)、《最后之良心》(1925)等。1928年,郑正秋、张石川将《火烧红莲寺》搬上银幕,“不想此片竟万人空巷,突破了国产影片的最佳卖座记录,明星公司的初衷本只想拍一集《火烧红莲寺》便了事,意想不到的卖座佳绩使经济正陷于困境之中的明星公司欲罢不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火烧红莲寺》一集集地拍下去。”明星公司在三年间竟连续拍摄了18集《火烧红莲寺》。在轰动的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其他公司纷纷效仿,造成了电影创作竞相模仿的现象,“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影片样式,即所谓‘火烧片’。中国银幕上曾几何时是‘一片火海’:《火烧青龙寺》《火烧百花台》《火烧剑峰寨》《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火烧平阳城》……武侠影片开始席卷中国影坛。”
因商业繁荣而发展的上海租界,最大的特点即是批量生产,以最高的效率、最低的投资获得最高的利润。这样的文化土壤特别适合滋生这种模仿的投机行为。有评论者称其为“上海的狂潮”:
上海滩上,每逢产生一种新事业,只消时髦些,发达些,就会有人跟着学步。如潮水一般的蜂涌起来。有人说,因为上海人富于“一窝蜂”的天性。也有人说,上海地近大海,天天饮足了含有潮水性的自来水。故一窝蜂的性质,已成为上海人底第二天性了。入民国后,最大的是“交易所潮”。其他如“话剧潮”“卷烟潮”“牙粉潮”“画报潮”“横报潮”“模特儿潮”等等,潮来潮去,已牺牲了许多金钱和许多生命。最近的“电影潮”和“武侠小说潮”还在继续产生,方兴未艾。唉,上海的狂潮!
不仅是“火烧片”成潮,各大电影公司看明星公司拍的武侠片赚钱,就大量效仿摄制武侠片,“在1929年至1931年间上海的50多家影片公司,就拍摄了250多部武侠神怪片,占其全部影片出品的60%以上”。另外,大中华百合公司批量摄制的具有“欧化”倾向的影片、各大电影公司竞相投机拍摄的大量古装片、爱情片以及“孤岛”时期,再度燃起的古装片拍摄热潮,都体现了租界商业主义、娱乐文化对这些电影创作的影响。
三、租界殖民性与民族性交织下早期电影的叙事意图
租界的开辟带来了上海都市腾飞猛进的发展,无论从物质层面的市政建设还是从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上海都跻身于世界大都市之列。但是这种发展“并非中国社会内部机制发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种自然选择,而是一种饱蘸着血与火的硬性植入,是一段夹杂着民族耻辱感与现代文明发育的双重历史”。因此,身在上海的人,一方面在享受着繁华发达的都市建设所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一方面又对西方殖民者在属于自己的领土上肆意妄为的行为感到耻辱和痛恨。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殖民主义的阴影相互交织,使得早期中国电影人不自觉地通过影像表达对上海的复杂情感,在展示上海摩登现代化的同时,揭露出深层的叙事意图,内隐着对这个“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批判。
效仿西方城市建设的租界上海,在给西方人带来相似感的同时,势必会给中国人带来了陌生感,中国内蕴的本土文化与西方殖民文化交错地呈现在租界上海中,容易给人带来奇异的体验,李道新先生称之为“梦幻之城”。“它的由柏油马路、汽车、洋房、霓虹灯、高鼻梁外国人和时髦侍女拼接而成的‘奇观化’外表,及其衍生出来的天方夜谭式的生活方式、或美丽或丑陋的人生传奇以及大喜大悲的急骤的生命体验,带给大多数中国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租界上海因给人带来的这些“震惊”体验,成为早期电影着意表现的对象。从最早外商拍摄的充满着猎奇眼光的短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1908)、《上海街景》(1908)、《上海南京路》(1901)、《上海租界各处风景》(1909)到中国电影人拍摄的滑稽短片《二百五白相城隍庙》(1913)、《店伙失票》(1913)、《脚踏车闯祸》(1913)、《打城隍》(1913)以及《滑稽大王游华记》(1922)、《掷果缘》(1922)等,无一不给中西方观众以“震惊”体验。与外商对上海都市风景记录式展览不同的是,中国早期的这些短片,在滑稽搞笑之外,内蕴着早期电影人对上海都市文化给外乡人所造成内在压迫的同情与调侃。从这点来说,短片中看似在展现外乡人在上海的种种窘迫“奇遇”,却揭示了身在上海租界区的编导在表达上海都市影像时的复杂心态,是对都市文明战胜落后乡村,西方殖民文化压倒老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像寓言。
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因租界上海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心,更加容易成为播撒民族主义精神和抵制殖民主义侵略的阵地。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上海都市风貌与市民生活状态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展示的中心。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加入到电影中,使得电影更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租界上海是“穷人的地狱”的一面。如《城市之夜》(1933)、《都会的早晨》(1933)、《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新女性》(1934)、《神女》(1934)、《渔光曲》(1934)、《生之哀歌》(1935)、《风云儿女》(1935)、《都市风光》(1935)、《新旧上海》(1936)、《十字街头》(1937)、《马路天使》(1937)等,均以租界上海为背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市民的挣扎与痛苦,影片多采用蒙太奇的交叉对比镜头,将穷人的悲惨与富人的不仁呈现出来;采用移动变位的镜头,展示摩登都市繁华的背后所掩藏的灰暗逼仄的生活环境,将一个充满着摩天大楼、光鲜亮丽与霓虹灯不断闪烁的夜上海与一个阴暗潮湿、充满着痛苦哀吟与鲜血死亡的夜上海并置呈现在电影中是这类电影惯用的技巧。
这是早期电影人创作这些电影的深层叙事意图,上海租界的时尚豪华与摩登现代是殖民主义血腥侵略的结果。它的存在强化着民族主义的情绪,成为左翼电影借此表达革命理想与爱国意识的着眼点,也使得影片的叙事遵循的是实现全民族解放的政治逻辑。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叙述政治”,包括所采取的揭示上海“异质性”的都市生活片段的剪辑、叙述结构上的贫富对立的策略等。上海租界文化的时尚摩登、奢靡颓废以及扑面而来的殖民气息给电影提供了向民众宣传救亡图存的材料。影片表面上看似在展示都市场域中中国民众的苦难生活,实质上是在否定西方的殖民主义文化入侵。从这方面来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多呈现繁华都市掩盖下的苦难图景,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多呈现中西杂糅的“欧化”倾向。太平年代,租界文化的殖民性与现代性相交织,让中国电影人对西式的观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采取矛盾、漠然甚至迎合的暧昧姿态。但在战时,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让中国电影人意识到紧跟着殖民势力而来的繁华是那么面目狰狞,惹人愤恨。必须努力揭示掩藏在其背后的民众创伤才是中国人的道义与责任所在。所以在左翼电影的叙事话语里,上海这座迥异于母体的半殖民化的现代化大都市必然遭到隐性的批判,租界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就此缝合进主流意识形态之中,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的契机。
结 语
中国早期电影创作、放映均离不开租界文化的影响。租界电影院林立,直接刺激了中国电影的生产与发展,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前来观影。《姊妹花》“在上海的新光大戏院(公共租界中区)公映时,创造了连映六十余天的票房纪录”。中国电影能够势如炮竹的发展,离不开租界电影院放映平台的支持。它尽管是外国影片的天下,“却并不影响中国民族电影业的蓬勃发展。相反,电影院同时在物质和文化上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种习惯——看电影去;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气候,本土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除此之外,租界的物质与文化景观,如百老汇大厦、银行大厦、上海邮政大楼、欧式洋房、沙逊饭店、政权交易所、基督教堂、海关大楼等高大的建筑;宽敞平坦的柏油马路、富有现代气息的有轨电车、豪华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及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变化绚丽的广告牌、疯狂冒险的跑马场、富有小资情调的咖啡厅、舞厅等都成为中国早期电影聚焦取材的对象。用都市的摩登繁华建构着电影的“奇观化”特征,吸引着不同层次的观众前来观影。在租界文化的都市语境熏染下,早期电影观众也逐渐形成,电影所带来的斑驳陆离的视觉奇观及摩登时尚的生活习惯、审美趋向对观众构成一种潜在的吸引力。他们逐渐从传统的茶园戏馆中走出,走进电影院成为他们在都市中的生活风尚。同时,由于租界的存在也刺激了电影杂志的创办,1921年中国电影的第一本铅印的专业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在上海创立。其成立的目的之一,即为“在影剧界替我们中国人争人格”,表明创刊者的初衷是为了抵制西方电影与文化的侵袭。尽管由于商业利润的原因,该刊物仍然以报道外国影片为主,但也为后来电影刊物的相继创办提供了借鉴作用。总之,租界文化影响着早期电影的风貌格调,为我们解读中国早期电影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