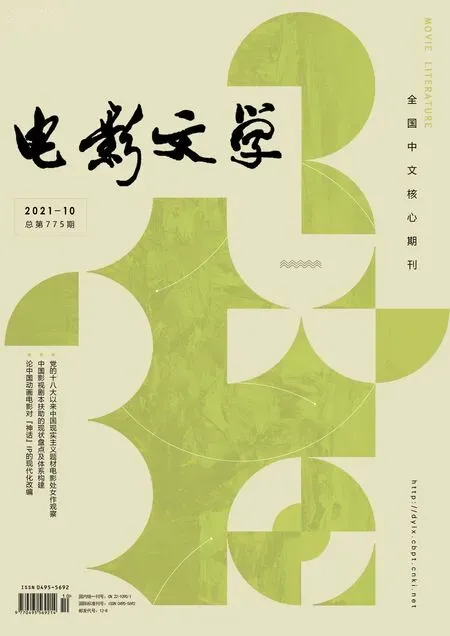刁亦男电影的类型化论析
2021-11-14王昱
王 昱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新生代导演刁亦男的创作一度被认为始终与商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不选择特别商业的题材和形式,基本都在关注一种当代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状态,写自己的故事,让别人去说”。但事实上,自《白日焰火》后,刁亦男电影在保留了作者性的同时,又展现出了清晰的商业性,其中犯罪类型片的典型模式有迹可寻,他依然在“写自己的故事”,却能与观众展开热切对话,并取得可观的票房收益。在国产犯罪类型片依旧整体低迷的当下,刁亦男所走的类型化道路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一、从“非类型”到“类型化”
单纯考量刁亦男作为导演创作的电影,我们不难发现,他有着一个从“非类型”到“类型化”的转向。以《白日焰火》为界,刁亦男前期的电影更接近独立电影的艺术范式,处女作《制服》以及后来的《夜车》,都带有明显的离心感性(eccentric sensibilities)特征。所谓离心感性,即一是导演在电影中的表达是极其个性化的,二是电影中有着以理性提炼的而有别于主流电影规范的意识形态或道德的内容。以《制服》为例,这部由贾樟柯担任艺术顾问,且以《小武》《任逍遥》的制片、剪辑等为创作班底的电影有着一定的“贾氏”印记:在叙事上,刁亦男淡化了情节,并且安排了开放式结局。小建和莎莎两人分别拥有两种身份且彼此隐瞒,但电影中并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场景与精心设计的情节,而只有人物碎片化的无可奈何的生存体验。最终电影在小健被真警察追捕,莎莎等待小健中结束。在《夜车》中,吴红燕是一名女法警,代表秩序与威严,她也确实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电影重点表现的却是她始终如片尾的白马,被情欲的鞭子抽打的绝望状态。她所交往的三个“相亲对象”,分别将她当成了泄欲、谋财和报仇的对象,以至于到最后她在明知李军有可能会杀死自己的情况下,依然走向李军,甚至提醒李军拿上装有凶器的包。在某种程度上,她作为一个维护法律的人却纵容了(潜在的)犯罪。两部电影均沉闷压抑,戏剧冲突让位给了人物的心理状态。
如果将刁亦男以编剧身份参与制作的影视剧也囊括进来,即《将爱情进行到底》《洗澡》与《爱情麻辣烫》,我们又能发现,这些被刁亦男视为“命题作文”的作品,恰恰是合格的类型作品。例如《洗澡》便是按照“市场细分”(Marketing Segmentation)制作的家庭伦理喜剧片,恰到好处的巧合设计、怀旧元素的加入以及新旧冲突的主题等,都能成功满足观众消除疲劳、娱乐身心的需要。也就是说,刁亦男完全能把握类型片的创作。
而到创作《白日焰火》时,刁亦男则是将自编剧时期起就相当突出的创作类型片的能力,与《制服》《夜车》时期对罪案题材、对边缘人物的喜好结合起来,并使之与自己的艺术偏好(如隐喻意象的运用等)结合起来,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类型化创作。除了制作上对明星演员的起用,电影充满悬念与张力,节奏明快,以及视觉语言冷峻严酷,打斗暴力血腥,且导演也以一种投入而非超然的态度介入人物命运中……电影成为一个实在的消费对象:观众的情绪、意见、审美以及情感宣泄,都得到了满足。为此,在《南方车站的聚会》中,悬疑、惊悚、暴力乃至明星等元素,都作为商业卖点而为刁亦男沿用,电影也确实进入主流市场视野中。
二、刁亦男电影的类型化表现
《白日焰火》与《南方车站的聚会》是典型的犯罪类型片,即以罪犯和警察/侦探为主角、以展示犯罪或侦破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电影,两部电影在题材、情节、人物关系、场景设计等方面,都是遵从这一类型片审美框架的。
(一)递进悬念与延宕情节
在犯罪类型片中,导演势必要设定一个悬念,即“设谜”,再带领观众“解谜”,这一悬念往往便是案件的真凶,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中观众无不希望波洛让真相水落石出。当代犯罪片还往往会有一个以上的案件,让剧情更为扑朔迷离。在《白日焰火》中,一开始电影就以碎尸案吊住观众的胃口,就在观众误以为真相大白时,又发生了包括警察被害在内的一系列连环案件,悬念可谓层层递进。《南方车站的聚会》则是一开始就交代了“凶手”是周泽农,观众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在警方的重重围剿中逃出生天,与妻子杨淑俊相会,或是以自投罗网的方式换妻子拿到30万元赏金。两部电影中,观众的视角分别是原来的警察、现在的落魄保卫科干部张自力的视角和惶惶不可终日的周泽农的视角,限知视角让观众一直揪心关切。观众与导演“解谜”的过程也是警方破案的过程。犯罪类型片无不选择延宕处理情节,即逐步将事件全貌铺开,让情节环环相扣,直到最后矛盾集中爆发时(警察抓捕吴志贞和击毙周泽农),观众累积的情绪一下得到宣泄。
(二)残酷现实与暴力美学
犯罪类型片往往都与现实接壤,剧情源自编导对不良社会现象与违法犯罪行为的收集整理,甚至直接搬取真实案件,如《那家伙的声音》《杀人回忆》等。电影中人物的生活场景真实且残酷,只有如此,才能感染与刺痛观众。《白日焰火》与《南方车站的聚会》的背景分别为哈尔滨与武汉,但刁亦男有意规避了两座城市繁华的一面,而聚焦于其没落、阴暗、惨淡的一面,并使其为剧情服务。如《白日焰火》中被用来抛尸的煤渣零碎以及残破肮脏的老工业区,张自力、吴志贞与梁志军的命运就被捆绑在这座城市中。也正是因为城市资源行将耗尽,经济不景气,吴志贞才会因为烫坏了别人的一件皮氅而走向犯罪。这一点与好莱坞影片如《日落大道》《亡命驾驶》等相似。在人们充满戾气,铤而走险之际,血淋淋的暴力场面也就不可避免。而犯罪类型片极为注意将这种暴力发展为一种形式美学。如片中梁志军以东北随处可见的冰刀杀人,而周泽农以雨伞杀人、以车锁打人,帮派成员用安全杆割断骑车者的头颅等,人物行凶之际无不凶悍冷血、出手利落,人性恶瞬间倾泻而出,甚至具备了某种仪式上的观赏性。
(三)正邪交错与情爱纠葛
除了暴力,男女情爱也为类型片用以吸引观众。在犯罪类型片中,警匪作为对立双方,往往又有着其他交集,人物在为罪案疲于奔命之际,也有着情感与身体欲求。如《沉默的羔羊》中食人狂魔汉尼拔既是罪犯,又是探员克拉丽斯的助手,更与她有着某种情愫。在《白日焰火》中,张自力在查案过程中不可自拔地喜欢上了吴志贞,而吴志贞对张自力的喜欢也掺杂了希望张自力为她摆脱心理扭曲的梁志军纠葛的私心,而就在吴志贞以为自己可以开始新生活之际,一心想恢复警察身份救赎自己的张自力还是出卖了她。《南方车站的聚会》中,陪泳女刘爱爱周旋于警方和黑帮老大华华等人之间,为了帮周泽农给杨淑俊争取到30万元的任务,两人上演了一出嫖客与妓女的戏码,但两人早已产生了真感情,在绝望的境地中完成了对彼此的慰藉。最终刘爱爱成为“见义勇为”的举报者,但她实际上又是狠辣残忍的周泽农的同伙。人物的正邪面貌并不分明,而他们伴随杀戮与利益纠纷的情爱更是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
三、刁亦男电影的类型化特点及启示
如前所述,刁亦男在《白日焰火》与《南方车站的聚会》两部电影中彰显了类型片定位,显示了与其他犯罪类型片之“同”,那么我们同样要注意到其与其他作品之“异”,从而更好地把握刁亦男电影的类型化特点,而有意于转向类型电影创作的电影人也能由此获得启示。
(一)保留艺术个性
优秀的独立电影导演或作者导演在投身类型片时,往往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艺术个性,避免自己的作品“泯然众人”。如彼得·杰克逊从“邪典”时期到魔幻大片时期一以贯之的表现主义影像风格,娄烨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沿用了自己的手持摄影特点等,刁亦男也不例外。动物作为既略显突兀却又富含深意的符号,不仅出现在《夜车》中,也出现在了《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白日焰火》中拾荒者不见人影,留下一匹马被居委会暂时收留,是刁亦男受雷蒙德·卡佛小说《羽毛》与《离家这么近有这么多的水泊》影响而提出要加进去的情节,马看似与剧情毫无关联,但实际上暗示了社区事务繁杂、人口失踪频繁的大社会背景,同时也与同样个性温顺、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吴志贞形成一种苦涩的对应。在《南方车站的聚会》中,警匪双方在动物园交锋,随着他们视线与足迹的移动,镜头扫过夜幕之下动物园里的动物们,老虎、猫头鹰、群鸟等无一沉睡,或是惊恐窥探,或是警惕打量,让观众为之心惊。刁亦男以此来暗示城市也是另一个丛林,同样有着你死我活的追猎与逃亡,人也有着兽性。当然,必须通过女性来重寻尊严与身份的失败男性、流行音乐等,也是刁亦男在两部电影中留下的个人印记,不再赘述。
(二)规避病态审美
毫无疑问,类型电影研究承认观众的重要性,而学者颜纯均甚至辛辣地指出,类型电影存在一种病态审美:“在类型电影中,观众的审美期待和选择偏好从一开始就多少有一点畸形。以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观众可以不在乎整部影片的完美自足,不在乎方方面面的不完美,只要求那些满足选择偏好的形态和特征超乎寻常地张扬与强化。对那些符合选择偏好的方面更强的期待,以及对那些不符合选择偏好的方面降格以求甚至不厌其烦,这正是类型影片观赏的普遍经验。”这也确实是广泛存在于类型片接受的普遍经验,如在武侠、动作类型片中,编导就不得不处心积虑地安排人物“五分钟一小打,十分钟一大打”,而观众也选择忽略这种频繁打斗背后的合理性,或剧情因文戏不足造成的单薄感。刁亦男则努力规避这一问题。与韩国犯罪类型片如《黄海》《杀人回忆》《追击者》等相比,可以看出刁亦男电影对暴力的渲染要更为克制。而与好莱坞的如《沉默的羔羊》《七宗罪》等贩卖缜密逻辑推理的电影相比,亦不难发现刁亦男无意于在设计智力游戏上进行炫技。此外,好莱坞犯罪电影常常会采用一种因果式线性结构来进行叙事,为矛盾安排一个确定的、封闭式的结局。而刁亦男则不同,两部电影的半开放式结局引人嗟叹不已,有别于一般类型片的大团圆结局。
应该说,对于传统类型片来说,刁亦男不是一个颠覆者,而是一个补充者。在经历了受束缚较多,但足以积攒经验的编剧时期,以及初登影坛,以小成本电影展现个性的时期后,刁亦男开始较为自如地尝试类型化转型。《白日焰火》与《南方车站的聚会》均体现了刁亦男对类型规则的自觉迎合,电影的商业属性也由此得到了充分发挥。值得一提的是,刁亦男又极为注重保留自己的艺术个性,并规避迎合观众膨胀欲望的病态审美,在固本盈利的同时,并未让电影流失真诚。可以预见到的是:如果刁亦男能将其在《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创作态度与热情延续下去,“刁亦男”无疑将成为一个形象丰满、定位清晰,于国内外均具有号召力的电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