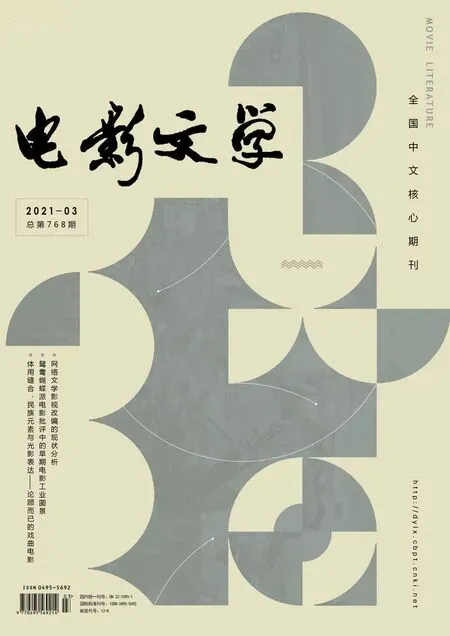体用缝合、民族元素与光影表达
——论顾而已的戏曲电影
2021-11-13金响龙
金响龙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戏曲电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样式,也是中国所特有的兼具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审美意蕴的歌舞故事片。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在戏曲文化断层、现代视听媒介的夹击下渐显式微,而各地方的戏曲电影虽迎来了短暂的繁荣,出现了《西厢记》《白蛇传·情》《雷雨》《大闹天宫》等一批优秀的戏曲电影,但这也仅能说明“戏曲电影正在被相对多种身份的观众出于不同观看心理而乐于接受的现实”,而不能否认戏曲电影的市场化羸弱、虚实关系失衡等诸多问题的存在。如何利用戏剧影视的技法,有效地缓解戏曲语言与电影语言之间的美学冲突,使中国戏曲艺术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情感诉求,是戏曲人和电影人需要共同解决的课题。在影像民族化与戏曲电影化探索中,顾而已采用“以戏就影”的创作理念,通过电影的艺术手段和表现形式,缝合了戏曲语言与电影语言之间的矛盾,完成了戏曲从舞台到银幕的转换和互动,推动着戏曲片从“舞台纪录片”向“新式电影”跨越。
一、顾而已与戏曲电影
顾而已(1915—1970),原名顾而锜,江苏南通人,中国著名编导、表演艺术家。20世纪20年代,南通的戏剧活动盛行,顾而已的父亲顾敬基经常带他去剧院看戏,童年时期来自地方影戏文化、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成为其之后与戏剧、电影结缘的主要原因。1936年,顾而已初涉影坛,加入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出演由史东山编导的故事片《狂欢之夜》,这使他在影坛上得以崭露头角。1938年,参演由卜万苍导演的剧情片《貂蝉》,顾而已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董卓”一角,因而被称为中国的“查尔斯·劳顿”。1942年,参演由陈鲤庭导演的历史剧《屈原》,这部话剧标志着顾而已表演艺术的成熟。1948年,顾而已在香港参与组建大光明影业公司,次年独立编导现实主义力作——《水上人家》。1952年起,顾而已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导演,独立执导或与他人合导《天罗地网》《春天来了》《消防之歌》《燎原》等10部影片,其中历史故事片《燎原》(1962,与张骏祥合导)是“他导演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部戏”,被观众称为“激动人心的好影片”。
顾而已将影戏理念和经验注入戏曲电影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955年,顾而已与石挥联合执导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采用电影特技和实景处理戏曲神话题材故事,打破了舞台时空和技术程式,为戏曲电影化的探索提供了较好的范本。这部影片的上映,使得黄梅戏一跃成为我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甚至还引发了香港创作“黄梅调电影”的风潮。1957年、1959年,他先后执导了现代沪剧电影《罗汉钱》与《星星之火》。在不破坏舞台演出精华的原则下,顾而已充分利用实景、场面调度和电影手段实现沪剧从舞台到银幕的转换。在叙事策略上注重人物塑造、情感表达和故事建构,而在主题内容上则更加强调进步性、现实性和冲突性,力图将沪剧通俗写实的美学形态呈现在银幕之上。1963年,独立执导黄梅戏电影《柳荫记》,编剧为桑弧,艺术顾问为严凤英和王少舫,这部影片是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的翻版,顾而已在场景设计、民族化表达、剧本电影化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重新回溯顾而已的戏曲电影创作历程,可看出其在影像民族化与戏曲电影化探索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顾而已将影戏理念和经验注入戏曲电影创作,“注意到发掘角色情感的细微变化、内心纠葛和思想矛盾,虽然有时不免夹杂些自然主义的成分,”但他使用多种电影手段和拍摄技巧将民族传统艺术融入电影影像,既实现了中国电影的“再民族化”表达,也弘扬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戏曲文化,为一些戏曲剧种和戏曲演员留下了音像资料。
二、顾而已的戏曲电影化探索
(一)“以戏就影”的创作理念
关于戏曲电影创作理念的争论由来已久。张骏祥在《舞台艺术纪录片向什么发展》中指出,戏曲影片是一种“新式电影”,这种电影要打破戏曲舞台的限制,还要“服从电影表现的规律,利用电影表现的便利”。崔嵬在《拍摄戏曲电影的体会》中提出,戏曲影片是一种“舞台纪录片”,“虽然戏曲片是以电影的形式出现,但它是以戏曲为内容,它必须建立在戏曲传统规律的程式基础上,保持并发扬戏曲的特点”。张骏祥和崔嵬等人的论述呈现出相悖的态势,反映出戏曲电影观念上的分歧与差异。蓝凡则在《氍毹影像:戏曲片论》中进一步总结和阐释,认为戏曲影片的类型应该分为“以影就戏”和“以戏就影”型,这两种类型是“戏曲片作为电影类型为应对和解决戏曲叙事原则与影像叙事原则之间矛盾的两种理念和方法”。
顾而已采用“以戏就影”的创作理念,推动着戏曲影片从“舞台纪录片”向“新式电影”跨越。戏曲电影的创作理念之争,其实质上就是戏曲与电影以谁为主体的问题,这与戏曲电影的观念认知、“虚实”处理原则有着必然联系,虽然形成了以“戏”或“影”为主导和“戏影”综合的创作理念,但从戏曲电影的争论和实践来看,戏曲电影的形态风格也只有“以影就戏”和“以戏就影”这两种。“以影就戏”型,是一种以“戏”为核的戏曲舞台纪录片,即在保持戏曲舞台原貌的基础上,利用电影化手段对戏曲艺术进行记录,将电影与戏曲的“唱念做打”相融合,较好地保留所摄戏曲剧目的艺术精华。而“以戏就影”型,是一种以“影”为主导的“新式电影”,即通过使用电影语言、写实化场景等手段突破戏曲舞台的束缚,尽量保留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和表演特点,注重戏曲电影的人物塑造、故事建构和艺术处理,极力创造出富有故事片审美特质的戏曲电影。从沪剧电影《罗汉钱》到黄梅戏电影《柳荫记》,顾而已均采用“以戏就影”的创作理念,彻底打破舞台时空和技术程式,使戏曲片由“舞台纪录片”向“新式电影”方向发展。在保持戏曲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特色的原则下,顾而已使用立体实景的拍摄方式,建筑室内空间相对封闭、真实自然,力求为戏曲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展现提供生活化的叙事空间。譬如,沪剧《罗汉钱》和《星星之火》都为现代戏曲剧目,自身的程式化较弱,在戏曲电影中便用高度写实化的布景,甚至是真实外景来构建叙事空间,从而替代了传统戏曲舞台中的很多虚拟场景假设,让戏曲电影的空间环境更加贴近真实生活,有效缓解了戏曲与电影之间的美学冲突;运用灵活自如的电影镜头打破舞台和剧场的制约,强调“电影化”的同时,也保持戏曲表演的艺术特色,使戏曲电影饱含故事片的视觉效果。譬如,沪剧电影《星星之火》和黄梅戏电影《柳荫记》中,充分利用多角度、多景别的电影运动镜头,突破戏曲舞台“三面墙”的束缚,不仅弥补了传统舞台上无法实现的功能,也保留了戏曲的表现形式和表演特点,为观众带来强烈的真实感和形象感;利用电影化手段对舞台表演形式进行改造,摆脱戏曲舞台上的表现手法,强化了戏曲电影的叙事表现力,带给观众不同于舞台演出的视觉感受。譬如,黄梅戏电影《柳荫记》中运用电影特技手段表现“仙女下凡”的场景,打破了戏曲舞台的形式结构,省略了舞台演出中“跑圆场”的程式表演动作,将戏曲舞台上无法呈现的视觉形象展现在银幕之上,推动着戏曲影片从“舞台纪录片”向“新式电影”跨越。
(二)“虚实结合”的场景建构
戏曲电影的场景是指人物活动与戏曲情节展现的空间环境,大致可分为写意性场景、写实性场景和虚实结合场景这三类。写意性场景,主要是依托演员的程式写意性表演或唱念而存在的,它与“简约空灵”的戏曲舞台空间无异,场景建构更加注重简约性和意象化。而写实性场景与虚实结合场景,都刻意强调“电影化”的审美风格,场景建构更加注重装饰性和生活化。但二者在具体设计和布置上又存在不同,写实性场景往往是以人工搭景和真实外景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空间环境,而虚实结合的场景则是将写实化布景、写意化绘景和演员虚拟表演所展现的空间相结合,构建出具有生活化、民族化审美特征的场景环境,使戏曲电影表现出亦虚亦实的美学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戏曲电影导演在场景设计与布置时,由于戏曲电影观念和审美取向的差异,往往会采取写意性或写实性的场景风格。前者是将戏曲电影当作舞台纪录片拍摄,而后者则是将戏曲电影当作故事片创作,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很容易放大电影与戏曲之间的美学冲突,让戏曲电影缺失古典意韵与现代影像融合之美。
顾而已使用虚实结合的场景建构方式,巧妙地缝合了戏曲写意与电影写实之间的矛盾。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布景和道具为人物、情节展现提供叙事空间,戏曲演员依靠唱念和身段表演进行叙事表意,舞台场景与戏曲演员之间形成紧密联系,这种联系虽然使戏曲艺术独具虚拟化、写意性的美学特征,但也容易造成布景与表演间的重复和矛盾。而在戏曲电影中,除了写意的戏曲与写实的电影之间有着根本矛盾,演员的动作、唱词与布景之间都会形成虚实之矛盾。在戏曲电影的艺术实践中,顾而已采用虚实结合的场景建构方式,既有效解决了电影语言与戏曲语言之间的矛盾,也让演员表演、空间环境的展现更加直观和生动,使戏曲电影的视觉观感和叙事元素得到强化。譬如,《柳荫记》“路遇”一场,前景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树等皆以写实化立体布景和道具呈现,而后景则以人工绘制的写意山水来表达。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真实化的布景、道具的使用,能够代替舞台演出中的虚拟场景假设,减少戏曲演员的程式写意性表演,而写意性的人工绘景是我国传统绘画形式美感的视觉呈现,这种绘画感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有助于戏曲电影的影像民族化表达,以及缓解戏曲表演的程式写意性与电影表演的生活真实化要求之间的矛盾。在电影镜头的统一下,导演将写实化布景、写意化绘景和演员虚拟表演所展现的空间相结合,形成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戏曲电影场景。这种电影场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装饰性,与戏曲服饰和人物活动的场所环境相协调”,又与电影的写实化要求、演员的程式化表演相契合,它不仅省去了戏曲电影中交代地点环境、上场自报家门等唱词和念白,让影片的叙事更加凝练紧凑,也为董永和七仙女的情感活动、唱段表演提供叙事空间,使人物、情节和场景环境这三者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更是有效地缝合了戏曲与电影之间的虚实矛盾,增强了戏曲电影的视觉观感,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
(三)“戏影耦合”的电影调度
戏曲舞台与戏曲电影均有不同的调度方式。戏曲舞台调度是指“人物在舞台上的位置及其移动的路线”,大致可分为人物调度和空间调度这两种形式。人物调度是改变演员程式化的移动路线、方向、走法等,空间调度则是将戏曲舞台的空间虚拟化和模糊化,这两种调度方式都是为了达到揭示人物情感、保持程式特色等目的。而戏曲电影的调度是“戏影耦合”的产物,即它是电影化手段和舞台调度方式的结合体,主要是以多种多样的电影化手段为主,兼用电影镜头内的戏曲舞台调度形式和技巧,以使戏曲电影中的舞台痕迹消失殆尽,让戏曲电影在视觉上更具真实感。
顾而已将电影化手段与舞台调度形式相融合,有效消解了戏曲电影中的舞台痕迹。传统戏曲舞台演出,由于舞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演员只能依靠走边、趟马等程式化动作进行表演。这种表演形式具有浓重的舞台化痕迹,很容易影响观演情绪。而在戏曲电影中,戏曲与电影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融合,不仅会造成戏曲舞台时空的“虚”与电影时空的“实”之间的矛盾,更会使戏曲电影中留存明显的舞台痕迹和剧场视点,让影片的审美风格显得不伦不类。在戏曲电影化的探索道路上,顾而已将电影化手段和舞台调度形式相结合,巧妙地解决了电影中的舞台痕迹问题,为戏曲电影增加了视觉与心理的真实感。譬如,沪剧电影《星星之火》“冤有头来债有主”一场,原戏曲舞台演出,“龙套”演员遵循着“镜框式”舞台的上下场方式,其在舞台上所站的位置、方向也基本不变,而刘英与杨桂英则通过程式化的唱念和身段进行表演,因而这场戏具有浓重的舞台痕迹和技术程式特色。而在戏曲电影中,顾而已将电影化的手段与舞台调度形式相结合,以此方式消解戏曲电影中留存的舞台痕迹。导演先通过杨桂英与双喜的“出画入画”镜头,表现人物空间位置和行进方向的变化,替代了舞台演出中程式化的横移和走曲线,增强了影像画面的真实感和动态感。之后使用全景镜头表现刘英和“龙套”演员的出场,而舍弃了传统戏曲舞台中演员固定的上下场方式。同时利用戏曲舞台的场面调度,将“龙套”演员的移动路线、方向加以固定,以起到烘托气势和表述情节的作用,避免了场面的凌乱之感。之后又运用正反打镜头、叙事蒙太奇交替表现杨桂英和刘英之间的唱念、形体动作,电影化手段和舞台演出形式的结合,代替了舞台演出中戏曲演员的某些程式写意性动作,从而消解了戏曲电影中的舞台痕迹,增加了戏曲电影的真实感和形式美感。
(四)“情景交融”的电影意境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范畴,也是民族题材电影最重要的美学原则。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从庄子到王国维等哲学家、文人对“意境”都有较为繁复的论述。“意境”理论最早萌发于先秦哲学中,庄子的“得意忘言”论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对“意境”的美学追求,为“意境”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人们开始将意境理论用于书画、诗歌创作中,王昌龄的“三境说”是中国文论术语中“意境”概念最早的出处,而苏轼的“诗画本一律”观点则说明了“意象”与“意境”的相通性,为诗画意境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近代的王国维提出“境界说”,其认为情与景是生成意境的基础,意境是情、景、事的交融与统一,这种理论观点将“意境”推向至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范畴,使得传统意境理论彻底走向成熟。中国电影艺术家将意境理论用于戏曲电影创作,营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银幕意境,让戏曲电影传递出“景外之景”和“象外之象”的美学意味。
顾而已将传统意境理论融于戏曲电影影像,实现了电影艺术的“再民族化”。戏曲电影是戏曲与电影手段相融合的产物,其意境的生成必然由戏曲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形态艺术造就。不过,戏曲的舞台时空和演员表演具有“意象化”的表现形态,这种“意象化”形态饱含民族化特色,也很容易生成空灵的意境,但观众审美水平、接受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又会使效果不尽如人意。而电影的镜头具有直观性、写实性特征,虽然很容易营造真实空间氛围,但这种高度“写实化”又会使电影缺失独特意象之美。因此,如何将写意性戏曲和写实化电影相结合,进而为戏曲电影构造出饱含民族文化传统和唯美观念的银幕意境,是摆在戏曲电影导演面前的一道探索题。在影像民族化的探索道路上,顾而已将传统意境理论融于戏曲电影影像,通过利用电影语言、古典美学技法和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不仅为戏曲电影营造出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银幕意境,亦实现了电影艺术的“再民族化”。譬如,《柳荫记》“满工”一场,导演先借用古典诗歌的技法,以“鹅”喻指、象征董永与七仙女,创造出“红掌轻摇爱意生,雪颈缠绵水传情”的古典诗歌意象,实现了戏曲情节内容的修辞化表达。之后运用空镜头表现中国画写意花卉,用来转场和营造“花团锦簇,美景交融”的空间氛围。在电影化的镜头调度下,又将写实化布景和演员表演所展现的空间相结合,构建出“虚实结合”的电影时空。而在这种时空中,导演又以“留白 ”式空镜头营造“鸟鸣山更幽”的审美意象,董永与七仙女触此景而生情,二人以程式写意性动作进行互动和表演,并对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导演将情、景、事进行完美融合,不仅营造出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银幕意境,也表现出董永与七仙女之间美好而凄婉的爱情,实现了影像艺术的“再民族化”的同时,更让观众产生移情与共鸣。
(五)“化虚为实”的镜头语言
“戏曲与电影具有各自独立的独特的表意体系。”传统戏曲舞台及其与观众距离皆固定,舞台演出只能依靠演员的“唱念做打”来叙事抒情和控制观众视点,且“剧场视点”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观众视角的受阻、审美情趣的丧失。而戏曲电影是以镜头为叙事单位,通过电影镜头转换和组接来实现叙事表意的目的,这种灵活自如的镜头对戏曲舞台元素进行改造、重组和融合,实现戏曲从舞台到银幕的转换的同时,更是将舞台上某些虚拟化的动作转化为真实的视觉形象,弥补了戏曲舞台上的诸多缺陷和不足,赋予观众不同于传统舞台的全新视觉感受。
顾而已借助镜头语言突破舞台时空的局限,完成了戏曲从舞台到银幕的形态转换。譬如,沪剧电影《罗汉钱》中,顾而已采用长镜头配合单一景别的形式表现小晚与艾艾月下幽会、互送定情信物。具言之,用长镜头表现小晚和艾艾之间的对白以及介绍场景环境,插入小晚的近景画面,用长镜头展现二人互送定情信物,插入定情信物“罗汉钱”的特写画面,用长镜头表现小晚与艾艾的托物寓意、借物抒情,插入小晚手拿小方戒的近景画面……这一段戏,顾而已使用7个长镜头配合3个单景别镜头来表现二人的美好爱情故事。在保持演员唱念的整体性与连贯性的前提下,再根据小晚和艾艾的唱段长短、唱腔节奏来调整镜头的运动轨迹与停滞时长,这不但将沪剧唱腔的悦耳动听、唱词的脍炙人口的特征呈现出来,实现了沪剧由通俗化升华到通俗美的境界,也将舞台程式化动作进行形象化表现,摆脱了传统戏曲舞台式的表现手法,使观众得以多景别、多角度和多空间地欣赏到戏曲的魅力与特色。再如,沪剧电影《星星之火》“隔墙对唱”一场,原戏曲舞台演出中,杨桂英与小珍子通过唱念表演来诉说这隔墙而不能见的相思之情。舞台时空和观众视角的固定性,使观众只能看到戏曲舞台的二维空间形象,这不仅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枯燥之感,也会淡化沪剧自身的精神内质和艺术风貌。而在戏曲电影中,顾而已利用多种多样的镜头语言,打破了舞台形式结构,给予观众不同于传统舞台的视觉感受。概言之,在“隔墙对唱”这场戏中,导演采用中、近景镜头和全景镜头来进行叙事与抒情。戏曲电影中交替出现的中、近景镜头能够规避戏曲舞台中的空旷之感,保持唱段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的同时,也强化了沪剧“板腔体”的唱腔特色,并将杨桂英的伤心、激愤之情以及小珍子的痛苦、恐惧的情感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赋予观众强大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全景镜头的空间“范围约等于剧院现场中观众与舞台之间的距离”,这种空间视野与剧场视觉效果有着某种类似。但在戏曲电影中,通过利用全景俯拍的形式,能够直观地展现人物与空间环境的关系,以及表现出杨桂英、小珍子的整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在真实生活化的叙事空间中,杨桂英与小珍子对唱:“白纸黑字落人手,生死不由我主张。天昏地暗满眼花,浑身疼痛苦难当……”电影运动镜头围绕人物的唱念和身段表演而进行自由调度,彻底打破了舞台时空和“剧场视点”的限制,这不但淡化了戏曲表演的虚拟性、假定性特点,更是将舞台上的某些程式虚拟性表演转化为真实的电影视觉形象,完成了戏曲从舞台到银幕的形态转换。
结 语
“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遗产, 戏曲应该得到重视, 而戏曲电影亦应该得到支持”。在保持戏曲的表现方法和表演特色的原则下,顾而已利用电影化手段将戏曲与电影相融合,创造出符合民族审美情趣和心理需求的多元化戏曲影像,实现了电影艺术的“再民族化”表达,使中国戏曲电影的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然而,在好莱坞“文化霸权”和“全球化”浪潮的侵袭下,中国电影正陷入缺乏独特性的窘境,民族化是其走向世界影坛的必经之路,而戏曲是“古典审美情趣的综合结晶和民族传统艺术的集大成者,成为电影借鉴传统文艺的优先选择”,因此在新环境背景下重新审视电影与戏曲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戏曲电影需要解决的终究不是本体元素、创作手法和电影市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观众对戏曲审美接受的问题,这是戏曲电影能否屹立于世界影视艺术之林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