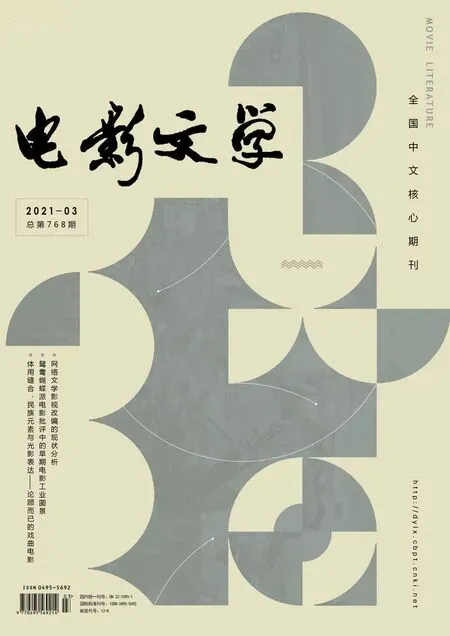“她者”的历史:严歌苓与“第五代”导演的个体写真与集体寓言
2021-11-13袁铭泽
徐 爽 袁铭泽
(1.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2.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0)
作为新时期中国电影艺术高峰的“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创作中向来偏爱文学作品向电影作品的挪移与改编,一个并非偶然的巧合是,数位“第五代”导演都与知名作家严歌苓合作,特别是近年来改编创作数部引起广泛关注的电影作品。相近的年龄使作者和导演共享相同的时代记忆,传奇性的情节构建正好契合受众的审美期待,文学作品对女性人物的观看塑造与电影作品对女性凝视的观看惯性不谋而合。本文观察“第五代”导演与严歌苓的改编及合作,包括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和《归来》、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李少红导演的《妈阁是座城》,此外,冯小刚导演与前三位导演年龄相近,与严歌苓经历相似,并且具有不凡的艺术影响力,因此其导演作品《芳华》也被划入这个序列。重点探讨“第五代”导演这个艺术群体在严歌苓的女性文学视域下,如何从女性生存的情感道德入手,体察女性主体所经历的时代事件,并以此观照作者和导演在文学和电影两个文本中,对女性心理与人性抉择的个体写真,以及对女性苦难与创伤历史的集体寓言。
一、“她者”:凝视中的欲望与权力
严歌苓文学作品及其电影改编的观看解构,可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先行探察:中国成长记忆、美国求学经历、好莱坞编剧经验,共同作用推动她成为一个“写作的游牧民族”。这样一个跨文化的女性职业作家,其创作多从民族与民族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罅隙,体察女性的生存困顿、人性的复杂幽微与时代的混沌蒙昧。
“他者凝视”的观看态度和观看角度,几乎作为标志性前景放置于严歌苓的多部作品中。“他者凝视”由两个文化语境构成:一是全球化背景下关于性别、种族、政治的后殖民主义,即为意识形态层面中把持凝视权威的西方宗主国,对作为被殖民的黑人、东方或其他族群的政治凌驾;二是网络信息化时代中关于视觉技术与影视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即为作为男权社会统治主体的男性,对处于“第二性”地位的女性施展权力压制与欲望投射。严歌苓作品以时代重大历史事件为政治隐喻切入点,叙事重点聚焦于女性形态各异的生存境遇,这种用女性生存隐喻历史境遇的寓言式结构,恰巧正是跟她同时期成长的“第五代”导演表现历史的影像偏爱,“第五代的艺术家则是要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断裂带,通过将个人的创伤性‘震惊’体验的象征化,来完成与中国历史生命的重新际会”。张艺谋对女性与历史的东方主义民族叙事,陈凯歌对历史与人性的悲剧性冷峻反思,李少红一以贯之的女性与历史表达,冯小刚对性别关系的市民文化喜剧表达,都与上述两种“他者凝视”的文化钩沉不谋而合,并且五部作品始终围绕女性角色多角度构建对历史与人性的凝视观照,故本文归纳这种观看形式为“她者凝视”。
(一)欲望指涉: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
严歌苓笔下关于女性的观看和凝视,不仅有女性一贯被凝视的欲望客体塑造,同时有女性主动地、无意识地对外界展开凝视与展露欲望,这种女性作者创造一个女性去观察女性,特别经过电影改编之后更加直观地呈现女性的凝视与欲望,极大程度地减少了女性的被看惯性,体现出既充满女性个人情绪质感又不失客观观察态度的自我意识萌发,是女性作者笔下层层嵌套对女性的凝视体验与欲望觉醒。
《金陵十三钗》建构了三层“她者凝视”,集中体现了殖民政治的权力压迫和女性主义的欲望投射:最表层的凝视毋庸置疑是影片中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宣泄,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士兵对中国妇女奸淫掳掠,影片情节的最大危机即是日本士兵对女学生们的残暴占有,同时还有美国人约翰对妓女们特别是玉墨的垂涎,但在日本士兵的危机压迫下,约翰对妓女们的欲望转化成了对女生们的救赎以及对妓女们舍身救人的敬仰,这里日本男性和美国男性对中国女性的欲望凝视,隐喻着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凌驾。第二层凝视则是妓女们对女学生的欲望救赎,她们作为影片中唯一的色彩符号,背负着“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千古骂名,相对女学生来说是整个道德话语中最底层边缘的群体,但她们却在危机爆发时刻挺身而出,代替女学生们英勇赴宴/赴死,此时她们不仅拯救了女学生的生命,还有对自我道德和灵魂的救赎,“欲望被赋予了创世记的意味:女性因欲望而沉沦,又因无欲而获救”。第三层凝视是贯穿全片关于书娟的“她者凝视”,导演通过设置“玻璃花窗”的影像符号,特别强调了视觉上的凝视行为,不断深化凝视与观看的感官体验。
无独有偶,《芳华》的“她者凝视”用年轻女性的身体写作展露青春情绪的欲望萌动,又用体味、军装、海绵等事件的身体鄙夷将何小萍驱逐出青春集体,而何小萍在刘峰遭遇道德流放之后开始失去对集体的归属感,最后精神死亡于被压抑不得释放的情感欲望。《妈阁是座城》的“她者凝视”体现在梅晓鸥自身理智与欲望的争斗,作为“叠码仔”,物欲驱使她迎接着赌客们的光顾,作为女人,情欲让她爱上赌客又不得不让她将赌客们赶出赌场。
(二)权力机制:身份人格的自我认同
“凝视的概念描述了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当我们凝视某人或某事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看’,它同时也是在探查和控制……我们的目的是控制它们,如视觉所扮演的角色和在社会身份的形成中看的动力学。”作者和导演对人物角色寄望重大,主要人物的身份处境错综复杂,因此,凝视行为中原本就存在的性别权力关系经过人物塑造之后,从单一的性别权力转向个体向集体社会的价值认同,更为精彩的是在这种个体与社会的权力角逐中,创作者还建构了个人对自我心理的身份认同和人格指认。
非已有小说原著改编,而是由严歌苓亲自操刀与导演陈凯歌合作编剧的《梅兰芳》,将历史指涉作为背景隐于剧情和人物之后,在同样具有视觉观看属性的电影银幕与戏曲舞台之间,别开生面地将“她者凝视”放置在导演个人经验对民国文化、戏曲艺术、时代人物的视觉中心主义解构上,围绕梅兰芳经历的凝视行为,展开从性别权力到身份权力的认同探讨。
梅氏经典剧目全是以女性身份示人,旦角的舞台扮相赋予他的假面性别俨然已经越过生理性别,使他在社会层面的性别指认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女性,因而影片中的梅兰芳因其女性扮相和职业身份,完全足以作为“她者凝视”的行为主体。影片中各种凝视梅兰芳的人都试图定义他的形象性别,与此同时,贯穿全片关于伶人权力地位与价值尊严的改写命题,使得观看梅兰芳的人们对他的性别想象与身份认同处于一种极为胶着的快感中。一方面为他精湛动人如臻化境的女性扮相戏曲演艺所折服,另一方面传统观念对伶人戏子“下九流”的贬低使他们不敢坦然表露对他的仰望和崇拜,并且梅兰芳还是女扮男装,这极大地挑战着近代社会封建与开明之交的道德体系。对梅兰芳女性形象的认可是一种带有耻感的夸赞,假面性别的印象在人们的凝视中越被深化,真实性别的存在于他自己的认同中就越发模糊。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性别认同中,影片将小我的焦虑转移到民族的危难:面对日本军官的强硬威逼,梅兰芳说出“在台下我是个男人”,坚决捍卫民族气节与个人尊严,在众多记者的注视下表明自己暂且搁置的舞台人格,并且蓄须明志,以男性面貌示人。
《归来》的“她者凝视”则建立在冯婉瑜心因性失忆后对陆焉识的反复等待,她对陆焉识的在场凝视与失效辨认映射出她对自己妻子身份的持续追寻,以及伴随身心权力失效之后道德(被方师傅欺压)与亲情(被女儿出卖)的认同失败。《芳华》的“她者凝视”体现在何小萍终生性地被边缘经历,无论是父亲遇难后母亲重组家庭的亲情被边缘,还是进入文工团后个人价值与人格尊严的身份被边缘,都指向她在集体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全方位坍塌。
二、“地母”:创伤历史的神化女性
“地母”是严歌苓笔下女性的一个典型意象,几乎能够概括她作品中所有女主角。“地母”意即“大地母神”,像土地一样卑贱,饱经创伤,却始终包容、坚韧慈悲的女性。严歌苓对“地母”人物的塑造,并不是简单地遭遇苦难,而是在建构宏大历史语境的前提下,绕开大多数和群体性的寻常生活,选取深藏在集体历史角落的边缘人物,通过描写这类边缘人物的苦难经历,特别是边缘女性与历史、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际遇勾连,以受难的女性折射苦难的历史,展现传奇性的人物经历与时代性的创伤记忆。“历史的暴行和权力往往把女性放逐出这个世界,但恰恰是女性完成了对历史最后的救赎,是女性‘地母’般的宽厚和爱缝合和温暖着历史的裂痕和伤痛。”
(一)极致情境:创伤经验的时空叙事
严歌苓笔下的故事“不传奇,毋宁死”,她十分偏爱制造大起大落的戏剧性情节,企图在饱满的戏剧张力中表现“地母”人物苦难的撕裂和包容的愈合。她无暇顾及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温馨,而是专注于挖掘特殊历史环境中的特殊事件,并将这些特殊历史“抽象化为极致情境,来让她的人物为难、碰壁、逾越、疯狂,从而陷入剧烈的耻感、痛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法明言的快感”。在极致的发生情境中钩织复杂细微的人性惊变,这样的极致情境一般具备三个元素:民族性的历史事件(时间)、文化芜杂的城市(地点,大空间)、特殊意义的封闭场所(场景,小空间)。文学文本体量庞大但传播效果较为间接,故对时、空、景的叙述全面而详细,电影文本体量精悍且传播效果十分直观,故对时间、空间的表现大而化之,重点表现饱含情节深意的封闭场所场景描写。
作为时间构成的民族性历史事件,“二战”和“文革”是严歌苓爱不释手的两个叙事语境,一个属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一个属于民族内部的纷乱,这样两个关于民族的时代性苦难历史催生着严歌苓笔下极致情境的构建。《金陵十三钗》正面直写了南京大屠杀对中国国民的创伤经验,尤其是日本军官对中国女性的性虐杀,展现了整个中华民族遭遇的苦难经历,以及受难民族中被残忍迫害的底层女性。《梅兰芳》则是侧面描写南京大屠杀前后时代人物价值判断的变化,体现了梅兰芳作为民族艺术家尽管痴心于戏曲表演,但在民族危难面前坚决捍卫民族尊严的宁死不屈。《妈阁是座城》也可作为战争迫害的延续划入这个序列,它虽然不涉及战争发生进行时的破坏冲击,但着重表现了澳门作为战后殖民地的战争遗留,在殖民历史中被别国统治的苦难经历。
“文革”对于严歌苓及“第五代”导演这样一批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群体意义特殊,“文革”发生时他们正在成长,政治倾轧并未直接作用于他们的身心,而事件结束之后的全民思想解放、经济腾飞又极大地拔高了这群人的话语地位,并共筑了新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艺术高峰。“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对于“文革”经验的书写更多属于跨文化的文化移植与文化想象,她所记叙的是宏大历史之下被淹没的边缘个体,用凄美细腻的笔调解构历史洪流中百经冲刷的个体人性。严歌苓人性话语之下的“‘文革’经验”,在“第五代”导演的影像中充满了“后伤痕”对宏大历史的泛化倾向,如《归来》大幅度删减《陆犯焉识》中“文革”发生时的苦难经过,影像重点聚焦于人物在遭遇苦难之后的情感指认;《芳华》在叙事与情节方面表现了主流历史话语下边缘人物的苦难经历,而情感偏向则是作者严歌苓和导演冯小刚对文工团共同记忆的青春追忆。
另一方面,城市上接历史下连场景,糅合时、空、景,描摹含蕴丰富的共时性城市文化,在碰撞激荡的文化间隙中推动极致情境朝向最具戏剧张力的状态生成。《金陵十三钗》让人一目了然,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战火纷飞如同炼狱般的南京城内,却保留一座超脱于日本侵略势力与中国被害民族二者之外的天主教堂,教堂这个封闭场所既勉力抵抗着外界的战乱危机,又承受着保护、延续内部女性贞洁与民族尊严的秘辛。《归来》原著中主要的城市景观是上海,反映了陆焉识留洋归来知识分子的身份,改编电影去除了上海城市,而是放置于不具名的北方某城市(拍摄地为天津),影片中最为重要的情节场景是火车站,冯婉瑜在火车站与陆焉识分别,又周而复始地奔赴火车站等待陆焉识,火车站象征着陆焉识肉身归来后精神身份的物是人非,以及冯婉瑜对陆焉识归来无限次失效的等待。《芳华》弱化了城市景观的叙事作用,没有特别提出事件发生的城市地点,但是它重点突出了封闭场所的场景构建,这是坐落于我国西南部某城市的文工团,严歌苓和冯小刚共同的文工团记忆将它美化成一个世外桃源,无论外界是政治动荡还是战争离乱,里面都只有激昂的音乐、灵动的舞蹈、青春的胴体,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或者集体,而承载着创作者对美好青春的想象性补偿,抽象为苦难环境中人性的萌动与质变。《梅兰芳》的城市景观经历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的位移,戏曲舞台则是两个城市景观共享的叙事场景,戏台记载了梅兰芳整个人格形成和传奇经历,战乱前北京的戏台见证着梅兰芳在改革戏剧形式中的挣扎成长,以及他和孟小冬短暂而珍贵的合作时光,还包含了导演对北京城市和京剧艺术的文化情结,战乱中上海的戏台则见证着梅兰芳坚贞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的个人尊严。《妈阁是座城》的“妈阁”即为澳门,叙事场景则是澳门城市最具代表性的赌场,原著中梅晓鸥及其家族关于赌场的沉浮俯仰,伴随这个城市从传统妈阁到现代澳门,在殖民历史的影响下关于赌场的利益风云,电影中则更多表现了澳门回归之后内地人群涌入澳门,梅晓鸥在赌场里面经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变化。
不难看出,教堂、舞台、火车站、文工团、赌场,都处于时间和空间急剧动荡的苦难遭遇过程中,作者和导演创作中的这些封闭场所却好像隔绝了外界的纷乱惊险,作为叙事场景编织着苦难人物的纯粹情感,是“地母”们慈悲人性的滋养温床,更是她们在苦难历史中保留无私包容大爱情怀的精神乌托邦,使原本满目疮痍的创伤经验变得柔情无限。
(二)地母再造:创伤记忆的温情回顾
“地母”的女性形象同时存在于小说原著和电影改编两类文本中,但由于不同的媒介属性,“地母”的形象塑造也发生了从表现创伤经验到表现创伤情感的重点迁移。作为文学文本主导者的严歌苓,构建特定事件中的时空叙事,通过制造历史、政治等社会性灾难的极致情境,呈现“地母”女性经历的时代性遭遇及其苦难创伤经验,作为电影文本主导者的导演,承接了严歌苓小说原著的时空构建和时代语境,进一步细描“地母”女性的情绪质感,站在后伤痕时代对创伤体验展开更具娱乐观赏属性的泛历史情感叙事。
《归来》和《芳华》是创伤记忆的一体两面,前者是“选择性失忆”,后者是“选择性记忆”,不约而同地在原有包容慈悲的“地母”塑造上,虚化创伤经验的悲情色彩,着重凸显了创伤记忆的情感温故。
小说《陆犯焉识》对严歌苓来说意义特殊,主角陆焉识的原型人物就是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因为对祖父的追念和家族亲属的嘱托,在这部作品中严歌苓罕见地以男性角色为描写重点,以男性视角为叙事切入,她将《陆犯焉识》完成得如同一本详尽的人物传记,仔细记录了陆焉识从小到老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生际遇,主要通过三次“出走—归来”的事件描写,形构陆焉识作为一个叛逆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的激荡剧变中反复寻找自由和归属。电影《归来》几乎重铸了《陆犯焉识》对自由追求、人性幽微、历史省思和时代变迁的多重观照,只选取了原著小说后三分之一的第三个“出走—归来”事件,叙事重点从男性陆焉识转向了女性冯婉瑜,着重表现冯婉瑜后半生的创伤情绪,以及陆焉识归来后对冯婉瑜创伤经验的体察。原著小说用小人物的人生波折表现大历史的动荡起伏,精彩纷呈的人物经历之下是沉郁厚重的历史印记与时代症候,改编电影将小人物和大历史都虚化为通俗剧的情节符号,剧情容量大幅删减之后的人物趋向表浅,观众无法得知冯婉瑜在陆焉识被迫流放之前早就遭遇着家庭和情感的重创,也只能从影片的浮光掠影中捕捉陆焉识的知识分子身份属性,同时由于影片重点表现的创伤人物是冯婉瑜,但最主要创伤事件“文革”的亲历者却是陆焉识,在这种情节与人物的重点错位下,标志性的时代语境被隐藏在角色的情感纠葛之后,时代事件的文化精神被消磨成叙事情节的前因或说缘起,不再具备对伤痕文艺作品的痛感体悟,而是对简单人物的温情回顾,“此种选择性遗忘,在影片叙事层面,或者在整个电影创作层面,无情地以‘缺席的在场’之方式,醒目地指向着‘历史’的被悬置”。
《芳华》也是充满作者个人经验的应邀之作,严歌苓和冯小刚年轻时都在文工团学习、生活过,但是严歌苓的女性视角和冯小刚的男性视角,在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中对文工团生活的表现,明显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面貌。原著小说《你触碰了我》主要讲述了刘峰、何小曼(电影中为何小萍)两个边缘人物的受难经历,他们一个是近乎神化的人,一个是始终矮化的人,在历史动荡时期被放大的集体遮蔽中,不断遭遇来自集体的抛弃和放逐。电影《芳华》对苦难人物的表现止于有所节制的惋惜感叹,更多的是饱含怀旧追思的温情描摹,“一部以政治/历史叙事为创作初始与视觉表象的影片,却在其深层结构上意指着当下的商业/消费文化,因了这种暗度陈仓的叙事策略,那段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定义的特殊历史,以及刘峰/何小萍的惨烈人生,却被机巧地转换为一种感伤与怀思的情绪”。特别是对于文工团这个符号化集体的青春记忆,甚至可以说《芳华》的主题刻画聚焦于性和暴力两个重点:影片对于文工团女兵的身体写作展露无遗,裸体淋浴,跳舞流汗,泳池嬉闹……性感场面肆意宣泄的荷尔蒙俨然和青春记忆画上了等号,关于主角刘峰的情感叙事重点表现人物的性萌动以及随之而来遭遇的道德暴力,同样关于何小萍的人物塑造也围绕被压抑的性萌动和层出不穷的道德暴力,影片在这种关于性的自然力量无处释放,和道德的规矩力量铺天盖地二者角逐之间,巧妙侧写了遮天蔽日的集体话语下,边缘人物被撕碎蹂躏的蒙昧人性。
结 语
严歌苓构建的“她者”语境,在凝视行为中塑造女性自我的欲望觉醒与身份认同,关于创伤历史的表述,则着力于时空叙事中的极致情境铺排,进入导演的影像视野中,“她者凝视”的视觉观感在色彩、构图和场景间有效放大,女性灵活跳跃于欲望主体与客体、身份认同生效与失效的多元间,同时切肤之痛的创伤经验经过泛历史叙事的柔焦,转化为真情守望与温情回顾。文字细致描摹了人生际遇与时代记忆,影像传神体现了情绪触觉与温情回忆,严歌苓和“第五代”导演的改编与合作,提供了一个严肃规范的文学与电影的媒介融合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