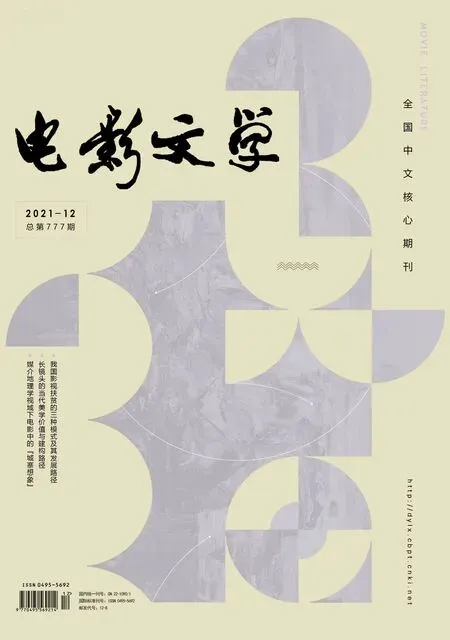民俗化的意义世界构建
——论近年来台湾地区电影民俗化创作的新趋向
2021-11-13李孟阳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临汾041000
李孟阳(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由电影《海角七号》所引发的台湾电影复兴浪潮以来,台湾电影就愈发自觉和普遍地在创作中从民俗文化里汲取养份,整体出现了一股明显的民俗化创作潮流,产生了众多民俗色彩鲜明的电影作品,如《流浪神狗人》(2007)、《蝴蝶》(2008)、《第四张画》(2010)、《鸡排英雄》(2011)、《龙飞凤舞》(2012)、《阵头》(2012)、《总铺师》(2013)、《大喜临门》(2015)、《神厨》(2016)等。近几年,这股民俗化创作潮流出现了新的创作趋向,出现了诸多民俗色彩更加鲜明的电影作品,其中又以《血观音》(2017)、《大三元》(2019)、《寒单》(2019)等电影最具代表性。总体而言,这些电影之所以能够代表一种新的创作趋向,原因在于这些影片在创作之初就结合导演对于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的深入认识,在创作中做到以民俗事象统领影片的形式和内容,运用民俗化的影像内在逻辑,建构起一个个鲜活的民俗化的意义世界,进而表达了在地民众的集体生活情感,并最终通过影片凸显了民俗的族群认同功能,有力确证了海峡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这一客观事实。
一、民俗事象:统领影片的形式与内容
自觉、普遍和广泛采用民俗文化是台湾电影民俗化创作潮流中的一大特色,近年来的这些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同样如此,均呈现出诸多鲜明具体的民俗事象。然而,近年来的这些电影在创作过程中对民俗事象的具体运用与之前的电影有所不同,表现得更加精进、全面和有机。具体来讲,影片导演从创作之初的构思到创作过程中的操作实践,都充分考虑民俗事象之于影片整体的结构性意义,在深入认识民俗文化的基础之上,巧妙运用民俗事象,以民俗事象统领影片的叙事形式与故事内容,使二者形成一个彼此交相呼应的整体关系。
《血观音》是导演杨雅喆创作完成于2017年的电影作品,该片是近年来台湾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的代表作品。片中最为突出的民俗事象是念歌艺术。念歌于清道光年间已经存在,是盛行于闽南及台湾一带的说唱艺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两百年来,念歌艺术深入民众的生活,不仅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娱乐,也发挥了劝善教化、新闻传播、政治宣传、宗教宣扬、历史传述等种种社会功能。该片之所以能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离不开导演对民俗文化的深入认识,以及对民俗事象的巧妙运用。导演杨雅喆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之所以会借助念歌艺术来讲述一个关涉善恶有报主题的故事,一是因为导演认为念歌艺术是一种说书形态,说书作为一种古老的叙事形态,会经常讲述一些曲折离奇、善恶有报的故事,这种叙事形态会与故事主题更为接近;二是导演认为借助于念歌艺术的使用,当念歌说唱者出场讲故事时,会迅速让那些无论是否听过说书的观众立即感受到一种亲切的讲故事的氛围。
在导演的这种认识下,影片通过对念歌艺术的巧妙使用,在叙事形式上为观众设置了一种听念歌说唱者“讲故事”的氛围,并与影片善恶有报的故事内容相结合,高度完整地呈现了一个“拍案惊奇”的戏剧性故事。影片开篇,导演首先为故事的发生设置一个悬念,再通过两位盲人说唱者(由我国台湾著名念歌艺术大师杨秀卿和储见智出演)带着悬疑评判口吻的说唱,概括了一个已经发生过的善恶有报的故事,即“别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实神明都了解,善报恶报、早报晚报,善恶终有报……我要说的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由此形成一个较强的电影叙事张力,利于吸引观众的兴趣,营造一个说唱者“讲故事”、观众“听故事”的良好氛围,与故事善恶有报的主题相呼应,预示了影片传奇式的叙事特征。同时,片中每到故事进展的转折处或关键时刻,说唱者都会出现,站在一个全知者的角度,或补充故事情节;或预告故事,设置悬念;或对即将发生的故事进行善恶因果评判,很好地衔接和厘清了故事剧情,加深了“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氛围。影片结尾,在所有人事关系理清之后,说唱者又出现,通过轻柔的唱词,配合着体现整部影片主旨的字幕——“世上最可怕不是眼前的刑罚,而是那无爱的未来”,为说唱者所讲述的传奇故事做了一个总结,呈现出三位女主人公的性格命运走向,凸显影片主题,同时也将电影收尾。从影片的整个叙事流程上来讲,虽然念歌说唱者只出现五次,但由念歌说唱者所引起的“我为您讲故事……故事讲完了”的听讲故事氛围却贯穿了整个叙述,并有效地将影片善恶有报的故事内容完整地包围在这个“引子—尾声”叙事模式框架之内,使影片的叙事形式与内容形成彼此照应的合力关系。
《血观音》在创作中巧妙运用民俗事象的方式,不仅区别于之前的台湾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而且还对之后的台湾电影创作产生了直接和有效的影响,影片《大三元》和《寒单》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大三元》被台湾媒体称为台湾20年来第一部关于麻将的贺岁片,显而易见,影片是以传统民间娱乐民俗中的麻将为主要叙事对象。影片在开头和结尾处以第三人称说书人画外音的方式为影片营造了听说书人讲故事的氛围,搭建了一个“引子—尾声”叙事模式框架,并且在这个叙事框架之内以麻将为叙事载体讲述一个类似于王子复仇记的、善恶有报的亲情故事。
黄朝亮是一位善于抓取和使用民俗文化的电影导演,《寒单》是其最新创作的一部以台东民俗“炸寒单”为主要内容的电影作品。导演是土生土长的台东人,对台东当地元宵节所进行的“炸寒单”活动非常熟悉,且曾经拍摄过一部关于这一节俗活动的纪录片,所以导演对于“炸寒单”的节俗内涵和扮演“寒单爷”的人的内心情感有深刻的理解。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导演才一改之前创作剧本时先设定故事框架,后根据故事框架填入人物的创作方法;而是在创作之初根据原有的理解和一些对于剧中人物的想法,进行实地走访,然后把适合的内容放进剧本。在这种创作思路影响下,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做到了依托民俗事象来统领影片的形式与内容。具体来讲,影片开篇的字幕不仅告诉观众“炸寒单”这个节俗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内涵,还预告了影片即将讲述一个发生于台湾东部小镇,关于“炸寒单”的故事,用文字为观众营造一种类似于说书人“讲故事”的氛围。这种开篇形式显然与“引子—尾声”结构中的“引子”作用相同,而这个“引子”不仅成功地将整个电影叙述包围在一个“讲故事”的氛围之中,且使得影片的故事内容、人物情感、主题表达都围绕着“引子”中的赎罪内涵来设定、展开,从而促使影片的叙事形式与故事内容融为一体,讲述一个以赎罪为主题的电影故事。
总之,从对民俗事象具体运用的层面来讲,相较于之前的台湾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近年来以《血观音》《大三元》《寒单》等为代表的影片,通过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运用民俗事象,做到了以民俗事象统领影片的形式与内容,从而使得民俗事象的呈现愈加有机合理,彰显了影片的民俗化风格。
二、民俗化的内在影像逻辑:民俗化影像风格的提升
之所以认定近年来的这些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代表了台湾电影民俗化创作潮流的新趋向,首先是因为这些电影在对于民俗事象的使用上,做到了与影片整体叙事形式和故事内容的有机结合,这是它们与之前的电影相比最为直接和鲜明的区别。更为重要和突出的区别在于,在民俗事象统领影片的形式和内容基础上,这些电影的内在影像逻辑也表现得更为民俗化,即在民俗化的电影语言思维引导下,这些电影通过风格化和民俗化的场景设置,适应性地选择和使用特定的电影技巧,巧妙地形成了影片整体民俗色彩鲜明的形式系统。正如大卫·波德维尔所说:“在任何一部影片中,某些技巧通常会形成自己的形式系统。而每一部影片在格式化的形式系统中,也会发展出特定的技巧。这种对于特定技巧的选择,在电影中呈现出具有统一性、发展性,且富有意义的手法,我们称作风格(style)。”事实上,在近年来的这些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中,民俗化的影像内在逻辑运用相当普遍,而这些电影也正是通过运用这种民俗化的影像逻辑生成了影片民俗色彩鲜明的形式系统,从而明晰、强化并最终提升了影片民俗化的影像风格。
影片《血观音》中,念歌说唱者总共出场五次,每一次出场时的场景设置都有着鲜明的风格化特征,从视觉和心理两个层面上彰显了影片场景设置上的民俗化色彩。例如,念歌说唱者第一次出场时的场景空间被精心设计成类似于民间信仰文化里地府阎罗殿的场景。台上是两位说唱者犹如审判者般分坐在阎罗王旁边弹边讲,以及一面以镜中画的形式播放着故事画面的镜子;台下地板上萦绕着一层用干冰制造的烟雾,牛头马面、手持刑具的小鬼以及即将被审判、处决的犯人分列其中;阎罗殿的两侧设置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下联是“善报恶报迟报早报终须有报”,横批是“你可来了”。整个场景空间布置得颇为讲究和精致,不仅重点突出了两位念歌说唱者,而且透露着一种阴森、诡异和审判的气氛,极具民俗化的风格色彩。事实上,随着时代变迁、市场需要和念歌艺术自身发展,念歌艺术的演出空间和环境布置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最初的简陋化逐渐发展为当下的精致化。正如台湾学者吴姝嫱在其著作《台湾念歌研究》中所说:“由此可见,发源于街头的念歌,进入表演厅,成为舞台艺术的演出节目之后,也开始利用戏剧的元素,运用布景、灯光、音响和服装,将念歌演唱精致化,借此吸引更多的观众。”实际上,影片中这种说书人场景设置,一方面从单纯的视觉层面加深了观众对影片中所呈现的念歌艺术的印象;另一方面则协助影片制造一种听讲故事的氛围,辅助影片建构一个由说唱者所引导的故事世界,从心理上引导观众逐渐进入到念歌说唱者所营造的叙事世界之中。
《血观音》民俗化的内在影像逻辑不仅体现在民俗化的场景设置中,同时也体现在特定电影技巧的选择和使用上。影片大量出现的移焦摄影技法和回忆手法的运用对观众来说极具引导性,有利于将观众对电影剧情进展的思考逻辑牢固地框定在由念歌说唱者设置的叙事流程和话语之内。作为一部剧情片,影片并没有采取主流剧情片中较为常用的经典好莱坞连续性剪辑手法来推进叙事,而是在诸多关键性的情节段落中大量使用移焦摄影,赋予单个镜头更多叙事信息,从而刻意引导观众视线,以更为直白的方式来表现剧中人物的心理状态,披露情节信息,承上或者启下,推进剧情发展。例如,片中有一个镜头是王院长夫人和林桑在谈论buffet,王院长夫人明确表示不赞成buffet这种餐食方式,下一个镜头紧接着就切到了棠夫人端坐的中景画面,这个镜头运用的正是移焦摄影。棠夫人坐在前景位置,后景是buffet餐台和端着盘子的客人,前后景之间以珠帘相隔。镜头先对焦在棠夫人和珠帘之上,后景模糊,而后镜头又对焦在buffet餐台和端着盘子的客人身上,前景是模糊的棠夫人镇定自若的笑容画面。这个看似略显粗糙和直白的镜头运用方式,一方面很好地表现出了棠夫人此时外表镇定、内心尴尬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则为接下来棠真去厨房通知修改菜品的情节段落做了铺垫,从而用电影摄影的方式与念歌说唱者讲述故事时对于人物心理状态和情节进展的语言表达相契合。另外,多次穿插在影片整体线性故事讲述流程中的回忆手法,很好地补充了叙事信息,解释了剧情。例如,片中多次重复穿插出现棠真回忆自己在马场偷听Marco和林翩翩谈话以及向林夫人讲述追马细节的情节段落,且每一次回忆段落的出现都有新叙事信息披露。这些回忆段落的多次穿插运用不仅对剧中棠真、Marco和林翩翩三人之间的关系有进一步说明,很好地解释了棠真的人物行为,而且在叙事流程上设置伏笔,衔接和解释了剧情,吸引了观众兴趣。事实上,在现代电影当中,诸如移焦摄影技法、时空复现回忆手法的运用已经相当普遍。但是,之所以认定《血观音》中使用的这些手法具有民俗化的电影语言思维,关键还要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叙事流程和话语之内。上文已经做出分析,《血观音》中,念歌艺术的运用统领了影片的叙事形式和故事内容,而这种手法的运用很好地转变了影片的叙事视角,将影片的叙事话语切换为了念歌说唱者所引导的叙事流程和话语。为了匹配这种说书人叙事流程和话语,导演才会在影片内在影像逻辑上做出选择,以移焦摄影技法、回忆手法等直白、刻意和富有引导性的电影技巧,与传统说唱艺术浅显直观、通俗易懂、善于重复、善用倒叙和伏笔等吸引观众的讲述特点相契合,从而生成了影片民俗化的内在影像逻辑。
所以说,电影《血观音》中民俗化色彩鲜明的场景设置以及民俗化电影语言思维的运用,共同形成了影片民俗化的内在影像逻辑,为影片生成了民俗色彩鲜明的形式系统,继而提升了影片民俗化的影像风格。事实上,在近年来的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中,《血观音》表现出的这种民俗化影像内在逻辑颇具代表性,其他影片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诸如《大三元》《寒单》等,这些电影也通过民俗化的影像内在逻辑,生成了民俗色彩鲜明的形式系统,深化了影片民俗化的影像风格。
《大三元》通过第三人称说书人画外音的方式转变了影片的叙事视角,在说书人的叙事话语之内讲述了一个围绕麻将而生成的虚构故事,因此,影片的内在影像逻辑围绕着说书人和麻将有了相应的安排、设置和匹配。一方面,影片在画面安排、场景设置和人物身份设定上具有鲜明的民俗化风格色彩,有效地引导观众进入了影片所设置的说书人叙事场域之中。例如,片名出现之前,伴随着说书人戏说麻将起源的画外音,出现的是与说书人话语同步的、有关麻将起源的动画画面;片中有着诸多详细的关于剧中人物打麻将的场景设置;剧中人物的姓名大多与麻将有关。另一方面,影片通过特定的镜头运动方式在影片的场景设置、人物出场介绍等方面与传统说唱艺术的讲述特点做到了匹配。例如,影片时而运用缓慢的由全景到中近景的摇镜头,时而使用快速的推拉镜头,以及富有吸引力的划像转场特效,来实现场景的切换,从而与说书人讲故事时的时空转换方法相契合;影片在设定剧中人物首次出场的方式时,多利用快速夸张的推镜头,并结合人物姓名字幕对人物进行近景表现和介绍,从而与说书人用语言介绍人物的方法在观众接受心理上形成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大三元》在场面调度和镜头摄影方面民俗化的电影语言思维运用,使得影片具有了民俗化的内在影像逻辑,强化了影片民俗化的影像风格。
《寒单》依托元宵节的节俗活动“炸寒单”,围绕着“炸寒单”的节俗内涵,讲述了一个以赎罪为主题的故事,因此影片不可避免地对“炸寒单”的具体场景进行细致展现,而影片民俗化的内在影像逻辑就体现在对“炸寒单”这个节俗场面的展现和运用上。片中对民俗事象的呈现不再只是偶尔地表现民俗活动的部分环节,而是在全片中结合人物关系、情节发展、赎罪主题,多次运用类似于纪录片拍摄的影像手法,尽量真实、客观和完整地将现实生活中“炸寒单”的节俗活动场景细致展现出来,从而一方面加深观众对于节俗流程的印象,深化观众对于节俗内涵和影片主题的了解,另一方面彰显和提升影片民俗化的影像风格。
总之,与之前的台湾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相比,近年来的这些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在影片的内在影像逻辑上有着显著的民俗化特征,也正是这种民俗化的内在影像逻辑使得它们具有了更加明显的民俗化影像风格,从而与之前的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形成了更加突出的区别,在影片风格打造上达到了台湾地区电影民俗化创作的新高度。
三、民俗化意义世界的建构与表达
从民俗学的角度上讲,民俗既是传统,又是生活。作为生活的民俗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是民众生活情感的表达,民众借助于民俗满足日常的生活,借助于民俗表达思想情感和文化心理。因此来讲,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就是民俗化的世界,民俗化的世界就是民俗与民俗主体和发生情境所构成的活动整体,“因而,民俗是集体心理、行为和语言的模式化情境下的生活表达”。
实际上,近年来的这些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通过对民俗事象的巧妙运用,使得影片的电影世界呈现为一个鲜活的民俗化的意义世界。这体现在影片的叙事形式依托于民俗事象而建构,影片的故事内容围绕着民俗事象而展开,影片的内在影像逻辑也表现为民俗化的电影语言思维。这就使得影片人为地围绕民俗设计了模式化的民俗发生情境,从而建构了民俗化的意义世界,继而通过影片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心理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可以认为影片所建构的民俗化意义世界就相当于民众民俗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因为透过这个民俗化的意义世界,民俗之于民众日常生活的现实性生活意义被深刻体现出来,现实世界的本真得以显现。
例如,《血观音》《大三元》和《寒单》等电影通过影片所建构的民俗化的意义世界,表达了在地民众真切的集体生活情感。《血观音》依托念歌艺术和菩萨意象这两个关涉善恶有报和宗教轮回的民俗事象,将影片整体呈现为一个善恶因果循环的民俗化意义世界。在这个民俗化的意义世界中,导演将台湾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搬上银幕,对主要人物在权力跟金钱方面的运作进行非常细致的描写,并通过念歌艺术和菩萨意象的运用来表达民众现实的生活情感,满足了民众对于善恶有报这一理想的渴望。影片经由这个民俗化的意义世界,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怀,表达了民众真切的生活情感,满足人们对于世俗种种现象的希冀。《大三元》在说书人的叙事话语之内,建构了一个围绕麻将而生成的民俗化意义世界。在现实社会中,赌博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家庭矛盾因赌博层出不穷,人们迫切希望解决因麻将等赌博方式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在《大三元》所建构的民俗化意义世界中,影片将麻将之于民众娱乐和休闲的意义重点突出,对其赌博性质进行摒除和批判,并通过麻将这个叙事中介和载体表现了在地民众希望家庭和谐团结的美好愿望。影片《寒单》围绕元宵节的节俗活动“炸寒单”,以“炸寒单”的节俗内涵之一——“赎罪”为核心,建构了一个有关“炸寒单”的民俗化意义世界。事实上,影片在创作中重点呈现和运用的节俗活动“炸寒单”,就是台东地区目前尚存且正在被民众进行的一种民俗,每到元宵节,民众通过参与这个节俗活动来满足自己对于生活的某种希冀。在影片所建构的民俗化意义世界中,民众在现实生活中对“炸寒单”这一民俗的心理被深刻地展现出来,即求富贵、还夙愿和赎罪,从而表达了民众面对生活中诸多现实景况而自然形成的生活情感。
总之,这三部影片都通过民俗化的意义世界对民众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映射,表达了在地民众真切的思想、心理和情感。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近年来这些民俗化创作倾向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围绕民俗事象,建构民俗化的意义世界,离不开影片导演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将民俗文化“视作日常生活流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放回到个体或群体的日常起居中,激活其参与现实生活的生命力,而不是将民俗文化仅仅用作故事背景,或建构叙事的装饰性成分”。正是基于此种对民俗文化的全新理解和认知,这些电影才能通过与民俗紧密相连的电影创作既凸显台湾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又构建具有在地精神、在地情感和在地文化的民众日常生活世界,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注和表达,实现电影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深切观照。
事实上,这些电影通过其所建构的民俗化意义世界,不仅表达了在地民众真切的思想、心理和情感,而且凸显了民俗的族群认同功能。“民俗的族群认同功能,是指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内,民俗成为所有成员的思想言行、宗教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社会秩序黏合的标志和记忆的符号,这些标志和符号是群体内部保持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纽带。”具体来讲,这些电影中族群认同功能的凸显一方面体现在民俗化的意义世界所呈现的民俗事象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民俗化的故事意义所表达的文化思想、心理和情感上。
民俗事象纷繁多样,如果将民俗的族群认同功能落实到具体的民众生活和民俗事象之中,那么这些民俗事象在客观上就是各个民族共同体的标志性符号,事实上,它们在本民族内部是自识别性的,相对于其他民族则是区别性的。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民俗是人们认同自己所属集团的标志,例如世界各地的华侨,虽然身处异地,但他们通过讲汉语、吃中餐、过中国传统节日等方式,与自己的民族保持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血观音》《寒单》和《大三元》等为代表的这些影片通过民俗化的意义世界所充分展现的民俗事象毫无疑问的是中华民族族群共同体意义的认同符号。例如,从影片中民俗事象的呈现上来看,《血观音》中的念歌艺术虽然是台湾念歌说唱者杨秀卿经过改良以后产生的“口白式念歌”,但是追溯念歌艺术的历史可以发现,念歌艺术于清朝道光年间已经出现,是盛行于闽南及台湾一带的说唱艺术,只是清代闽南地区的汉族移民台湾之后,将念歌艺术带到台湾,并且在怀念家乡、开拓家园的过程中对念歌艺术进行了地方性的改变。影片中的菩萨信仰也属于中国人极为看重的佛教信仰,这点无论是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三元》中的说书作为一种传统的说唱艺术,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起源很早、影响深远的民俗艺术。麻将牌同样是起源于我国的一种民间游戏娱乐民俗,原称麻雀牌,它是中国人在长期社会生活和劳动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大众化的游戏形式,“在其从起源到定型的发展过程中,被注入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精华元素,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并且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品位和生活习性”。《寒单》开篇的字幕已经对“炸寒单”这个节俗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不仅说明其来历、活动内容和具体内涵,且介绍其目前在台湾的现状,这已经鲜明地将其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岁时节日——元宵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个略显陌生的节俗活动,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目前不仅存在于我国台湾地区,且在福建地区同样流行。
民众生活在特定的民俗中,长期受到民俗的熏陶和培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民俗汇聚为一种文化根脉情结,紧紧地将个人与群体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在具体的空间内又具象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表达,诸如语言、行为、信仰、文娱、制度等,成为群体内部自识别的文化标志和象征符号。当人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和家乡之后,他们对于群体的观念、对于家乡的观念就浓缩在民俗的点滴之中,体现在风俗风物、行为举止、心理表达等之中,深深地扎根于民俗文化的心理之中。从这个层面上分析,近年来的这些电影通过其所建构的民俗化意义世界所表达出的文化思想、心理和情感鲜明地彰显了民俗的族群认同功能。譬如《血观音》通过民俗化的意义世界所表达出来的民众对于善恶有报这一理想愿望的渴求,恰恰是中国人从古至今都迫切希望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社会心理;《大三元》建构的民俗化意义世界,表达了影片希望家庭和谐团圆的主题,而这一主题是中国人在家庭生活中一直希望实现且努力奋斗的目标。中国古代诗词里大量关于家庭团圆的诗词也证明了人们对于家庭和谐团圆的渴望;《寒单》通过所建构的有关“炸寒单”的民俗化意义世界,深刻地将民众对于这一节俗活动的民俗文化心理体现出来,即求富贵、还夙愿和赎罪,这也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心理相契合。
所以说,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这些极具台湾本土特色的电影所构建出的民俗化意义世界中,无论是民俗事象的呈现,还是民众思想、心理和情感的表达,都具有明确的民族内部自识别性。基于此,影片自身的民俗族群认同功能得以凸显,进而从客观上加强和促进了台湾民众对于中华民族族群的情感连接,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再次确证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这一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台湾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只是单纯通过对民俗事象的展现来确认民俗的族群性,而近年来以《血观音》《大三元》和《寒单》等为代表的这些影片则借助于民俗化意义世界的建构,将民俗事象与民俗文化心理融为一体来表现民俗的族群认同功能。当前,由于台湾社会相对复杂的历史事实和多元的社会状况,台湾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对于国家、族群和地域认同的迷茫,这也同样反映在台湾电影的创作当中。电影人企望借助于电影创作来理清和确证台湾的真实身份,从而将台湾电影变成了“一个不断挑战和重新定义群体、种族和国家关系的领域”。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将目光投向在地的民俗文化,通过民俗文化来摆脱身份认同危机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
结 语
纵观近些年来以《血观音》《大三元》和《寒单》等为代表的台湾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可以看出,尽管在对于民俗元素的运用上还存在着些许值得商榷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与以往的台湾民俗化创作倾向电影相比,这些电影所呈现出的以民俗化的意义世界构建为核心的电影民俗化创作理念,使得民俗元素在电影创作中的价值得到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体现,为台湾电影的民俗化创作潮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资借鉴、模仿和传承的电影创作策略,丰富了台湾地区的电影艺术创作。另外,更值得重视的是,借由这种电影创作理念的确立和运用,林林总总的民俗文化得以彰显,民俗文化天然具有的、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基因得以显现,民俗文化的族群认同功能得以凸显。基于此,这些影片观照台湾社会现实、表达民众生活情感、和谐在地生活、沟通族群关系等方面的文化价值得以被体认。因此可以确定,近年来的这些电影确实呈现了台湾地区电影民俗化创作潮流的新发展趋向,进一步讲,或许以这样的方式运用民俗文化的电影,才可以说是真正的民俗电影。事实上,分析近十年来的台湾电影可以发现,民俗文化已然成为其创作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成为在地精神和在地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民俗与电影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关系。正是这种民俗化的创作倾向,使得台湾电影在电影美学和电影文化方面拓展了新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