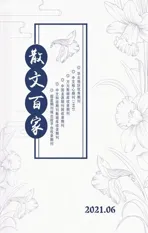三教合流时代下的罗汝芳诗歌
2021-11-12吴同
吴 同
山西大学文学院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谥号“明德先生”,江西南城人。其思想成就被牟宗三先生喻为泰州学派的“唯一特出者”,近溪的邸中壁上刊有“明镜止水以存心,太山乔岳以立身,青天白日以应事,风光霁月以待人。”此四句,不仅刻画出了罗汝芳对其自身的约束,也彰显了其诗学理想,兼顾了他作为思想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有明一代,儒者作为诗人的身份似乎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重视。但是诗歌中饱含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能够反射出作者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态,实是先人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应被人们遗忘在角落。本文拟以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的诗歌为研究中心,从诗歌创作的角度体味思想家关于心学以外的生活情趣和思想诉求。
一、诗与儒——坐起咏歌俱实学
罗汝芳一生为学,是泰州学派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罗汝芳融合自身对于《论语》《易经》的解读,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引领下系统地阐释了天机说、赤子之心、孝悌慈思想、生命之学和大人之学,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了孔孟的思想宗旨,极具教化作用。不过,要论其学说从形成到完善的具体化过程,则是在他一次次的讲学活动中凝练而成的。在罗汝芳晚年的讲学中,时常以音乐和诗歌作辅以配合演讲,时而静默,时而兴叹,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启发个人之天机。作为经教内容之一的诗教向来是儒家传承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在众人吟诗声中,罗汝芳一边阐释和传授实学,一边也言明着自己的诗学态度:诗歌若能表达思想,发挥教育之能,便无需拘泥形式音韵。
言及诗中的音韵问题,罗汝芳也在讲学中有所阐释。众人因歌心斋先生“入室先须升此堂”诗句,而音韵声牙,不得和协,或问其故。罗子曰:“七言八句,是唐人之诗,又谓之律诗,盖唐人作此诗,其字其句、其音韵、其平仄,如法律然,分毫差不得。……至于讲学诸儒,则止以诗咏学,而其律少谙,间或于春夏秋冬之调难合尔。”近溪提倡,诗者有为诗之道,为学者有为学之道。当诗歌用于咏学时,便不应过于苛刻音韵声牙,将所言之工夫讲清楚即可,无需更加发挥。
罗汝芳亦曾被讲堂童子歌诗所感染而强调其教化作用,曰:“天下之善,贵在扩充。吾人能因一念忻喜诸生之心,推之必欲其由壮而老,……教化与,风俗美,其容顷刻怠缓耶!”罗子将诗歌看作一剂能够振奋人心,教人为善的精神良药,并希望能够推己及人,使世人皆能从诗歌中汲取向善的能量。他的许多诗歌都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仁爱天地的情怀,如《题郭梧阳泉鹿图》中,“乔松千尺云俱苍,磷磷石底流泉香。餐松饮泉集群鹿,相呼呦呦鸣笙簧。呦呜式燕邦家光,示我世世欲周行。”诗中意象多引自《诗经》,自然之景,祥和世态,显示了作者自足自适的情怀,也对后人提出了达道至善的心愿。可见,不管在诗学理想还是诗学实践的角度,罗汝芳都致力于用诗歌去传承儒家正统思想。
“由诗歌,便可以和平心气 ;由礼立,便可以坚定德性。”这便是罗汝芳对于诗歌的态度。可见,在罗汝芳的思想体系中,他已然将儒教思想内化于心并传授给平民百姓,从诗歌中领悟真谛,再讲思想凝练入诗歌里面,诗歌与思想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二、诗与禅——三千尽是光明界
杨止菴《上士习疏》云:“罗汝芳师事颜钧,谈理学;师事胡清虚(即宗正),谈烧炼,採取飞昇;师僧玄觉,谈因果,单传直指。”黄宗羲也曾在《明儒学案》中如此评价近溪思想:“所谓浑沦顺适者,正是佛法一切现成,……不落义理,不落想象,先生真得始祖禅之精者。”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则将罗汝芳思想比作“圣学中的禅学”,可见近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然而,罗汝芳直言“禅家之说,最令人躲闪,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转头出来,复归圣学者,百无一二”。因忧虑佛家之学与圣学相冲突,他从不在公众场合讲述禅学。但是在其诗歌作品乃闲暇之作,罗汝芳并没有这样的忌讳,其诗歌中处处可见禅学的踪影。
一般来说,须是明确涉及佛教用语或思想的作品才能被称之为佛禅诗。罗汝芳的诗作不算多,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罗汝芳现存的仅152题诗歌中,光是以佛学为主题的佛禅诗作品就占22篇之多,如《宝陀岩次何冡宰韵》《夜游莲花峰》《董比部过访从姑不遇次谢》《宿罗田岩和罗念庵韵》《石莲洞》等,形式多样,既有古体,也有近体,还有绝句;内容一般以游历佛寺之所见闻或与游山玩水所抒之感居多,其间多佛教意象,如跏趺、尘刹、大士、空花、无生等,充分说明了近溪先生对于佛教的亲近程度。《憩观音岩》为近溪品读胡直之诗后有感而作的一首七言近体诗:“……潮音久漫传沧海,大士今应在翠微。尘剎三千那可度,衡峰七十总堪归。同心况有当年约,我愿风前便拂衣。”这首诗作于南岳衡山。禅意颇浓,潮音、大士、翠微、尘剎、三千都乃佛门用语,潮音在本诗中指僧众诵经之声,磅礴的诵经之声传感到了沧海之外,而菩萨则隐于这青翠掩映的山腰幽深处,作者置身于南岳衡山的清幽环境之中,泉水的清脆宁静和潮音的庄严宏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景色与佛门完美融合。
除了亲临佛寺,在与密友的交谈之中亦可体现近溪的禅趣,《沈玉阳枉顾从姑次韵》便是一首与友人相互唱酬的用韵诗 :“风光林影翠纷纭,秋色山中月正殷。五马旌旄行卷雾,半空楼阁坐看云。香浮瞿衲青莲社,霞衬仙姑紫玉裙。况是清平调歌管,不妨尊酒对晴曛。”在秋色正浓的傍晚时分,和好友坐于山中林舍,把酒对月,在风光林影之中看到了一片仙境与禅境的影像,暗香浮动、仙姑紫裙,伴有清平管调,颇具禅意。此外,在当时,佛寺已然成为士大夫游赏交谈的一大去处。在《董比部过访从姑不遇次谢》中就描绘了诗人与旧友一同游赏佛寺的情形,“松径云俱寂,岩廊客漫经。泠泉寒自响,香供夜谁能。赖有长空月,三更送佛灯。”清幽的禅寺,古朴的檀香,佛前的灯火,与友人走在岩廊之中,听着不绝如缕的诵经之声,使人获得一种内心安宁平静之感。
三、诗与道——翻身便欲骑箕斗
吴道南曾赞誉罗汝芳诗歌:“短什长歌,天机鸣籁,鸿裁清牍,灵茁敷芬。”,说明了罗汝芳先生的文学实绩主要体现在山水诗上,其风格清隽奇丽,灵幻飘渺,心境与景物在他的笔下皆完美融合。据笔者统计,在全部的152题诗歌中,写景诗占据了绝大部分,以山峰、湖泊、寺庙尤胜,且其中穿插着大量的游仙修仙以及仙境有关的意象,如丹丘、浮丘、玄都、琼岛、琳宫、瑶坛、壶天等。这些山水诗大多意境深远、格调高雅且想象力丰富,在山川景色之中领悟“道”的深刻内涵,是罗汝芳山水诗歌的一大特色。
罗汝芳与道教的结缘最早要追溯到他求学时期,他曾拜师胡宗正研习《易经》的学问,而胡宗正正是一名道士,受其影响,近溪也从他身上汲取了“道”的智慧。万历七年,罗汝芳和胡宗正等一行人南下广东讲学,从当时所作的几首七言古体诗《濛山岩次前韵》《桃津次前韵》《石华山次前韵》等,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罗汝芳对道教的兴趣。如《濛山岩次前韵》意象辽阔,超脱物外,最为绝妙。“满前星月夜低垂,翻身便欲骑箕斗。蓬壶咫尺去甚便,弱水飞度无须船。回看兹土忽辽邈,一坯远寄严云边。”诗歌前半部分叙事,后半部分写景,看着夜色下闯入眼帘的星星月亮,便生发想象,幻想自己身骑箕斗到达了蓬壶仙境,但是作者并未一味地描绘仙灵情趣,而是望向现实,以故土为名表明自己的内心对于欲望的收敛,极尽彰显“辞近而旨远”的艺术风格。
而游仙诗自魏晋以来开始流行,其写作由头曾被著名诗人虞集概述得十分准确:“外无世虑之交,内无声色之惑,其发辞摅思,殊有飘飘凌云之风焉。”生动说明了诗人的创作手法与其人生境界之间的关系,而罗汝芳正是因澄净淡泊的心灵境界,文辞生动幽远,使得诗歌呈现出独特的缥缈之感,并非因“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而作。《桃津次前韵》便是这样一首气象开阔的游仙诗,“世尘眼底浮空花,满前扰扰争喧拏。避喧偶得桃源路,问津却到秦人家。津桃万树绚晴曝,香风阵阵遥相续。……有时狂歌宴西池,有时烂醉翻北斗。忽然忆我初来年,津头漫尔呼归船。种桃主人尚未老,忻然一啸迎花边。”作者为了避喧而前往仙境,将饮酒之乐提升到了使其精神满足的层面,并在狂歌宴酒之时以醉酒之态来表达仙境飘乎浪漫的追求,但是当回忆往昔,作者仍然依恋于世间美好,并积极寻找归途,重回现实世界,可见这绝非厌世而作。
在道教之术和神仙信仰的影响之下,罗汝芳找到了一个能够恣意发挥的奇妙世界,在山水氤氲下创作了大量的游仙诗歌,用来承载那个摆脱了自我束缚的超现实世界,寄托自己的生命理想,也让世人看到了他未曾展示过的一面——一个思想家的无拘无束的精神徜徉。
四、结语
罗汝芳作为一位在明朝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兼具重要的人,敢于突破传统,又能将思想、文学融为一炉,实为难得。总体来说,罗汝芳的诗歌多坚持儒家的道德本位,推崇的还是儒家的“中和”之美。因其内心的祥和安适,自然之景在他的笔下多呈现出清淡自然之态,即使是夸张奇异的游仙诗,诗人感情也能做到收放自如,雍容平和,这是他人格精神的主动选择,深刻体现了其思想修行。在罗汝芳的诗歌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其文学实绩,他的文学水平是远高于明代其他思想家的。其诗正如其人,洁净精微,温柔敦厚,我们从诗歌中能感受到诗人平和澄净的心态,而仁爱万物的儒教精神、慈悲怜悯的佛教精神、缥缈神圣的道教精神共同铸就了诗歌思想的内核,实是晚明文学研究所不可多得的重要素材。
注释:
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三》,页762。
2.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页858。
3.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页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