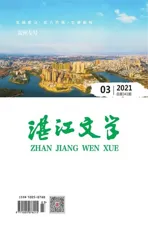雷 腔
2021-11-12黄宇
黄 宇
一
当那些久远而零散的记忆被厚重的岁月一点一点覆盖,直至消磨殆尽,在匆匆而过的时光中,鲜少有人会记得曾经生养自己故乡的最初模样。
我的故乡位于广东最南部的雷州半岛。如今因工作原因虽已离开故乡多年,也从来不刻意去回忆有关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不是因为背井离乡的漠然,更不是因为被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所迷醉,但凡人都是容易遗忘的动物,对于过去的是是非非,不管是快乐还是伤痛都想化作一场过眼云烟。如今的故乡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宽阔的公路取代了羊肠小道,高耸的大厦取代了简陋的平房,虽然故乡依然是那个故乡,但它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正逐渐形成另一个陌生的时代。
有时身在异乡的我会在午夜惊醒,依稀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回荡,那声音从深喉之中发出,或如泣如诉,或平淡无奇,或慷慨激昂,或婉转柔情。这种腔调,只有在故乡才能听到。而在异乡待久了,连头脑也被同化,形成固定的异乡思维模式,虽然我还认得那种腔调,但每次细细聆听时,它总会不经意地消失了,仅残存在我有限的记忆里。许多年过去,我的喉咙里始终潜伏着一种奇怪的性情,这种性情伴随着情感的欢乐或悲伤而演变成不同的声音。
故乡有一出地方戏叫雷剧,每逢过节时,村里都会举办大型雷剧演出。雷剧的演出台还没搭建好,村里的男女老少们总是早早地搬出板凳跑到台下兴奋地占位,而我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位雷剧迷。我总喜欢抢坐在最前排,仰头看着台上化了各种妆容的人在用不同的腔调演绎着人性深处的伦理道德。在欣赏雷剧的同时,我仿佛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里隐藏着一种腔调,这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声音。
平日里,我喜欢用这样一种腔调去表达对故乡的依赖和思念,安静澄明地释放出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情感之声。这样的释放是酣畅淋漓的,却是一种只能独自承担或狂欢的姿态。
在我出生的雷州半岛,这块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南蛮之地的半岛,每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上都流淌着这种性情,这是一种滔滔不绝的流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像胎记一样烙印在他们身上,既显性又隐蔽,显性的是人的性情,隐蔽的是生活的沉重,到底是何种力量的驱使,让这里的祖祖辈辈要用这种独有的腔调来表达生命的喜怒哀乐。
二
从高中毕业那年开始,离开故乡已近十年,在外地多年的我虽然尽可能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来掩盖隐藏在自己身上的故乡胎记,但总会因为腔调中无法改变的乡音而暴露身份。这是一种果断而坚决的声音,没有任何准备地从喉咙里倾泻而出。我将这种腔调称为雷腔。这种腔调是由雷剧演变而成,近年,经过雷剧工作者的不断探索、改革,雷剧已拥有八十多种腔调。
这样的陈述是一种书面上的文字介绍说明,它毫不相干地遗留在雷腔上,掩盖住它灵魂深处情感火焰的激荡四溢。这样的火焰和情感显得凄凉而唯美,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严,但雷州人民带着这种固有的腔调已经成为他们对外宣称自己身份的一种骄傲。我之所以道出这样的腔调并不是弘扬保护传统文化,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向着岁月荆棘密布的纵深走去时,沿途中,伴随着笑与泪,不断地收获和失去,但那些固有的,留存的所有困惑也随之慢慢被解开。虽然这不是刻意而为,但这种性情如顽疾一样依附在我身上,让我对它产生了依赖。我丢掉了孩童的率真天性,接着又遗失了少年的求知勇敢,导致青年的暮气沉沉的我最终丢掉了故乡的质朴,连同骨肉和血液里的气质。唯一保留的便是这口雷腔。
多年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只身乘着南上的汽车,在阴冷的夹杂着各种生活气味的车厢里,看着窗外飞快后退的景物:田野,河流,只有天空是静止不动的,我的心一直在默默念叨:“从此,我就是一个南上的无家可归的游子。”这种虚无的游荡感穿透我的肉身,渗入我的灵魂,它发出低沉的哀号,声声如泣,这才是我最真实的心灵写照,但之前一路行走,却没有发现这种隐藏在生命阴影部分的特质,它就像建在云端之上的空中楼阁,此时,我的耳朵仿佛听到一种腔调在轻轻地吟唱着流浪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从喉咙深处迸出的雷腔,字字真情,如母亲的叮嘱,轻轻地回荡在耳边,以前总感觉流浪这个词汇离自己太过遥远,没想到如今却近在咫尺。
在慢慢接近流浪的轨迹上,我却浑然不知,但它突然来到面前,我才想起需要重新看待跟随了自己二十多年的雷腔,这隐藏在性情深处最真实的声音,带着锐利的棱角,在异乡横冲直撞,完成着自我的汲取与释放,以及对寂寥生命的神圣朝拜。后来我的家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先是爷爷因病去世,之后年幼的妹妹又因绝症离世。在这之后我的性格变得孤僻,但遇到同有着雷腔的老乡时,却好像寻到知音,敞开心扉能聊上三天三夜。后来当我终于在写作中找到情感的宣泄口时,隐藏在身上的这种腔调反而不怎么明显了。但我深信只要拥有雷腔的人,面对和灵魂的对话,一定会得到生命的释然。它会与心灵融合,然后在身体中汇聚成一股爆发力,直冲喉咙,等待最后释放而出。这导致,有时我遇到无法释怀的事情时,会跑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用雷腔尽情地呐喊,直到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完全清空。
有一次,在经历了一场考试之后,我和朋友去参加聚会,在聚会上我喝醉了,又恰巧朋友们在起哄中让我唱一首歌,原本性格内向的我在公开场合很少说话,在朋友之间,我给人的印象是腼腆而拘谨。这样的性格,别说在众人面前唱歌,就是让我在众人面前说上一句话都是一个天大难题,但偏偏那晚,我借着酒劲,竟然答应了,而且点了一首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喜庆气息的歌曲。
当我用雷腔唱完时,在座的朋友都被我喜庆的情感深深感染了。直到聚会结束,所有人全部散去之后,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悄悄走到外面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将肚腹中所有未消化干净的东西连同无法言表的苦楚全部倾泻而出。当我清醒过来时,才发觉之前自己所有的喜庆心情都是伪装的,一切只为了讨得众人的欢心,并掩盖自己的无助。在聚会中,我收到一个成绩查询的回复短信,那场考试我失利了。当卸下那些伪装的沉重外衣后,我感到十分轻松,终于又可以做回自己,终于又回到了对自身,对世界彻底坦诚的悲伤之中。我本以为可以在这场愉快的聚会过后可以彻底摆脱悲伤,但没想到它又在我的内心深处开始肆无忌惮地蔓延。
在那场考试失利后,我怀着伤心的情绪重新上路,在经历第二次考试时,虽然分数考得不高,但总算比上次有所进步。在某天的一个夜晚,我在城市的一条深巷里穿行,突然听到从巷子里一户人家的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清瘦男人蹲在自家的门边,随着屋内的音响播放一首经典歌曲《梅花三弄》,清瘦男人跟着歌曲的节奏用雷腔深情款款地唱了起来,虽然男人唱的声音不大,但由于巷子幽静,我还是能听到他安静而澄净的雷腔。
每次听到这首歌时,我都十分熟悉,熟悉到能在每一句歌词中体悟出一种渗入骨髓和灵魂深处的痛感。
这种心境并不限于歌曲本身,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和我的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到一起。于我,早已融入歌曲的本身,成为故事的主角,更成为生活的主角。在这首歌曲结束后,我走到那位男人的跟前,和他交流了起来,没想到他和我竟是同乡。他在城市的一家服装厂打工,租住在这栋楼房里。见我是同乡,他也回给了我同样的热情。从他刚才的歌声中,我能理解他作为异乡人寄居在这里的心境。我问他怎么不回去发展,他的回答也很简单:之所以呆在城市里不愿离开,只为了最初的坚守。
异乡人就像过气老歌,即使再动听,早已被这座纸迷金醉的城市里的其他腔调掩盖。我对他的回答虽然在意料之中,但还是感到少许的意外,坚守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悲伤领悟。刚开始,我和他说着并不纯正地道的普通话,后来渐渐熟悉起来,我们干脆以雷腔交谈。在异乡,在那样一个安静的夜晚,没想到从我口中迸出的雷腔竟变得那么地生涩难听,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我在异乡的悲伤情感削弱了我对雷腔原本滚瓜烂熟的记忆。交谈了一会,我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后来,我忙于生计,再也没有和他有过任何联系,时间过去了近一年,直到年底时,我突然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他的工厂拖欠员工的工资,想和我暂时借一点钱过日子,等他发工资了就还给我。我二话不说,马上答应了。他在电话那头稍稍迟疑了一会,也许是不相信曾经在一年前仅仅见过一面的人,竟然会这么爽快答应借钱给他。
三
我深知,在这座人心叵测的城市,借钱本来就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但作为同乡,他和我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我找不到任何拒绝借钱给他的理由。当我见到他时,感觉他比上次变得清瘦了一些,但看上去精神饱满,他的一口雷腔依然娴熟。显然,我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乡在城市遭受磨难,只有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在来到这座城市的几年时间里,我看过太多人世的悲欢离合,正因为这样,逐渐变得有些麻木。但同时又在与麻木顽强抗争着。所以我必须站起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以消除自己的悲伤。
当我将钱递给他时,他那张面黄肌瘦的脸露出一道笑容,在谢过我之后,他匆匆地消失在城市的人流当中。
很快临近春节了,在中国,春节一票难求,我排了一上午的队,好不容易才买了一张硬座票,在充满着各种无聊烦闷气息的硬座车厢里煎熬地度过了近十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故乡。刚回到故乡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那位同乡打来的电话,他请我去唱歌。我欣然答应了。在小小的包厢里,他又约上几位同乡,如今他们都和我在同一座城市,或打工,或读书。我们又用雷腔点唱了几首歌,每次用雷腔唱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而凄凉的熟悉。在那次聚会之后,我们又再次道别了。
二十年前,我怀着梦想呱呱坠地,二十年后,我从故乡人逐渐变成城市人,不管是否愿意,故乡的年轻人总会有坐上前往城市的长途汽车的那一天,去强制自己转变角色。在刚坐上去往异乡的汽车时,每个人的性情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这种激动源于对原本身份的厌弃,对故乡熟悉到麻木的环境的厌倦,离开是最好的解脱。
那时,年轻的我恨不得马上甩掉故乡人的身份,从而永远寄居在城市,哪怕只做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城市人。当汽车载着我向城市进发时,没有想到日后会再回到故乡,我就像一滴新鲜的血液,城市就是一颗大心脏,我正准备给这颗大心脏输入更有活力的血液。反而面对与故乡的分离,我变得果断而决绝,变得冷漠而彻底。当我身在城市这个寄托着曾经的伟大梦想的摇篮时,突然发现,以往所有根植于故乡里的记忆逐渐被尘封起来,当我回望,故乡在一种汹涌的狂潮的腔调中崩塌。树林,老屋,小巷,河流等与故乡有关的一景一物再次被我努力地回忆起,另一方面又被迫逐渐地淡出我的记忆。
在故乡和几位同乡聚会的那个夜晚,后来被我无数次地回忆起,我意识到,悲伤是无法消除干净的,因为旧的悲伤尚未消除,新的悲伤又在不断形成。在二十年前,我不知道悲伤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名词,在二十年后,我却不得不在梦里一次又一次迎接悲伤的到来。要真正成为一名城市人,需要用一生去努力,需要在漫长的岁月里忍受着来自现实的各种各样的严刑拷打,更需要整个家族的男女老少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前仆后继地成为城市一滴又一滴的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才能将一名我身上封存了二十多年的雷腔彻底祛除,再烙上时尚的城市腔调。许多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群正忍受着这种改变的悲伤。如果不愿成为城市人,也可以选择返回故乡,从此在故乡里默默无闻地娶妻生子,平淡生活,直到老死。这种悲伤,我同样无法接受。
四
虽然我所去往的城市同属广东,但在这里飘荡了数年的我依然不会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并不是我回避学习粤语,我知道是自己身体填充了太多雷腔的元素,导致粤语的气息无法进入我的身体。但我如今终究还是生活在城市,于是总是逼迫自己一定要尽快学会这里的语言,只有这样才不会受排挤。当又一年的春节来临,我返回故乡时,我感觉身体里的雷腔气息虽然被城市化的进程冲淡了,但耳根与心灵依然是纯净的。一年前在城市偶遇的那位同乡又打来电话,他要在故乡举办的一个文化晚会上登台演唱,正因为这事,我才特地从城市赶回来看他的演唱。
恍惚间,我的脑海中映出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在故乡为生计而日夜忙碌奔走的背影。父亲一直比较沉默,他很少去外地,在故乡总是习惯用雷腔和别人沟通。在故乡工作几十年,他没有去争取更大的职位,始终当着一名普通的图书馆职员,刚开始我以为父亲不思进取,逃避现实,后来才知道这是他负担起沉重生活的一种隐忍姿态。母亲同样在故乡几十年,始终做着地位卑贱的环卫工作,顶着周围人鄙夷的目光,独自一人扛下了所有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以及那些不能言表的悲伤。我被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所散发出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时常能感受到来自他们在坚定的雷腔中所隐藏的力量。这让我在城市与故乡之间没有了决绝的勇气,我尽可能地在影响着自己情感的城市与故乡两地之间协商妥协,直到能安身立命。
短暂的年假一晃而过,这天我坐上了开往城市的长途汽车。这条路线我已经来回往返了许多年。车上坐着的人都是从故乡去大城市,有着一口娴熟雷腔的人,在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是城市人,有的正准备成为城市人,有的依然对城市充满好奇与向往。当乘务员开始验票时,我竟然不小心用普通话和她说话。一旦坐上这样的客车,我的思维就忍不住变成城市的惯性。好在车上也有一些讲普通话的人,在乘客之中还是能分清谁是城市人,谁是故乡人。因为在他们身上都有着一口流利的雷腔,这些来回往返在城市与故乡之间的人们,本身就带着一种离别的悲伤。
五
我的外公是乡下人,还是一名雷剧演员,从小唱雷剧出身,年轻时在戏台曾经演过穷酸书生,为考上状元,博取功名,悬梁刺股,拼命学习,当终于熬到在暖春三月赴京赶考时,却因俊美的外貌而被沿途的富家女相中,为了儿女私情,放弃理想,沉醉红尘,最后抱憾终生。这样俗套的剧情,外公用标准地道的雷腔默默地,不厌其烦地唱了一辈子,在戏班里唱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戏骨。成为我在雷腔的语言环境里最敬重的一个人。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忙碌,他们经常将我寄托在外公家时,那时,农村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风俗活动,比如土地公生日,小孩满月,老人祝寿等。每次举办这些风俗活动,总要搭台唱戏,外公是村里戏班的骨干演员,每次登台都少不了他这个主角,自然他也成了最忙碌的人。每次唱戏演出总在晚上,而且进行到很晚才落幕,外公家离戏台很近,只隔了一道墙。时间早的时候,我就到戏台下的观众席坐着看,如果感到累了,就一溜烟跑回去睡觉。我躺在外公家的床上总习惯听着从外面隐隐约约传来的雷剧的声音才能安 然入睡,这种声音有时浑厚低沉,有时 清亮高亢,有时温和婉转,而我的耳膜 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同时拥有不同腔调 的雷腔。它给了我最可靠的安全感,让 我忘记了独自寄居的孤独和不安。 记得有一次,我看外公唱的一出雷 剧,那出雷剧由于剧情的设计,只有外公一个人在台上唱,那晚台下的观众虽然很多,但令人惊奇的是,外公似乎无视他人,将整个戏台当成了他的个人专场,虽然他年事已高,但他对这出雷剧的改编,包括唱腔的许多细节把控上都进行了精心的处理。外公把古老的雷剧唱得既熟悉又陌生。我相信那个晚上,台下的其他戏迷们也看懂了外公唱的这出育人劝世,深藏人生哲理的雷剧。而且我一直隐约感受到外公的身上藏着一道隐秘的光芒,这道光芒平时被琐碎而沉重的生活遮蔽了,只有在属于他的戏台上,这道光才会完全释放出来。外公虽然热爱雷剧,但在他根深蒂固的思想里,唱雷剧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渺小得令人无法直视。唯一能摆脱这种渺小便是前往大城市工作或者寄居,以前外公总是经常这样对我说。后来,当我真的有机会到大城市学习和工作时,才发现大城市并非自己愿景中所想象的那样美好,这里充满了轻浮的狂欢,以及人心的叵测。人们疯狂地为自己掠夺各种资源:教育、工作、生活。这里的人们为自己逃离了农村感到庆幸,为自己日渐退化的乡音感到幸福。当我了解到大城市的一切真相后,无奈自己已经是寄居于此的异乡人。当我想把这个真相告诉外公时,他已经去世了。外公走得很突然,因为老家祖屋被一位兄弟私下卖了,外公得知后非常生气,和那位兄弟吵了起来,不幸心脏病突发,就这样一场心脏病夺走了他的生命。
这种突然就像侵入我身体的城市之音,要将我体内的雷腔彻底清除干净,从此做一个彻底的城市人。但外公曾经在戏台上遗留下的雷腔让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尊严,我不敢将此时自己的心灵与外公的心灵做比较,在我看来,外公虽然离开了,却留下了一个永远以雷腔为荣的灵魂。在这点上,虽然我的身体虽然还存在,但实际上只是一副躯壳,因为我始终未能做一名真正的雷州人。
当我写到这里,喉咙忍不住发出阵阵颤抖,虽然斯人已逝,我再也不能从老一辈的雷州人那里听到标准的雷腔,但这些年以来,我只身漂泊在外,尝遍了人生的苦辣辛酸,有时也会因为孤独而以雷腔自言自语,在这种孤独中我的喉咙悄悄保存着最纯粹的雷腔,虽然这不是刻意而为,但我知道雷腔在我身上永远不曾消失,只是有时候它被生活杂音暂时遮蔽了。不管我是雷州人,还是异乡人,或者未来还会拥有不可预知的多重身份,但我对雷腔的情怀始终不变。我在写作中,用回忆的笔道出了故乡内心的辛酸苦辣,更用真实的声音喊出真切的雷腔。它不豪迈,不亢奋,它只是一个族系对内的亲切之声,一种对外的美丽文化符号。但它唤醒了我,也唤醒了数以万计的故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