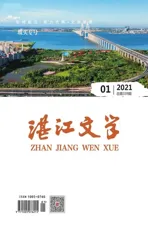感受地坛(外一篇)
2021-11-12卢凌日
卢凌日
一
地坛,因一个名字而深刻。
2018年的夏季,我到了北京也小住了一段时间。有着余暇,地坛便成了我一处想去的地方。
清凉的一个上午,我寻问着去了。
出了安定门地铁,一路上,满园子似乎熟悉的情景不断地在我的脑际浮现——
那个祭坛,那四百多年的历史沧桑;那抹斜阳,那亘古不变的朝夕轨道;那春夏秋冬,那明晦晴雨的变化景色;那个母亲,那束可怜又焦灼的寻找目光;那大栾树下,那个捡拾“小灯笼”的智障女孩;还有那苍黑的古柏、高歌的雨燕、草木生长弄出的声响;还有那长跑天才、那对老夫妻、那饮者、那唱歌青年、那优雅的女工程师……十五年,弹指一挥间,这时空、这景物、这些置身其中的人,怎样给出了让一个不幸灵魂沉重思考的种种人生?
宿命是人活着对命运无法解答的解答。人一出生就已经是一个毋庸讨论的答案而不是一道问题了。只不过答案不是一下子全部裸现让你看个明白,而是在生命的过程中慢慢展示、让你慢慢体验。
宿命就像一串杂色的珠子吧,白的黑的红的绿的亮的暗的早就排列好在一起。有时为了要让人看出惊奇,冥冥之中也会作了巧妙的安排。
我想,园子不管是方、是长、是圆,里面一定有一条环园的跑道,要不就吸引不了那个长跑家的到来,让两个无奈的灵魂碰在一起——一个是长到最狂野的岁月突然被病魔击倒而只能躺在轮椅上的青年;一个是因言获罪而被政治偏见刷下来的长跑天才。都有伤痛,都有苦闷,也都有着共同的心声。有趣的是,当长跑天才企图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时,结果却是一次次喜剧性的展现。
喜剧常常是捉弄人的。他首次参加春节环城赛,跑了第十五名,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他充满希望,也倍加努力。
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橱窗里却只挂出前三名的照片。他以为这是要求不同的结果,仍然信心百倍。
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却又挂出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蒙了。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出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跑了第一名,橱窗里的照片就只有一幅环城赛的群众场面。他彻底明白了,成绩总是抗不过政治偏见的洗刷,这个新闻宣传橱窗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是容不得他跻身其中,那政治上的解放更是天大的妄想。
他在彻底绝望而不彻底甘心的赌气下,最后来一次告别赛,以三十八岁的高龄夺得了第一并且破了纪录。一位不明底细的专业队教练惋惜地对他说:“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无言,只好苦笑。
说起来,我也曾经为这样的一幕苦笑过,类似的遭遇,总是教人摇头愤慨。幸喜我走的不是一条只能凭强壮体能才能实现的成功之路。不然,被耽误了的青春,像那位长跑天才,机会来了腿却跑不动了。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宿命当然也隐藏着种种缘分,缘分总是值得珍藏的。
那么,那张无奈又寂寞的轮椅成年累月地戗在地坛中,这时光,自然会令他更珍惜每一次的遇见。可以看出,在回忆中写出那么多细微而又让他眷念怀想的细节,不是有心人是做不到的。正是这些颇为稀奇的细节描写,常常令我有着莫名其妙的联想。
——那对老夫妻,总爱在薄暮时分来到园中散步,铁定到环园走一圈,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非常守时。两人春夏秋冬的服饰变化,既有规律,也很体面。那个娇小的妻子,总爱攀着高大丈夫的胳膊,像被磁铁吸附着游走。开始还是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夫妻,在十五年的风霜磨洗中慢慢变老了……
夫妻厮守,相濡以沫,感情的投契自然需要,但当俩人过于专注了,是不是身外的人和事就上不了他们的心头呢?十五年的春夏秋冬,不算漫长也不算短暂,在园子里走动的差不多换了一茬人,他们还是最守时到来的一对,也是和轮椅上那个不幸的残疾者遇见最多的一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总该有个问讯、有个关切、有个交谈吧?是生理的障碍还是心理的障碍,他们之间始终是无言地擦肩而过。难道,这不算缘分?
——那个独特的饮者,那卓尔不群的饮酒姿势,每走五六十米便选定一处地方,一脚踏在石凳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眯着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进一大口酒,把酒瓶摇一摇再挂上腰间……
人生百态,形形色色,个性自是不同。大千世界,如果只认定一种标准、一种范式来强调个性,这个世界就变得十分乏味了,何况,这对于个人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饮者,衣着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怎么说都是个市井小民。可他活得自在,活得潇洒,活出了他的人生滋味,谁能说他不幸福呢?
——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每天从北向南穿过园子去上班,傍晚又从南向北穿过园子回家,别人很难有她那般的朴素与优雅,而且在园中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竟似有悠远的琴声……”
我凭空想象,轮椅上那个孤独者为什么害怕想象她丈夫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担心她落入厨房?是不是在他虚拟的一块空间中,有着一个满足的性世界?这对他是一种幸福呀!
——一个小伙子,每天都来到园中练歌,也一定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唱,唱半个小时或整整一个上午。“文革”时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文革”后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行的咏叹调……
他算是最幸运的一个了,没有生理残缺,也没有什么政治污点吧,不然,那种轻松活泼富有喜剧情调的歌曲就上不了他的心头,也不会唱得那么豪迈、那么清亮。也许像他唱的那首歌一样“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后来成了一位歌星了。可惜当年没有留下可以印证的姓名。其实这点也无关重要,因为那个轮椅上的残疾青年,后来大受社会关注,他们的邂逅,是一次值得向人诉说的缘分。我很担心,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那座纯洁神圣的文学殿堂已经不大受关注了。
二
地坛,装载着各式各样的人物,装载着各式各样的人生际遇,同时装载着一个时代的乐与苦。这些,却给那个不幸的残疾者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生命思考。
现在不用说了,作为旅游景点的地坛,摆放了四百多年,该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了。但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有意保留历史的残缺,让人们去凭吊古迹的苍茫和让人去寻找那个不向命运屈服的轮椅车辙?还是把那些残破的、崩颓的景物修复一新,夸耀着时代的光彩,华装艳服地让游人享受新时代的风光美景?我加快了脚步,迎面,一座巍峨的牌楼,金碧辉煌,“地坛”两字就写在上面。当我连续走进两道大门,放眼四望,一幅具体的和一幅抽象的图景突然碰击在一起。
想象与现实总是两个门框里各自进出的一对,很少能有同步的时候。刚才那种苍茫、古远、静谧,顿时被充实饱满、蓬勃热闹的景象所替代。行走间,陌生、熟悉,熟悉、陌生;重合、分割;分割、重合。景生心,心生景,浮想联翩……
地坛无疑受了一个鼎盛时代的打扮。为了青春、为了活力、为了更美,时代也需要打扮。
打扮需要人工的施为。
没有池子,用大塑料缸一圈一圈围起来蓄水种植荷花。盛夏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虽无“接天无穷碧”的气势,却也有“映日别样红”的风姿。比起湖生池种,塑料缸里的荷花更显得亲和,不是那种“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孤傲,这种人工“旱地荷池”竟有十多处分布着,我不断看到爱美的姑娘们跻身其中搂着—株花朵来拍照。
一方方规整分割着的林圃,新植的柏树,像一队队昂首挺立的士兵,青翠、葳蕤、挺拔。在绿荫掩映下的人行道,行走其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或搭肩勾臂,或携手搂腰,或相互嬉逐,一派悠闲,一派怡然。
新辟出的一方不大的小广场,在父母陪同下的一群小孩子,每人手中都捏有一袋鸟食,逗耍着一群啄食的鸽子,淘气的小麻雀也毫无忌惮地掺杂其间。小孩子们总想凭鸟食的诱惑,靠近抓起一个,偏是机灵的鸟儿,躲躲闪闪或倏地飞起,就是不让小孩子们的企图得逞。
显然,门球场同样是打扮后的摆放。这一天,几个门球场同时进行着比赛活动而且各具特色的球衣队别分明。没有奔跑,没有呐喊,各自专注着滚动的小球,气氛是那么恬静和谐。在这里,这个属于老年人的“球世界”,平添了几许悠然。悠然地上场,悠然地瞄准,悠然地击球,连那个小球也滚动得悠悠然然。在“海峡两岸门球友谊赛”的名义下,这份悠然更显得庄重与自得。
一个多人围观的圈子内,正进行着摔跤比赛。与门球比赛截然不同的是,两名对手,虎视眈眈,在裁判哨子的指挥下进行着互不相让的决斗。场面上的对手自然会让人看得分明,有的明显处于劣势,但并不气馁,屡败屡战;有的明显处于优势,但并不轻敌,愈战愈勇。有的棋逢对手,更是打起精神寻找对方的可乘之机。我惊奇的是围观者的文明礼貌,不喧哗、不吆喝,间或只有轻轻地几声赞赏或惋惜。
拐过一个方向,不远处飘来几声昂扬高亢、熟悉又陌生的京剧:“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我寻声望去,一方舞台上正进行着群众曲艺比赛。这也许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下面的观众都不大关注台面歌手的表演,只是随意听着或者拍着板子轻声相和。
我来了才知道,芳泽坛就是那个祭坛。它显然也是经过打扮了,不见苍苔、不见衰草、不见颓颜。地方天圆,方方正正,按照中国传统宇宙理念,建造得一丝不苟、静穆而神圣地躺着。它应该记得那张轮椅,应该记得那个练歌的小伙子,应该记得偶尔也会闯进来的长跑天才。但它现在已被保护起来凭票参观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我想它多少有点不情愿,像从前那样多好,它会相信,人们已经懂得了它的存在意义,都会维护它历史所积淀的价值。
从芳泽坛出来拐向东边,原来我想寻找的古柏就在这里,而且都被铁栅栏保护起来了。它们一棵棵,偻背秃顶,像紧抱着双臂的老人站着,一副看多了看惯了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它那裸露着的筋骨,粗粝凹凸弯扭,突兀得让人读进了历史的深处。你倘若设问,那张轮椅怎样了?那对从中年走到老年的老夫妻怎样了?或者是那个卓尔不群的饮者怎样了?它肯定会讪笑你:“孙子们,我都在这里站了三百多年了,比这些更别致、更奇特的事儿多着呢,这些事情,你们上心,我不上心呀!现在,我们都被用铁栅包围保护起来了,不见我们都挂上了‘光荣牌’吗?这才是我们活出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地坛2010年将原有的牡丹园改造成的中医药养生文化园。这是我国第一家以中医药养生文化理念建造的主题公园。
我走马观花,无心解读其中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原理,只觉得回廊曲径,小桥流水,茂林修竹,假山石凳……好一个清新幽雅,优生赋闲的好地方。
这里也是歌者、舞者、弈者、拳者的小天地,琴声悦耳,歌声悠然;舞姿翩跹,马步稳健;围观对弈,坐看甩牌,气场十足,人脉涵和,生命的韵律尽在这里飞扬。
……
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在年轻。而地坛,却有着日久弥新的魅力。我想,宿命也肯定有着它的时代特征和内涵,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宿命。是否时代对宿命也有着矫正的力量?这种“天问”,有谁能回答?在四百多年的流动岁月中,人事更迭,历史苍茫, 轮椅已成为过去,天才的长跑家、捡“小灯笼”的智障女孩……都已成为过去。毋庸置疑,被时代打扮了的地坛,会更多地珍藏着幸福的记忆。
那一声声的吆喝
日子闲着,吃过早餐,我总爱到离家不远的海滨公园逛逛。
走在大街上,一辆小车戛然停在身边,后车窗探出一个头来:“卢老板,还认得吗?”他有意扯下口罩让我辨认。
我开始一愣,但随即想起来:“呵……好多年不见,胖了呢!”其实他并不胖,是原来太瘦了。
“我不收气都五年啦。”
“现在去哪呀?”
“前面开车的是我女儿,去看看新房子的装修。”他说时,驾驶座前同时拧过两张笑脸,虽然戴着口罩,也遮掩不住青春的妩媚俏丽。两相酷似的眉眼,我一下子什么都明白过来。
“哦,日子甜啦!”
“等搬新房,请你去喝一杯!”话里充满着幸福感。
“好呀,先祝贺你!”我竖起拇指头夸他,他一声拜拜,车子便开走了。
我望着远去的车影,好像这一遇见是赫尔墨斯的有意安排。一幕幕的往事,路边的景物也似乎随着往事变换。
1989年我搬进了政府宿舍大院。大院的十几幢楼房,楼层都不高。旁边的马路还是刚修好的四车道。我搬家的物件最脏最笨重的是那两箱煤球和那只煤炉。
“收瓶充气啰!”早午晚三刻,这一声声的吆喝,宿舍区的每一扇门窗都回避不了它的敲打,但我不大理会。
生活总是迟到的我,是1991年才开始煤改气。也是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声声的实质存在。
吆喝的人三十七八岁,瘦瘦不大的个子,下腮尖尖,两扇大大的招风耳特别惹眼。
他趿着一双旧塑料拖鞋,衣着邋遢,夏天甚至光着上身,只在胳膊搭一条汗巾,既可垫肩,又可擦汗。他骑的那辆旧自行车,后架绑着两根短木,满满拴上皮条,是专门挂气瓶用的。送气多的时候,短木左右各挂两瓶,上面还搁上一瓶,他得直起身子,双手抄起车把,腿使劲往下蹬,样子有点吃力。我有时在楼道上遇见他,只见他半驼着背让气瓶结实地压在肩膀上,一手扶瓶一手叉腰,同样是吃力地一步步蹬着楼梯。
由于煤改气,我和他有了几次交集,也渐渐了解到他是附近的村民,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左右无兄弟也无姐妹,就凭自己的肩膀扛气瓶过生活。
说实话,爱人很不喜欢他的粗鲁,每送气来,那扇玻璃隔门就被他拍得震天价响。爱人不止一次唠叨过:“往后不叫他换气了,隔门别让他拍坏!”
我出于对他身世的同情,总是劝着爱人,往后叫他轻点就是了。可是,当面说时,他腼腆得像个小女孩,小鸡啄米地频频点头。但送气来时手劲还是那么大。我只得告诉他,下次送气,你先在楼下喊一声:“三楼的气!”,我就开着门等你了。这一招果然灵验,后来才明白,他是以每一瓶气计工酬的,轻拍门生怕屋里人反应不过来,耽误了他的时间。
爱人有洁癖,看不惯他的样子,尽管他在门外脱了拖鞋,爱人还是不让他踩进房来,总是要他把气瓶放下才由自己搬进去。这种时候,他常常用一种不屑的目光往里面扫一眼,然后掉头蹬蹬跑下去。
有一回,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在我面前争口气还是什么的,抬到了98元的一瓶气,我干脆给他100元大钞说不用找。他可不接,一手挡着我要关上的门,一只手插进裤兜里掏出一把现钞,但没有两块零的,这才不好意思地接过说了声:“下次下次,我记得的!”走到楼梯拐弯处还不忘回过头来说一声。
一月一瓶气,铁打的准。他送来气,看着我从口袋掏出一百元,手往裤兜一插,四块钱就递到我面前,显然是有备而来。
岁月静好,十年一晃而过。我退休下来待在家里的时间长了,接触他的身影也自然多了。他骑的那辆旧自行车不知什么时候已换上了挂卡的三轮板车,唯独不变的是他每天早午晚三刻的吆喝,那一声声高分贝的声音,总是清亮亮的从不嘶哑。我想,如果他得到命运的青睐,很可能就是一名出色的男高音歌唱家。可是,可是……人生的种种遭遇就在这种种的可是中无奈。
依然的春夏秋冬,依然清亮亮的吆喝。忽然一天,板车上坐着两个大约四五岁的小女孩,两人互相抓着一副扑克玩耍。三轮板车慢慢地蹬着,吆喝声也似乎轻悠了好多。一段时间里,他都是这样地带着两个小女孩收气。
爱人告诉我,他命苦,找不到老婆,这是路边捡来的一对弃婴。亲邻怪他一下抱回两个,他说抱起这个那个哭,抱起那个这个哭,他硬不了心。我一肚子疑惑,这四五个年头,一个单身男人,而且整天在外边跑着,一双孖女,喂羹喂水,换衣洗尿,他是怎么忙过来的?还是爱人告诉我,世上好人多,亲邻有心帮,这多亏左邻右舍的几家大妈,好不容易拉扯这么大。
2014年,宿舍区已通了煤气管。很多户头已不再需要他换气了,而我却是迟迟没有接通,原因是爱人总是犹豫不决,一怕用气贵,二怕不安全。二十多年来,可以说我一直是他最牢靠的用气户。平时街边碰上我,老远就喊:“卢老板,逛街呀!”可笑的是,不管我什么装束打扮,甚至是背包拖箱的出差回来,他一样是“逛街呀”这句话。
他不是那种头脑灵活的人。不难推想,在他艰苦的生涯里,有过多少热情温暖的手在扶持着他?最直观的是他那送气工具。从要绑要扎的旧自行车换上了不用绑扎和多载多放的三轮板车;从日晒雨淋的三轮板车再换上人坐在四面挡风的驾驶室里,同时带上了高音喇叭帮助吆喝的三轮电动车。他每一次生活的改变都必须有人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甚至要亲身代劳。就是那一双孖女,从嗷嗷待哺到长大成人,念小学,念初中、高中,虽说没考上大学,穷人孩子早当家,早早就出来创业,但就是这么个过程,靠他微薄的收入和低能的人生也是很难做到的。这里少不了亲朋、邻里,学校、政府的帮忙和资助。
现在好了,一双女儿,如花似玉,而且做着服装生意,有了车也买了房。日子幸福着,那一声声清脆的吆喝声也终于落到蜜罐里。
公园里的几树凤凰花,迎着早晨的阳光格外红艳。我站在公园边望着大海,波涛滚滚,一浪接一浪,到底是前浪带后浪,还是后浪推前浪?也许各人截取的断面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判断。我似乎觉得,在每一个浪头的褶皱里都隐藏着一个密码,需要人们的正确解读才能领悟大海的奥秘。人类社会,同样在生活褶皱里隐藏许多需要打开才显露的真相。假如不是今天的遇见,那一声声的吆喝,在我的脑子里肯定是凄苦、不公等定义。
……
一阵风过,涛声喧哗,我想的还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