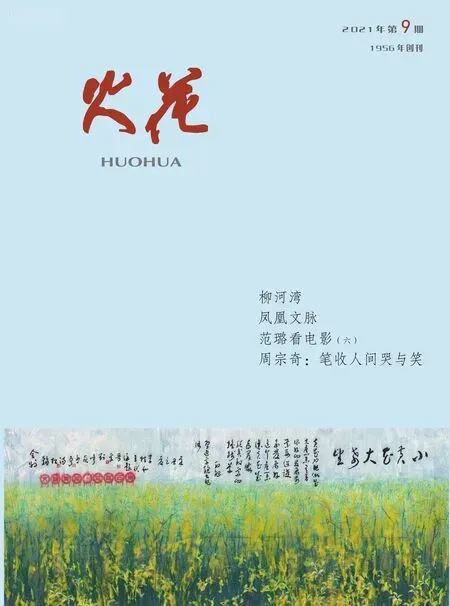在淌往小清河的涓水里『捍流』
2021-11-11王一秀
王一秀
小清河南边才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所在,没有近山,却有东岸的一小片丘岭。一条河流从村庄东边南北流过,她叫涓河。汇入北面,进了潍河,再北是小清河。
涓河入潍后,是否成了小清河的第一干流?小孩子的我们,不知道。
它紧贴着村子东侧,妻子小时,在伸往河中的大柳树粗粗的枝杈上,几个女孩鱼贯练习过跳水。我们喊:小红帽,不害怕,站在河崖掰杈巴!她抹一把钻出河面的脸上的水,回骂我们几个坏小厮。
如果它足够宽广,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枝杈,我的村庄就是这条枝杈上的一粒花苞。
但是,平日它只是一条涓细的河流,没有一条船在水面上行驶。即使在汛期河水猛涨的时候,它也就是五丈多宽的样子。
当然,水性好的也不敢在这时一个猛子就想窜潜到对岸,从对岸水中得意地露出脑袋来。
在村庄的东南角,出了大量恐龙化石的龙骨涧崖下,有一座石砌拦河坝,离南边姜太公钓鱼台仅百八十步。上岁数的二猫打猎瞧见,钓鱼台下老鳖出来晒盖儿,鳖盖像盛饺子的八印锅盖垫儿那么大。
它始建于四清、社教时,连同于北向流经焦家庄子、烟家庄、流过吕标——公社驻地,又流向北辛庄子、邱家七吉、大村,最终流向曙光、赵家黑龙沟的引流干渠。竣工时,县里来了剧团和文艺宣传队做了慰问演出。
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副这般的样貌。
相较其它地方,拦河坝下第二个去往东岸焦家庄子、吕标的河口,河水要深许多。我们夏天偷偷摸摸下河,是不敢到第二个河口往南一段的对岸水里去的。当然,除了水深之外,还有道听途说的一些传说之类的神灵,据说是出没在那里的。而且,湾拐那里的水,隔岸看过去的确阴森森的,让人凝视之下不由得转换视线。
不过,好友运邦告诉我,那一片的蕴藏还是很丰富的。有大如手掌的河蚌,还有在泥沙混融的崖水岸边穴居的螃蟹,有探进崖边水底淤泥里就能两手压住的泥鳅,有浑身滑腻背脊上藏一根暗刺可划破人手的黄锥,还有大大小小的鲫鱼……
在夏汛过后的初秋,运邦带我来河边做过河中捉鱼的第一票儿。在不算水深的地方摸了一会儿鱼,在水浅的地方,我们截住一片水域,“捍流”——
“捍流”,一定得是水流地势高下明显的滩段。这个“流”,是过河随“大流”的“流”,是四声。如果用“溜”,是用在多条河汊并流体现主水流时;或“蹓”,用于“蹓鱼”的“蹓”时,也是去声、四声。
运邦会看“流”,选的都是别的捉鱼人开堵、堵开了多次的“熟流”。“熟流”货不多,都是水流中进入的新鱼,但堵上流水口后流干得快。一会儿的工夫,可以“捍”两三段这样的“流”儿。
最拽人心弦的时段,是下水口张上须笼的地方,在最后仅有几米水流、水势形不成高低的时刻,必须要用铁锨拥移掺杂了大大小小鹅卵砾石的河沙,逼水。
这段平缓的水,往下水口越逼越近,七八尺变成了五尺,“花翅”鱼开始跳跃。越拥越快,越挤越快,越逼越快。三尺,二尺,一尺,半尺,沙挤水逼近笼口,鱼儿全逼进了须笼里。
再谋第二拨鱼获,我眼热一段鱼儿很多、不停地跃出水面引诱你堵水的滩段。运邦看出不好弄,说,这段是稳水,堵了排不干的。我坚持说,你看有多少鱼,你看有多少鱼!运邦大我一岁,村邻行辈高我一辈,敦厚让人,又是我母亲嘱咐了再三的:“你是长辈,一定带好你侄儿,多长眼色,不能吃了亏。”运邦又是每次都嘿嘿笑着应承了的。我都会对娘说,运邦须笼铁锨都带全了的,我们绝对不会有事儿的——这次,自然又承让了我,服从了我的错误认定。
筑好下口,先支好须笼,又围堵五丈出头的南北长的小沙堰形成“流”形,累得我俩满头大汗。合力闸住上口,我就一厢情愿地等水流干。我们趴在主流河水里泡着,尽量耐心地等水势下消。等啊等啊,不见水少。以铁锨当舀桶,在下水口往沙堰外舀泼,舀水哗哗,不大一会儿,胳膊就累酸了,却不见水少。平稳的地势,稳稳的水流,哪有流干露沙滩的痴望?
我不甘,提议用铁锨来吧。有的地方水深及膝,实在不是两个十岁孩子力所能及的。大人来用抽水机抽,怕是也得一顿饭以上的工夫。
只得把这段做罢,掘开上口放水。下口取出须笼,竟有惊喜,水声惊扰,竟乱蹿进了三条花翅。花翅很鬼的,游速也快,竟也入我们的网笼之中了。
好在鱼篓里有了斤半多河鱼,虽然没有运邦和他爹“大泥狗”一夜捉上半水桶十几斤的战果,但这对我来说,也是初次经历满满的喜悦了。
运邦是一条鱼也不要的,全给我。倒进灰陶洗衣盆里——这种在呈子文化遗存里东夷人早已使用的灰陶盆,显大。添几瓢水,盆里鱼就显得有半盆了。还有舀浅了水捉鱼前,我们踩到的几枚巴掌大的河蚌。这算是带鱼货回家,全交给了母亲。
河蚌的肉质,做好了才不显得口感显老,直接煮来吃,是嚼不动的。母亲是将它们煮过后,剁碎,滚上面,炸成小蚌丸子,再做菜汤,有些像现在“海鲜蛤蜊汤”的做法,味道是很鲜美的。
小河鱼,被母亲掇择干净,煎了两大盘,余下的做了汤。汤里还有两条泥鳅。这在荤腥稀有的苦日子里,实在是一次改善。
河鱼,鱼品并不低。清明节时上坟,我们这里是上古传下来指定要用河鱼的。
鱼头里有“火”,是指吸引劲儿,上瘾的意思,就有了又一次。我俩带了水桶、扒网筢子、鱼篓,还有两张铁锨。不是汛期,河水一直不深,不到膝盖的样子。我们让水桶和鱼篓在身边漂着,用铁锨去挖水边的淤泥。一锨下去,就露出一截淡黄色的身子,赶紧将两只手伸进首尾处的淤泥截住,慢慢捉牢,果真是一条大个儿的泥鳅!还从来没有捉过这么大的泥鳅,心里“咚咚”跳。两人小心翼翼,倒手要把它放进桶里,岂知这样大的泥鳅已经生长多年,已精得很,不知怎么就从两对小手中间滑出去,水面打了个花就不见了。
心有不甘的我俩,还细细搜寻,却连个影子也见不着了。
心里惦记着,初冬,又约运邦去河崖用扒网子“扒”过一次鱼。
“扒鱼”的扒网子,半圆形,网面连结的弓棍,杏儿粗,半圆弦上用一块耐磨的薄舌板。这舌板要一次次贴紧河底拖过砂砾,所以用耐磨的槐木最好。舌板两头要有两根交叉撑起的撑棍儿,好架住顶头绑定在弓背上的长杆。
姥娘真是心智慧巧的大家门户。她见我心心念念的想要个扒网子,心疼十岁的外孙,仅看了看运邦借来的一个,心里就有谱了。像结头发网子一样,结网就给我做了一个。
连带着,还给我结了一副七八尺长的抄网。抄网的故事,曲折在网脚儿铅锡坠儿的得来上,这得在另一个同样引人的故事里另说。
初冬的河水,经了深秋,一碧清澈。往往在岸边有对夹粗柳树的地方,塌坎下柳树根须游水,也留鱼。一朵朵的清苔你我相连,随水流上下微微掀动。清苔之下,就藏了静静的小鱼。并且,你以为仅仅是藏小鱼的地方,往往会爆出惊喜。
以运邦之经验,是他执扒网子观水选鱼情下手的。我提了他从家里带来的鱼篓,跟在他身后,屏息静气。
他两手执七八尺长的长杆,大大的网头虎视着水面。“刷”地出手,长杆滑在手掌顺到杆梢,两手压水飞快倒替着往身边“扒”,一定要贴紧沙砾底面,飞速,小鱼儿尽与清苔被扒网子扒了上来。往岸沙上一振,鱼儿跳跃,往往会有几条,“趴谷郎子”居多。运邦嘱我,翻翻清苔,别落下。我快速翻找,嘴里应着“没有了、没落下”,再小跑着跟上去。
曲柳下,水窝子,明显有鱼儿在清苔里游进游出。清澈的水下,像隔了玻璃看景一样,清清楚楚。“刷”,又是一下,“扑楞扑楞”,竟扒上来了两条虎口长的鲫鱼!急速出手,又扒上来一条!明确看到,受惊的水下,还有几条大鱼蹿远了。在长杆刚刚够不到的地方停住,观察它们舍不得的冬巢。
我恨不得下水,缩短扒网子与大鱼的距离。运邦说,没法子的,没法子的,鱼在水里,灵性超过人的几倍呢!
我要过扒网长杆,说,我试一下,我试一下。运邦边把长杆让给我,边劝:白搭!人不能贪心的。水中鱼,云中鹤,天地人。
这,一定是他从大人嘴里学来的话。
我哪管那什么云中鹤,学着运邦的动作,“刷”地一下子,长杆从手掌中滑出去,速拖速拉,沙滩上一振,几条小鱼就跳跃着。心中不服,又“刷”,再“刷”,仍是三两条“趴谷郎子”。
清苔下,已无大货。
鱼,不傻。
激动,向往;期待,失望;不服,仍是失望;再前寻,惊喜终没复再出现。
一扒网下去,本来跟上来几条小鱼就已足够惊喜。意外扒上来大的,提了胃口,反而丢了喜悦,失望频频了。
生活中时时有的桥段,是不是也这样?
人心贪而不足。
运邦连鱼篓也一块给了我。
冬日,湿鞋,冻脚,就这一次。
小清河在村北六里多,去到那里需要沿涓河河崖北行,穿越大片的白杨树林子,再外面,西侧是肥沃平整的河业地田野。因我多在初夏时节去河滩的桑椹林摘桑仁子,田野里是一望无际拔了穗的小麦。而在我此后多年的梦里,也都是走在麦田间长满荠菜的垄上,向着小清河的方向一步步贴近。
比起它的第一干流,小清河要宽广得多,水也深得多。经常有那种像几只小船串在一起的船队经过,排首是动力船,柴油发动机“哒哒哒”的马达声传出老远。如果恰好离小清河不远,我听到这特殊的声音就会兴奋起来,“哒哒哒”的声音由弱变强,我的身影也距离小清河由远及近。很快,我下到河滩,看见船头劈开水面驶过来。然而很快,它又在我的凝视中蜿蜒着消失了。我似乎有模糊的印象,就是看见行船的人走出船舱,蹲在船帮上用河水洗菜。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我似乎记别的事儿记得精准,对此却已不大好确定了。村子里的大人为了不让孩子到远河边,往往这样吓唬我们:小清河上跑船的,会抢小孩的。你们不要到那么远的小清河边玩,他从船上跳下来一把把你抱上船去,就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据说确有此类事情曾发生,说谁家的孩子被抱上船,后来又被在上游老远的村子里的亲戚给送回来了。
我对大人此类的言说好像没什么感觉,心里却对那些行船的人充满了好奇,又好生羡慕。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他们在行船中都做些什么?他们总是这样吗?行驶在一条河流中,舱外的一切就这样贴近又旋即远去,就像永不歇止的时光。他们折回船舱,再弯腰出来的时候,眼前就一定又是一片不一样的风景。彼时彼刻,他们会生出怎样的感触呢?
我的家乡是鲁东南昌潍大平原上的一个村庄。八百里昌潍大平原,黎明的河边,因峻青讲的故事而四下里闻名。它的地貌特点与它现在所在的地区完全一致,那就是放眼即是田野,而很远才是丘陵乃至山峦,哪怕一片小小的丘陵或者只有两朵马耳的山峰。
这至少是一种遗憾。尤其年龄还小,还没有机会离开家乡,我除了知道“山”的概念,在书中看到过山的样子,却是无缘近距离一睹一座山的真容的。于是更加觉得,身边没有一座山,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生活缺欠。
这种感觉并非独有,它甚至在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我们同龄伙伴的集体情结。因为总听人讲,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登高是可以爬上南边很远的马耳山的。后师毕业的三叔,在马耳山东边、西边都教过书;在他之前,父亲和大伯在马耳山东边上过国民榆林小学。尽管多次尝试,也去接近一座山的影子,但我还是将其归咎为登临的机会不够。因为在当时,即便是县城也鲜见高层建筑,而乡村的“高层建筑”,只有队里烤烟房的大烟囱。这样的烟囱,各个生产队都有。直到多少年后我主考监巡惠民,才知道此地位于小清河北岸的石村,确实有一座很高的大烟囱。但那个烟囱和砖窑,好像已经废弃。在残缺的遗迹中间,一座烟囱兀自挺立,更加显得孤绝无双。我小时候是不会来这地方的,不能登临远望,而是只来小清河旁兜风?初夏应该去采摘桑椹桑仁子,盛夏河崖上乘凉,还有寻找那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零星散落的河崖下的滑石。还有那哪儿也及不上的龙骨涧的龙骨,那可是绝对正儿八经正宗的恐龙化石!而那座烟囱,只是就那么醒目地兀立在那里,让人怎么瞩目?这种烟囱的形制其实多年并没有变化,是用耐火的烧结砖砌成,根基稍粗,向上渐细,一侧有一遛铁把子可供攀爬上下。我印象中似乎在梦里也攀爬过,准确地说是爬上去了几蹬,然后赶紧下来,而把“登高可见远山”的念头隔断到九霄云外。现实生活中,其他同伴的胆量仿佛也仅在仿佛而已。听说有人确实攀爬到顶过,大概是近村里的小伙子。他不仅爬了上去,而且还随身携带了一个大包袱准备做降落伞。结果,从顶上一跃而下,却摔断了腿。这实在是很惊险又很遗憾的事儿。
而关于我的村庄的格局,我在和臧克家先生交谈起龙骨涧时,有过大致的描述。
村子的确不小,四百多户,村中只有两条南北路。其中一条在中间,将这个不小的村庄一分为二;另一条在村东头,沿着村庄的边缘向南通到村南,接上南环小郭家庄一片,再向南不远,负责东拐,上东河。北环当时也有了,不知西环现在成了没,再西,南边四里的洼里村,家后通往潍徐公路国道的一条南北路,已在黄鳝沟西,算作是西环有些牵强。它的西面已经没有人家,只有漫坡的庄稼。
村中的东西路有三条。最南边一条称为村前街,是小郭家庄的街;第二条是中街,似乎是东西中央大街的意思,但远没有南北中央大街有故事和多风景;第三条没有名字或者我忘记了它的名字,也可以叫后街,是最北边的一条。其中,中街的两端是村子的东西两头;后街从两侧延伸出了村子;南街只有半条路,它从村中的南北路起始,东段一直向东,到了队场东边,南拐再东,直通往东边涓河岸。向西一段,就是村校门前,再向西,没了路,是广袤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