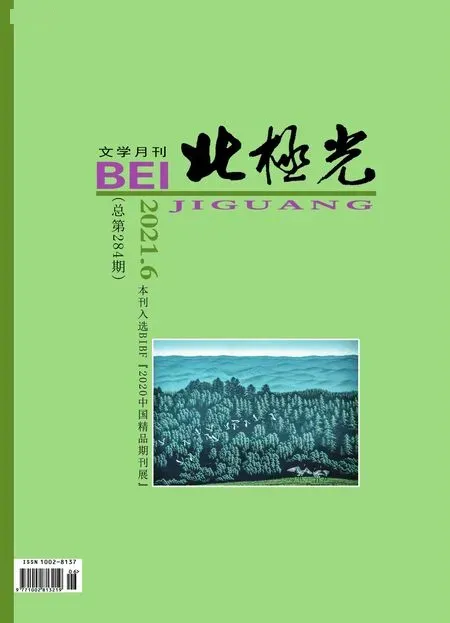语词中的沉思与生命驻足的地方
——左远红诗集《离爱还有多远》读后
2021-11-11邢海珍
□邢海珍
左远红是我多年来一直有所关注的诗人,她主要写诗,也写散文和小说。我喜欢她的诗,尤其那些趋于内向的、有许多生活琐细痕迹的诗,很像一个人默对着远方的山影或云彩,在语词中沉思,自己对自己说些什么。2016年,她出版了诗集《离爱还有多远》,我读到了诗人2015和2016两年所写的诗作。顺手翻开诗集,翻到一首《灰暗中的人》时,我慢慢地读下去,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他说:明明是三个人!三个!
他竖起指头,直抵她内心的洪水
几十年,换一条船的命
船说:我早死了
你交换的不过是空气
子弹在飞,她小声说:击中我吧
灯亮了,一个声音还在重复:击中我吧
大背景是“灰暗中”,写的或许是梦境,角色间在交流,很有戏剧性。诗写得清晰冷静,跳跃从容,有些魔幻玄思的色彩。在叙述中呈现灵异的情境,内蕴着足够的形上之思。左远红的诗沉稳老练,看出了功力。再翻下去是一首题为《照片里的人》,写实中有虚化,实多于虚:
教堂里,三表哥回头与嫂子说话
旁边叫大卿的男孩打着哈欠
我家先生抿着嘴看着三表哥,同时等待
新娘和她的父亲从旁边走过
二表哥斜身安静地坐着,隔开的位置
一个女子望着镜头……
这是2013年春天,杏花开放
侄女的西式婚礼即将开场
我在场外,像另一些亲人在照片之外
不经意的年月
总是让我们忽略
常来常往的美好
冷风中再次侧头
发现三表哥在蜡烛旁边
蜡烛在遗像旁边……
诗的构思非常巧妙,写人世的沧桑之变,诗人选择“照片”这个角度,不同的人幻出幻入,诗中插入时间和场景的定位。在实虚的变化中跳脱自如,平和内敛,无浮泛之气,韵致极为深远。“不经意的年月/总是让我们忽略/常来常往的美好”,就连感叹也处于低调状态。这样的诗,很让诗人多了几分底气。
诗人左远红也和许多平常人一样,人生路上或许不无坎坷与波折,内心世界装着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伤痛。她的诗中可以触到一些近似某种暗物质的隐忧,时而缠绕于语词之间,情思深处偶有一些沉重。
写在诗集之前题为《一些不能避开的话题》的文中,说到诗人余秀华对她近年诗歌的影响:“这样一个有着明显身体‘缺陷’的乡野女子却以超越诗歌的智慧和力量抒写苦难中的挣扎、陷落、甚至是‘败坏’。不能否认,她‘苦难’中最深切的部分与我内在的残缺与创痛无声地契合了。我再一次面对诗歌时,感受着异样的神奇。我重又写诗,于是就有了2015年春天至2016年春天那些忧郁的黄昏,我与初雪、与落日、与池塘、与鸟鸣、与苍凉灵魂的一次次对视;有了一个50岁女人隐形者一般朝内心要神旨,朝内心要救赎,朝内心要洁净,朝内心要一条通往永恒的圣爱之路。也许,这就是我诗歌的容貌,她不可能漂亮,但她应该沉实”。是的,我亦有同感,余秀华确实是一位有才华、有天赋的诗人,是人生命运的某些共振,就会深刻地影响另一个也在写诗的人。当苦难的汁液渗入我们肌肤、骨髓的时候,说不定在哪一天里会让灵魂深处的诗歌醒来。
对于诗人左远红来说,余秀华的出现或许只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但那是一次有效的唤醒。“2015年春天至2016年春天那些忧郁的黄昏”,给予了一位内心有些寂寞、有些沉静的诗人以丰沛而深切的灵感,这让她的那些有些暗淡的时光因为诗歌而豁然一亮。于是我读到了左远红的行云流水般的《母亲节》,她的灵性让那些本该是流水账的内容成了暖意无限的诗:“早起,一边洗衣服/一边煮三份蛋/侄女睡眼惺忪走过来/节日快乐,拥抱一下/我一边举着铲子/一边拥抱她暖乎乎的身体/中午去教堂/出来的时候/同他去吃饺子/另一个侄女打电话/说鲜花晚上送到/大侄说:姑,我订好了饭店/晚上去接你/我说:好好陪妈妈过节/不许折腾/安静。洗完澡看看镜子里的人/心里说:真像妈妈/再老一些吧,一定更像”!平淡的日子,琐碎的生活,我们去哪里寻找诗歌呢?就把眼前的诸多物事写成流水账吧,左远红用心到笔的文字回答了我们。平淡、琐碎到底是不是诗,关键是看其中寓含了什么,人情人性充溢期间,使平常的事物有了色彩和温度,诗就出来了。这时的“流水账”就变得顺畅自然,而且有了生机与活力。
诗人以平实、质朴的写法,描写了远年的人和事物,让我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那些质朴而又不乏灵性的诗行里,居住着一个情深意重的人。读左远红的诗,你会走进那个真切生动的年代,走进真性情的人心之中。《致诗人陈丹妮》是一首多么深情柔软、亲切美好的诗呀!诗人丹妮也是我非常熟识的诗人和编辑,她虽然年纪不大却已离世多年。读这首回忆往事的诗篇,自会有诸多感动和对人间生死两茫茫的感伤。在左远红的笔下,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与诗人的相处交往,一幕一幕动人的往事,真是魂牵梦绕:
年轻的丹妮,她用朴素的手帕扎起马尾辫
她轻声说话,隔着眼镜细致地打量人
后来,她绘声绘色讲诗人们的故事
然后大笑,额头亮得像跳跃的烛光
……
一大片串串红映亮的秋日下午
我终于如愿有了一张与丹妮的合影
这合影一直嵌在我乡下老屋的镜框里
爸妈时常指着照片对亲戚乡邻说
这戴眼镜的姑娘是城里有名的诗人
……
你的心如丝绸,原应有一份爱
也如丝绸般细腻。但我们不知道
你经营一生的诗歌中,有没有你的爱情城堡
里面的他一生伫立着,供你梦想依偎
读这样深切走心的诗,我不能不感动,曾经熟悉的人,还活在美好的情境里。情景依旧,情思悠远,读后让人总是感念不已。左远红是一位有情怀有境界的诗人,她的诗中蓄满了人性的暖意,她是以与人为善的心思打量这个世界。正像她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我所热爱的人们,我们迟早都会被时间或空间隔开,如果还会彼此想起,我会持续对你们的热爱和祝福。如果你们也想起我,请你们远远地原谅我,或者嘲笑我:一个生活中的弱者,一个心底单纯的人,一个厚道的人,一个永远不懂得变通的人。多少年来,我领受着来自你们的美好馈赠,也承受着另外一些暗处的中伤和没有缘由的冷落。但不变的是我热爱你们,我珍视人生的每一次擦肩,每一种交集,每一场共事,每一个微笑……”(《一些不能避开的话题》)诗人的心是敏感的,无论是温暖或伤痛,都会唤醒她心灵深处的诗意回响,哪怕在暗淡的记忆里也会溅起悲悯的星光。在怀念和思考中,亲人和往事在诗中存在着,那么亲切,那么随遇而安,深情的抒写在美的氛围里沉淀为生命的气象。
《豆腐坊》是一首追怀远年乡村亲人旧事的诗,做豆腐的现实场景如在目前,爷爷剥麻,大豆腐也“一板一板地压好”,时光如温婉的麻绳,缠绕着亲情和回忆。诗人这样写道:
我6岁,我踩着新雪跑在爷爷前面。爷爷说,慢点,别摔着
多年后,爷爷更老了,生产队不用他了。他在一个个黄昏
帮我母亲纳鞋底。他用的麻绳,我无比熟悉……
在生活和生命的进程中,诗人笔下的小细节就像一道道清晰的纹理,雕刻出我们不断忽略的岁月影像。当童年、青春一闪而过的那些瞬间出现在字里行间的时候,便有清泉般的心灵波流潺潺而来,唤起我们许多匆忙而过途程中丢失的美好印象。这样的诗写方式,让我想到了散文,就像散文的“怀旧”被诗人挪移到诗中,一些更为自如舒展的叙事的出现更加增进了一种平常心,或可以看做是左远红的另一种贴近生命的方式吧。
由童年记忆牵引和构建而成的童话精神世界,是左远红诗歌的一个重要精神维度,她善于把童年的记忆与后来的人生境遇打通,进而形成一种不断延长的生命景观,不断加大思辨色彩,创造了一种联系着深层体验所关联的童话情结。短诗《十二印大锅》成诗于一次很微小的童年记忆,而诗的落脚点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推断“归宿”:“那年夏天/家里就剩一只下蛋的鸡/忘了家里来了什么贵客/妈妈用十二印大锅/炒一个鸡蛋/我疯跑着玩耍/经过妈妈的身边/妈妈飞速地将一块炒鸡蛋/塞进我嘴里/亲妈的热度/让我这个不能生养的女人/一生无法炮制”。一首充满着童趣“春色”的诗意情境,一下子跌落于严酷成人话语的“秋霜”之中。虽起自于童年,但结束于对整个生命的观照,是以一种体验的深度为童话做“结”。
从童话的角度来阅读,《直到他等我长大》是一首意蕴深远的诗作:
新砖砌成的房子还没有猪入住
这些给猪盖的房子是村里最漂亮的房子
一间一间挨着,落日浇在上面的时候
它们像抹了一层辣椒油。我这时总会一个人爬上半截子砖墙,我在心里指点江山
哪一间给母猪,哪一间给公猪,哪一间给猪崽
哪一间给猪崽的爸爸妈妈。一个下午
我也没有数完,后来我放弃了,我站在墙头
对着不远的村路唱《映山红》,唱《赤脚医生向阳花》
我盼望我唱歌的时候,他正好骑着自行车经过
他住在镇上,他面目清秀,他有细长的手指
他拉手风琴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的手指
后来,我想为他盖一排通红通红的红房子
把猪全部赶走,我和他每天在房子里拉琴唱歌
直到月牙升起,直到麻雀噤声,直到他等我长大……
这是一首很独特的诗,诗的前半部分写猪的房子,房子很新,是“村里最漂亮的房子”,是一种孩童之心,要给各类别的猪分配房间。后半部分写一个人,“他”是一个爱恋的对象,在想象中要把猪的房子变成“他”的房子。但当时“我”还小,这就是一种童年美好的恋情,“他拉手风琴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的手指”,童心沉浸在光阴的流水中,命运落实着一种等待,“直到他等我长大”。诗人用了那么多的笔墨写猪和猪的房子,寓含童趣,也是一种情境的衬托,后面表达了“爱”的执着信念,营造了美好的希冀与美的诗意童话。
左远红的诗写得冷静,有自觉的深度追求,写人写物,写景写境,有情怀有思想,但诗人很少直抒胸臆,而是进行自己语词的沉思,隐喻自在其中,心性和形而上的品质提升了诗的纯度。《那一场初雪》中的意象化,隐含着许多低沉、缓慢的忧思,人间世界冥冥中的落寞,或是生命过程的一种必然,一切都将消逝,包括初雪,“死去的掌声”或是“震落的锈迹”,如果“突然回到心上”,或能看见“灯芯里的孩子”“草芥中的女人”,又如何留存初雪的风景。诗的结尾这样写道:
初雪啊,其实你哪儿都没有去
你就和一口井待在原地
洗净落日的杂质
淘干井底最后一滴水
初雪和井都在“原地”,要“洗净落日的杂质”“淘干井底最后一滴水”,坚持自我纯净的本色,守住生命最后的价值。清初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强调了诗人的主观性对于客观景物的驾驭,“情”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诗意构成的角度看是不无道理的。就如“初雪”“老宅”等意象都是诗人的情感寄托,说到底还不是客观景物的呈现,而是主观的心象之维。诗中事物都有陈旧的颜色,不止是眼中之物,而是与往事、回忆关系紧密,是“情哀则景哀”的内在之思。
左远红的诗有着深刻的思辨精神,即使是表现生活的现实景象,也不是在表面涂抹,而是如王昌龄所言,是“以心击之”“深穿其境”,使其在隐喻的情境中达成张力的效果。在《2016:纪念周总理逝世40周年》一诗中,诗人回避了惯常的政治性内容,而是深入挖掘人性之核,指向伟大的献身精神:
这个智慧的老人,这个瘦弱的孩子
今生都不属于她啊,唯有此刻
她把他抱在怀里
他那么安静,那么听话
像她忍住泪水里欲碎的山河
像风扶起一株死去的海棠
诗人写貌得神,抒情没有浮泛之气,凝重洗练,尤其最后两句“像她忍住泪水里欲碎的山河/像风扶起一株死去的海棠”极为贴切,极为开阔大气,真可谓“境界全出”,写出了生命深处的真性情。
许多年来,左远红一直为诗而默默地努力,在语词中沉思,那是她生命驻足的地方。诗集《离爱还有多远》是诗人苦心求索的标志性建筑,那些沉实、深切的人生体验与感怀,是灵魂深处的血色结晶,闪烁着耀眼的人性之光,照耀我们的拳拳之心,照耀我们人生之路的诗与远方。人生苦短,但诗路漫长,追求未有穷期,在诗意中行走,左远红肯定会愈加优秀,我们期待她的好诗问世。